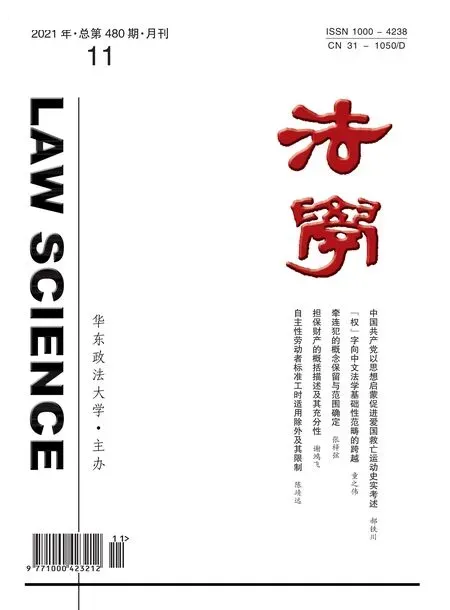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中法檢權(quán)力的沖突與協(xié)調(diào)
●陳明輝
2018年修正的《刑事訴訟法》將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確立為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制度。但新法通過之后,法院對檢察院量刑建議的采納率一度下降,直至2019年底量刑建議的采納率才回升到79.8%。〔1〕參見張軍:《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20年5月25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https://www.spp.gov.cn/spp/gzbg/202006/t20200601_463798.shtml,2021年10月10日訪問。同年12月的“余金平交通肇事案”又將法檢權(quán)力的沖突問題推到了風(fēng)口浪尖。由于該案一審法院未采納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導(dǎo)致檢察院提起抗訴,二審法院非但沒有支持檢察院的主張,反而加重處罰被追訴人,引得學(xué)界普遍將該案視為審判權(quán)與檢察權(quán)的正面沖突。不少一線法官也在相關(guān)熱帖中表達(dá)了自己的抵觸情緒,指責(zé)該制度下檢察權(quán)對審判權(quán)的僭越。此后,訴訟法學(xué)界圍繞“余金平案”發(fā)表了一大批成果,法檢雙方在量刑建議與量刑權(quán)上的沖突引發(fā)了大量爭論。然而,相關(guān)研究更多地是偏向于訴訟法層面的討論,對于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中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是否侵入了審判權(quán)這項核心爭議,學(xué)界至今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tǒng)、明確的研究結(jié)論。本文將梳理訴訟法學(xué)界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及其論據(jù),然后通過對《憲法》上法檢權(quán)力的規(guī)范分析,指出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對憲法上法檢權(quán)力格局的影響,最后運用合憲性解釋方法提出解決法檢權(quán)力沖突的方案。
一、檢察權(quán)有無侵犯審判權(quán):既有觀點及其論證
對于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確立之后,檢察權(quán)有無侵入人民法院審判權(quán)的核心領(lǐng)域,訴訟法學(xué)者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需要說明的一點是,目前所討論的檢察權(quán)有無侵犯審判權(quán)的問題并不是指檢察機關(guān)在行使職權(quán)的時候違反法律規(guī)定不當(dāng)干預(yù)法院的審判活動,而是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新《刑事訴訟法》中將本屬于審判權(quán)的核心職權(quán)轉(zhuǎn)移給了檢察機關(guān),使檢察權(quán)與審判權(quán)配置偏離了憲法對法檢權(quán)力的基本定位。
(一)檢察權(quán)侵犯了審判權(quán)
相當(dāng)一部分刑事訴訟法學(xué)者認(rèn)為《刑事訴訟法》第201條要求法院“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的規(guī)定,使檢察院獲得了法院的部分審判權(quán)。至于這種權(quán)力轉(zhuǎn)移是否構(gòu)成對審判權(quán)的侵犯,即便在這些學(xué)者中也存在不同的理解。
有幾位學(xué)者明確表示,《刑事訴訟法》第201條中的“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違背了《憲法》上關(guān)于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quán)的規(guī)定,因此應(yīng)當(dāng)將該條款徹底刪除。其理由有四:(1)現(xiàn)行《憲法》明確規(guī)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quán),而審判權(quán)的核心權(quán)能就包括了量刑權(quán),量刑建議的剛性約束力導(dǎo)致了量刑權(quán)的轉(zhuǎn)移。〔2〕參見魏曉娜:《沖突與融合: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本土化》,載《中外法學(xué)》2020年第5期,第1225頁。(2)我國現(xiàn)行司法體制采納的是職權(quán)主義的訴訟模式,“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違背了控審分離原則,使控方獲得了部分審判職能,而法院的審判權(quán)變成形式性的審判權(quán),因此,《刑事訴訟法》第201條在立法論上存在嚴(yán)重失誤。〔3〕參見孫遠(yuǎn):《“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的立法失誤及解釋論應(yīng)對》, 載《法學(xué)雜志》2020年第6期,第112頁;杜磊:《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適用中的職權(quán)性邏輯和協(xié)商性邏輯》,載《中國法學(xué)》2020年第4期,第232頁。(3)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將定罪量刑權(quán)實質(zhì)上給了檢察機關(guān),并使審判權(quán)的行使陷入兩難困境。因為按照新《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實質(zhì)性權(quán)力給了檢察機關(guān),但錯案責(zé)任仍由法官承擔(dān),這顯然違反了權(quán)責(zé)分離原則。為避免錯案出現(xiàn),法官會不斷與檢察官就定罪量刑進行協(xié)商,而這又有違審判中立原則。〔4〕參見馬明亮:《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中的協(xié)議破裂與程序反轉(zhuǎn)研究》,載《法學(xué)家》2020年第2期,第128頁。(4)從比較法的角度而言,即便是在實行辯訴交易的國家,量刑建議對法官也不具有拘束力。〔5〕參見魏曉娜:《結(jié)構(gòu)視角下的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載《法學(xué)家》2019年第2期,第119頁。
還有不少學(xué)者雖然承認(rèn)“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的確對審判權(quán)造成了限制,客觀上使檢察機關(guān)分享了審判權(quán),但這些學(xué)者并不關(guān)注檢察權(quán)有無侵犯審判權(quán)這個憲法問題,而僅從訴訟法的角度考慮這項制度設(shè)計是否有助于提升訴訟效率。因此,其立場較為溫和,基本趨于認(rèn)可該制度的合理性,甚至認(rèn)為讓檢察機關(guān)分享部分審判權(quán)恰恰是這項制度的精髓所在。〔6〕參見閆召華:《“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適用中的“檢”“法”沖突及其化解——基于對〈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的規(guī)范分析》,載《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20年第5期,第143頁。
(二)檢察權(quán)沒有侵犯審判權(quán)
訴訟法學(xué)界的不少學(xué)者和法檢系統(tǒng)的專家大多認(rèn)為,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下,檢察機關(guān)的量刑建議的確是對法院提出了剛性要求,但檢察機關(guān)沒有因此侵犯或分享法院的審判權(quán)。其論證模式主要有三種。(1)公訴權(quán)論證。這種論證認(rèn)為,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案件中的量刑建議本質(zhì)上還是求刑權(quán),是公訴權(quán)的一部分。雖然現(xiàn)在要求法院“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但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最終還是要法院來確認(rèn)和裁定。鑒于法院掌握著最終的決定權(quán),即便法院完全采納量刑建議,也不應(yīng)將《刑事訴訟法》第201條中的“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理解為檢察院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中分享了審判權(quán)。〔7〕參見樊崇義:《關(guān)于認(rèn)罪認(rèn)罰中量刑建議的幾個問題》,載《檢察日報》2019年7月15日,第2版;卞建林、陶加培:《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中的量刑建議》,載《國家檢察官學(xué)院學(xué)報》2020年第1期,第141頁。(2)控辯雙方合意論證。這套論證認(rèn)為,過去的量刑建議對法院沒有拘束力是因為二者是簡單的檢察權(quán)與審判權(quán)的關(guān)系,但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之下,量刑建議是檢察機關(guān)與被追訴人協(xié)商之后達(dá)成的合意,故而法院“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并且這與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quán)并不矛盾。〔8〕參見陳國慶:《量刑建議的若干問題》,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年第5期,第8-9頁;胡云騰:《去分歧凝共識確保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貫徹落實》,載《法制日報》2019 年12月11日,第9版。(3)類比論證。這套論證將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的法檢關(guān)系塑造為世界潮流,然后展開中西對比,試圖證明法檢融合是大勢所趨。〔9〕參見盧建平:《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事實認(rèn)定與法律適用爭議評析》,載《中國法律評論》2020年第3期,第113頁。
對比來看,正反兩方的觀點與論證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細(xì)一琢磨,兩方的觀點在論證上存在共同的問題:一是論證方式過于籠統(tǒng),缺乏細(xì)致的規(guī)范分析,論據(jù)和結(jié)論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沒有得到充分展開;二是各種論據(jù)都缺乏一個穩(wěn)固的邏輯前提,論者往往是拿出一個自認(rèn)為成立的論證前提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一前提是否能夠成立、是否能夠為人所接受值得懷疑。因此,盡管所有的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研究都涉及法檢權(quán)力的沖突問題,但很多時候大家根本沒有站在同一個頻道展開對話,上述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之間也少有正面交鋒,以致大家各執(zhí)一端,未能達(dá)成基本共識。
二、憲法上法檢權(quán)力的基本結(jié)構(gòu)
新《刑事訴訟法》中的“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是否使量刑建議變成了一項權(quán)力,以及這項權(quán)力究竟是屬于檢察權(quán)還是審判權(quán),是相關(guān)理論爭論的核心爭議點。在回答“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是否使檢察權(quán)侵犯審判權(quán)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從憲法上界定檢察權(quán)和審判權(quán)的核心領(lǐng)域及其相互關(guān)系,明確法檢權(quán)力的憲法界限,以此作為判斷新《刑事訴訟法》的權(quán)力配置是否違反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quán)的依據(jù)。
(一)法檢權(quán)力的核心領(lǐng)域
梳理現(xiàn)行《憲法》中關(guān)于各大國家機構(gòu)的規(guī)定,可發(fā)現(xiàn)我國《憲法》對各大國家機構(gòu)采用了一種不對稱的四階構(gòu)造。所謂“四階構(gòu)造”是指現(xiàn)行《憲法》同時采用機構(gòu)名稱、機構(gòu)性質(zhì)、權(quán)力類型和職權(quán)范圍四個核心概念來創(chuàng)設(shè)一個國家機構(gòu)單元。所謂“不對稱”是指現(xiàn)行《憲法》中的六大國家機構(gòu)并未全部遵循四階構(gòu)造的設(shè)計體例。嚴(yán)格來說,現(xiàn)行《憲法》上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都屬于三階構(gòu)造,《憲法》僅規(guī)定了這兩大機構(gòu)的名稱、性質(zhì)和權(quán)力類型,并沒有直接規(guī)定這兩大機構(gòu)的職權(quán)范圍。但由于《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分別列舉了法院和檢察院的職權(quán)范圍,法院和檢察院也可視為四階構(gòu)造。
1.檢察權(quán)的核心領(lǐng)域。我國國家機構(gòu)權(quán)力配置的特點在檢察權(quán)上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如果按照西方分權(quán)原則的邏輯,人民檢察院既然名為“檢察院”,那么其權(quán)力就應(yīng)當(dāng)是檢察權(quán)。至于檢察權(quán)可以被劃分為多少項具體職權(quán),這完全取決于對“檢察”二字做何種法律解釋。我國《憲法》上的檢察院雖然也叫“檢察院”,行使的也是“檢察權(quán)”,但《憲法》又同時規(guī)定了檢察院的性質(zhì)為“檢察機關(guān)”和“法律監(jiān)督機關(guān)”,〔10〕現(xiàn)行《憲法》第3條第3款使用了“檢察機關(guān)”,第134條又將檢察院界定為“法律監(jiān)督機關(guān)”。《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列舉的檢察院職權(quán)范圍也不僅限于一般意義上的檢察權(quán),而是額外列舉了多項法律監(jiān)督職權(quán)。因此,我國檢察院的機構(gòu)性質(zhì)、權(quán)力類型與職權(quán)范圍并非一一對應(yīng)的關(guān)系,而是存在機構(gòu)性質(zhì)、權(quán)力類型和職權(quán)范圍之間的錯位。
在這種錯位結(jié)構(gòu)下,學(xué)界對于檢察權(quán)形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解讀。部分人緊緊扣住“檢察權(quán)”這一權(quán)力類型,建議把人民檢察院改造成西式的公訴機關(guān),使檢察機關(guān)、檢察權(quán)、檢察職權(quán)相統(tǒng)一。〔11〕參見陳衛(wèi)東:《我國檢察權(quán)的反思與重構(gòu)——以公訴權(quán)為核心的分析》,載《法學(xué)研究》2002年第2期,第3-19頁;蔡定劍:《司法改革中檢察職能的轉(zhuǎn)變》,載《政治與法律》1999年第1期,第24-27頁。另有部分人傾向于遵循現(xiàn)行《憲法》上“法律監(jiān)督機關(guān)”的機構(gòu)性質(zhì),把人民檢察院的職能定位與職權(quán)配置朝著法律監(jiān)督方向改革。〔12〕參見苗生明:《新時代檢察權(quán)的定位、特征與發(fā)展趨勢》,載《中國法學(xué)》2019年第6期,第224頁。這兩個方向?qū)z察院權(quán)力范圍的影響非常顯著。前者意味著檢察院的權(quán)力會被限縮為純粹的公訴權(quán),后者則意味著檢察院的權(quán)力可以不斷向法律監(jiān)督方向擴張。出于對列寧法律監(jiān)督理論的堅持以及對現(xiàn)行法律制度的尊重,國內(nèi)的主流意見支持后一個解讀方向。在經(jīng)歷了2018年的監(jiān)察體制改革之后,人民檢察院擴張業(yè)務(wù)所倚重的就是“法律監(jiān)督機關(guān)”這個權(quán)力增長點。
為了縫合“檢察”與“法律監(jiān)督”的張力,老一輩的檢察理論家提出了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一元論。該理論有兩個基本論點:第一,在我國憲法體制下,只有人民檢察院這一個專門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guān);第二,檢察機關(guān)的所有職權(quán)都屬于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性質(zhì)。〔13〕參見王桂五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制度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180頁;張智輝:《法律監(jiān)督三辨析》,載《中國法學(xué)》2003年第5期,第16-24頁;石少俠:《我國檢察機關(guān)的法律監(jiān)督一元論——對檢察權(quán)權(quán)能的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解析》,載《法制與社會發(fā)展》2006年第6期,第23-35頁。這種法律監(jiān)督一元論實際上是用法律監(jiān)督來定義檢察權(quán),檢察權(quán)的核心權(quán)能公訴權(quán)也被解釋為法律監(jiān)督的一種具體手段。〔14〕同上注,王桂五主編書,第87-88頁。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一元論試圖用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來界定檢察權(quán),其實質(zhì)是想用檢察機關(guān)四階構(gòu)造中的第二階——機構(gòu)性質(zhì),來統(tǒng)合第三階的權(quán)力類型和第四階的職權(quán)范圍,從而完成對檢察院機關(guān)性質(zhì)、權(quán)力類型、職權(quán)范圍的整合。但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一元論并不能終結(jié)檢察院機關(guān)性質(zhì)、權(quán)力類型與職權(quán)范圍之間的張力,反而帶來了更多的理論謎團。因為所有關(guān)于國家權(quán)力劃分的政法理論中并無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這么一個權(quán)力類型。無論是現(xiàn)行《憲法》還是相關(guān)組織法,都沒有出現(xiàn)“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這個字眼。現(xiàn)行《憲法》的確是用了“法律監(jiān)督機關(guān)”來界定人民檢察院的性質(zhì),但對于其權(quán)力類型,《憲法》明白無誤地用的是“檢察權(quán)”。加上法律監(jiān)督本就是一個語焉不詳?shù)母拍睿瑢z察權(quán)解釋為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并沒有解釋出新東西,反而容易引發(fā)檢察權(quán)與其他具有監(jiān)督性質(zhì)的權(quán)力的混亂。畢竟,檢察院不是唯一的監(jiān)督機關(guān),某項職權(quán)具有法律監(jiān)督性質(zhì)或者法律監(jiān)督功能也不代表該項權(quán)力就是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
所以現(xiàn)在更多的學(xué)者不再以法律監(jiān)督的機關(guān)性質(zhì)去統(tǒng)合檢察權(quán)和檢察職權(quán),而是承認(rèn)人民檢察院的性質(zhì)、權(quán)力類型和職權(quán)范圍之間存在錯位。這批學(xué)者形成了三個核心論點:第一,嚴(yán)格區(qū)分“法律監(jiān)督機關(guān)”和“檢察權(quán)”,指出檢察權(quán)才是檢察機關(guān)的權(quán)力類型,法律監(jiān)督僅僅是一個功能性的概念,現(xiàn)行法律體系中并不存在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的概念;第二,對檢察權(quán)做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解,不從檢察權(quán)這個概念中去劃定檢察權(quán)的范圍,而是根據(jù)《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所列舉的諸項職權(quán)來界定檢察權(quán)的范圍;第三,放棄權(quán)力類型和職權(quán)范圍的完全對應(yīng)關(guān)系,承認(rèn)檢察權(quán)與檢察機關(guān)的職權(quán)之間存在一定的錯位,即檢察機關(guān)的某些職權(quán)可能并不屬于檢察權(quán)的性質(zhì),而是其他類型的權(quán)力。〔15〕參見韓大元:《中國檢察制度的憲法基礎(chǔ)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頁;萬毅:《法律監(jiān)督的內(nèi)涵》,載《人民檢察》2008年第11期,第39頁;王志坤:《“法律監(jiān)督”探源》,載《國家檢察官學(xué)院學(xué)報》2010年第3期,第34頁;田夫:《論“八二憲法”對檢察院的“雙重界定”》,載《東方法學(xué)》2013年第6期,第157頁。
傳統(tǒng)的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一元論試圖用“法律監(jiān)督”去定義“檢察”,當(dāng)下的檢察權(quán)一元論則是用“檢察”去整合“法律監(jiān)督”,〔16〕參見閔釤:《檢察與監(jiān)督——“四大檢察”的理論基礎(chǔ)與時代價值》,載《人民檢察》2019年第22期,第56頁。這兩種思路都不可能改變檢察機關(guān)性質(zhì)—權(quán)力—職權(quán)這三個位階的錯位關(guān)系。這種錯位關(guān)系根源于現(xiàn)行《憲法》的制度設(shè)計及其背后的法律監(jiān)督理論,只要憲法還將人民檢察院定性為法律監(jiān)督機關(guān),檢察與法律監(jiān)督的內(nèi)在沖突就會一直存在。由于無法根據(jù)“檢察”或“法律監(jiān)督”劃定權(quán)力范圍,檢察權(quán)或者所謂的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的外延最后只能取決于《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對檢察機關(guān)的職權(quán)列舉。因此,在這個錯位結(jié)構(gòu)中,無論用誰去定義誰,都像是一個循環(huán)論證的文字游戲。
《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20條列舉了人民檢察院的八項職權(quán)。從訴訟程序的角度看,人民檢察院的前四項職權(quán)基本上都屬于檢控職能,后三項職權(quán)屬于監(jiān)督職能。檢控和監(jiān)督明顯屬于兩個不同的角色,前者屬于訴訟程序中的一方當(dāng)事人,后者屬于在整個訴訟程序之上的監(jiān)督者。可見,在組織法所列舉的檢察權(quán)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中,公訴職權(quán)還是公訴職權(quán),監(jiān)督職權(quán)還是監(jiān)督職權(quán),它們并沒有真正合二為一,所以我們很難給我國憲法體制下檢察權(quán)劃定一個明確的邊界。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公訴職權(quán)與法律監(jiān)督職權(quán)是檢察權(quán)的兩個內(nèi)核,并且這兩個內(nèi)核都具有一定的伸縮性。〔17〕參見田夫:《監(jiān)督與公訴的關(guān)系——以蘇中比較為中心》,載《清華法學(xué)》2019年第1期,第44頁。從這些年的制度變革來看,最高人民檢察院一直試圖從公訴和法律監(jiān)督這兩個方向充實自己的權(quán)力,雖然2018年監(jiān)察體制改革取消了檢察院反貪反瀆這部分法律監(jiān)督職權(quán),但檢察機關(guān)不斷從公訴職權(quán)這個方向擴大公訴權(quán)的范圍(公益訴訟)和強度(量刑建議)。
2.審判權(quán)的核心領(lǐng)域。現(xiàn)行《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雖然也采用了四階構(gòu)造的方式來建構(gòu)人民法院的組織架構(gòu),但人民法院的機構(gòu)名稱、機構(gòu)性質(zhì)、權(quán)力類型和職權(quán)范圍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錯位。這個四階構(gòu)造中的核心概念是“審判權(quán)”,《人民法院組織法》除了劃分各級法院的案件管轄權(quán)之外,沒有對審判權(quán)進行實質(zhì)性劃分。因此,相較于檢察權(quán)的復(fù)雜構(gòu)造而言,審判權(quán)的內(nèi)涵相對簡單。盡管法院或多或少地享有部分立法權(quán)和行政管理權(quán),但審判權(quán)始終是法院無可爭辯的核心權(quán)力。
簡單而言,審判權(quán)就是對原被告雙方的法律爭議作出一個合法/非法的法律判斷。這種極具辨識度的權(quán)力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被動性。審判權(quán)是一種消極權(quán)力,它的啟動依賴其他主體將一項法律爭議提請到法院面前,并且這項法律爭議必須發(fā)生了現(xiàn)實后果。第二,排他性。原則上審判權(quán)只能配置給法院而不能與其他國家機關(guān)分享。第三,獨立性。審判權(quán)必須排除法律之外的不當(dāng)干擾,這些干擾可能來自其他國家機關(guān)、法院系統(tǒng)內(nèi)部和社會力量。第四,終局性。這是指審判權(quán)行使的結(jié)果——法庭判決,在法律上具有最終效力,除了上訴或再審之外,不能被審判權(quán)之外的法律程序推翻。〔18〕參見陳瑞華:《司法權(quán)的性質(zhì)——以刑事司法為范例的分析》,載《法學(xué)研究》2000年第5期,第45頁。
審判權(quán)包括兩項核心權(quán)力:管轄權(quán)和裁判權(quán)。管轄權(quán)劃定了審判權(quán)的管轄范圍,裁判權(quán)則是對法律爭議的處理,后者無疑是審判權(quán)最核心的領(lǐng)域。裁判權(quán)的行使是一個將法律規(guī)范適用于具體案件事實的過程。這一法律適用過程可以分解為兩個方面:一是根據(jù)案件事實作出法律定性,即合法還是違法;二是根據(jù)法律定性施加相應(yīng)的補救或懲罰。在刑事法領(lǐng)域,這兩個方面就是定罪和量刑。以此觀之,定罪權(quán)和量刑權(quán)就是刑事訴訟法上的裁判權(quán)的兩項核心權(quán)能。認(rèn)定事實真?zhèn)蔚臋?quán)力并不是審判權(quán)的必要組成部分。這部分權(quán)力可以交給法官,也可交給陪審團、檢察官或其他機構(gòu)。因為事實認(rèn)定是一個經(jīng)驗問題,“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rèn)為事實構(gòu)成只能單獨由專職法官來認(rèn)定,因為這是每一個受過普通教育的人都能做的事,而不只是受過法律教育的人才能做的。”〔19〕[德]黑格爾:《法哲學(xué)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wù)印書館1961年版,第235頁。只有當(dāng)需要對案件事實進行法律評價的時候,即將已經(jīng)查明的事實歸于法律的概念體系之下時才涉及法律適用問題,這才是審判權(quán)真正的權(quán)力領(lǐng)域。〔20〕在美國刑事訴訟制度中,部分案件的定罪的權(quán)力也交給了陪審團,但這是美國憲法以公民憲法權(quán)利的方式授出的。也就是說,盡管陪審團分享了法官的審判權(quán),但這種分享是憲法明確認(rèn)可的。參見[美]約書亞·德雷斯勒:《美國刑事訴訟法精解》(第二卷·刑事審判),魏曉娜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頁以下。
(二)法檢權(quán)力的平衡關(guān)系
從現(xiàn)行《憲法》上看,檢察權(quán)與審判權(quán)的關(guān)系主要涉及憲法上的兩項基本原則:一是《憲法》第131條規(guī)定的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quán)原則;二是《憲法》第140條規(guī)定的分工負(fù)責(zé)、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
現(xiàn)行《憲法》第131條的規(guī)范內(nèi)涵可分解為五個層面:第一,“審判權(quán)”被《憲法》 授予了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quán),“獨立行使”包括了權(quán)力配置上的排他性,即唯有人民法院才能行使審判權(quán),也包括了權(quán)力運行上的獨立性,即其他主體不得干涉審判權(quán)的行使。第三,審判權(quán)的依法獨立并沒有排除中國共產(chǎn)黨、人民代表大會、檢察院以及2018年之后成立的監(jiān)察機關(guān)的合法干預(yù)。第四,人民法院的審判獨立不是絕對的,而應(yīng)當(dāng)受法律的限制。“依照法律規(guī)定”是一個法律保留條款,它包括正反兩個方面的內(nèi)涵:一是法律可以對審判權(quán)的行使作出規(guī)定,即立法權(quán)塑造審判權(quán)的行使;二是人民法院只需要按照“法律規(guī)定”行使審判權(quán),即排除了其他規(guī)范性文件對審判權(quán)的干預(yù)。第五,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法律對審判權(quán)的塑造是有限度的,因為審判權(quán)與立法權(quán)一樣是憲法權(quán)力,立法權(quán)不能濫用法律保留掏空審判權(quán)的核心領(lǐng)域。〔21〕參見[德]康拉德·黑塞:《聯(lián)邦德國憲法綱要》,李輝譯,商務(wù)印書館2007年版,第265頁。
現(xiàn)行《憲法》第140條則規(guī)定了在辦理刑事案件中檢察權(quán)與審判權(quán)的活動原則——分工負(fù)責(zé)、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所謂“分工負(fù)責(zé)”,是指公安機關(guān)行使偵查權(quán),檢察機關(guān)行使檢察權(quán),法院行使審判權(quán),三機關(guān)各司其職。所謂“互相配合”,是指公檢法三機關(guān)在工作程序上相互銜接,而不是互設(shè)障礙、相互刁難,更不是一味為了辦案效率進行流水線作業(yè),公檢法互相開綠燈置事實真相和法律規(guī)定于不顧。所謂“互相制約”,是指公檢法的職權(quán)行使都不能絕對化,成為獨立王國,而是要受到其他機關(guān)的權(quán)力制約。對此,彭真曾表示:“公、檢、法三個機關(guān)是相互制約的。在外國,只準(zhǔn)檢察機關(guān)監(jiān)督別人,不準(zhǔn)別人監(jiān)督它。我們則規(guī)定這三個機關(guān)之間實行分工負(fù)責(zé)、互相制約。公安機關(guān)要捕人,檢察院可以不批準(zhǔn);檢察院不批準(zhǔn)的,公安機關(guān)可以提出意見或控告,這不是互相監(jiān)督了嗎?檢察院起訴的,法院可以判也可以不判,檢察院對法院作的判決認(rèn)為有錯誤的,也可以提出抗議,這又體現(xiàn)了互相制約。”〔22〕《彭真?zhèn)鳌肪帉懡M:《彭真年譜》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16頁。在刑訴法學(xué)界,一般認(rèn)為控審分離原則是《憲法》上“互相制約”的一個具體原則。〔23〕參見劉計劃:《控審分離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頁。在上述原則基礎(chǔ)上塑造的刑事訴訟制度中,檢察權(quán)、審判權(quán)與辯護權(quán)的關(guān)系大致呈現(xiàn)這樣一個基本結(jié)構(gòu)(如圖1所示)。

圖1 我國傳統(tǒng)刑事訴訟中的法檢關(guān)系
在這種刑事訴訟結(jié)構(gòu)中,最為核心的兩組關(guān)系是以控辯平等為基礎(chǔ)的控辯關(guān)系與以控審分離為原則的法檢關(guān)系。法庭上的正義能否得到實現(xiàn),就取決于這兩組關(guān)系中權(quán)利與權(quán)力、權(quán)力與權(quán)力是否平衡。不過,在中國憲法體制下,檢察院除了公訴權(quán)之外,還有法律監(jiān)督這項非常重要的職權(quán)。這項職權(quán)在刑事訴訟中是指《刑事訴訟法》第20條第(五)項規(guī)定的訴訟監(jiān)督權(quán),即抗訴權(quán)。檢察院既是刑事訴訟的一方當(dāng)事人,又是審判活動的監(jiān)督者,是否會損害審判獨立呢?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的朱孝清表示,訴訟監(jiān)督僅僅是啟動二審程序或?qū)徟斜O(jiān)督程序,并不是對案件做實體性處分。“刑事訴訟中的裁判員始終都是法院,而不是檢察院。”〔24〕朱孝清:《中國檢察制度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xué)》2007年第2期,第119頁。照此理解,至少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確立之前,檢察院與法院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大致是平衡的。
三、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對法檢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影響
法檢機關(guān)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并不局限于現(xiàn)行《憲法》和國家機構(gòu)組織法的授予,《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中的一些條款也會影響法檢權(quán)力的配置。實際上,每一次訴訟法的修訂,或多或少地都會產(chǎn)生組織法上的效果。檢察院對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法律監(jiān)督就是在三大訴訟法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中逐漸發(fā)展出來的。2018年刑訴法修改所確立的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也對組織法上的法檢權(quán)力關(guān)系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其中,影響最大同時也是引發(fā)爭議最多的當(dāng)屬《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第1款關(guān)于檢察院量刑建議的規(guī)定。
(一)量刑建議的權(quán)力化
我國量刑建議制度源于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后一些基層檢察院的實踐嘗試。〔25〕參見李仁和:《量刑建議:摸索中的理論與實踐——量刑建議制度研討會綜述》,載《人民檢察》2001年第11期,第24頁。2010年2月,最高檢下發(fā)了《人民檢察院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dǎo)意見(試行)》。該意見明確規(guī)定:“量刑建議是檢察機關(guān)公訴權(quán)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lián)合發(fā)布了《關(guān)于規(guī)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根據(jù)該意見第3條和第4條的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提出量刑建議,被追訴方也可以提出量刑意見。2012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將量刑建議寫入了《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量刑建議制度推進到這一步,我們可以對其性質(zhì)做一個簡單的界定。
1.量刑建議制度一開始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改革公訴工作機制的一項內(nèi)容,盡管2010年的聯(lián)合發(fā)文意味著這項制度獲得了法院和公安部門的承認(rèn),但在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正之前,量刑建議并沒有進入法律層面,僅是檢察院的一項內(nèi)部工作制度。
2.量刑建議被檢察院視為其公訴權(quán)的一項內(nèi)容,但它的引入并沒有實質(zhì)性地增加公訴權(quán)的范圍或者強度,因為此時檢察院的“量刑建議”與被告方的“量刑意見”一樣,是訴訟當(dāng)事人站在各自立場的自我主張,對法院并沒有約束力。
3.量刑建議制度在不斷走向規(guī)范化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增加量刑建議的強度。2010年《關(guān)于規(guī)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 規(guī)定的是“一般應(yīng)當(dāng)具有一定的幅度”,而2012年《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規(guī)定的是“可以具有一定的幅度,也可以提出具體確定的建議”。從幅度量刑建議到確定量刑建議,表面上是增加了對檢察院辦案能力的要求,實際上由于訴訟監(jiān)督職權(quán)的存在,這一變化也在無形中增加了法院量刑的壓力。
然而,2018年《刑事訴訟法》改變了此前量刑建議的性質(zhì)。該法第176條第2款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認(rèn)罪認(rèn)罰的,人民檢察院應(yīng)當(dāng)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適用緩刑等提出量刑建議。”第201條又規(guī)定:“對于認(rèn)罪認(rèn)罰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這兩個條款意味著量刑建議的權(quán)力化。在立法學(xué)上,“可以”“應(yīng)當(dāng)”和“必須”都可以用來授予權(quán)力或施加義務(wù)。其中,“可以”一般意味著被授予權(quán)力的主體行使這項權(quán)力是被法律允許的,同時也是有選擇的,被授權(quán)的主體享有行使還是不行使這項權(quán)力的自由裁量權(quán)。〔26〕但在涉及公民權(quán)利保障的語境中,“可以”就有可能被限縮解釋為“應(yīng)當(dāng)”。See Alec Samuels, ‘May’ and ‘Shall’ and ‘Must’:Power or Duty? Statute Law Review, Vol.41, No.1, 2020, p.91.“必須”一般用于設(shè)置義務(wù)。“應(yīng)當(dāng)”有時候表示授權(quán),有時候表示設(shè)置義務(wù)。在表示義務(wù)時,“應(yīng)當(dāng)”等同于“必須”,只不過語氣更為緩和。在表示權(quán)力時,“應(yīng)當(dāng)”意味著被授權(quán)的主體不僅可以行使這項權(quán)力,而且有義務(wù)這樣做,它沒有行使還是不行使的自由裁量權(quán)。《刑事訴訟法》第176條第1款規(guī)定的人民檢察院“應(yīng)當(dāng)……提出量刑建議”是一個授權(quán)條款,這里的“應(yīng)當(dāng)”表示的是權(quán)力。而第201條第1款的“人民法院……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是義務(wù)條款,這里的“應(yīng)當(dāng)”表示的是義務(wù)。這兩個條款合起來構(gòu)成了一個明確的法律規(guī)范。
之所以將《刑事訴訟法》第176條的“應(yīng)當(dāng)”解讀為權(quán)力,而將第201條的“應(yīng)當(dāng)”解讀為義務(wù),是因為法律權(quán)力的一個核心特征就是權(quán)力行使這個行為包含了一個實質(zhì)性的“決定”(decision),〔27〕See Andrew Halpin, The Concept of a Legal Power,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16, No. 1, 1996, p. 152.而權(quán)力的支配對象必須接受權(quán)力主體的這個決定。〔28〕See Donald J. Kreitzer, An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Power, The 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45, No. 4, 1965,p.377.在量刑建議這個問題上,檢察院無疑是作出定罪和量刑決定的權(quán)力主體,法院是接受定罪和量刑決定的義務(wù)主體。要是沒有《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第1款對法院的義務(wù)設(shè)置,第176條第1款規(guī)定的量刑建議將與被告方提出的量刑意見一樣,對法院沒有約束力。但是,當(dāng)法律規(guī)定法院“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后,量刑建議就不僅僅是一項程序性的建議了,而是成為了一項實質(zhì)性的法律權(quán)力。只有當(dāng)量刑建議“明顯不當(dāng)”或出現(xiàn)列舉的五種例外情形時,法院才能徑行判決。〔29〕按照哈特對法律權(quán)力的定義,法律權(quán)力就是義務(wù)的缺席。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中,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權(quán)是實實在在的權(quán)力,而法院的量刑權(quán)卻被施加了“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的法律義務(wù)。(See H. L. A. Hart, Essays on Bentham: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97.)如果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僅僅是“不當(dāng)”,而沒有達(dá)到“明顯不當(dāng)”,法院也必須采納檢察院的量刑建議。
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聯(lián)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發(fā)布了《關(guān)于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指導(dǎo)意見》(以下簡稱《指導(dǎo)意見》)。《指導(dǎo)意見》第40條僅規(guī)定“量刑建議適當(dāng)?shù)模嗣穹ㄔ簯?yīng)當(dāng)采納”,至于量刑不當(dāng)?shù)譀]有達(dá)到明顯不當(dāng),這個區(qū)間的量刑裁量權(quán)歸誰所有,《指導(dǎo)意見》在這里并沒有明說。與《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相比,《指導(dǎo)意見》似乎在這里向法院讓了半步。但仔細(xì)一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這讓出的半步?jīng)]有多大意義,新《刑事訴訟法》已經(jīng)將量刑不當(dāng)?shù)譀]有達(dá)到明顯不當(dāng)?shù)倪@個區(qū)間的量刑裁量權(quán)劃給了檢察院,別說《指導(dǎo)意見》沒有明示這個裁量權(quán)給誰,就算《指導(dǎo)意見》將這部分裁量權(quán)給了法院,也會因為司法解釋與法律規(guī)定的不一致而導(dǎo)致無效。因此,《指導(dǎo)意見》在這里并沒有真正讓渡出權(quán)力。不僅如此,《指導(dǎo)意見》第40條第2款還明確要求法院不采納量刑建議的要履行說理義務(wù),相當(dāng)于對法院施加了額外的義務(wù)。
因此,在《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確立的“以采納為原則,以不采納為例外”的規(guī)則之下,〔30〕參見苗生明、周穎:《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適用的基本問題——〈關(guān)于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指導(dǎo)意見〉的理解和適用》,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年第6期,第22頁。量刑建議已經(jīng)從公訴人的意見轉(zhuǎn)變成為公訴人的權(quán)力,完成了從程序性權(quán)力向?qū)嵸|(zhì)性權(quán)力的轉(zhuǎn)變。而采納量刑建議已經(jīng)成為了法官的一項法定義務(wù),很多檢察院就是據(jù)此對未采納其量刑建議的法院判決提出抗訴的。〔31〕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檢察院單方提出抗訴的案件大多都是因為法院未采納量刑建議而引起的,適用法律錯誤和原審程序違法是其主要理由,而這兩項理由均指向了《刑事訴訟法》第201條。參見張青:《認(rèn)罪認(rèn)罰案件二審實踐的邏輯與反思》,載《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20年第6期,第132頁。此外,從量刑建議的提出過程來看,各地關(guān)于認(rèn)罪認(rèn)罰案件的實施細(xì)則,基本仿照人民法院規(guī)范化量刑的要求,其精準(zhǔn)化量刑建議的提出方法、步驟與法院的量刑活動幾乎完全相同,只不過一個叫量刑建議,一個叫量刑裁判。〔32〕參見陳實:《認(rèn)罪認(rèn)罰案件量刑建議的爭議問題研究》,載《法商研究》2021年第4期,第165頁。
(二)量刑建議權(quán)對審判權(quán)核心領(lǐng)域的沖擊
《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的量刑建議權(quán)究竟屬于檢察院的公訴權(quán)還是法院的量刑權(quán),在量刑建議制度啟用之初就產(chǎn)生過一些爭論。當(dāng)時的主流意見認(rèn)為,量刑建議屬于檢察機關(guān)公訴權(quán)的范疇,它只是法院形成量刑裁決的參考,因此不存在量刑建議侵犯審判權(quán)的問題。但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確立之后,量刑建議已然完成了權(quán)力化。沿著上文對我國憲法體制中法檢權(quán)力的分析,我們可以用一個三段論來審查量刑建議權(quán)是否侵入了審判權(quán)的核心領(lǐng)域。
1.大前提:根據(jù)現(xiàn)行《憲法》第131條的規(guī)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quán),定罪權(quán)和量刑權(quán)作為審判權(quán)的核心權(quán)能受憲法保障;根據(jù)現(xiàn)行《憲法》第140條的“分工負(fù)責(zé)、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檢察機關(guān)不應(yīng)侵入審判權(quán)的核心領(lǐng)域,即檢察機關(guān)不能實質(zhì)性地行使定罪權(quán)和量刑權(quán)。
2.小前提: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進入《刑事訴訟法》之后,定罪權(quán)還在法院手中,但量刑權(quán)卻受到了明顯的限制。除非檢察院的量刑建議違法或明顯不當(dāng),否則法院必須接受,并且檢察院的量刑建議一般為確定性量刑建議,這大大壓縮了法院的自由裁量空間。
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確立之前,法院量刑權(quán)的范圍包括:(1)量刑建議合法卻明顯不當(dāng),量刑權(quán)屬于法院;(2)量刑建議合法但不適當(dāng)(未到達(dá)明顯不當(dāng)?shù)臉?biāo)準(zhǔn)),量刑權(quán)屬于法院;(3)量刑建議合法且適當(dāng),量刑權(quán)屬于法院。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確立之后,量刑權(quán)被分割為:(1)量刑建議違法,法院無需采納量刑建議,量刑權(quán)屬于法院;(2)量刑建議合法卻明顯不當(dāng),法院也不用采納量刑建議,量刑權(quán)屬于法院;(3)量刑建議合法但不適當(dāng)(未到達(dá)明顯不當(dāng)?shù)臉?biāo)準(zhǔn)),法院必須采納量刑建議,一旦法院不采納就會引起檢察院的抗訴;〔33〕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編譯部副主任董坤研究員明確表示:“量刑建議有些許偏差,但非明顯不當(dāng),法院也需保有寬容度和容錯性,采納量刑建議”“量刑建議明顯不當(dāng)?shù)模ㄔ喝孕枋艿匠绦蛐约s束,不能直接裁判,而是建議檢察機關(guān)先行調(diào)整量刑建議。”參見董坤:《認(rèn)罪認(rèn)罰案件量刑建議精準(zhǔn)化與法院采納》,載《國家檢察官學(xué)院學(xué)報》2020年第3期,第28頁。(4)量刑建議合法且適當(dāng),法院必須采納量刑建議,量刑權(quán)實質(zhì)上由檢察院行使。
在這一變化中,法院明顯失去了合法且適當(dāng)和合法不適當(dāng)這兩大最為主要的量刑裁量權(quán)行使的情形,并且由于確定性量刑建議的普遍采用,在這兩種情形中法院絲毫沒有裁量空間,量刑權(quán)已經(jīng)徹底交給了檢察院。實踐中,法檢雙方對于量刑建議不適當(dāng),但又未達(dá)到明顯不當(dāng)這個量刑空間,產(chǎn)生了激烈爭奪。由于檢察院系統(tǒng)內(nèi)部對量刑建議的采納率設(shè)定了相當(dāng)高的考核標(biāo)準(zhǔn),檢察院對于法院是否采納其量刑建議極為敏感,法院的不采納往往會引起檢察院的抗訴。但不是所有法院都會買檢察院的賬,因此在不采納量刑建議而引發(fā)的抗訴案件中,法檢雙方在量刑權(quán)上的矛盾就會暴露出來。例如,在“楊振元詐騙案”中,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是6個月以上管制,一審法院判了6個月拘役,兩級檢察院提出的抗訴理由認(rèn)為量刑建議并無明顯不當(dāng),法院未采納量刑建議屬于嚴(yán)重程序違法。〔34〕參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02刑終753號刑事裁定書。根據(jù)筆者訪談的一些刑庭法官的反饋,對于這種壓迫式的量刑建議,大部分法官會選擇服從,但也有少數(shù)法官會不采納量刑建議。
在量刑建議合法但明顯不當(dāng)和量刑建議不合法這兩種情形中,法院的量刑權(quán)也產(chǎn)生了實質(zhì)性的變化。當(dāng)量刑建議明顯不當(dāng)時,法院必須通知檢察院進行調(diào)整,只有當(dāng)檢察院拒絕調(diào)整之后法院才有權(quán)將其更改。此時法院的量刑權(quán)實際上已經(jīng)變成了量刑監(jiān)督權(quán)。同理,法院對檢察院不合法量刑建議的不采納,同樣也是一種量刑監(jiān)督權(quán)。前者屬于合理性監(jiān)督,后者屬于合法性監(jiān)督。在這兩種情形中,法院量刑權(quán)的行使都以檢察院量刑建議的提出為前提。認(rèn)為檢察權(quán)沒有分享審判權(quán)的公訴權(quán)論證顯然混淆了量刑權(quán)與量刑監(jiān)督權(quán)的差別。
3.結(jié)論: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高適用率、高采納率和高確定性量刑建議的背景之下,《刑事訴訟法》已然對量刑權(quán)進行了實質(zhì)性調(diào)整,檢察機關(guān)量刑建議的權(quán)力化拿走了大部分原本屬于審判權(quán)核心權(quán)能的量刑權(quán)。
主張量刑建議沒有侵犯審判權(quán)的合意論證認(rèn)為,量刑建議是控辯雙發(fā)的合意,是權(quán)力+權(quán)利,因此法院“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量刑建議不算對審判權(quán)的侵犯。〔35〕參見郭爍:《控辯主導(dǎo)下的“一般應(yīng)當(dāng)”:量刑建議的效力轉(zhuǎn)型》,載《國家檢察官學(xué)院學(xué)報》2020年第3期,第19頁。這種論證并沒有意識到法律權(quán)力代表的是一個意志自主空間,這種意志自主空間并不因被追訴一方的同意而被取代、被掏空。況且,對比一下《刑事訴訟法》中刑事和解制度中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達(dá)成的“合意”對法院的約束力就會發(fā)現(xiàn),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中量刑建議對法院的約束力強度究竟有多大。刑事和解是兩方私主體在平等自由的情況下達(dá)成的和解,合意的程度比被追訴人與檢方的合意要高得多。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檢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法律也只是規(guī)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從寬處罰”,而沒有要求法院應(yīng)當(dāng)采納檢察院的建議。
支持量刑建議權(quán)力化的類比論證認(rèn)為,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是一種代表世界潮流的新刑事訴訟模式,因此不能以原有的審判權(quán)與檢察權(quán)的關(guān)系來理解這項制度。這種觀點同樣是難以成立的。我國的司法制度是由憲法建立的,《刑事訴訟法》也繼承了《憲法》中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quán)原則以及刑事案件中公檢法“分工負(fù)責(zé)、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在沒有修改這些基本原則的情況下,重構(gòu)一個新的刑事訴訟模式本身就有違憲之嫌。在比較法上,雖然各國對于量刑建議是否屬于公訴權(quán)并沒有形成一致意見。但各國已達(dá)成高度一致的是,量刑建議從未被作為一項對法院有約束力的法律權(quán)力授予給檢察機關(guān)。〔36〕具體的情況統(tǒng)計,參見曹振海、宋敏:《量刑建議制度應(yīng)當(dāng)緩行》,載《國家檢察官學(xué)院學(xué)報》2002年第4期, 第118-122頁;王順安、徐明明:《檢察機關(guān)量刑建議權(quán)及其操作》,載《法學(xué)雜志》2003年第6期,第25-26頁。英國傳統(tǒng)的觀點認(rèn)為量刑是法官的專屬權(quán)力,控方不應(yīng)當(dāng)試圖在量刑方面影響法庭。英國2004年版的《皇家檢察官準(zhǔn)則》并沒有明確禁止檢察官有類似意圖或行為,但檢察官在量刑方面的影響也僅限于提醒法官。參見[英]安德魯·阿什沃斯:《量刑與刑事司法》,彭海青、呂澤華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9年版,第457-458頁。
四、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中法檢權(quán)力沖突的合憲性調(diào)控
(一)對 “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進行合憲性限縮
如果把我國國家機構(gòu)體系比喻為一棟建筑,那么審判權(quán)和檢察權(quán)就是這棟建筑的兩根柱子,柱子與柱子之間當(dāng)然也需要橫梁來加固,但如果橫梁架設(shè)得不合理,傷及了柱子的核心部分,就危及整個建筑的穩(wěn)定和安全。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設(shè)計中,一旦將“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解釋為只要檢察機關(guān)的量刑建議沒有超過“明顯不當(dāng)”的臨界點,法院就必須采納量刑建議,那么“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就會像一個楔子深深地打入審判權(quán)這根柱子中。對此,有必要對這個權(quán)力配置的“楔子條款”進行適當(dāng)調(diào)整,讓審判權(quán)與檢察權(quán)的關(guān)系重回現(xiàn)行《憲法》和組織法上的平衡結(jié)構(gòu)。實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并不一定要啟動法律修改程序,刪除“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而是可以采用合憲性限縮的法律解釋方法,對“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進行合憲性限縮,不再強調(diào)量刑建議對法院的強制約束力,使量刑建議重新回到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正之前的程序性權(quán)力。
所謂合憲性限縮解釋,是指當(dāng)某些法律規(guī)范涉嫌與《憲法》相沖突時,為了使法律規(guī)范符合憲法的精神、原則和規(guī)范,而對法律規(guī)范進行一定的目的性限縮解釋,使原本與憲法相沖突的法律規(guī)范符合憲法。對“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的合憲性限縮包括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
1.重新界定法院“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量刑建議的理由。目前對“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量刑建議的理解,均偏向于將量刑建議看作是檢察機關(guān)的一項權(quán)力,將法院看作是這項權(quán)力的義務(wù)主體。這種形式化的理解容易制造法檢之間的對立情緒,不利于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順利推進。對該款進行合憲性限縮解釋的第一個方法就是對該款進行一個實質(zhì)化的理解。法律之所以規(guī)定法院“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是基于量刑建議本身是合法合理的,同樣法院之所以采納檢察機關(guān)的量刑建議也是因為量刑建議是合法合理的,而不是因為這個量刑建議是檢察院提出來的。照此理解,檢察機關(guān)對于法院未采納其量刑建議而提起的抗訴,其理由也應(yīng)該是法院未能準(zhǔn)確量刑,而不是法院沒有遵從檢察機關(guān)的量刑建議。在這個邏輯之下,法院和檢察院關(guān)于量刑建議的權(quán)力之爭,就從誰有權(quán)量刑轉(zhuǎn)換成為誰量刑正確。
近期最高院刑事審判庭公布的“蘇桂花開設(shè)賭場案”可以視為準(zhǔn)確運用“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的典型案例。在該案中,瀏陽市人民檢察院對一審法院的判決提起抗訴,其抗訴理由并不是質(zhì)疑法院量刑的正確性,而是“法院在事先并未書面或口頭征求檢察院是否調(diào)整量刑建議的情況下徑行在量刑建議幅度以下作出判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一條之規(guī)定”。該案的檢察院無疑將量刑建議理解為它的一項權(quán)力,法院必須采納否則違法。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是否應(yīng)當(dāng)采納量刑建議不置可否,而是將重心放在瀏陽市檢察院量刑建議和一審法院量刑結(jié)果的正確性上,認(rèn)為原審判決“定罪準(zhǔn)確,量刑適當(dāng),審判程序合法”。〔37〕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編:《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27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26-27頁。因此,二審法院的判決消解了法檢的權(quán)力沖突,同時也節(jié)省了司法資源,可為類似案件的處理提供參考。
2.限縮“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的適用范圍。根據(jù)2018年《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第1款的規(guī)定,在定罪正確且無其他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時,法院“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檢察機關(guān)的量刑建議,但該條第2款又同時規(guī)定,人民法院經(jīng)審理認(rèn)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dāng)”的,應(yīng)當(dāng)依法作出判決。在這兩款之間實際上有一個量刑的中間地帶沒有規(guī)定,那就是對于“一般不當(dāng)”的量刑建議,法院究竟應(yīng)當(dāng)采納還是可以不采納。檢察機關(guān)對“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普遍作擴張解釋,認(rèn)為“一般不當(dāng)”的量刑建議法院也應(yīng)當(dāng)采納。〔38〕參見陜西省人民檢察院課題組:《認(rèn)罪認(rèn)罰案件量刑建議精準(zhǔn)化——內(nèi)涵新解與采納規(guī)則重構(gòu)》,載《法律科學(xué)》2021年第3期,第152頁。但從協(xié)調(diào)法檢權(quán)力沖突的角度而言,應(yīng)當(dāng)對“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的適用范圍作限縮解釋。只要法院的判決在實體法規(guī)定的量刑范圍之內(nèi),檢察院應(yīng)當(dāng)保持克制,一般不應(yīng)當(dāng)針對法院的量刑提起抗訴。當(dāng)法院判決與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存在重大分歧時,檢察院向上級人民法院提起抗訴之后,該量刑建議對二審法院也不應(yīng)具有法律上的強制約束力。
(二)在“互相配合”原則下實現(xiàn)法檢關(guān)系的良性互動
對“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作合憲性限縮并不是要否定檢察院在推動量刑建議和量刑精準(zhǔn)化方面的努力,更不是否定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而只是適度抑制不斷進擊的檢察權(quán),預(yù)防因量刑權(quán)的轉(zhuǎn)移帶來的司法責(zé)任問題和司法能力問題,以及其他可能產(chǎn)生的系統(tǒng)性風(fēng)險。公檢法三機關(guān)應(yīng)繼續(xù)協(xié)同推進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完善和實施,繼續(xù)推進量刑精準(zhǔn)化工作,為法院提供更為明確可靠的量刑參考。但是,量刑建議的作用應(yīng)當(dāng)是協(xié)助法官更好地定罪量刑,而不是越俎代庖替法官量刑。為實現(xiàn)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提升司法效率的初衷,可以充分利用“分工負(fù)責(zé)、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中的“互相配合”原則,在工作制度和方式上協(xié)調(diào)法檢關(guān)系,讓量刑建議無需權(quán)力化也能取得良好效果。〔39〕參見李奮飛:《論認(rèn)罪認(rèn)罰量刑建議與量刑裁決的良性互動》,載《暨南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20年第12期,第59-62頁。
1.庭審前檢察院應(yīng)就量刑建議進行充分論證,并積極與法院進行量刑溝通。要實現(xiàn)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初衷,就要讓量刑建議通過說服而不是強制來使法院采納。一方面,檢察院在與被訴人達(dá)成認(rèn)罪認(rèn)罰具結(jié)書之前,可以與法院進行適當(dāng)溝通,聽取法院意見。另一方面,檢察院在認(rèn)罪認(rèn)罰具結(jié)書中應(yīng)盡可能寫明達(dá)成此種量刑建議的依據(jù)和理由,尤其是寫明被訴人、辯護人、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意見。目前格式化的具結(jié)文書僅簡要地記載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所涉罪名與法律依據(jù)、檢察機關(guān)量刑建議、被追訴人與值班律師自愿簽署聲明等事項。因此,有必要強化量刑建議的說理性,降低在審判環(huán)節(jié)辯方提出異議的可能性。
2.庭審中檢察機關(guān)應(yīng)向法院說明定罪量刑的主要考量,盡可能地展示量刑建議的產(chǎn)生過程,以取得法院的理解和信任。法院不采納量刑建議的原因大體有三個:一是真切地認(rèn)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dāng)”,二是認(rèn)為量刑建議構(gòu)成了對審判權(quán)的威脅,本能地抵觸量刑建議,三是不了解量刑建議的產(chǎn)生過程從而對量刑建議的合理性產(chǎn)生懷疑。因此,在庭審過程中,檢察機關(guān)有必要還原量刑建議的產(chǎn)生過程,讓法院理解量刑建議的合理性。法院在收到檢察院量刑建議之后,如果認(rèn)定量刑建議“明顯不當(dāng)”,應(yīng)及時告知檢察院予以調(diào)整。即便法院沒有通知檢察院調(diào)整量刑而徑行判決,由此而產(chǎn)生的程序瑕疵也不應(yīng)被認(rèn)定為審判程序違法。〔40〕同前注〔37〕,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編書,第29頁。除此之外,作為控辯雙方的合意結(jié)果,檢察院在接到法院調(diào)整通知之后,有必要與被起訴人、辯護人進行協(xié)商,而不能單方面修改量刑建議。
3.庭審后法院應(yīng)在裁判文書充分說明不采納量刑建議的理由和依據(jù)。量刑建議是控辯雙方經(jīng)過量刑協(xié)商之后達(dá)成的合意,法院對此應(yīng)當(dāng)予以充分的尊重。如果法院認(rèn)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dāng)”,且檢察院在收到法院的調(diào)整通知之后拒絕調(diào)整,或調(diào)整之后法院仍認(rèn)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dāng)”的,法院可以不采納量刑建議。但法院在裁判文書中不能簡單地寫一句“量刑建議明顯不當(dāng),故本院不予采納”,而應(yīng)詳細(xì)解釋檢察機關(guān)量刑建議過輕或過重的理由,并提出法院量刑的核心考量。這樣既能降低被訴人上訴的可能性,也是對檢察機關(guān)量刑建議的正面反饋,能夠消弭或減輕法檢雙方的沖突,減少檢察機關(guān)提出抗訴的可能性。〔41〕202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lián)合發(fā)布的《關(guān)于規(guī)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5條第1款第2項已明確要求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在刑事裁判文書中說明量刑理由,包括“是否采納公訴人、自訴人、被告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發(fā)表的量刑建議、意見及理由”。
五、結(jié)語
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是為了提升司法效能、節(jié)約司法資源、促進司法公正而推行的一項重要制度,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司法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成果在全國得到深入推行。量刑建議制度是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是控、辯、審三方關(guān)系的交叉點和爭議點,采用何種思路理解量刑建議實際上就是采用何種思路理解法檢權(quán)力關(guān)系。法檢權(quán)力關(guān)系本質(zhì)上是個憲法問題,相關(guān)司法體制改革也必須有憲法思維,有必要從憲法學(xué)的角度對相關(guān)爭議展開分析。無論是“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還是“檢察主導(dǎo)”都必須遵循現(xiàn)行憲法確立的國家權(quán)力體系的基本原理,都必須符合現(xiàn)行《憲法》對檢察權(quán)和審判權(quán)的基本定位。為了協(xié)調(diào)法院和檢察院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實踐中的可能沖突,必須對“一般應(yīng)當(dāng)采納”條款進行合憲性限縮解釋,重新界定法院遵從檢察院量刑建議的理由,并通過“互相配合”原則來實現(xiàn)法檢關(guān)系的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