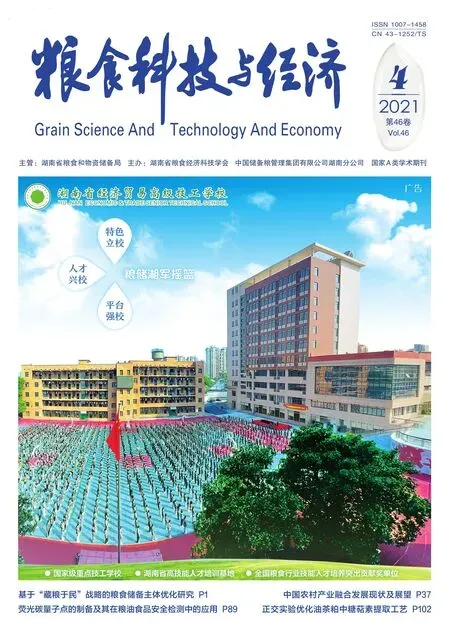糧食生產保障立法面臨的復雜關系分析
穆中杰,張 晨,胡 瑞
(河南工業(yè)大學 糧食政策與法律研究所,河南 鄭州 450000)
七十二行農為首。“三農”問題一直是黨和政府工作重中之重。抓農業(yè)農村工作,首先要抓好糧食生產[1]660。當前我國糧食生產領域面臨的形勢:一方面,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1978年以來實施的系列強農富農惠農政策,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不斷鞏固提升,2018年糧食產量6 579億kg,比1949年增長4.8倍,年均增長2.6%;人均糧食產量472 kg,比1949年增長1.3倍,守住了國家糧食安全底線[2],實現(xiàn)了溫飽型糧食安全。另一方面,糧食生產面臨著一系列嚴峻挑戰(zhàn)。耕地數(shù)量和質量呈雙降趨勢,備用耕地幾乎沒有,保障糧食種植面積困難重重,科技支撐能力滯后于現(xiàn)代農業(yè)發(fā)展需要,糧食生產經營設施基礎薄弱,風險防范能力脆弱,并且種糧比較收益偏低,種糧隊伍積極性不高且力量偏弱,國家糧食安全隱憂重重[3-5]。從更深層次來講,當代中國糧食生產保障立法面臨著如下矛盾亟待解決。
1 糧食生產相關主體之間的關系
糧食安全保障立法所涉法律關系較為復雜,既有行政主體之間的縱向行政法律關系,又有民事主體之間的橫向民事法律關系。有時甚至可以說,兩種法律關系縱橫交錯、相互交織。僅就糧食生產而言,不同利益主體對于經濟、社會、生態(tài)等效益目標均有追求,但又各有側重。對于中央政府來講,實現(xiàn)國家糧食安全的社會效益目標是其首要目標,而其采取激勵和監(jiān)管糧食生產措施,實現(xiàn)較好的經濟效益是次之目標;對于地方政府來講,無論是開展產銷合作還是自主生產,由于隸屬關系和政治大局要求而不得不慮及社會效益,實際上更傾向于追求經濟效益;對于糧食生產者(本文指以種植糧食為主要業(yè)務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包括種糧農民、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來講,經濟效益無疑是其追求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目標,社會效益實現(xiàn)只是一種客觀效果;對于糧食消費者來講,能夠買到物美價廉的糧食是其唯一追求,至于糧食是國內生產還是國外進口并不重要,糧食生產所涉的這三種效益似乎與他們關系不大。至于生態(tài)效益,由于其不是顯性目標,只有富于歷史責任感的政府才會對其特別重視,成為其主動追求目標,其他相關主體不會將其列為主動追求目標。
基于相關主體對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tài)效益的目標追求,認為糧食生產領域最核心的關系是政府和糧食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它們之間的關系可以歸納為“要糧”與“要錢”的關系。糧食生產者的經濟訴求能否得到滿足直接關系到國家糧食安全是否有保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低價收購”“無償調撥”等計劃經濟手段已經不具有可持續(xù)性,可行的方式是尊重市場主體的訴求,按照市場方式來取得糧源。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補貼就變得必不可少,而糧食生產者只有在獲得較好的經濟效益情況下,才會主動去種糧,履行供糧、供合格糧的義務。否則,糧食生產者的種糧積極性將會受到挫傷,最終損害的是國家糧食安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出去的不愿回鄉(xiāng)干農業(yè),留下的不安心搞農業(yè),再過十年、二十年,誰來種地?農業(yè)后繼乏人問題嚴重,這的確不是杞人憂天啊!”[1]678“誰來種地”成為中央決策層關注的重點問題,充分證明政府“富裕農民、提高農民、扶持農民”[1]677-680的措施和力度不夠,糧食生產者的經濟訴求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
2 種糧面積硬要求與土地經營自主權之間的關系
長期以來,黨和政府對糧食生產均有穩(wěn)定糧食播種面積的“硬要求”。早在20世紀50年代,國務院就有耕地面積“硬指標”要求,“五年計劃規(guī)定擴大耕地面積257.9萬hm2,是最低的指標,必須盡可能地用各種辦法超過這個數(shù)字。”[6]為了保證多產糧,毛澤東同志提出“田頭地角,零星土地,誰種誰收,不征不購”[7]。實踐表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種“硬要求”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能夠落地實現(xiàn)的。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這種“硬要求”越來越受到農民土地經營自主權的約束和挑戰(zhàn)。以全國第一小麥生產縣河南滑縣落實上級有關糧食播種面積的“硬要求”為例,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毫不放松抓好糧食生產,推動藏糧于地、藏糧于技落實落地,糧食播種面積穩(wěn)定在1.1億hm2。”2019年中共河南省委一號文件明確更加細化落實“硬要求”:“力爭優(yōu)質小麥面積達到90.0萬hm2、優(yōu)質花生面積穩(wěn)定在146.7萬hm2、優(yōu)質林果達到96.7萬hm2左右”。2019年滑縣人民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以文件落實分解指標:“力爭優(yōu)質專用小麥單品種成方連片種植達到0.7萬hm2、優(yōu)質花生種植達到2.3萬hm2,將玉米種植面積壓減至7.3萬hm2以下;擴大紅薯面積達到0.1萬hm2”。從形式來看,從中央到地方均有文件明確要求,糧食種植面積“硬要求”落地問題應該不大。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文件上的土地數(shù)字最終要體現(xiàn)在農民的田間地頭。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17條和第18條規(guī)定承包方在履行維持土地農業(yè)用途義務的基礎上,有權自主組織生產經營。這樣,種糧面積“硬要求”最終落地到農民田間地頭的時候出現(xiàn)了問題,農民承包的土地不用來種糧(比如用來種菜等)怎么辦?誰有權行使有關強制措施?采取有關強制措施的法律依據(jù)又是什么?
3 糧食生產高成本與種糧收入低效益之間的關系
糧食生產成本的高低有兩個參考尺度:一是國外糧食生產成本,二是種糧比較收益。兩者相比,種糧比較收益于糧食生產成本而言更具有直接的參考價值,它直接關聯(lián)到糧食生產者種糧積極性的高低。以2010—2019年河南省小麥每公頃均成本收益為例(見表1、表2),在這10年間,每年平均每公頃生產成本約為8 213.0元(最高年份為2014年的8 755.5元),每年平均每公頃產值約為13 393.3元(最高年份為2015年的15 229.5元),每年平均每公頃生產收益約為5 180.6元(最高年份為2015年的6 724.5元);近5年,該3項依次為8 436.1、14 515.4、6 079.3元。盡管與10年間每年平均每公頃的生產收益和生產成本相比,近5年二者均在增加,如果按每個農戶擁有0.67 hm2耕地來計算,半年收入也才4 053元,與到城鎮(zhèn)務工經商或城鎮(zhèn)居民相比,種糧收入相差甚大[8]。

表1 2010—2019年河南省小麥每公頃均生產成本

表2 2010—2019年河南省小麥每公頃均成本收益
就全國情況而言,據(jù)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張云華指出:2015年,中國玉米、稻谷、小麥、大豆、棉花等主要農產品公頃均總成本分別為16 255.8、18 031.8、14 764.5、10 120.6、34 326.6元,分別比美國高出56.05%、20.82%、210.42%、38.44%、222.84%。中國農業(yè)邁入“高成本”時代,農業(yè)生產效率與國際競爭力相對下降,進口農產品增加[9]。而國家的政策取向僅僅是“穩(wěn)定種糧農民補貼,讓種糧有合理收益”(2020年以前政策取向為“保障農民種糧基本收益”),因此糧食生產高成本而種糧收入低效益矛盾交織的直接結果是沒有人愿意從事糧食生產。要解決“誰來種糧”的問題,必須妥善解決糧食生產高成本和種糧收入低收益這對矛盾,讓農民不再因為經濟收益而沒有體面。
4 搶收搶種文化傳承與農業(yè)機械推廣之間的關系
搶收搶種文化在我國源遠流長。在農業(yè)機械尚為新鮮物件的年代,每年麥收秋種季節(jié),種糧農民一方面忙著收割麥子,披星戴月守候在地頭,在天剛亮的時候就已經割倒了大半畝麥子,趁著麥子還帶有“潮氣”就急匆匆地拉到了麥場里,開始打曬環(huán)節(jié);另一方面,拉麥車返回地里時,車上裝載的是秋糧種子、播種耬以及所需的化肥等農資,在剛剛收割完畢的麥田里播下了秋天的希望(有的秋糧需要麥壟點種)。這期間的一日三餐,多是家人把飯菜送到田間地頭。俗話“麥子上場,小孩兒沒娘”正是搶收搶種文化的真實寫照。但是,近年來,搶收搶種文化隨著農業(yè)機械的推廣逐漸異化,其承載主體逐漸由政府和種糧農民的共振演變?yōu)檎莫毥菓颉?/p>
據(jù)筆者參加的有關糧食經紀人隊伍調查[10-11],每當麥收(稻收)季節(jié),農機服務提供者把糧食從地里收割完畢,糧食經紀人在田間地頭就直接把糧食拉走,在此期間種糧農民只是把地塊交代清楚。如果和糧食經紀人比較熟悉,種糧農民甚至連地頭都不去,直接由其收割運輸結賬了事。在天氣正常的情況下,這種方式影響微乎其微,但如果突遇冰雹、大風等極端天氣,莊稼會因來不及收割而給種糧農民帶來嚴重損失。在問及種糧農民為何不再搶收的原因時,種糧農民幾乎都這樣解釋:主要依靠農機服務來收割莊稼,一會兒就可以收割完成,遇到極端天氣的概率太小了;萬一遭受損失,市場上也不會缺糧食,更何況這個損失可以靠打工來彌補。該情況表明,隨著農業(yè)機械化的推進,搶收搶種逐漸停留在政府文件要求層面,而種糧農民這一最終落實主體已經淡化許多了,糧食安全存在著潛在的威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耕文化是我國農業(yè)的寶貴財富,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不能丟,而且要不斷發(fā)揚光大。”[1]678盡管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開展耕讀教育”,但在實施“藏糧于技”戰(zhàn)略背景下,如何傳承搶收搶種等農耕文化已經成為迫切的現(xiàn)實問題。
5 農業(yè)走出去與應對措施少之間的關系
推動農業(yè)走出去對于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但迄今為止,農業(yè)走出去仍然存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zhàn),并且缺少有效地應對措施。國內因素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方面,“走出去”企業(yè)自身存在能力缺失的“短板”,比如企業(yè)多為融資能力弱、應對風險能力差的中小企業(yè),不僅缺少“走出去”所需要的各類綜合性人才,而且企業(yè)在技術應用上缺少自主技術研發(fā)推廣平臺,相互之間存在著競爭無序的情況;另一方面,政府有關配套完善的支持政策沒有跟上,促進農業(yè)“走出去”的信用擔保制度、保險制度、海外農業(yè)直接投資制度等方面尚有待完善,政府與“走出去”企業(yè)缺乏有效的結合機制。
國外因素主要涉及硬件和軟件兩個方面。硬件方面,東道國倉儲物流等基礎設施比較薄弱,致使交通成本昂貴;軟件方面是主要制約因素,比如東道國對國外農業(yè)投資實行保護性政策,對于購買土地或者并購企業(yè)有諸多限制,對于國外農業(yè)投資者在本國的用工有諸多限制,甚至有的東道國由于政局不穩(wěn)致使政治風險較大。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發(fā)生以后,“雙循環(huán)”戰(zhàn)略格局已經成為今后很長一段時期的被動選擇,農業(yè)“走出去”的風險還面臨著健康威脅。迄今為止,僅有西安愛菊集團等少數(shù)企業(yè)較為成功地“走出去”,為更多企業(yè)“走出去”提供了經驗借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農業(yè)走出去,要充分研判經濟、技術乃至政治上的風險,提高防范和應對能力”[1]677。糧食生產保障立法應該為支持農業(yè)“走出去”提供制度支撐,從而為相關企業(yè)獲得支持或者救濟提供法律依據(jù)。
6 結 語
糧食生產保障立法要處理的關系較為復雜,除本文重點探討的糧食生產相關主體、種糧面積硬要求與土地經營自主權、糧食生產高成本與種糧收入低效益、搶收搶種文化傳承與農業(yè)機械推廣、農業(yè)走出去與應對措施少等幾個主要關系外,還有糧食生產條件的有限性與糧食供給的持續(xù)性、糧食生產持續(xù)豐收與糧食供求結構失衡等關系需要結合糧食流通安全保障立法斟酌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