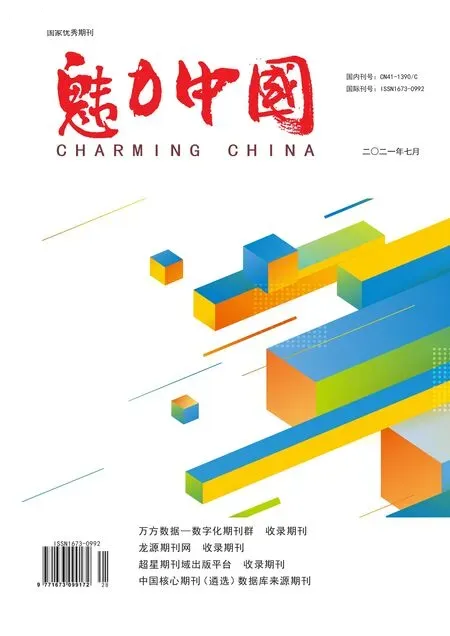新媒體輿論引導在小區治理的作用初探
裴馳宇 劉雨業
(浙江舟山日報社,浙江 舟山 316000)
現代社會,人們關注自己的居住品質,關心所在小區的生活環境、物業服務。可以說,隨著住宅供給市場化的深入,人們在擁有了通常是自身最大的家庭資產——房產的同時,開始關心自己與房產相聯結的方方面面,這不僅關系到房子的保值增值,而且直接影響自己的生活質量。家庭,作為社會的基礎單元,以房產這一物化形式來作為載體。居民自治意識的萌發,又讓人們迫切需要通過各種渠道表達自己的主張,與鄰居尋找共振,一起打造自己美好的家園。
恰恰,我們的基層社會治理,在引導小區業主自治管理這一塊,是相對欠缺與薄弱的。即便是一線城市北上廣深,也是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懵懵懂懂,鮮有成功經驗可以總結。
本人作為一名地市級媒體的新聞工作者,從2008 年開始,從傳統平面媒體轉型至網絡媒體、新媒體,在運用新媒體渠道合理輿論引導,讓居民小區治理走向規范方面,積累了一些心得。小區運行規范了,居民的生活安定得到了保障,十分有利于社會的穩定。
一、從業主“群”著手,把好業委會成立關
一些物業小區的管理亂象,往往是從小區業委會失控開始。而小區業委會的產生,業主大會籌備組是基礎。這幾年來,城市居民小區業委會,屢曝負面新聞。從籌備組的產生到業委會選舉,亂象叢生。有籌備組成員被毆打、有“兩個業委會”相互爭權、有業委會受干擾遲遲不能成立的……部分業主打著“居民自治”的招牌,利用小區業主希望改變現狀的愿望,裹挾民意,試圖掌握小區權力,令小區業主大會召開之路布滿荊棘。
現行的國務院物業管理條例,以及國家建設部的“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指導規則”,對小區首屆業主大會籌備組的產生,條款相對原則,并沒有具體執行的細則。
其中,《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指導規則》第十條規定,“首次業主大會會議籌備組由業主代表、建設單位代表、街道辦事處、鄉鎮人民政府代表和居民委員會代表組成。籌備組成員人數應為單數,其中業主代表人數不低于籌備組總人數的一半,籌備組組長由街道辦事處、鄉鎮人民政府代表擔任”。第十一條,“籌備組中業主代表的產生,由街道辦事處、鄉鎮人民政府或者居民委員會組織業主推薦……籌備組應當將成員名單以書面形式在物業管理區域內公告。業主對籌備組成員有異議的,由街道辦事處、鄉鎮人民政府協調解決。”籌備組中的業主代表如何推薦后確定產生,國家有關法規沒有具體規定。
現在網絡發達,相當多小區自發建了業主群。其中的活躍參與者,以業主群為平臺,組織自薦推薦票還是比較方便的。如單純以推薦票數量為唯一標準決定進入籌備組名單,則極易產生部分業主的意見代替了全體業主意見的情況,也易導致業主資格不符合的情況出現。因此,街道社區對籌備組人選的審核把關相當關鍵。
如基層街道社區不對籌備組自薦推薦過程以及具體人選加以審核把關,管理小區的權力極易落入到意圖不明者手中,而屆時木已成舟,政府部門加以挽回難度甚大。小區管理失控,可能讓居民正常生活失序,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子,后果堪憂。
我們看到,有的省市在物業管理辦法中,已經加入了“對籌備組、業委會候選人予以資格審核”的條款,動員小區兼合式黨支部成員、勞動模范、優秀志愿者進入業主大會籌備組,成為業委會候選人。在立法層面對小區業主大會籌備組的產生及選舉程序,給予法制保障,確有必要。
小區業主的意識大多是隨大流、從眾的,呈現無規則的“布朗運動”狀態。但當有了“業主群”這一平臺,大家從“意見領袖”的發言中,相對容易形成共識,進而公推出有聲望的業主代表。通過小區業主群的發動,尤其是運用群主的輿論引導能力,發現遴選業主中的優秀分子,顯得尤為重要,讓候選人員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打通民間與主流的“兩個輿論場”,為下一步業主大會的順利召開奠定基礎。
二、凝聚群體合力,讓“正能量”作主導
一個具有充分代表性、尊重最大部分業主利益訴求的業委會,是一個小區之幸,能讓一個小區管理井井有條,促進社會穩定;而一個代表性有局限又過于任性的業委會,則會讓一個小區陷入困境,甚至影響業主的基本生活。
目前,城市小區的物業企業、業委會與業主之間,產生的磨擦與爭議,相當頻繁。矛盾糾結,到了需要尋找理論突破的時候。究其原因,我們內地的物業管理制度,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從香港引進的。到現在,發現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物業管理制度,與我們現行的基層治理是存在某種沖突的。一個物業小區,從業委會的選舉產生,到物業公司的選聘解聘,它需要充分調動業主的參與意識。如果缺乏大多數業主的參與,所表現出來的業主群體意識發生偏差,把小區引向混亂。這,也應該是我們的最需要關注的方面。
以浙江舟山群島新區沈家門一個和潤金樽小區的物業更迭為例。該小區硬件不錯,在沈家門被稱為“十里漁港頭等艙”。但部分業主卻因為糾結于小區里安排了兩幢安置房,拒付物業費,蔓延開來,物業公司當了“冤大頭”,難以為繼,無奈撤出。
筆者所打理的房產類微信公眾號《住在舟山》第一時間,對此情況作了報道,2015 年10 月16 日,《沈家門和潤金樽花園陷入瀕危時刻》;此后,接連幾天,《沈家門和潤金樽花園物業停擺第二天:各方緊急商討出路》《垃圾溢出、樓道燈滅,高層面臨“無家可歸……沈家門和潤金樽危情第三天》,指出下一步面臨的情況:小區里以高層為主,沒有物業公司,公共部位電費無人支付,電梯可能停掉——這等于業主日常生活難以為繼。
筆者及時聯系了小區業主群的群主,了解業主們的想法。這位群主有一定擔當。他認為,小區業主不能糾結于過去歷史,而應齊心協力,先把費用收齊,把小區拉出困境。
運用公眾號的投票,以和潤金樽業主群群主的發言引導,《住在舟山》接連推送了五篇報道。2015 年10 月21 日《和潤金樽高層以一業主當場跪下:求求你們不要吵了,電梯停了我們怎么辦》、2016 年2 月2 日《欠繳物業費等同于拖欠保安保潔的薪水,舟山一小區的名聲傳到省城了》、2016 年5 月19 日《沈家門和潤金樽花園業主進入自救倒計時》、2016 年5 月28 日《放下執念、拯救家園——沈家門和潤金樽花園業主發出心底吶喊》、2016 年7月10日《在沒有物業的日子里,他們這樣來守護自己的家園》……層層推進,逐步凝聚起了小區里的“正能量”。一批理性的業主站了出來,成立了小區“自救小組”,并與街道社區銜接,成為小區未來業委會的雛形。在電梯被市場監督部門貼上封條的那一天,“自救小組”出面,延續了電梯維保。小區居民的正常生活得以維持。
三、讓市場的歸市場,引導樹立“花錢買服務”觀念 要小區長治久安,居民得樹立付費買服務的意識
在我們的城市居民小區治理中,存在著有物業公司管理的小區,與無物業的小區。當一個小區的物業公司越來越濫,或者物業公司本身也不想繼續干下去時,小區居民發現,原來有沒有物業公司都差不多,特別是一些上了年份的多層小區,它不繳物業費,這么多年來,日子不也過來了嗎?而有了物業公司我還要交物業費,受物業人員約束時,他一定會選擇不要物業公司,省下一筆物業費,而由基層社區來承擔最基本的保潔民生服務。
這樣的結果,人性的導向是,越來越多業主會選擇不繳物業費,而由社區來提供基本服務。這樣的情況蔓延開來,就是越來越多小區沒有物業打理,社會向下接軌。
當一個居民小區物業公司撤出,而后繼又沒有新的物業公司肯接手,小區居民生活陷入混亂,淪為無物業管理小區,那么,作為政府部門、基層社區有沒有義務去管理小區?維持最基本的保潔服務,讓高層電梯維持運行,保障居民最基本的生活條件不受影響?
舟山和潤金樽小區在物業公司撤出之后,確實出現了居民生活受嚴重影響的局面。筆者作為房產新媒體《住在舟山》的打理者,與小區“自救小組”的核心成員密切互動,一步一步引導如何組建業委會,再引進物業公司。在延續一年多時間里,合計推送了十六篇有關和潤金樽小區的報道。
在2017 年1 月1 日,和潤金樽小區迎來了頤景園物業進駐,居民在小區大門放起了鞭炮,小區終于走上正軌。
舟山和潤金樽小區至今運行順暢。從物業脫管、電梯停運再到小區組建業委會、引進新物業,這一系列過程成為小區解決物業脫管危機的“教科書”式樣板。《住在舟山》公眾號與房管、街道社區積極溝通,幾乎是手把手地指導小區居民如何“自救”,讓這近千戶居民的小區走出困境。
事后,舟山市房管局分管物業的負責人士評價,媒體的輿論引導,在處理小區物業脫管事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潤金樽花園居民與物業矛盾一度突出,曾鬧到派出兩車特警前來維持秩序。由于輿論介入,及時疏導,讓居民主流意識回到維護穩定、積極自救的軌道上來,一個行將“崩盤”的住宅小區得到了挽救。
現代小區治理中,要厘清這樣一個界限:基層社區不能代替物業公司去做事情。市場的歸市場,行政的歸行政。一定不能縱容拒繳物業費的“老賴”從中得益。有的小區物業公司因為陷于虧損,幾次想撤出,但因為社區動員,幾番挽留,高層沒了電梯可不是小事,才終于留下。而居民看到,反正物業公司不會撤,我索性物業費拖著遲交或者不繳也可以。由于社區的接管,反而縱容了這些不交物業費的業主。它不是一個市場行為。
而我們的媒體,有必要通過層層推進,擺事實講道理,讓廣大業主群體明白,“服務得花錢來買”,這跟一戶人家請保姆同樣道理,只不過一個小區聘請物業公司,是依賴業主的集體意愿。集體意愿出現偏差,則小區運行堪憂。
隨著現代物業管理制度的推進,業主群體參與小區自治意識的萌發,不同意識業主之間,存在著不同的訴求。如果合理引導這些訴求,這就需要我們媒體發揮作用,在各級政府和建設房管部門的主管指導下,為基層社會治理的穩定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