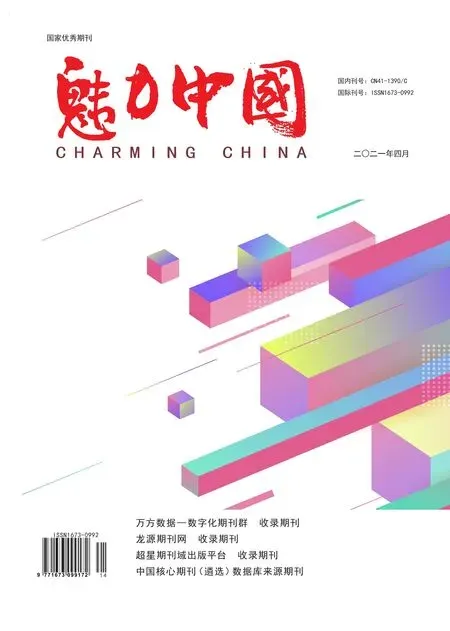城市非正式就業群體的生存狀況研究
——以大慶市為例
張安琪 曾媛媛
(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黑龍江 大慶 163316)
一、問題的提出
非正式就業是指具有非正式的雇用關系、未進入政府征稅和監管體系、就業性質和效果處于低層次和邊緣地位的勞動就業。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各國經濟的持續調整,非正式就業群體日益壯大,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報告顯示:全球有20 億人口正在從事非正式就業,占全球就業人口的61%以上,而全球93%的非正式就業是來自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2010 年世界銀行對中國六座城市展開問卷調查,得出中國33%的城鎮非農就業為非正規就業的結論,但因該數據未對建筑與加工制造部門的外來農民工進行調查,所以國內學者表示該項數據嚴重低估中國的非正式就業比例。由此可見,非正式就業在我國的整體經濟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
我國非正式就業的出現與改革開放相伴而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傳統正規的就業部門吸收就業能力不足,于是大量勞動力開始自謀生路,構建了非正式就業的雛形。同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使得農村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在比較優勢的作用下加速了人口流動,構成了非正式就業人群的主要部分。現實生活中非正式就業蓬勃發展,但現有的非正式就業服務卻難以真正滿足該群體的真實需求,如因服務系統不健全而導致非正式就業人群得不到即時就業信息、技能培訓和其他相應服務,這既讓非正式就業人群陷入低收入的經濟困境,也進一步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分割。
二、大慶市非正式就業群體的生存狀況
大慶市位于黑龍江省西南部,北方冬季漫長,農閑期的農民通常會選擇外出務工,受文化水平、工作時間、工作地點等原因限制,農民群體很難獲得正式就業機會,于是他們成為了城市非正式就業中的主力軍。同時,富有“油城”之稱的大慶市近年來強調轉型發展,企業的組織結構優化升級釋放出新一批城市勞動力,進一步壯大了大慶市非正式就業群體的隊伍。此外,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大慶市吸引了一批外部省份地區的人前來謀求就業機會,勞動力的不斷涌入卻不能與正式的就業崗位相匹配,進一步導致了大慶市非正式就業的產生。
本次調查對象為大慶市非正式就業人群中的裝修及其他家居服務類工人,該類人群常年聚集于定點街邊,以身側立牌為標志,牌上書寫如刮大白、通馬桶、修管道等內容,等待雇主“找上門”來。通過調查,大慶市非正式就業群體的生存狀況呈現出物質生活水平低、精神生活空虛、社會生存壓力大三項顯著特點。
(一)物質生活水平低
非正式就業人群就業機會少、能力差,只能在低報酬的崗位工作,且被替代性極高,這就導致他們沒有穩定可觀的經濟來源,無法保障其基本的生活水平達到正常標準。尤其是近年來大慶市高收入人群增多,推動城市消費水平提高,引發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之間的差距加大,在此種情形下,非正式就業群體的收入在飲食方面只能滿足吃飽這一基礎需求,追求飲食質量則成了虛妄。同樣在居住場所方面也只能達到風吹不著、雨打不到這樣的初級標準,居住位置、居住面積、居住環境則沒有能力去進一步考慮。
(二)精神生活空虛
非正式就業人群雖然沒有固定的工作場所,但卻有集中的“工作等待區”。為了使等待的過程不難熬,大多數人會選擇找點“樂子”來讓時間快點度過,而“樂子”的主要形式表現為聊天、打牌、玩手機、喝酒等。當調查員詢問,是否想過通過其他的方式來度過等待期時,絕大多數人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在于身邊的人都是這樣做的,只要來到這個地方,就會自然而然地融入進這樣的娛樂方式中。可見,同輩群體的消遣方式選擇對身邊人的影響是極其顯著的,而消極的娛樂方式不僅表明該群體的精神世界極度空虛,而且也為城市的市容市貌管理帶來了新的問題。
(三)生存壓力大
由于大部分非正式就業群體為農村涌向城市的勞動力,故調查顯示大部分人是背負著沉重的家庭經濟壓力來到城市務工的,原生家庭的經濟負擔讓他們在遠離家鄉的城市也依然透不過氣來。除此之外,非正式就業者表示,社會大眾對他們的認可度很低,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容易被人輕視,尤其是從農村涌向城市的非正式就業者,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為其帶去了心理壓迫,致使其出現了嚴重的城市融入問題,二元的身份分割在就業、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諸多領域皆為其帶去了巨大的生存壓力。
三、大慶市非正式就業群體生存狀況不佳的原因分析
(一)能力受限
教育水平是影響非正式就業的關鍵因素,大慶市非正式就業群體中大部分人教育水平不高,從文化程度上看,初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工人約占三分之二,他們主要從事高強度、重體力的工作。因為職業技能受限,沒有辦法從事專業性強的工作,加之該群體缺少進一步提升職業技能的想法和機會,所以他們只能從事低端性的勞動,接受收入低的現實,甚至面臨可以被隨意替代的結局,導致其陷入當下的生存困境中。
(二)缺乏主動性
大慶市非正式就業群體外出務工主要依托以親緣、地緣關系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社會信息網絡,這往往意味著在他們出發前對大慶知之甚少,來到新的環境中只能依賴初級關系為自己提供生存支撐。所以模仿“前輩”的生存方式,每天在固定的場地等待工作找上門,能為其帶去安全感,但消極式的等待既浪費時間、又效率低下,直接影響其經濟收入。同時在社會關系網絡的影響下,這部分人將逐漸被周遭同類群體所同化,具體表現為“混日子”式的生活方式不斷消弭著其身上的新鮮感與主動性,長此以往致使其陷入被動的工作局面中,難以改變現下的生活窘狀。
(三)缺乏自我保護意識
非正式就業群體中的大部分人是外地人,而非本地人,同等的工作量,外地人的工資總會比本地人的低,緣于他們不了解當地的工資水平與制度。同樣,時常加班卻從未得到相應的經濟補償更是家常便飯,甚至還有一些用工單位以欺騙的手段逃避為其繳納保險。因為缺乏自我保護與維權意識,非正式就業群體的薪資狀況不容客觀,這也間接導致該群體形成消極的自我評價,認為自己低人一等,這樣的認知為其帶去無限痛苦與折磨。
四、改善大慶市非正式就業群體生存狀況的思考
非正式就業群體的身份構建在實踐中彰顯著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步伐,但是相應政策法規的缺失,以及非正式就業服務平臺的尚未有效搭建,使得該群體陷入物質生活水平低、精神生活匱乏、社會生存壓力大的生存困境之中。為進一步改善非正式就業群體的生存狀況、為其增加經濟收入,從現實可行性角度來說,積極探索新型服務平臺搭建具有重要意義。如何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來臨之下,運用互聯網的技術賦能實現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突破傳統方式下被動等待式“求職”路徑的弊端,解決“客戶找人難,人求活難”的雙重難題,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現實議題。該項問題的解決不僅能使非正式就業人群的就業情況得以較為穩定性的改善,而且有利于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