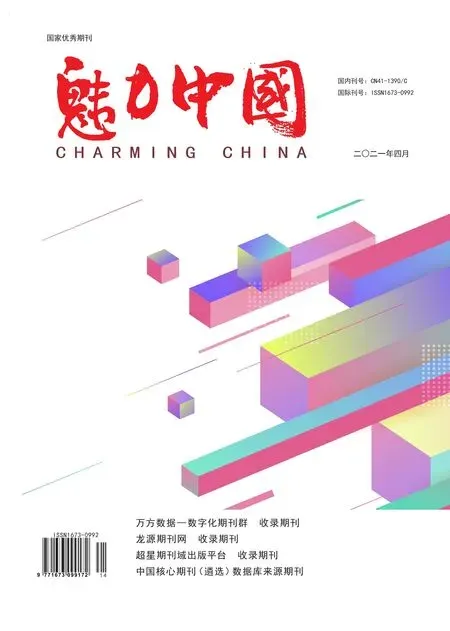蝴蝶亦夢,夢亦蝴蝶
——電影《蝴蝶夢》中的藝術神秘色彩解讀
陳煉
(四川外國語大學,重慶 400031)
一、引言
《蝴蝶夢》電影原著為英國的女作家達芙妮· 杜穆里埃的小說《Rebecca》,原著以女性Rebecca(呂貝卡)的名字作為書名,而電影將其翻譯為“蝴蝶夢”,使人聯想到中國古典故事——莊周夢蝶,以“蝴蝶”和“夢”為主體意向,營造出一種虛無縹緲、朦朧神秘、轉瞬即逝的氣氛。且整部影片中,希區柯克所運用到的藝術手法也是具有與夢境一般空靈、詭異、夢幻的神秘色彩,又帶有蝴蝶一般美好的小溫情式的愛情色彩,讓人置身蝴蝶亦夢,夢亦蝴蝶的神秘世界。
該影片主要講述了一位年輕女子在一次偶然中遇見了男主——曼德利莊園的主人德文特,女主人公以為他要跳海自殺便阻止了他,此舉動使德文特氣憤不已,他們也因此結下了緣。后來,二人因為機緣巧合相識相知而逐漸熟悉,慢慢地墜入了愛河。不久,男主人公便決定將女主人公帶回曼德利莊園。本以為幸福的生活就此開啟,可是沒想到這個莊園充滿了秘密。整個莊園到處都是前女主人——呂貝卡的影子,管家的態度和反應也咄咄逼人,這讓女主人公很難適應,充滿懷疑和恐懼。在莊園里發生了一系列離奇的事情,隨之而來的卻是真相的揭露。該影片情節起伏,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和藝術色彩。整個影片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其神秘感,神秘藝術的存在使作品散發出更獨特的魅力,探索其神秘色彩也將是一大亮點。
二、神秘藝術的存在
藝術作品之所以被創作出來的意義在于能夠通過多個方面、維度、視角讓讀者身臨其境于作品當中,而藝術色彩的呈現,更是作品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神秘色彩的建立,讓整個作品披上了一層面紗,觀者需要在作者的思想當中,展開延伸,以此對整個作品展開更深層次的聯想。
“神秘”是對未知世界的好奇,是對未知領域的探索,是置于人們常識以外的事實。談及神秘色彩,人們常常將其于宗教、法術等玄幻情節聯系起來,因為它常常是超脫現實的事物,所以令人不由得感到好奇。而在文學作品中加以神秘色彩的運用,能夠給讀者營造出更具興趣的閱讀氛圍,讓人不由自主地翻開下一章節。除了本身趣味性得以增強,也能夠將讀者置入其神秘的氛圍當中,讓讀者展開更多的聯想,可以稱之為是一種閱讀體驗上的思維延伸。我國古代小說中,常喜歡運用一些神話故事,以提升作品的神秘色彩,而隨著寫作手法的不斷更迭,一些更具現代化的神秘色彩作品也孕育而生。
電影《蝴蝶夢》被賦予了以下標簽:神秘、哥特風、懸疑、浪漫···在拍攝中,導演希區柯克采用了多種藝術手法,將神秘色彩展現得淋漓盡致,讓整個故事情節時刻保持著緊張、懸疑的氛圍,也正是因為神秘藝術的存在,才使得電影有了更多值得探索的價值。
三“莊周夢蝶”式的虛實關系
《蝴蝶夢》這部作品,從一開始的命名上,就“夢”緊密聯系。夢境在我們的一般印象當中,它是神秘、亦真亦幻的,它既充滿著美好的情愫,同樣也是轉瞬即逝的物象,給予我們的空靈與虛無,它既朦朧的不可觸及又如同流星般的轉瞬成空。作為“夢”的特性而言,在看到該題目的時候,便讓整部作品充斥著的是一種憂傷的情感,同時也為整個作品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讓讀者忍不住去探求這夢里存在的虛實。
從題目來看,《蝴蝶夢》電影參考原著為英國女作家達芙妮· 杜穆里埃的小說《Rebecca》,原著以女性Rebecca(呂貝卡)的名字作為書名,而電影將其翻譯為“蝴蝶夢”,使人聯想到中國古典故事—莊周夢蝶,蝴蝶在中國來說是浪漫感傷的,如蝴蝶,是愛情的象征;如夢,是幻象的象征。暗示劇情朦朧空靈,美好但易破碎,為作品增添了一絲憂傷色彩。以題目的神秘感留給觀眾無限的想象和揣測,鋪墊神秘氣息。
從情節來看,題目命名也暗示了女主角的人物性格,劇中的女主將自己反復代入前女主人呂貝卡,與之進行比較,以至于最后迷失自我,分不清男主愛的究竟是自己還是呂貝卡的影子,也正如莊周夢蝶,夢醒后一時分不清自己是莊周還是夢里的那只蝴蝶。劇中的女主人公自從跟著男主來到曼德利莊園后,她的身邊隨處皆可見可聞可感的都是前女主人的影子,她甚至覺得自己只是一個替代品,所以她的生活開始變得迷茫而無助,在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一切籠罩著她,促使女主人公的性格塑成。
從人物設定來看,原著的命名無疑不在體現該女性呂貝卡是全書極其重要的一個角色,但該角色一直只存在于其他角色的口中,在電影開頭就已經死去,至始至終從未出場,卻作為全劇最大的線索貫穿情節,這一點看來頗具神秘色彩。觀者通過女主人公的聯想展開,又與第一人稱展開敘述,與女主人公同時站在一個視角,對呂蓓卡的存在展開無限的遐想,為其添加了一絲神秘的色彩。她從未出現,但她又從未離開,她如同幽靈般的存在于各個角落。特別是當女主人公無意間穿上呂蓓卡穿過的衣服,眾人眼中的悵然若驚,更是將呂蓓卡身上的神秘氣息提升到了頂點,作為觀眾的我們,不得不去聯想眾人慌亂的原因,進而去聯想呂蓓卡的真實模樣。在人物關系的創作中以虛實糅合的方法呈現給觀眾以神秘恐懼的心理效果。存在與不存在的碰撞、虛實與真假的結合,虛實手法的運用,讓作品的神秘色彩再度升溫,為電影蒙上神秘氣息。正是由于前女主人公給女主人公強大的心理壓迫,使其命運也加上了一層濃重的宿命感傷色彩。二者命運的離奇化成一種神秘的力量,不可琢磨的力量,命運的神奇也渲染了影片的神秘色彩,使觀者看之,泣之,傷之。
從在虛實中結合冷色調,將整個電影塑造得更加撲朔迷離、陰森黑暗,給人以神秘而詭異的氣氛。畫面的黑白虛實,加之影片設定的英國的環境氣候,陰雨連綿,陰暗潮濕,雨水所掩蓋的不僅是畫面,還有真相。環境色彩的冷淡,畫面的虛實,易產生一種憂郁氣氛,而神秘感便在這樣的氣氛當中凸顯出來,它很好的做到了環境與色調的相互結合,讓觀眾置身于神秘的情境當中,去探索故事的軌跡。
四、參照物的設立手法
不論是寫文章還是藝術創作,都需要選定參照物,參照物的設立可以使得整個作品更加有層次感和立體感。作為一部懸疑題材的電影,《蝴蝶夢》在一開始便引出前任女主呂貝卡作為參照物,全劇以一人稱的手法展開敘述,觀眾與后女主人公一樣,充當了“探案人”的角色。而作為參照物的呂貝卡恰好就成為了整個故事的“線索”,女主人公以此為參照,通過呂貝卡透露出的種種形象,以及她對于整個莊園的影響力作為線索,逐步深入,以求探明真相。如此設定的好處在于,故事從一開始的時候,導演便早早地留給觀眾“線索”,讓整部作品看上去更具神秘。它的神秘在于參照物的無形身份,即真實存在,卻從未出現,同樣也在于參照物的強大影響力,讓我們可以透過與參照物有聯系的角色的真實表現作為線索,進而對整個故事進行深入。這樣的設定讓整部劇更像是一部偵探推理題材的電影,先將線索拋給觀眾,與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起探案,進而找到真相。
同時,電影將情節環境的參照物選定為英國多雨的氣候,原著的作者杜穆里埃是英國康沃爾人,康沃爾位于英國的西南部,氣候多雨,陰暗潮濕,她將作品基調也定為黑暗、凄涼的,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然環境的作用。電影延續了自然環境的影響,參照的依舊是冷色調,使得作品更加具有恐怖、懸疑的氛圍,也能更好地烘托出主題,為全劇奠定基調。電影所參照的社會環境是英國社會狀況的真實寫照,通過對真相的揭露實則也是對英國上流社會黑暗、丑陋、壓抑的批判,使得電影帶有一定的政治揭露意義。
對于懸疑題材的電影,神秘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通過設定參照物為線索的方式,它非常自然地將這種神秘營造在觀眾無法直接察覺的層面,再通過正常的故事情節發展,讓觀眾在不知不覺進入導演想要創造的意境當中。比起刻意的營造尷尬的神秘感,喪失作品原有的藝術效果,這樣更身臨其中的沉浸式體驗,這才是神秘藝術色彩的真魅力所在。它無法直接觀察,但它又時刻籠罩著這部作品,無形的體驗才是最佳的藝術呈現。
五、哥特風元素的神秘之道
電影保留了原著中的哥特風格,哥特風格是一種陰森、詭異、夸張而神秘的藝術風格,所體現在一些符號元素,特別是以頻繁使用縱向延伸的線條作為一大特征。在電影開頭,一個線條式的長鏡頭直接拉近觀者的目光,搭配黑色色彩的視覺沖擊,帶著觀眾通往曼德利莊園幽長的道路,給人以神秘詭異的感受。伴隨電影開頭的一句臺詞引入畫面:“曼陀麗是座墳墓,我們的恐懼和苦難都深埋在它的廢墟之中。這一切再也不能死而復蘇。我醒著的時候想到曼陀麗莊園,從不覺得難過。”“The house was a sepulcher,our fear and suffering lay buried in the ruins.There would be no resurrection.When I thought of Manderley in my waking hours I would not be bitter.”這是女主人公夢囈一般的自言自語,照應題目“蝴蝶夢”,令人撲朔迷離。
如何在作品當中加以神秘色彩的運用,環境上的敘述是必不可少的,原著在環境上的描寫也巧妙地運用到了哥特風元素。比如哥特式的城堡,大而陰森,空洞地給人以壓抑感;比如陰暗的森林,密集沒有生氣,似乎要把人困住于此;比如呂貝卡房間關的嚴嚴實實的窗戶,暗含善與惡的分割,生存與死亡的通道;比如教堂外青苔遍地的石階,驚濤駭浪的濤聲·· 這些元素不僅在視覺,也在聽覺和感覺上給人以感官沖擊,在塑造神秘詭異氛圍上,起到了不可小覷的作用。電影保留原著,從環境方面展開的拍攝,使觀者仿佛親自踏入曼陀麗莊園,它那充斥著的陰森氛圍,正好就為整個故事添上了神秘色彩。作為觀眾而言,我們不得不去好奇,這個莊園里是否埋藏著許許多多的秘密。而正是這樣的手法,通過環境烘托出整個故事的神秘氛圍,照應了它“夢”的主題。
哥特派小說式手法的運用,哥特風原本是指的一種建筑風格,但是到了18 世紀中期,開始成為一種新的小說樣式,作者將自身想象融入作品,以超現實的描寫手法創作,描繪一些負面場面,比如懸崖峭壁式的愛情,社會的陰暗面,人物的畸形心理等。由于電影改編自小說,在拍攝中運用到了小說里面的哥特式小說風格來拍攝人物。所采用到的反轉及夸張手法很好地推動情節發展,使劇情起伏,在電影中,一直沒有鏡頭給到前女主人公呂貝卡,僅僅是通過照片和仆人的口頭表述,夸大地描述出她的樣貌以及品行,讓人以為她是一個完美無暇,美麗動人的女人。實際上,在后面的劇情中,她的惡劣品行逐漸暴露,呂貝卡實際上是一個并不完美的女人,她是一個道德淪喪,貪慕錢財的人,是上流社會偽善特征的代表,有著很多缺點以及不好的行為,揭露了該人物內心的陰暗和丑陋的一面。這種錯誤的認識,反映出當時社會的三觀顛覆,將虛偽、奢華、腐朽的上流社會視為好,對他們不進行批判而是縱容、同流合污,而好的品質卻沒有在上流社會出現。這樣的反轉也是哥特派小說一大亮點,給電影的情節增加了神秘感,讓觀者先對呂貝卡產生吸引和敬畏感,隨之又產生厭惡和唾棄感,帶動觀眾的心理。
六、黑白色彩的視覺沖擊
作為電影而言,需要通過觸覺、聽覺、視覺等各個方面構造整體藝術的呈現。而色彩對于我們觀眾而言,是直接接收到信息,極富主觀的感覺。色彩的搭建,對整部作品而言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蝴蝶夢》這部作品受制于當時年代的電影技術,是一部由黑白灰色調拍攝而成的電影,盡管在2020 年本部電影迎來了彩色版的重制,但是老版的黑白色調的魅力仍然不可忽視。對于觀眾而言,一部黑白色調的電影,首先聯想到的便是時間,它可以很自然地將觀眾帶入到故事所寫的時代當中。
對于這部頗具懸疑的電影,黑白色調同樣能增添其神秘感,我們無法從視覺上讀取到劇中的色彩,但是并不影響觀眾對其產生的想象力。術上的瓶頸,也似乎并不影響導演對于整部作品的把控。例如《蝴蝶夢》中的一幕經典場景,當女主人公受到管家太太的哄騙時,意外的穿上了昔日男主前任的禮服,男主驚訝不已,他的姐姐更是直呼其名“呂貝卡”。雖然這一幕只是用黑白的鏡頭呈現,但是導演巧妙的運用了光影,當女主人公走下樓梯時,透過窗外陽光的照射,在女主臉上反復的光影,襯托出了女主人公內心千絲萬縷的緊張情感。僅僅這樣一個鏡頭,便讓整部電影的神秘感再度提升,暗示“我”對于眼前發生的一切疑惑不解,同時也暗示了故事情節的跌宕起伏,以及女主人公日后命運的種種改變,而“我”始終是不明白眼前這一切發生的緣故,作為觀眾的感受也同樣如此。神秘感與眼前的陽光相互照應,美好的夢境也隨著這縷透過的陽光照穿現實。
在原著中作者達芙妮·杜穆里埃擅長概念隱喻的手法。石南花的意向在文中出現三十多次。原文提到:“黑乎乎的林子頓時稀薄了下來,那些無名的灌木不見了蹤影,路兩旁可以看見遠遠高出人頭的血紅色墻壁——汽車駛入了石楠花叢。石楠花的突然出現使我有些慌亂,甚至有些吃驚。在森林中行駛時,我沒料到會有這樣的情景。石楠花紅艷艷的,嚇了我一跳。這種植物一株挨著一株,茂盛得令人難以置信,看不見葉子,也看不見枝干,只有滿目血淋淋的紅色,俗麗而怪誕,跟我以前見過的石楠完全不同。”這里的石楠花是具有色彩,且嚇人的,但是由于當時1940 時代的技術限制,這一幕幕經典的鏡頭都只能用黑白色調顯示,失去了它原本的色彩。雖然在2020 年對電影進行了色彩重新繪制,但是加以色彩的絢麗之后的電影,卻失去了它本該保持著的神秘感。在1940 年版的黑白色調中,盡管它沒有顏色,但是它卻為觀眾提供了無限想象的可能,讓觀眾通過自己的想象力,去感知這些鏡頭應該以怎樣的顏色呈現,從而讓觀眾更沉浸于這個故事當中去。所以,對藝術作品恰當地運用色彩,可以使原來的作品創造出更多的想象空間,讓觀眾是真正地參與到這個故事中來,而不是以情節強硬推動著觀眾向前觀看,這樣反而喪失了本該有的無限的想象空間。
正是導演對于色彩藝術的精妙掌控,才讓一部黑白色彩的電影煥發出彩色的情感,給予觀眾視覺上的沖擊。電影巧妙地利用了人類的視覺感官,完美的呈現出它想表達的神秘感,與色彩藝術相互結合,使整部劇的情節更加撲朔迷離,讓人琢磨不透。
七、封閉空間中的重復手法
影片中將曼德利莊園塑造成一個封閉空間,鏡頭重復給于隨處可見的“R”標志,這是Rebecca 的首字母,象征了前女主人呂貝卡的標志。“R”標志在衣服上、絲巾上、門上、家具上,隨處可見,“R”標志的重復出現,不僅使女主人被壓抑得無處可逃,也使觀眾彷佛置身其中被緊緊包圍。如此高頻重復的鏡頭,充分地向觀眾透露了該情節的重要性,更是給觀眾提供了影片故事的“線索”,它像是開啟真相大門的鑰匙貫穿整個劇情,讓影片變得更加扣人心弦。通過在封閉空間內重復的手法,自然的營造出一種耐人尋味的神秘感。
影片中重復出現的特寫鏡頭還有“門”,呂貝卡所居住的西廂的那扇門,女主人公一直對其充滿了好奇與恐懼,想要打開看看,這扇門顯得很陰森,似乎門后隱藏了巨大的罪惡和秘密,以及通往呂貝卡房間的階梯和通道,都顯得那么神秘而詭異。重復的手法將神秘色彩加重,起到強調作用,同時給觀眾以重點關注感。
由于電影所選環境是陰森恐怖的,大海整日被籠罩在烏云之下,陰森的氣氛被渲染得更加恐怖,女主人公在封閉的房間內,每日都可以聽見海浪擊打巖石的聲音,聲音的重復,彷佛將其包圍。利用視覺和聽覺上的重復,使畫面更加神秘而恐怖。
在莊園這樣封閉的空間下,女主人公每天還會面對仆人和管家,而管家對待女主人公的態度更是讓人捉摸不透,甚至令人感到氣憤。管家每日對女主角重復的擠兌,以及重復的話語,在封閉空間下顯得尤為刺耳和令人難受,這也形成了一種恐怖氛圍和神秘感,讓觀眾猜不透管家的想法和內心,想要去探索其原因和根本。
八、鏡頭下的敘述方式
《蝴蝶夢》這部作品,主要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展開敘述,對于觀者而言,站在了一個上帝視角當中,從一開始便知道整個故事的真相。但作為女主人而言,并不知情。而觀眾正是通過第一人稱的方式,置身于故事的世界當中,以女主人公為中心,展開整個故事的進程。這樣的好處在于讀者的代入感更強,很容易就進入作者設定的情景。
電影中采用了兩種鏡頭敘述方式,一是限制性敘述,二是非限制性敘述。類似于電影中的客觀視點和主觀視點,客觀視點不帶有主觀意識,只是采用普通觀眾視覺進行記錄和拍攝場景和事件,電影中的景物、場景拍攝采用客觀視點。主觀視點是從劇中人物視角拍攝,可以帶領觀眾隨著角色走進劇情,具有體驗感和代入感。
(一)限制性敘述,就是將觀眾對視角限制,所獲得對信息僅限于主角鏡頭所獲知對范圍。這樣對鏡頭手法類似于我們寫作常用到的第一人稱法,電影中開始以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使觀眾借助女主人公“我”的視角,如同身臨其境一般,感受劇情發展。在“我”想要探索呂貝卡的秘密時,鏡頭一直跟隨著“我”所走,“我”看到那扇緊鎖的門的緊張和恐怖感,也給了觀眾同樣的感受,此后女主人公對于呂貝卡的發現大都采用了限制性手法,讓觀眾親身體會到神秘與恐懼。
(二)非限制性敘述,指的是觀眾擁有更全面的視角,也可以稱之為“上帝視角”。觀影的觀眾就像是整個故事的“窺探者”能直面整個真相,而跟隨故事主人公去成長,去探明其中的虛實。比如在影片中,當女主人公穿上呂貝卡生前的裝扮去參加宴會,觀眾都已經猜想到這是一場陷害,但是只能替女主默默緊張,等待后面劇情的發展,在已知中塑造未知,這是非限制敘述手法的神秘之處。
兩種敘述方式的結合,是該片營造神秘懸疑的重要手法,前者可以讓觀眾有更好的代入感和體驗感,后者則賦予觀眾更廣泛的感受和想象,使影片的神秘色彩更具戲劇張力。
九、中西方隱形女主人公對比
此方面雖可以視為引申方面,但是也可以在中西作品對比中探究一些神秘性和藝術性。《蝴蝶夢》這部電影講述的故事情節似乎與我國近年來熱播的古裝電視劇《甄嬛傳》如出一轍,同樣都是故事中并不存在,卻時刻提及的前女主人對現女主人的生活方方面面的影響。《蝴蝶夢》中的呂貝卡與《甄嬛傳》中的純元皇后都是介于無形與有形的人物,他們的形象全憑電影中其它人物的口述,這種似有似無的神秘感給整部作品帶來了頗具懸念的效果。他們對于整個故事起著參照物的作用,將現有的女主人公與前任進行反復對比,推動女主人公產生各種的聯想,從而影響著整個故事情節的發展。而《甄嬛傳》最大的不同在于它融入了我國封建時期的傳統思想,將對于女性的真善美融入至純元皇后的形象當中。與她而言,她僅僅只是權利斗爭下的一枚棋子,她需要受到傳統思想的大量束縛。《甄嬛傳》中有一幕經典的鏡頭,在皇帝最初選妃的時候,當太后聽到待選嬪妃沈梅莊未讀過四書五經時,欣慰的回應了一句“女子無才便是德”便將中國封建時期對女性的刻薄凸顯的淋漓盡致。于純元皇后而言,她是封建社會完美的女性形象,但她最后卻慘死于弱肉強食的宮廷斗爭當中,展現出作者對這種思想的反諷與批判。
上映于1940 年的《蝴蝶夢》卻與傳統的東方文化不同,劇中的女主人公出身低微,但男主人公卻擁有奢華的莊園,他們之間的愛情并不平等,僅僅建立在男主人公的“施舍”當中。但隨著女主人公在劇中的不斷成長,以及她想要探尋呂貝卡真實形象的過程中,彰顯了女主人公心智上的成長,她開始追求的是平等的戀愛,她不再對丈夫的所作所為絕對服從。與純元皇后面對等級森嚴的制度無可相比,《蝴蝶夢》更想表達的是女權主義思想,是農耕時代與工業革命的交替,是過去女性與現代女性的轉變。而呂貝卡的形象卻與之截然不同,她既風流成性對感情不忠,又愛慕虛榮,貪圖其丈夫的財富。不得不說作者在兩者形象上的鮮明對比,不僅僅只是對兩位女性的對比,而是結合歷史背景下的批判,進而將故事升華至社會及人性的思考。兩部作品在故事上情節類似,但究其目的都是結合時代背景的深入刻畫,打開觀眾的想象,為觀眾提供無限遐想的可能,神秘感是兩者共同的精髓所在。
十、結語
此篇對《蝴蝶夢》神秘藝術色彩的解讀,從神秘藝術的存在、“莊周夢蝶”式的敘事關系、參照物的設立手法、哥特風元素的神秘之道、黑白色彩的視覺沖擊、封閉空間中的重復手法、鏡頭下的敘述方式、中西方隱形女主人公的對比八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希區柯克導演嫻熟的藝術手法將電影的神秘夢幻表現的淋漓盡致。它讓觀眾在觀影的同時能夠打開自己的思維展開對劇情的想象,透過這種神秘的氛圍,去揭開故事的真相,最后享受一場極佳的感覺盛宴。神秘手法的運用賦予作品更高的想象空間,也讓它的藝術價值得以體現,更為導演希區柯克在世界電影發展中奠定了成功的基礎。
《蝴蝶夢》是一部神秘而夢幻的作品,在電影的歷史當中,它從未平庸,不論是對文學作品的提煉,還是與中國文學作品的結合,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呂貝卡成為一種虛無的信仰,變成虛幻的“夢”,是上流社會的腐朽污濁之氣,女主人公所經歷的種種也似一場“夢”,這樣的夢籠罩了一層面紗,夢亦蝴蝶,蝴蝶亦夢,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彷佛使人置身神秘世界,如夢如幻,無法自拔。電影使觀眾得到了極高的審美滿足,它似夢非夢,卻又亦真亦幻,它遙不可及,卻又是你我能感知的情感。最后電影透過神秘反射出的真相,無疑是一次導演與觀眾共同的心靈旅程,得以讓它在宏大的電影歷史長河中,留下鮮明的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