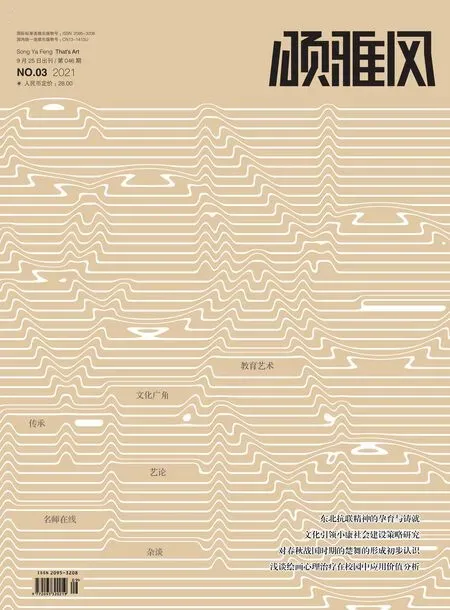論漢代瓦當演變中的審美意識體現
◎劉沁宇
瓦,《說文》解釋為:“瓦,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形也。”段玉裁釋:“凡土器未燒之素謂之坯,已燒謂之瓦。”瓦當最早出現于西周,在春秋戰國時期和秦朝發展,在漢朝達到高峰。漢代瓦當既繼承了秦朝瓦當的藝術風格,又在當面、結構、風格等方面進行創新,形成了漢代獨特的藝術風格。漢代瓦當的發展與演變與漢代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民族風格、階級關系等方面有密切的關系,因此隨著漢代皇朝的變化,瓦當的風格及所體現的倫理性也在轉變。瓦當發展的高峰期在西漢,西漢建立相關與生產關系相適應的體制,促進生產力發展,經濟文化的繁榮促進了瓦當的發展;東漢時期瓦當由西漢的張揚開放的風格轉向保守進而漸漸沒落。漢代瓦當的發展演變是漢代人審美觀與倫理觀演變的結果。
一、禮與教
漢代初期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的黃老學說。“禮”在鞏固政權、確定君臣尊卑以及維護社會和諧起到重要作用。這從賈誼的《新書》中可以體現出來:“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強弱有位,禮之數也。”賈誼的禮治思想是對荀子禮治思想的繼承與發揚。
漢武帝時期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確立以儒家倫理為正統的文化,使儒家禮治思想和政治、經濟、教育結合,推崇董仲舒“大一統”“三綱五常”理念。其中,對“孝道”的提倡尤為突出,建立內外分明的符合現實需要的君權維護手段。東漢時期將讖緯之學與經學及禮治結合起來,使禮制染上了一層神學化的色彩。
在漢代瓦當的形態風格等方面,也要體現儒家要求的仁義、孝悌、忠義、尊卑等級的理念,具有濃厚的禮教色彩。其根本原因還在于儒家思想。不同階層使用的瓦當的種類必須要按照儒家“禮”的規則去約束,以示禮的追求。董仲舒吸收道家、法家、陰陽家思想,結合儒家思想,系統提出“天人感應”“天人合一”學說。“天人合一”學說目的在于為天子的存在提供合理依據。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對王權懷有敬畏之心。
二、“美”與“用”
瓦當最早發現于西周,這個時期的瓦當實用性較強。西周瓦當以素面瓦當為主,多為半圓形,呈青灰色,主要用于保護屋頂檐頂椽頭。受儒思想影響,瓦當的首要功能是其實用性。漢代圓形瓦當既增大了面積空間,給予椽頭保護作用,又給瓦當的紋樣提供了更多的形式可能性。對稱性結構的瓦當也更牢固,符合力學原理。西漢瓦當沿襲秦朝時期瓦當風格,以動物紋、神獸紋為主,強調其審美性;再到文字瓦當出現,運用隸書和繆篆來體現其書法美學韻味。漢代初期瓦當以實用性為主,強調實用,東漢瓦當基本上為圓形,實用功能增強,此時瓦當審美意識減弱。到西漢,審美意識增強,而此時的審美是在實用性的基礎上進行升華。
圓形瓦當體現了穩定、完整的“圓之美”。《周易》記載了早期的圓道觀,即自然宇宙按照“發生——發展——消亡”模式運行,周而復始,生生不息。后期出現的“天人合一”“陰陽五行”等學說也源自于此。漢代的圓形瓦當造型依圓取勢,使當面紋飾及器型呈現“圓潤周轉”的形式美感。如“永奉無疆”瓦當便以飽滿的圓形為輪廓。漢代文字瓦當多為篆體,清代書法家王澎在《竹云題跋》:“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便指圓勁,“圓”所包含的張力通過篆書的筆畫線條與布局體現出來。在“圓”的結構中,漢代瓦當呈現出厚重質樸的人文氣息。
漢代瓦當紋飾結構主要分為結構對稱、螺旋形結構及自由結構。對稱結構是中國傳統審美意識追求。對稱性結構傳達出秩序、莊嚴、穩重的美感,且統一與圓形結構中。雖裝飾效果受到空間限制,但在有限的面積中以不同的紋飾都能恰好置于其內并體現出對稱均衡的美感。而這種整體和諧的布局效果實際上是以儒家思想最內在的審美感受。螺旋形結構的特點在于從中心逐漸向外旋轉,使其具有動感。主要表現在葵紋和水渦紋,呈飛輪之勢。漢代水渦紋多以單一圖案出現,水渦由當心向外旋動,呈現韻律感和積極向上的審美感。水渦紋瓦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自然崇拜。自由結構的瓦當主要表現在漢代文字瓦當上,有順時針方向、逆時針方向、十字交叉方向等。但無論結構如何自由都會受到瓦當形制的限制,這種“不自由”也受到一定形式美的理念、規律等內在規約。
三、“神秘”與“理性”
從瓦當類型變化來看,漢代瓦當從“神秘”走向“理性”。從圖案紋瓦當到圖像紋瓦當再到文字瓦當反映了漢代人從自然崇拜到圖騰崇拜、神權崇拜到王權崇拜的轉變。
圖案紋瓦當流行于西漢初期,主要包括云紋瓦當、植物紋瓦當及水紋瓦當。其中以云紋瓦當為主流。云紋瓦當始于春秋戰國,在秦漢時到達巔峰。數量繁多,種類豐富。漢代初最流行的是蘑菇云紋瓦當,西漢中期云朵紋瓦當成為主流。云紋瓦當的形勢特點由具象到抽象、由簡到繁。主要以瓦當中心為中點,對云的形狀進行重復變化組合,圖案飽滿,形制規整。
漢代云紋瓦當的主流地位與社會盛行的成仙觀念密不可分。“神仙”是雙重結構性詞語。“仙”繁體作“僊”。劉熙《釋名》:“老而不死曰僊”。僊,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許慎《說文解字》:“僊,長生遷去。”長生不死是成仙的特征。“神”指天神,許慎《說文解字》:“天神,引出萬物者也。從示、申”。在漢人觀念中,神是早已注定的,是萬物的創造者與主宰者,無法逾越,只能頂禮膜拜;“仙”則可以通過修煉或服食仙丹等方式羽化升仙。《后漢書》記載:“密縣上成公”初行久而不還,后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成仙的本質即長生不死,靈魂升天。長沙馬王堆墓出土的《人物龍鳳圖》《人物御龍圖》帛畫中可以看出漢人對于升仙的追求。云為自然界的氣體,作為“氣”的變形,與仙人云氣相連;同時在魂魄以氣的形式升天啟發下形成云紋。《逍遙游》記載:“藐菇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將云紋所代表的神仙觀念嫁接至瓦當上,云紋瓦當的盛行也不足為奇。
圖像紋瓦當分為動物紋瓦當和神獸紋瓦當。相比圖案紋瓦當,其做工更為精細,審美意識體現得更為明顯確切,體現了漢人的圖騰崇拜。將圖騰觀念蘊含在瓦當中是漢人對于圖騰崇拜的明確體現。最為代表性的是漢代的四神紋瓦當,是經先秦文化洗禮后的產物。四神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代表東南西北四個方位。青龍象征水,為農作物的神,代表萬物生長。從漢朝起,龍就被確定為皇權的象征。皇宮大殿上多為青龍瓦當,起到樹立皇權權威的作用;白虎象征軍隊,可趨避禍害,對白虎紋的崇拜反映人們的敬畏之心;朱雀象征祥瑞,神話中的南方之神,其影響與龍不相上下,是讖祎之學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漢代神秘主義審美意識的體現;玄武紋是蛇和龜的結合體,龜為匍匐狀,蛇盤曲在龜上。龜蛇結合是長壽與力量的結合,表現漢人對生命力的祈望。四神紋瓦當是神獸與漢人審美意識相結合的產物,是“理性”與“神秘”結合的代表作。
文字瓦當的出現標志中國古代瓦當發展到鼎盛時期。尤至西漢后期,文字瓦當取代圖像瓦當占主導地位,多用于宮殿、禮制建筑。主要可分為吉語瓦當、禮制建筑物瓦當、墓葬名瓦當、官署名瓦當、歌功頌德瓦當等。王權崇拜是古代中國政治價值的主要核心內涵,古代的器物、建筑不僅是使用物體更隱喻深刻的政治內涵。在中央集權高度統一的漢代,文字瓦當便承載著這一濃厚的王權崇拜意識。歌功頌德瓦當對漢代發生的歷史大事及賢臣稱贊歌頌的記錄,是對漢代帝王豐功偉績、民族關系的真實記錄。官署名瓦當用于皇權機構,如軍事保衛部的瓦當、樂府機構瓦當等。以“衛”“倉”字為代表,“衛”為軍營,代表漢代的強大軍事力量;“倉”為糧倉,是漢代農業發達的體現,二者皆體現了漢代的強大國力。官署名瓦當以文字彰顯權力,體現漢代對農業軍事的重視。禮制建筑物瓦當主要用于宮殿,文字與圖案相結合,其意義在于統一意識形態、凝聚社會民心,為穩固皇權統治發揮積極作用。
吉語瓦當是人們對于美好生活愿望的體現,主要分為:一、祈求長命百歲,如“千秋萬歲”瓦當、“長生未央”瓦當、“長生無極樂”瓦當等;二、追求健康快樂、家宅平安,如“長樂未央”瓦當、“永保子孫”瓦當等;三、追求富貴, 如“大富”瓦當;四、祈福國泰民安,如“永保國阜”“漢併天下”瓦當等。吉語瓦當形制多為圓形,也有少數半圓形瓦當。結構規整,字體幾乎全為篆書,也有少許在篆書上變形,如“千秋萬歲”瓦當,字體采用鳥蟲篆,字體蜿蜒,字首為鳥狀,生動有趣。吉語瓦當是對世俗權力崇拜的另一種表現,以吉語為表現形式。在讖緯之學盛行,神權崇拜泛濫的時代,漢人們認為瓦當上的吉語能給主人帶來吉祥。文字瓦當的盛行,不僅豐富了瓦當藝術同時生動鮮活反映當時社會經濟、政治思想狀態。
漢代瓦當與漢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密切聯系,《易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瓦當所蘊含的審美意識與其結構的實用性融合是“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的結合。漢代瓦當從圖像紋瓦當到圖案紋瓦當再至文字瓦當的過程中,是神秘主義到理性主義的轉變,在這種理性主義中包含著其特有的感性與審美。這種特有的審美極為多樣的紋飾形式里包含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即上述所說的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王權崇拜。瓦當的審美意義是實用性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