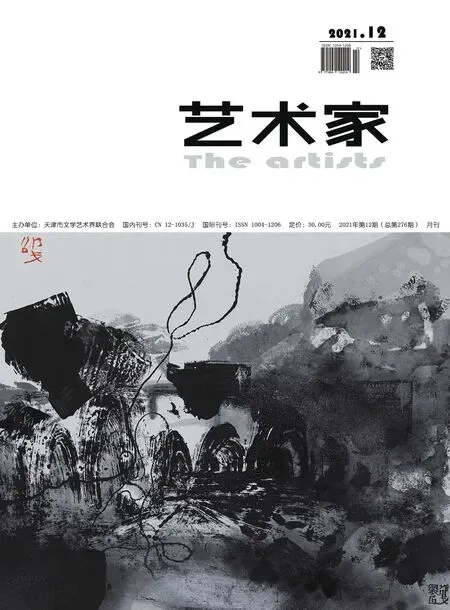狄青小說中的平民世界
□邵 迎 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
□盧 楨 南開大學文學院
縱覽天津小說創作界,20 世紀60 年代出生的作家可謂其中堅力量。他們大都潛心于中短篇小說寫作,或關注人文歷史,或還原市井百態,抑或抒寫情感人生……而狄青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狄青關注現實,近些年頻出力作,先是以《繳槍不殺》《閉嘴》等小說集精當呈現城市“小人物”的生存空間,彰顯其對“平民世界”的探問與追求,而后又以中短篇小說集《我不要你管》,更進一步拓展了對這一問題的思考。
自投身寫作以來,狄青一直以一種平視眼光和平常心態,關注和描寫蕓蕓眾生,特別是抒寫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他往往將人物置于時代轉型的大背景下探討人物生存的諸多可能性,或是在權力話語操控的生存場域之中表達自己對現實問題的冷靜思考,為小人物立傳,為時代作出注腳。小說集《我不要你管》中,匯聚融合了24 個背景迥異的各種小人物的生存景觀:為領導開車的司機,進工廠打工的鄉下女人,電影院的領位員,辦公室里的小公務員,研究所里的小科員,歌舞廳里的小姐,三流院校的普通講師,鄉里的文化站站長……把這些人物放回真實的話語現場,分明和現實讀者一樣,是蕓蕓眾生中謀求生計的普通人,既與光鮮的外表無緣,也沒有顯赫的身份光環。這些性格特征各異的平民人物競相登場,演繹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曖昧與冷漠、平淡與離奇。讀者體會作品人物的生存與毀滅,往往會投射出自身處境,生發些許的熟悉和共情。狄青就是從尋常人的視角講述著百姓的喜怒哀樂,讀者能夠感同身受,自然地代入聯想到自己的周遭人生與心靈現實。煙火人間,喜怒哀愁——狄青小說中的人物基本是平民身份,不管是城市中卑微打拼的蕓蕓眾生,還是游走在鄉野村鎮間的凡夫俗子,由于經濟基礎脆弱,權力資本缺失,注定了他們無法成為時代的弄潮兒,無法從容應對社會的種種變遷,甚至很難自由地支配自身的命運,而最終難逃成為他人操控對象的命運,陷入悲劇的人生境遇。如果將注意力集中在這樣的平民世界,對這些平民人物的生存時空進行一番文學掃描,或可發現一些比較集中的文本特質。
首先,不論主人公身份、地位、職業如何,狄青總是將人物置于難以疏解的“困境”之中,這成為推動小說情節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這些身處困境的人往往具有善良的心性,他們的肉體抑或心靈被粗糲的時代劃傷,無從醫治,傷口也難以愈合,無力改變自己的困境,卻也不愿傷害他人。在困境中,人有可能展現自己最為卑瑣的丑陋存在,也可能獲得一種超越意識,向世界表達善意與包容的一面。正因對“善”的抒寫,狄青的很多文本人物都充滿了人性的亮色。
在《那年冬天的第一場雪》中,作者透過主人公王秋風的內心世界,表達了小人物對人生和未來的無力感:王秋風感覺自己就像一個放風箏的人,在漫天狂風中緊緊攥著一只本不該屬于自己的風箏,關鍵是,甭管這風箏屬于別人還是屬于自己,他都已經攥不住了。他作為領導的司機,要替交通肇事的領導去頂罪,雖然最終證明了清白,但他仍然為那個被撞成殘疾的女孩而內疚。狄青筆下的主人公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地位不高,膽量不大,重要的是,他們生活在底層,卻最能秉持真誠、善良的精神品質。一般來說,生活在特定環境或者權力場域的人未必能夠認清自身的卑微境遇,也無法獲得超越自身“階層/階級”的能力去改變生存現狀,從壓迫者變成主導者。就像老舍說的:“生在某一種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個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魚似的,它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狄青不會像有的作家那樣,為作品中的主人公賦予傳奇般的經歷,甚至讓小人物在一個個“機遇”的錯合塑造中翻身變鳳凰,獲得自身階層和地位的提升。對于作家而言,現實不是童話,它難以被改變也不可能被孤單的個體超越。柔弱的個人如果選擇與堅硬的現實對抗,那結果只能是以卵擊石,頭破血流。既然現實的砧板牢不可破,那么個體想要收獲心靈的寧靜和精神的平衡,仿佛只能選擇隨遇而安。《那年冬天的第一場雪》的最后,王秋風最終和那個遭遇車禍的女孩走到了一起,女孩的一句話點出了她對生活的理解:“能活著就好,還要那么多干嘛。”看似風輕云淡,其間卻蘊含了現代人對生活的無力感和精神的幻滅,同時也道出了人物面對“困境”所表現出的堅強與達觀。
《那年冬天的第一場雪》的標題充滿了詩意和浪漫的色彩,但目睹作品中種種殘酷而真實的人生之后,幾乎所有人都會為那些人生際遇頗為“不順”,甚至有些倒霉的小人物的命運唏噓不已。浪漫的故事標題和殘酷的文本現實仿佛形成一組極富沖擊力的矛盾,用浪漫為殘酷賦值,透露出寫作者的反諷心態。從小說集《繳槍不殺》開始,狄青便經常利用文本,含蓄而內斂地折射出現代社會的諸多病態。在這部集子中,我們亦能看到一個個被金錢和權力壓榨的主人公形象,他們想追求簡單與平淡的生活,可這反倒成為虛妄的愿景,難以實現,似乎只有從“欲望”的前線上不斷退守,方能收獲暫時的精神平衡。看《越軌的貓》,主人公李東風即將被提拔為單位的處長,消息傳來,周圍的人都對平時并不起眼的老李刮目相看。同學老田為了搞“情感投資”,特意帶平日里膽小怕事的李東風去按摩,卻被警察帶走審訊,最后還是在老田的“運作”下才“安全”地被保出來。李東風感到老田無故請他又保他,必然是有所圖謀,日后肯定會求自己利用職務之便做違規的事。可現在把柄在人家手上,李東風頓時如坐針氈。深思熟慮之后,他竟然辭去了處長職務。在眾人不理解的目光中,李東風收獲了難得的自在與踏實。在這個講求關系、物欲橫流的時代,李東風這樣的人自然是吃不開也混不下去的,他剛剛上任就面臨人生的一大困境——授人以柄、不得不以權謀私,而他解決困境的方法則是放棄自己的處長身份。看似選擇了逃避,實際上卻蘊含著人生的智慧,彰顯出其依然留存的那份善良。不追求權勢,也就能夠避免傷害他人,過自己小富即安的日子。你可以說這個角色不思進取,缺乏膽識,但這番自給自足的心靈富足和精神平靜,又有幾人能夠擁有呢?看《找死》這部短篇,主人公馬小康也面臨著人生的困境:與妻子離婚、單位效益不好自己遭遇下崗、因為找不到工作整天無所事事……這是一個煩躁不安的靈魂,他甚至悲觀厭世,希望有一天能夠“自我了結”。為了排遣心中的郁悶,他去找昔日的哥們兒一訴衷腸,卻發現人家混得比自己還要慘。他又想在死前去一趟娛樂中心找個小姐,來感受一下日常生活不可企及的人生。故事的詭異之處在于,馬小康在和按摩小姐的交談中發現她出賣肉體是為了掙錢供弟弟念書,按摩小姐竟然有如此高尚的人生目標,那么他還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于是,他認真地鼓勵自己“想點好事兒”,凡事也要“往好處活”,不要讓自己活得沒意思,也讓別人活得沒意思。他甚至向警察保證“以后要好好活著”。一次與按摩小姐偶然的相遇,改變了馬小康的人生,甚至將他從死亡線上拽回。這種充滿“偶然”卻不乏真實的要素,就形成了文本荒誕與真實互喻的關系,并成為這篇小說內在的推動力。在狄青筆下,小人物的結局盡管“看上去很美”,但我們依然能讀出隱含其中的些許酸楚與憂傷。作家的可貴之處在于,他能夠讓文本中的人物去承受真實的生活痛擊,卻用人物所有的人生信念維持他們自身在話語現場的存在感與尊嚴感。人物雖“小”,但精神信息卻異常豐富。
平民意識的又一重表現是縈繞在字里行間的幽默感,這種幽默感屬于作品中的人物與情節,也是作家自己的寫作特質。生活中的狄青屬于善于觀察的人,他自己少言寡語,不會輕下斷語、妄作評價,但每每發言,又都在幽默中透露著機鋒,充滿智慧的穿透力。他將自身的話語風格移植到文本中,使“文如其人”實至名歸。《多大點事兒》篇幅很短,整體而觀可以算作一個鄉村“輕喜劇”,講的是鄉領導讓文化站站長馬燕西接待市里來的專家,說是要考察“馬莊秧歌”的申遺工作。這些活計把馬燕西累得團團轉,還搭進去大量的金錢和關系。面對親人和旁人的不理解,他的口頭禪便是一句“多大點事兒”。小說的結尾是圓滿的,也是耐人尋味的:秧歌申遺成功,市里的經費也劃撥到位,而鄉長卻告訴馬燕西,經費要先給干部們建一個籃球場。在充滿喜劇色彩的大團圓背后,依然存有作家對官僚作風的批判,只不過,這種批判的聲音被馬燕西一句“多大點事兒”解構了。這是老百姓的智慧,他們在權力面前被動選擇自保,“多大點事兒”——看似達觀、敞亮、不計較,實際上包含了一種對現實妥協的隱約委屈和無力感。從這個角度反觀馬燕西,他的口頭禪如同現代人的精神勝利法,嬉笑間透露著無奈,隱含著作家對人與權力之間關系更為深入的思索。作家詼諧幽默地處理,不由得使人聯想起劉恒的中篇小說《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其將普通工人張大民一家的窘困生活用貌似充滿“喜劇元素”的情節輕松寫就,但深究其里,張大民用充滿個人特色的輕松“貧嘴”解構著自己無力承受的生活艱辛和沉重感。而馬燕西的“口頭禪”正如張大民的“貧嘴”一樣,是對無法回避的生活困境不得已采取的辦法,在自我解嘲的幽默書寫背后,潛藏著作家的懷疑與批判精神,其本質仍然是一出寓悲于喜的“輕喜劇”。
從閱讀者的角度來看,但凡那些能夠使人不忍釋卷的作品,往往因其涉及對奇人奇事的雕琢刻畫,或是對歷史片段的史料鉤沉,抑或是對市井風貌的細膩抒寫。總之,這種文本需要具備我們常常言及的所謂“可讀性”,也就是有“抓人”的故事和人物形象。短篇小說微言大義、短小精悍的文體特點,要求作家必須會講故事,能夠以精彩的情節吸引讀者。按照趙玫的評價,狄青的小說正是那種“好看”的文本。故事性強,情節推動感明顯,說的都是凡俗小事、家長里短,但經他渲染又顯得生動迷人。《我不要你管》中的寧默一心想要報復拋棄他和母親的生父,他想到的報復方式是侮辱生父和別人所生的女兒,但當他看到身患重病不久于人世的那個“姐姐”時,又從內心深處萌發了對這個女孩的同情,最后寧默得知,自己的復仇其實是一場誤會。貫穿故事情節的,是一個個“偶然”的因素,將這些“偶然”納入日常生活的海洋,卻又能發現這竟然就是我們正在遭際的一個個“必然”。在藝術想象力和現實表現力之間,狄青以他的智慧為文本建立起平衡,他挖掘文本內在的精神美,不斷拓展小說藝術的表現力,這對他而言可以并行不悖。《火鍋愛情》選取的是一個仿佛已經被講俗了的“窮小子愛上富家女”的故事,女孩鄧晴晴的父親早年插隊時與農民齊本貴結成莫逆之交,改革開放后,生活在城市的鄧家家境較好,一直照顧著居住在農村的齊家。齊本貴的兒子齊連山一直喜歡鄧晴晴,卻因城鄉的階層差異和文化差異無法獲得鄧晴晴的芳心。直到鄧晴晴年齡日益逼近“剩女”的時候,她才終于意識到勤勞、樸實、忠誠的齊連山才是她最喜歡的那個人。在講解這個頗為老套的故事時,狄青的筆法顯得生動俏皮,最后一個情節寫到兩人在一起吃火鍋憶舊情,齊連山說:“當初我來城里辦事,頭一回吃這火鍋就愛上了,不用打火,老是這么熱乎,想吃燙嘴的就扒拉扒拉,想吃溫乎的就不管它,這多好,挺像咱過的日子……”“看著冷,吃著熱”的“火鍋愛情”,定格了對平凡之人自身而言最為神圣的瞬間。故事是老套的,而人物的心理活動則紛繁多變。狄青正善于捕捉稍縱即逝的心靈信息,用符合作品人物思想意識的短促、平實的口語,對平民生活作出溫情表達。
綜觀狄青近些年的創作,他已經可以在狹窄而逼仄的中短篇小說空間中游刃有余地擔當馭者,嚴肅地行使小說家“講故事”的職責,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漸次走進小人物的生存空間。今天,評價一個作家是否優秀,就要看他身上是否具備一些專屬其身的精神元素和寫作向度,作者正是能夠利用這些元素,并在其激勵下實現持續性寫作。對狄青而言,其創作主體精神中不變的元素首先來自對生活的認知態度。無論抒寫小人物的精神苦悶,還是還原現代人的日常生存、在現實的基礎上構筑文學想象,狄青的文學世界總是離不開他周遭的凡俗生活。可以說,生活賦予他創作的養料,他也始終虔誠地敬畏生活,汲取蘊含其間的養分。米蘭·昆德拉曾說過:“發現只有小說才能發現的,這是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所以才有布魯因的論斷:小說家就是“能對司空見慣的東西產生重新好奇的人”。能夠寫成小說的人,必定意味著能夠發現世界上各種奇異的精神元素,并具備將這類元素按照自己的心靈邏輯排列、組合,構筑成篇的能力。真正的小說家應該都是生活的發現者。這是狄青的寫作方向,也是他的藝術精神。這種探索值得我們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