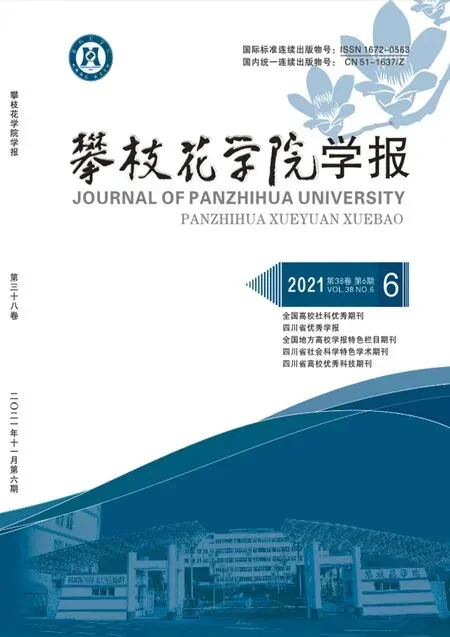滇越濮拉人的族群記憶與文化特征
李 娜
(楚雄師范學院 管理與經濟學院, 云南 楚雄 675000)
濮拉是一個有語言無文字的跨境族群,主要分布在中國和越南。中國境內的濮拉人屬于彝族的一個支系,人口30多萬,在越南,他們被劃分為一個單一民族——濮拉族(越南境內稱之為“夫拉族”),人口1萬多。盡管分隔兩國且歷經時代變遷,但作為同一族群,中越兩國的濮拉人至今還有交往,且還保留一些共同的族群記憶和文化特征。
一、濮拉人的族群歸屬
國內的濮拉人,自稱“濮拉頗”、“濮瓦頗”、“濮頗”、“博卡頗”、“阿扎”、“昨科”,他稱“濮族”、“濮瓦族”、“黑濮拉”、“白濮拉”、“花濮拉”、“筲箕濮”,并有仆拉、卜喇、蒲喇、蒲那、樸剌、樸臘、樸拉、普拉等同音異寫。越南濮拉人則分為黑濮拉、白濮拉、花濮拉、漢濮拉、佬濮拉、舍佛等支系,自稱、他稱也很多。如黑濮拉自稱“母彝巴”;花濮拉自稱“葡酷巴”;漢濮拉自稱“濮拉頗”;佬濮拉自稱“博柯巴”、“阿普”、“舍佛”等。與此同時,越南黃連山、山蘿、萊州等省的舍佛被當地瑤人、苗人稱為“濮拉人”,而另一些民族則稱其為“普”或“佛”。在越南,盡管濮拉和舍佛的自稱和他稱各不相同,但在這些濮拉人和舍佛人的心目中,以及鄰近其他民族的印象中,他們都是同一民族,包括分布各地的不同支系。由于各個支系的名稱都不能代表整體,因而“濮拉”這個使用最廣泛的名稱就成為該族的正式名稱。
濮拉人是較早在滇南地區生息的彝族先民之一。何以稱之為“濮拉”?其稱謂來源有三:一說“濮拉”為祖先分支的人,“濮”為“祖”,“拉”為分支或分叉,說他們是祖先分支出來的一杈枝人,是尼部的后裔。“古代彝族尼、濮、羅三大支分流情況,羅部還沒有從尼部分出之前,濮部已從尼部分出來了,濮表示以男祖魂的葫蘆為崇拜對象,是彝族進入父系社會以后,從尼部分流出來了。”[1]“至今居住在紅河兩岸的濮拉人,大多不知篤慕(彝祖)為何人,也不知‘六祖’分支之事,只知道他們的祖先是很早很早以前,從彝族中分出來的。而在滇西和滇南一帶的彝族,較多的部分也沒有‘彝族六祖’的概念,足見他們多屬于‘彝族六祖’的旁系,甚至有的連旁系也不是,而是從古夷人的其他部族融合或篤慕前就分支的一個獨立支系。”(1)龍倮貴主編:“紅河彝族文化調查” (內部資料),昆明:云南宏光印務有限公司印制,2006年,第30頁。
二說濮拉為濮人、濮族,是濮水(滇南紅河)的濮人,是古代濮人的后裔。如史料《漢書·地理志》記載:“仆水(濮水,指滇南紅河)出繳外,東南至來唯入勞。”[2]又如朱希祖的《云南濮族考》也說:“余謂仆族(濮族)因仆水(濮水,指滇南紅河)而得名,不如謂仆水(濮水)因仆族(濮族)而得名,猶如僰道因僰族得名也。”[3]再如《蒙化志稿》說:“倮倮有二種,一種即古之羅羅摩,為哀牢九族之一,唐南詔細奴邏也,一種為蒲落蠻,即古濮之后……訛濮為蒲,雖不同俗,亦近似。”[4]“羅羅摩”指的當是彝族無疑;至于“蒲落蠻”亦作“濮拉”,即今分布于滇越的濮拉人。
三說濮拉人是彝族中的“樸支系”。如尤中先生在《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中這樣寫到:“元朝以前,滇南和滇東南一帶的‘烏蠻’、‘白蠻’分為許多部。除一部分白族和‘徙莫祗’人之外,有一部分‘白蠻’顯然與‘烏蠻’共同組成大大小小的部落,但長期以來誰也沒有征服誰,而地域相近者則聯系比較密切。元朝以后,這些‘烏蠻’、‘白蠻’混合的各部落的界線被逐步沖破,但歷史上形成的這個區域性集體的文化特征卻保留了下來,這就是‘樸喇’。近代彝族中有一部分自稱‘潑哇’、‘潑拉培’、‘圖拉拔’、‘頗羅’、‘昨柯’,或以為屬于彝族中的‘樸支系’,漢族仍然稱他們為‘樸拉’、‘卜拉’,‘普拉’。”[5]
1954年4月以前,國內的濮拉人還尚未劃歸彝族,1953年1月,滇南個舊市境內成立了首個濮拉自治鄉——“個舊市阿龍古仆拉族自治鄉”,1954年5月,中央民族語言識別調查組到個舊地區調查研究后,經報國務院批準,才將濮拉人劃歸彝族。而在越南,直到1979年3月2日,越南政府作出在全國統一使用《越南各民族成分名稱》的決定后,“濮拉”才作為一個經過正式確定的名稱被劃分為一個單一民族。
二、濮拉人的族群記憶
濮拉是滇南和滇東南地區的土著彝民,明清之際流落江外及越南北部山區。時至今日,中越兩國的濮拉人仍還有往來,且還保留一些共同的族群記憶。
(一)濮拉人在歷史上的分布及遷徙
在分布上,紅河流域是滇越濮拉人的主要活動區域,尤其以紅河中下游一帶較為集中。過去有關濮拉人分布的記載,見清道光《云南通志稿——南蠻志》引《皇清職貢圖》說:“樸喇,一名樸臘,古蒲那九隆之苗裔,南詔蒙氏為尋甸部,至元初內附,今臨安、廣西、廣南、元江四府均有此種。”[5]清時的臨安府轄境為今天建水、金平、石屏、通海、峨山、新平、蒙自、紅河、開遠、文山、河口、屏邊、馬關、西疇、麻栗坡等縣市;廣西府轄境為師宗、彌勒、丘北縣;廣南府轄境為廣南、富寧縣;元江府轄境為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江城縣。如今,國內濮拉人的具體分布情況與上述時期大致相同,而越南的濮拉人也主要分布在紅河沿岸的老街、安沛、河江、萊州、黃連山、山籮等省份。
在遷徙上,滇南、滇東南地區是濮拉人遷徙途中的主要中轉站,這主要表現在遷入、遷出兩個方面。首先,從遷入方面來看,古時濮拉人多從昆明、大理方向進入滇南紅河、滇東南文山兩地。具體的遷徙情況是:開遠濮拉先民自昆明方向流入;屏邊的濮拉老人講,遠古時代,他們的祖先住在大河淌水的地方(疑指今金沙江流域),后遷居昆明,又由昆明以部族、宗族的形式分兩路集體遷徙。一路從昆明出發,經通海、建水、石屏、紅河、元陽、蒙自、彌勒、開遠、個舊、屏邊,屬于曲線遷徙路線。另一路經昆明、呈貢、宜良、羅平、瀘西、彌勒、開遠、蒙自、屏邊,基本上直線遷徙路線;紅河縣虧容地區濮拉人張氏、普氏口傳,他們的祖先于明末清初從寧州(今華寧)出發,經開遠馬者哨、石屏斐尼、小沖、者孔、尼么貝堵等地,再從小河底順河而下,渡紅河定居于紅河南岸的虧容山梁至今;另一部分紅河濮拉人口傳,他們的祖籍在點蒼伯腳(今大理點蒼山),順“濮水”(今紅河)流域巍山、雙柏、新平、元江而下,渡紅河散居于紅河南岸的干熱河谷山梁上,有的繼而順江而下,遷居元陽、個舊、屏邊、金平定居;[2]文山州自稱“阿扎”的黑濮拉,是南詔至大理國時期從北向南遷徙定居于今文山、硯山等地的;而自稱“昨科”的白濮拉有一部分是因天災人禍從大理地區逃難出來,經玉溪、江川、通海等地來到文山、硯山縣居住,據文山縣追栗街彝族鄉大興寨村李、龍兩姓講,其祖先遷來已將近800年,其中在文山壩子居住了500余年,遷往山區近300年。[6]
其次,從遷出方面來看,滇南紅河、滇東南文山兩地是濮拉人跨境遷徙過程中的主要遷出地。越南濮拉人在歷史上是由滇南紅河、文山兩州部分縣市遷徙進入的,具體時間尚不能確定,但可以肯定是在元、明、清時期從云南遷去的。因為元以來實行的改土歸流,云南彝區的很多土官被流官替代,民族壓迫極為殘酷,階級矛盾尖銳。同時,明正德年間在云南的阿寺、阿霧彝民起義和明崇禎年間的普沙事件、大西軍攻打滇南、吳三桂反清、鄂爾泰血洗彝族土司等歷史事件都對彝族地區的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在這些事件前后,很多彝族為躲避戰亂、免遭屠殺而紛紛外逃,這其中包括不少濮拉人,因此,大多數的濮拉人遷出的時間在明清之際是可以肯定的。[7]
另外,在濮拉人跨境的遷徙過程中,佬濮拉有一支從屏邊、河口遷出;另一支從個舊、金平入越南。至今居住在紅河沿岸的老街、安沛、萊州三省的佬濮拉與云南省金平縣馬鞍底鄉的阿普支系仍有聯系,據佬濮拉“博柯巴”的稱法與云南屏邊縣“博卡頗”相同,他們應屬同一個支系。[8]另根據上世紀70年代越南學者的田野調查記錄,漢濮拉先民遷入越南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主要從云南馬關縣和麻栗坡縣遷出,甚至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還有零星小部分遷來孟姜、北河生活。[9]還有學者提出漢濮拉是從彝族的濮拉潑支系分離出來的。至今,越南漢濮拉同中國分布于云南省文山縣、馬關縣的彝族濮拉支系仍然有著多方面的關系。[10]
(二)有關漢文史料對濮拉人的描述
濮拉是一個有語言無文字的滇越跨境族群,沒有自己文字記載的歷史。而已有漢文史料對其記載很少,僅可大致勾勒出濮拉人在歷史上的文化輪廓。
濮拉族名首見于明代,明景泰年間,陳文撰寫的《云南圖經志書》卷三《臨安府風俗》載:“居村落者名為蒲剌,形丑而性悍,短衣跣足,首插雉尾,身佩甲兵,以采獵為生業,獲禽多者稱為同類之最也。”明天啟年間劉文征撰《滇志》卷三十載:“樸喇……婚喪與玀玀同,而語言不通。在寧州者強悍,專務剽掠。”雍正《師宗州志》卷下《土司考·附種人》說:“樸臘倮羅,性桀驁,依山為險,服飾亦似沙人,形黑好斗,畋獵為務。”康熙《阿迷州志風俗志》說:“樸喇,言語不通,……山居火耕,遷徙靡常。衣麻,披羊皮,弩矢隨身,專記仇怨。”康熙《新平縣志》卷二說:“卜喇,性軟,居深菁開山地,栽蕎稗。不見官,不納糧。”康熙《廣西府志》卷十一《諸彝考》說:“樸喇,在水下地方,多依大維摩山居住,食生物生蟲,獷悍為甚。”嘉慶《臨安府志》卷十八“土司志”載:“……樸喇面黑,性野喜斗,語言不通,蓬頭跣足,衣不浣濯,臥用牛皮,覆以羊革氈衫。”道光《云南通志》引《伯麟圖說》說:“普拉羅羅,力勇,居山巔……。白樸喇,性耐勞,耕余劈竹為筐,入市易食,寒燠一絺衣,諸夷中之特貧者。”[5]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明清時期漢文獻中記載的濮拉人“形丑而性悍”、“性桀驁”、“強悍,專務剽掠”、“獷悍為甚”、“力勇”、“專記仇怨”、“形黑好斗”、“性野喜斗”、“不見官,不納糧”,多是“未開化”的粗野山民形象:在生產上,他們“以采獵為生”、“山居火耕,遷徙靡常”,成為“諸夷中之特貧者”;生活上“蓬頭跣足,衣不浣濯”、“衣麻,披羊皮”、“食生物生蟲”;不通漢語,甚至與倮倮(彝族)都言語不通;不善交往、貿易……可見,漢族志書記錄的濮拉族群的歷史是一種被選擇過的社會記憶,這些記憶在描述濮拉人的言語之中多帶有歧義,甚至將其視之為異類;但從另一方面也說明明清時期的濮拉人受漢文化影響較小,與漢文化習俗存在較大差異,仍保持著自己鮮明的文化特征。
三、濮拉人的文化特征
明清以來,在多族群交錯雜居的社會環境下,滇越濮拉人仍保持著與包括彝族其他支系在內的周遭其他族群之間互動的邊界,形成和保留了自己獨具特色的風俗習尚,并使之成為族群身份的重要文化表征。
(一)生存環境
從過去到現在,滇越濮拉人都主要生活在荒漠化、石漠化嚴重的高寒邊遠山區,生存環境惡劣。首先,從國內史料的記載來看:雍正《師宗州志》卷下《土司考·附種人》說:“樸臘倮羅……依山為險……”;嘉慶《阿迷州志》卷六“種人”載:“惟撲拉多住深山密箐中……”;道光《云南通志》引《伯麟圖說》說:“普拉羅羅,居山巔……”;《廣西府志》卷十一《諸彝考》說“樸喇,在水下地方,多依大維摩山居住……”[5]可見,國內濮拉人過去多深居山野。而如今在越南,濮拉人也主要生活在北部山區。越南的北部山區分為兩類:一類是河江省同文、苗旺的高山、石山區;另一類是高平省保樂縣的高原、土山區,而幾乎所有的濮拉人都居住在高山、石山區,生存環境惡劣。
其次,從濮拉語地名、人名中也可看出其生存環境的惡劣。如滇南紅河縣政府所在地迤薩鎮,“迤薩”是濮拉語,意為“干旱缺水”;又如開遠市濮拉人的聚居區碑格鄉,“碑格”意為“石山過去一點的地方”。另據筆者的調查了解,碑格鄉分上半鄉和下半鄉,上半鄉人濮拉語叫“臘拔頗”,意為“生活在最高山上的濮族人”;下半鄉人叫“呆占頗”,意為“居住在云彩之外比較遠的地方的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碑格上、下半鄉人所生活的區域都屬于巖溶地貌,這些地方多被條狀山地、谷地分割,山高坡陡,露頭石頭多,對農業生產限制很大,當地濮拉人現在吃的大米多是用雜糧換取。而同樣在越南,對于所有分散居住在高山上的濮拉人來說,他們的村寨很小,約有十幾戶,且住房離田地很遠,主要是為了防止放養家畜時毀壞莊稼,因為這些莊稼多是在石頭窩里栽種的,十分來之不易。
(二)生計方式
滇越濮拉人多深居山野,長期保持著采集狩獵和刀耕火種的生計方式,生產力較為落后。如明景泰年間《云南圖經志書》卷三《臨安府風俗》及《馬龍他郎甸長官司風俗》記載:“居村落者名為蒲剌……以采獵為生業,獲禽多者稱為同類之最也。”“境內有蒲蠻之別種曰車蘇者,即蒲剌也。居高山之上,墾山為田,藝蕎稗,不資水利。然山地磽薄,一歲一移其居,以就地利,暇則獵獸而食之。”又如康熙《阿迷州志風俗志》說:“樸喇……山居火耕,遷徙靡常。”乾隆《蒙自縣志》載:“仆喇性略訓于母雞,居必深林密菁,刀耕火種,不治水田,幾易其土,以養地力,三年復耕舊垅,五谷兼種……。”再如清道光年間《云南通志稿——南蠻志》引《皇清職貢圖》說:“仆喇……耕山種木棉,取禽鳥為生。”《云南通志稿》引《伯麟圖說》說:“白樸喇,性耐勞,耕余劈竹為筐,入市易食,寒燠一絺衣,諸夷中之特貧者。”[5]
由此可見,過去濮拉人的農業生產是典型的旱作農耕,即“墾山為田,不資水利”“刀耕火種,不治水田”“幾易其土,以養地力,三年復耕舊垅”“然山地磽薄,一歲一移其居,以就地利”,這種“山居火耕”的生產方式使得濮拉人“遷徙靡常”。遷入越南后,濮拉人仍沿襲著這種旱地農耕的生產方式,向旱地撒種或者用尖木棍戮一小穴,點種入內。同國內一樣,他們以種植蕎稗、玉米、薯類等五谷為生。另外,狩獵也是濮拉人一項重要的生計來源。滇南濮拉人酷愛狩獵,過去他們常“弩矢隨身,取禽鳥為生”,并且以“獲禽多者稱為同類之最也”。在越南,濮拉男子也特別擅長用毒箭獵獲猛獸,并且善于制作和使用弩。而在勞作之余,滇越濮拉人常“劈竹為筐,入市易食”,靠手工勞動以彌補經濟收入的不足。至今紅河、文山等地的濮拉人仍擅長竹編,他們的編織品如竹蔑帽、竹蔑桌、竹背籮等,一般都是由外地商販到家里收購或街天交易,在當地集市都享有盛譽。同樣,越南的濮拉人也善于編織藤制品和竹器,他們編制的衣箱、餐具等品種繁多、花色齊全、色彩鮮艷,深受其他民族同胞的喜愛。
(三)生活習俗
惡劣的生存環境,落后的生產方式,使滇越濮拉人至今仍保留著自己獨特的生活習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語言服飾。語言上,滇越濮拉人主要操彝語東南部方言,少部分操南部方言。過去他們能通漢語者很少,甚至與彝族其他支系語言不通,如今族群內部仍以本民族語言為主要交際工具,多數婦女和未入學的兒童都還不懂漢語和其它彝族支系的語言。如開遠碑格鄉的濮拉人,50歲以上的人不會說漢語,40——50歲會說漢話的人占少數,30歲以下的人才會說漢語,也說民族語言。而女性多數不會說漢語,一些年輕婦女是通過打工與外界接觸以后才會講漢語。同樣在越南,萊州、山蘿、黃連山地區的大部分濮拉人,至今依然沿用本民族語言,而小部分濮拉人因與其他民族雜居,已不再單純使用本民族語言。如沙縣的花濮拉和黑濮拉長期與哈尼族雜居,語言已受部分哈尼族語言的影響;北河縣的漢濮拉,受漢文化影響較早,會使用中國南方漢語,但大部分的濮拉人仍記得本族母語。
服飾上,過去濮拉人生活條件艱苦,衣著簡陋。見嘉慶《阿迷州志》卷六“風俗志”載:“惟獛拉多住深山密箐中,……冬夏只著麻布單衣,冷則披羊皮于背……其各種婦女,有跣足者,穿鞋及短襪者。至服色各有所尚,不相易也”。[5]如今濮拉人“衣麻披羊皮”的傳統,作為族群普遍的民俗事項已經消失了,但濮拉婦女服飾“各有所尚,不相易”的情況仍保留至今。如在滇南和滇東南地區,不同自稱和他稱的濮拉婦女服飾各異,但無論老少,她們都喜歡穿著色彩鮮艷的民族服裝,而且自己做衣服。濮拉婦女特別擅長手工刺繡,為自己及家人縫制服裝,并且生有女孩的人家會教自己的女兒做服裝。同樣在越南,濮拉婦女也承擔著種棉織布、為全家縫制衣服的任務,服飾基本上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受其他民族的影響不大。
婚姻家庭。滇越濮拉人多是族內婚,婚戀自由,婚禮簡單,婚后從夫居,實行父系家長制。關于過去濮拉人的婚俗,據康熙《阿迷州志風俗志》載:“樸喇……大概諸彝服食習尚,略有異同,至于婚姻,各自為類,不相混亂。”[5]可見,過去濮拉人很少和其他族群通婚,多行“各自為類,不相混亂”的族內婚,如今滇南濮拉人仍沿襲這樣的婚嫁傳統。如在開遠碑格濮拉人民間,洪水神話廣為流傳,神話中就把“按姓分居”,“同姓不婚”作為人類安居樂業的前提。直到現在,這樣的傳統仍是碑格濮拉人的村規和祖訓。另外濮拉人婚戀自由,婚禮簡單,婚后從夫居,實行父系家長制。同樣在碑格,濮拉人戀愛自由,姑娘成年后約伴單獨居住,晚上,小伙子們約伴上門對歌。相互看上后,就帶回男方家同房。小伙子連續把姑娘帶回家三次,男方的父母或兄嫂就出面說媒。媒人第一次帶一對雞、十來斤酒、一袋包谷面或米,俗稱“喝小酒”。第二次帶上“喝小酒”談好的禮物,和新郎一起到姑娘家,俗稱“喝大酒”,也就是舉行婚禮。婚禮十分簡單,也就是親朋好友在一起吃頓飯,無任何儀式。同樣在越南,濮拉男女青年自由戀愛結合,婚前有許多場所讓他們婚前發生性關系而不被禁止。父母不包辦,沒有早婚的習俗。一對男女相愛,雙方各自稟告父母,舉行一次雙方家屬及親戚出席的酒宴就算結成夫婦。婚禮可以立即舉行,也可以等兩三年后,待籌齊米、肉等物時再舉行。女方嫁妝通常有碗筷、鍋鑊,被、席、刀、鋤,種雞,種豬等,婚禮簡短,最多持續半天到一天。男方給女方的彩禮一般是一套衣服、一個銀質項圈,五十公斤肉、二三壇酒。男子極少入贅,如果岳父母家中確有困難,則女方偕丈夫一起回娘家幫忙。婚后濮拉人從夫居,實行父系家長制,子女隨父姓,財產由兒子繼承,女兒分得些許嫁妝,子女成婚后即自立門戶。
喪葬祭祀。滇越濮拉人過去行火葬,后改行土葬,喪葬習俗略有不同,其他祭祀活動均大同小異。濮拉人行火葬的習俗見乾隆《開化府志》卷九說:“白樸喇性最樸,……喪無孝服,亦不用棺,以木架扛送火化。”[5]如今,濮拉人去世都實行土葬,只是葬俗各異。如滇東南文山的濮拉人對不同的年齡段死者,埋葬方法及程序有所不同:對剛出生未滿月的嬰兒死亡,稱“臍風”(破傷風),認為是“鬼使神差”,處理方法就很草率;青壯年人死亡,給新穿戴裝棺,簡單祭獻,不擇葬日不看地,草草安葬;老年人死亡則大操大辦,需履行報喪、開紙、安葬、復山幾個過程,擇日安埋。安埋頭天開紙,殺豬宰羊祭奠,一般親朋送紙錢及現金奠儀。安葬當日,要請祭司為死者吟誦《指路經》,指導死者靈魂回到祖先發祥地,指路終點多是昆明和大理兩個方向。安葬翌日復山,孝子都上墳獻飯后回家供靈牌。靈牌設在堂屋正中的供桌上,過年和清明節是濮拉人祭祖的兩個重要時節。
在越南,濮拉老人死后一般停靈二至三天才下葬。斷氣當天,死者家要宰殺動物上供,動物宰殺后,把一部份肉腌酸,留著做道場時置于墳頭祭奠用。下葬時同國內一樣,死者家屬也要請祭司為其指路,而指路終點則是紅河、文山兩地,濮拉亡者接受指引的線路也真實地描繪了濮拉先民的遷徙路線。安葬十三天后做道場,修墳。儀式從頭天下午開始直至次日清晨結束,來祭奠的親朋比出殯時還多,他們認為這是送亡靈回冥府的日子。下葬后頭三年過年時,家人來掃墓、祭祀,此后就不再照管墓地,改在家中祭祖。越南濮拉人的祖先神臺置于堂屋中,神臺后面置一塊竹壁隔開,逢除夕、年初一、二月龍日祭供祖先。他們認為成人亡故是由于熱鬼前來索命,所以亡靈很快便去墳地;而幼兒夭亡則是由于冷鬼前來索命,亡靈不易回故土,常在活人身邊游蕩,使活人常鬧病。所以每隔三年的二月間馬日,家家戶戶都要舉行一次驅鬼的祭祀儀式,以求全家健康無恙,家禽免遭瘟疫。
其他祭祀活動,越南濮拉人以祭山林為主,他們在定居時就選村子上方的一片原始森林為神林。全村公祭時間是農歷的二月,屆時全村男子舉行公祭活動,嚴禁砍伐神林里的樹木,對森林的保護他們有一套嚴格的規定,違者將受到高額的罰款。這種祭山林的活動,在國內的濮拉人中也較為為普遍,他們稱之為“祭龍”。即在每個濮拉村寨旁,指定一片山林稱為“龍山”。在龍山上,指定一棵高大筆直繁茂的硬木樹為“龍樹”。每年農歷二月或四月的鼠日或馬日就在“龍樹”前舉行祭龍儀式。參與祭龍的也全都是男性,女性不得參與。對龍山的管理,村規民約都有嚴格的規定,任何人無論出于何種原因,不能動龍山的一草一木,否則,將受到嚴厲的處罰。
節慶飲食。滇越濮拉人節日較多,尤以過大年節、火把節較為隆重。關于這兩個節日的記載,見雍正《阿迷州志》卷十“風俗”:“(年末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灶,彝人于是曰拜年,相互慶會。……其六月二十四夜,村寨田宅悉燃火炬,名曰火把節。膾生肉食之,以此為獻歲。”[5]如今,滇南紅河流域的濮拉人仍逢臘月24至26日過年。過年時殺豬、踩粑粑、釀高粱酒、祭年神、祖先,送灶神,請客吃飯,很是歡樂熱鬧。火把節則更為隆重,過去“膾生肉食之”的風俗(稱之為“剁生”(2)關于“剁生”的記載,見乾隆《蒙自縣志》:“惟六月二十四日,土人以為節,祀祖有剁生之俗。作法以牛、豕、雞、魚之腥,細切為齏,搗椒蒜和之以變其腥,然后碎切瓜菜雜而啖之,名曰生。亦古人鮮食之遺也。”)一直延續至今。在物質生活不太豐富的古代社會,剁生堪稱佳肴,隨著科學衛生知識的普及提高,如今剁生已從人們日常生活中淡出,但逢年過節期間,由剁生派生出的“辣白旺”(涼拌生/熟雞血)仍是滇南濮拉人族群記憶中不可磨滅的一道美味佳肴。相較之下,越南濮拉人的節日飲食則相對簡單,節日期間,他們主要用雞和豬肉作祭品祭拜祖先。此外,越南濮拉人的主食玉米,糯米很少,由此,糯食便成為他們節慶或祭供時一道必不可少的珍稀佳肴。
四、結語
濮拉作為彝族眾多支系中人口較多、分布較廣的滇越跨境族群,至明清以來,雖分隔兩國且歷經時代變遷,但作為同一族群,中越兩國的濮拉人至今還有交往,且還保留一些共同的族群記憶和文化特征。與此同時,滇越濮拉人因長期生活在相對封閉的地理文化單元之中,和周邊其他民族(包括彝族其他支系)族群界限明顯,始終保持著自己的鮮明的文化特征和族群認同意識。共同的歷史記憶與遭遇是族群認同的根本要素,越南的多數濮拉人都有一個舊時來自滇南及滇東南的族群記憶,這是他們與云南濮拉人的一種紐帶聯系,也是他們維系族群認同的一種天賦的聯結。此外,語言服飾、婚喪祭祀、節慶飲食等都是濮拉人區分于其他族群的文化特征,這些特征都被認為是濮拉人的“本土模式”。這種模式提供給濮拉人一種自我形象,同時也成為滇越濮拉人建構族群認同可資利用的文化內容:會不會講濮拉話,穿不穿濮拉服飾,是濮拉人區分本族群與其他族群的重要依據;以族內婚為基礎構建的婚姻家庭對于締結牢固的族群成員之間的聯系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喪葬指路指引死者靈魂回到祖先發祥地與之團聚,強化了祖先認同和族群意識;濮拉人通過定期的祭祀祖先、神明信仰、節慶習俗等活動,促進了共同價值觀與認同的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