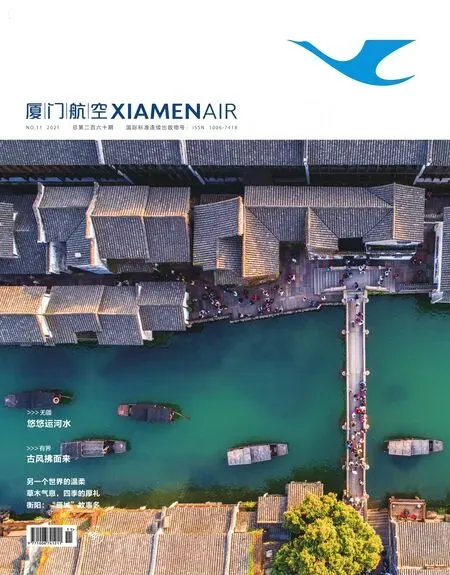一輪明月耀天心
撰文_曹放
夜空,幽藍的夜空,一輪明月,輕云如絮,那如絮的輕云溫潤而柔軟,一層層、一朵朵、一縷縷,鋪展得無涯無際。夜空是那樣的遼闊、浩茫而又深邃……云頂山,橫臥鷺島東南,巖壑幽深,草木蒼翠,山巖極頂“手可摘星辰”,憑欄望遠,九龍江浩蕩入海,鼓浪嶼、南太武、大擔二擔、大小金門,雄洲霧列,廈金海域的濤聲隨著潮水的起落,彌散在一望無際的臺灣海峽……這是2021年的夏秋時節,許多個夜里,我就是這樣沉浸著時光。
徘徊在山道上,仿佛孤獨成了自己的命運,由此,我想到了尼采。初次了解尼采,是我的大學時代,那時,20世紀80年代初期,存在主義以其巨大的人生叩問,撞擊著我們的心靈。“上帝”死了,價值重估,世界是荒謬的,現實的異化,人格的撕裂,存在的尷尬……尼采及其存在主義,構成了對我們巨大的精神誘惑。然而,尼采并不是垮掉,他相信“超人”的力量,他說:“只有經歷過地獄磨難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然而,更深一次的然而,尼采的內心又是那樣的矛盾和痛苦。他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有一句這樣的話:“我們在永遠的虛無中漂流,不是嗎?”山道彎彎,清風陣陣,由尼采,我思考并感嘆著古往今來,又想到了他的精神傳人卡夫卡的一條箴言:“目標是有的,道路卻沒有:我們說有路,不過是躊躇而已。”抬頭望天,倏忽間,一顆流星劃過……
佇立云頂天臺,微風輕拂,那是一種沁入骨髓的舒爽,更是一種激蕩頭腦的清醒。魯迅,于今誕生一百四十周年了,而他的代表作《阿Q 正傳》也于今問世了一百周年。魯迅,這個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小個子文人,憑借一支筆,卻將自己拉升到了“民族魂”的高度。而且,在20世紀亞洲文化版圖上,他和印度泰戈爾、日本川端康成占據了最大的疆域,并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魯迅陳述過自己創作《阿Q 正傳》的主旨,說是要“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他“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里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魯迅,矢志“我以我血薦軒轅”,對于奴性,對于逆來順受,對于狼面前是羊、羊面前是狼,對于精神勝利法,對于諸如此類的這些國民性,他堅決徹底地批判;對于阿Q、對于祥林嫂、對于爭搶人血饅頭的癆病鬼們,他是那樣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如今,《阿Q 正傳》已經問世一百周年了,想想阿Q 們所代表的那些國民性,至今時或可見,我們還是繼續“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嗎?哼,哈哈,也有人放出如此一說:順其不醒,安其不為,讓他們自生自滅吧。“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沉吟著魯迅的詩句,云朵掩映了月亮的時候,我的目光眺望著廈門大學與南普陀寺方向,仿佛看見了1926年10月21日,魯迅和太虛和尚緩緩地并肩走過叢林……
晚風吹來,極目處,海天無盡,最后融匯在一片深不可測的黑洞里。一陣莫名的惆悵襲上心頭:當科學成為新的“上帝”,是否會直接動搖人類普遍價值的根基?工業革命以來,尤其是二戰以來,人類登上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巔峰,普遍建構起來的兩大價值觀最符合人類的天性:一是,人類擁有自由意志,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二是,沒有人比他本人更了解自己,沒有人能替自己做決定。然而,技術和算法的崛起正在動搖著這兩大基本前提。人類給計算機下達指令,計算機再根據算法給出人類想要的結果,這整個過程中人類的思想和觀念幾乎沒有任何參與的余地。科學技術可以控制人,甚至直接消解人的自由意志。這樣,人類擁有自由意志,這個人類普遍價值的第一個根基就被新的技術撼動了。可怕呀,技術對人們自由的剝奪竟是這樣的悄無聲息!自由選擇,而非強制,是一項不證自明的人的基本權利,但是,如果技術和算法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呢?算法最后成了我們的君主,我們主動交出了決定權,什么都只能聽從算法的控制和擺布。這樣,我們人類普遍價值的又一個根基也被無情地抽離了出去。科學是如此的無所不能,在大數據面前我們只能俯首稱臣。這是喜劇呢,還是悲劇?有人說了這樣一個段子:“你得抑郁癥了,不是因為你的精神痛苦,而是因為植入你頭腦中的芯片沒電了。”科學對人腦的革命竟是如此這般,細思,你能不驚恐嗎?月下徘徊,我想起了哈耶克《科學的反革命》中的一句話:“當人們沿著一條給他們帶來巨大勝利的道路繼續走下去時,他們可能陷入最深的謬誤。”一陣晚風吹來,月光下的樹影亂了,亂得斑斑駁駁……
人類正在與新冠病毒艱難地搏斗,沒想到,辛丑夏秋之際,我們廈門也被推上了火線。硝煙終于散去,散去的還有很多很多……在這段難忘的日子里,我留下了一些怎樣的精神印痕呢?很欣慰,我留下了一首小詩和一篇短文。
一首小詩:《仰望星空》。
我喜歡仰望星空。
即使被流放在陰森的墳場上,
荒野里鬼哭狼嚎;
我喜歡仰望星空。
即使被困頓在懸崖絕壁上,
退無可退、進無可進;
我喜歡仰望星空。
即使流浪在刀叢中,
生命懸于一線;
我喜歡仰望星空。
即使陷身在火海中,
死亡已是唯一的命定。
是的,即使是在這樣一些時候,
我還是喜歡仰望星空!
因為星空中有一顆北斗,
它會指引我靈魂飛升的方向;
因為星空中有一條銀河,
它會渡扼我遭受的一切苦難;
因為星空中有一座摩羯,
它會加持我陰陽輪回的力量;
哦,還因為,星空中有一位女神,她總是在我虛弱灰暗的時候,
給我磅礴的力量和光芒四射的希望……
我仰望星空,
身心披滿了晶瑩的月光;
我仰望星空,
世界突然變成了多維多彩多情的模樣;
我仰望星空,
心頭蕩漾起了一種超越紅塵的歡欣;
我仰望星空,
生命就像流星雨一樣,奔流、繽紛、綻放……
“曹主任:謝謝您!喜獲您新創詩作的分享,來回拜讀了數次,環顧四周的氛圍是如此的貼切!您,隨手捻筆,總是帶來驚艷!我也隨著您的筆觸抬頭仰看窗外的天空,試著在一片黑暗的夜空里找到您說的星海……可惜,隔海的山上在大雨之后顯得格外的寧靜,空氣中飄散著些許的惆悵,好生羨慕您的流星雨……”感謝臺灣師大音樂學院林淑真教授!捧讀她的點評,我當即回復:“尊敬的淑真老師:您的涵養、才華與氣質令我深深敬佩,您的境界有時會讓我幻覺到有如流星雨一般的景象。這首小詩,從某種意義上說,表達的也是對您的境界的一種仰望和敬意。”
一篇短文:《唯見一輪空月》。
歲在辛丑,八月既望,余閑登云頂,徘徊山道,時有清風徐來。風過松竹間,颯颯如低語輕吟。
一壺茶,一卷書,沉醉天臺小閣。尋大江東去,問佛祖西來,想群雁南飛,嘆老馬北顧。滄滄乎,溟溟乎,浩浩乎,蕩蕩乎!一部青史,竟都是黎民痛、士子哀、英雄血、美人淚,更幾多灰飛煙滅。
起坐信步,遙感關山飛渡;低回玄思,不知天涯何處。舉頭間,萬古長夜,唯見一輪空月。
“時人常以駢文徒具形式之美,卻不知形式與內容間的有機關系,對仗是漢字的特色,有意、形、聲結為一體的美感,故傳世之句,乃多駢文之作,關鍵只在寫者功力。曹兄此作,詞工意深,卻自然之至,讀之,或慨然,或曠遠,既得古今同月之嘆,亦寄關山飛渡之思。”這是臺北書院山長林谷芳先生的點評。“美文,古風盎然。千古同一嘆!”這是著名學者資中筠先生的點評。”唯見空月!佛門之所以長盛不衰,因為它是空門。好文章,有東坡《赤壁賦》之風!”這是著名作家唐浩明先生的點評。感謝你們,我尊敬的老師!你們的鼓勵讓我不敢懈怠。細細品讀老師們的點評,我的腦海里更深刻地烙印下了弘一法師的詩句:一輪明月耀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