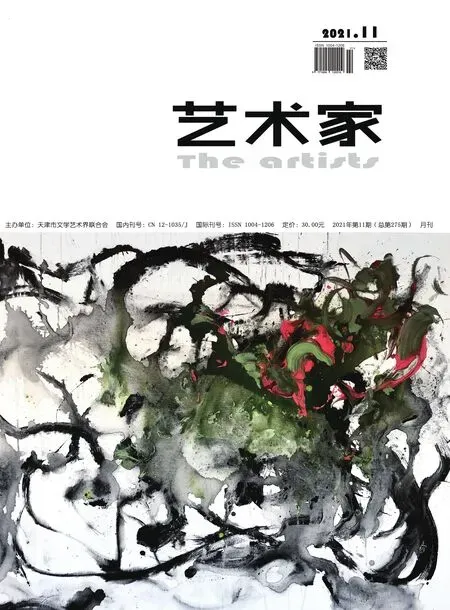德沃夏克《a小調(diào)小提琴協(xié)奏曲》民族風(fēng)格的解讀
□文 蕊 天津音樂(lè)學(xué)院
一、德沃夏克和《a小調(diào)小提琴協(xié)奏曲》
安東·利奧波德·德沃夏克(1841—1904),19 世紀(jì)捷克著名音樂(lè)家,捷克民族樂(lè)派的代表人物。德沃夏克自幼學(xué)習(xí)音樂(lè),最先在教堂的唱詩(shī)班學(xué)習(xí)鋼琴,后進(jìn)入布拉格管風(fēng)琴學(xué)校上課,畢業(yè)后在樂(lè)團(tuán)擔(dān)任管風(fēng)琴手,并在工作之余進(jìn)行創(chuàng)作。1870 年后,德沃夏克先后推出了多部歌劇和管弦樂(lè)作品,在歐洲聲名鵲起,并收到了多所音樂(lè)學(xué)院的邀請(qǐng)。1892 年,德沃夏克遠(yuǎn)赴美國(guó),出任紐約國(guó)家音樂(lè)學(xué)院院長(zhǎng)。在此期間,他不僅創(chuàng)作出了《自新大陸——第九交響曲》等佳作,還培養(yǎng)了一大批優(yōu)秀人才。晚年的德沃夏克回到捷克,并于1904年悄然離世。
《a 小調(diào)小提琴協(xié)奏曲》是德沃夏克早期的作品,也是其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初步確立的一首佳作。1897 年,德沃夏克的好友,小提琴演奏家約·阿希姆邀請(qǐng)德沃夏克創(chuàng)作一首小提琴協(xié)奏曲,德沃夏克經(jīng)過(guò)三年創(chuàng)作和三年修改后,最終將這首作品搬上了舞臺(tái)。作品中,德沃夏克通過(guò)對(duì)大量捷克民族民間音樂(lè)素材的借鑒和運(yùn)用,不僅展示出了捷克壯美的自然風(fēng)光,還表現(xiàn)出捷克人民勤勞質(zhì)樸的民族精神及深沉濃郁的愛(ài)國(guó)情懷[1]。一個(gè)世紀(jì)后,其作品仍廣泛奏響于世界各地的舞臺(tái),展現(xiàn)出長(zhǎng)久的藝術(shù)生命力。
二、《a小調(diào)小提琴協(xié)奏曲》的民族風(fēng)格
(一)旋律的民族風(fēng)格
旋律是觀眾感知音樂(lè)作品風(fēng)格的第一要素。在這部作品中,旋律的民族化風(fēng)格主要表現(xiàn)在走向和色彩兩個(gè)方面。首先是旋律的走向,從整體來(lái)看,這部作品的旋律呈波浪式的發(fā)展趨向,即旋律先從高音區(qū)開(kāi)始,然后慢慢地回落,最終落在主和弦上。這種走向也與捷克的民族音樂(lè)走向一致,通過(guò)起伏有致的旋律線讓情感表現(xiàn)得更加豐富。其次是旋律的色彩。一方面,斯拉夫民族有著悠久而豐富的民歌文化,可以給創(chuàng)作提供源源不斷的素材;另一方面,小提琴的音色醇厚,長(zhǎng)于抒情,極具音樂(lè)感染力。所以在這部作品中,德沃夏克主動(dòng)在旋律的歌唱性方面做文章,讓小提琴化身為一個(gè)女高音,唱出溫潤(rùn)而質(zhì)樸的旋律。比如,在第一樂(lè)章主部主題的樂(lè)句中,德沃夏克便采用了以自然音為主的旋律線,這正是捷克民歌中最常見(jiàn)的旋律構(gòu)成形式,讓人不自覺(jué)地跟著哼唱起來(lái)。在第三樂(lè)章中,德沃夏克又采用了跳躍的自然音,讓小提琴唱出了清脆明亮的歌聲,給人以輕松歡快之感。
(二)和聲的民族風(fēng)格
自浪漫主義時(shí)期開(kāi)始,和聲的作用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到了19 世紀(jì)后半葉,在民族樂(lè)派音樂(lè)家的筆下,和聲更是成為彰顯作品風(fēng)格的利器。德沃夏克的《a 小調(diào)小提琴協(xié)奏曲》也不例外。其一,德沃夏克對(duì)傳統(tǒng)的和弦形式進(jìn)行了充分的運(yùn)用。對(duì)于民族民間音樂(lè)而言,創(chuàng)作者和表演者的音樂(lè)專業(yè)知識(shí)和技能相對(duì)有限,所以多采用一些傳統(tǒng)且簡(jiǎn)單的和弦形式,運(yùn)用最多的便是三和弦。作為最基礎(chǔ)的和弦構(gòu)成形式,三和弦具有形式簡(jiǎn)練、音色純凈的特點(diǎn)。在這部作品中,第一樂(lè)章的第一個(gè)和弦便是主三和弦,起到了全曲骨架的重要作用。在第四和第五小節(jié)中,為了配合旋律的下行走向,則分別使用了減三和弦,讓旋律與和聲的配合更加默契。而且在旋律的結(jié)尾處,再次回到了主三和弦上,整個(gè)和弦配置分明有序。其二,德沃夏克還根據(jù)樂(lè)曲的實(shí)際表現(xiàn)需要進(jìn)行了創(chuàng)新。比如,在第二樂(lè)章的中部,為了配合調(diào)式從A 大調(diào)朝著F 大調(diào)的變化,德沃夏克先后使用了多個(gè)降七級(jí)和降二級(jí)和弦,增添了一種朦朧的色彩,一直到主和弦出現(xiàn)后,這種朦朧色彩才結(jié)束。由此可見(jiàn),德沃夏克的創(chuàng)作觀是開(kāi)放和多元的,他不但善于吸收,而且善于創(chuàng)造,獲得了全新的音樂(lè)表現(xiàn)效果。
(三)節(jié)奏的民族風(fēng)格
節(jié)奏對(duì)音樂(lè)風(fēng)格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德沃夏克在創(chuàng)作中,對(duì)節(jié)奏也是十分看重的。以這部作品來(lái)說(shuō),其一,德沃夏克實(shí)現(xiàn)了音樂(lè)節(jié)奏和語(yǔ)言節(jié)奏的融合。捷克語(yǔ)從屬于斯拉夫語(yǔ)言體系,但是在歷史中,由于國(guó)家受到德國(guó)的多次侵?jǐn)_,德語(yǔ)在當(dāng)?shù)刂饾u普及。19 世紀(jì)末,捷克民眾恢復(fù)本民族語(yǔ)言的呼聲日益高漲,德沃夏克作為一個(gè)愛(ài)國(guó)音樂(lè)家,自然不會(huì)對(duì)這種訴求視而不見(jiàn)。他在這部作品中,融入了斯拉夫語(yǔ)言前重后輕的語(yǔ)音特點(diǎn),因此作品中有著大量“強(qiáng)弱弱”節(jié)奏的運(yùn)用,甚至還加入了重音記號(hào)進(jìn)行強(qiáng)調(diào)。在此基礎(chǔ)上,德沃夏克還多次運(yùn)用附點(diǎn)節(jié)奏,這同樣是與斯拉夫民族語(yǔ)音語(yǔ)調(diào)相一致的,體現(xiàn)出了其對(duì)本民族語(yǔ)言的重視。其二,德沃夏克對(duì)民族民間舞曲的節(jié)奏進(jìn)行了巧妙運(yùn)用。斯拉夫民族是一個(gè)能歌善舞的民族,在一些節(jié)慶活動(dòng)都會(huì)跳起熱情而歡快的舞蹈。其中當(dāng)數(shù)富里安特舞蹈最為普及。其節(jié)奏特點(diǎn)是三拍子中包含著部分二拍子,營(yíng)造出一種切分節(jié)奏的感覺(jué),為舞曲注入了向前發(fā)展的動(dòng)力。為了模仿這種節(jié)奏,德沃夏克先為三拍子節(jié)奏標(biāo)注了連音記號(hào),又在二拍子的弱音上標(biāo)注重音記號(hào),巧妙地實(shí)現(xiàn)了與富里安特舞曲節(jié)奏的一致性,充分展示出了精湛的創(chuàng)作功力。
三、德沃夏克民族化追求的啟示
19 世紀(jì)末20 世紀(jì)初,小提琴?gòu)奈鞣絺魅胫袊?guó),開(kāi)始了在中國(guó)百年的發(fā)展歷程。為了使其在中國(guó)落地生根,開(kāi)花結(jié)果,中國(guó)音樂(lè)工作者隨即開(kāi)展了小提琴民族化改造工作,并先后推出了一大批具有鮮明民族風(fēng)格的小提琴佳作,這也讓很多演奏者在國(guó)際舞臺(tái)上享有盛譽(yù)。通過(guò)對(duì)德沃夏克《a 小調(diào)小提琴協(xié)奏曲》的創(chuàng)作分析,筆者獲得了深刻的啟示,現(xiàn)從以下幾個(gè)方面來(lái)闡述。
(一)堅(jiān)定民族化的創(chuàng)作
德沃夏克深處歐洲,卻仍然提出了民族化創(chuàng)作的主張,并予以全面踐行。對(duì)于中國(guó)來(lái)說(shuō),小提琴本是一門外來(lái)藝術(shù),民族化發(fā)展更重要、更迫切。一百多年來(lái),歷代音樂(lè)家創(chuàng)作的《搖籃曲》《烏蘭巴托的一天》《梁祝》等,不僅實(shí)現(xiàn)了這門藝術(shù)在中國(guó)的普及,也為世界小提琴藝術(shù)的發(fā)展做出了突出貢獻(xiàn)。在新時(shí)期背景下,世界文化多元化發(fā)展環(huán)境已然形成,文化競(jìng)爭(zhēng)更加激烈,所以仍然要將民族化作為根本性的創(chuàng)作方向。第一,在創(chuàng)作素材方面,以往的創(chuàng)作多取材于民族音樂(lè)并達(dá)到了良好的創(chuàng)作效果,這是值得繼承和發(fā)揚(yáng)的。與此同時(shí),隨著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工作的深入,更多優(yōu)秀的民族音樂(lè)素材被挖掘,這正是當(dāng)代創(chuàng)作者大有可為的好時(shí)機(jī)。第二,在創(chuàng)作風(fēng)格方面,在文化多元化發(fā)展的今天,創(chuàng)作者應(yīng)樹(shù)立起文化自信,全面展示中華民族特有的審美追求,如天人合一、自強(qiáng)不息、勤勞勇敢等。這不僅是創(chuàng)作本身的需要,更是創(chuàng)作者的責(zé)任和義務(wù)。
(二)探索民族化的演奏
演奏是小提琴藝術(shù)最基本的展示和傳播方式,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在西方漫長(zhǎng)的歷史發(fā)展歷程中,小提琴藝術(shù)已經(jīng)形成了一套科學(xué)和完美的演奏技法體系,需要進(jìn)行全面學(xué)習(xí)和運(yùn)用。此外,從民族化的角度來(lái)說(shuō),有了民族化的作品,就必須要有民族化的演奏方式與之相契合,如此才能使民族風(fēng)格得到全面的展示。對(duì)此需要從宏觀和局部?jī)蓚€(gè)角度入手。宏觀方面是指探索出一套全面的適合中國(guó)小提琴作品演奏的技法體系。雖然每部作品的形式和內(nèi)容并不相同,但是作品都有民族化追求,所以還是有共性可循的,這體現(xiàn)在運(yùn)弓、發(fā)音、力度控制等多個(gè)方面。在運(yùn)用這些技術(shù)時(shí),演奏者的身體機(jī)能應(yīng)如何調(diào)整,演奏動(dòng)作應(yīng)如何設(shè)計(jì)和運(yùn)用等,都應(yīng)得到梳理和總結(jié)。對(duì)此,大提琴演奏已經(jīng)走在了前列,結(jié)合了“易經(jīng)”思想、中西經(jīng)絡(luò)學(xué)說(shuō)的中國(guó)大提琴演奏技法體系,已經(jīng)得到了眾多演奏者的充分認(rèn)可。因此,小提琴演奏也需要學(xué)習(xí)和借鑒。微觀方面則是指演奏者應(yīng)該對(duì)作品進(jìn)行全面的分析,進(jìn)行充分的演奏準(zhǔn)備[2]。例如,這首作品是取材于蒙古族的民歌,那么演奏者就需要對(duì)蒙古族的長(zhǎng)調(diào)、呼麥等進(jìn)行學(xué)習(xí),如此才能讓作品的民族化風(fēng)格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示。
(三)推動(dòng)民族化的教育
受歷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中國(guó)的小提琴教學(xué)歷來(lái)都是以西方作品為主。西方小提琴作品固然經(jīng)典,但是從民族化的角度來(lái)說(shuō),中國(guó)小提琴作品的冷遇,顯然已經(jīng)成為民族化發(fā)展的阻礙。這就需要我們從點(diǎn)滴做起,讓廣大師生真正認(rèn)識(shí)到中國(guó)小提琴作品的價(jià)值及演奏中國(guó)小提琴作品的意義。很多學(xué)生受到年齡、閱歷的限制,一度認(rèn)為演奏中國(guó)作品是一種“土”的表現(xiàn),唯有西方作品才正宗。而實(shí)際上,中國(guó)作品的價(jià)值和魅力是絲毫不遜于西方作品的,比如《梁祝》等作品在西方同樣得到廣泛認(rèn)可。特別是在學(xué)生身心和智力、閱歷和經(jīng)驗(yàn)相對(duì)有限的情況下,教師應(yīng)肩負(fù)起這份重任,從重視中國(guó)作品做起,率先垂范,將民族化理念貫穿于學(xué)生學(xué)習(xí)生涯的始終,繼而為民族化發(fā)展以及中國(guó)小提琴學(xué)派的構(gòu)建打下最為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結(jié) 語(yǔ)
19 世紀(jì)中葉,以斯美塔那、德沃夏克、格里格、強(qiáng)力集團(tuán)等為代表的民族樂(lè)派,成為西方音樂(lè)發(fā)展的中堅(jiān)力量。他們致力于民族音樂(lè)文化的復(fù)興,為本民族的音樂(lè)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更對(duì)世界音樂(lè)的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dòng)作用。對(duì)于中國(guó)來(lái)說(shuō),小提琴是一門外來(lái)的藝術(shù),在20 世紀(jì)初傳入中國(guó)后,被中國(guó)的音樂(lè)工作者進(jìn)行了民族化改造,并獲得極大成功。這不僅讓小提琴在中國(guó)落地生根,也為世界小提琴藝術(shù)的發(fā)展做出了突出貢獻(xiàn)。在新時(shí)期背景下,世界文化多元化發(fā)展環(huán)境已然形成,中國(guó)小提琴創(chuàng)演,仍需要將民族化作為根本發(fā)展方向,為其在中國(guó)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打下最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