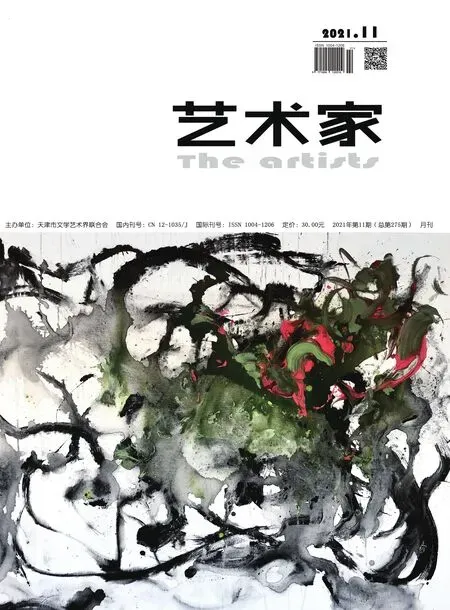蒙古馬作為精神圖騰對造型藝術的影響
□姜鵬乾 內蒙古大學創業學院藝術學院
蒙古馬不僅是蒙古民族人民從古至今的伙伴、摯友以及財產,還是一種精神圖騰。這是因為蒙古馬具有堅強、勇敢、剛毅和隱忍的特征。
蒙古馬主要分布于蒙古草原和新疆的一些地區,蒙古馬體型矮小,其貌不揚,既沒有英國純種馬的高貴氣質,也沒有俄羅斯馬的身材高大,但蒙古馬是世界上耐力最強的馬種,可以在相對惡劣的天氣情況下生存。蒙古草原的冬季氣溫可以達到零下40℃,在這樣的極端天氣下,很多動物無法生存,但蒙古馬卻以一種堅韌的品格,加上自身厚厚的皮毛,扛過寒冬。它可以靈敏地找到冰雪覆蓋下的草層,得以保存體力。蒙古馬的耐力和忍受力很強,它能不吃不喝跑上百里。蒙古馬也是很重視親情的馬,它能準確認出父馬、母馬、以及兄妹馬,并保持很好的家族關系。所以,蒙古族人稱馬為義畜,除非萬不得已,很少吃馬肉,因而馬死后大多會得到很好的安葬。蒙古馬是很富有英雄氣概的,例如,在《狼圖騰》一書中,姜戎寫道:“一匹頭馬為了自己的族群敢于與狼搏斗。”蒙古馬一直以來被視為一種精神圖騰而存在著,被一代又一代的造型藝術大師描繪創作著。從最早期陰山發現的巖畫,到以蒙古馬為創作點的雕塑作品、壁畫作品,再到如今的油畫、國畫、版畫,無不訴說著創作者對蒙古馬的喜愛與贊美。
北方草原文化是最古老的生態文化之一。中國北方遼闊壯美的蒙古高原上孕育了自由豪放、矯健強悍、熱情好客、能歌善舞、勤勞寬厚的民風民俗,創造了綿延千年的游牧文化和光輝燦爛的草原文化。而蒙古馬作為蒙古族人的文化與生活載體,被賦予極高的評價和贊美。
蒙古馬與造型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人們對蒙古馬的造型藝術表達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從最古老的陰山巖畫中我們可以發現,人們對蒙古馬的精神崇拜由來已久。在人類社會早期,人們就開始用生活工具、石器來描摹馬的動態,為后人留下大量珍貴的文化遺產。內蒙古藝術學院的阿斯巴根教授常年研究蒙古馬的造型藝術,在他看來,史前考古世界的洞窟巖畫距今已有5 萬年的歷史,其中關于馬的造型繪畫占有很大比例,而以東亞草原巖畫作為主題的社會性造型思考也占很大比例。古人對馬的極大的情感投入與審美造型藝術表達延續至今,而當代的造型藝術家仍在繼續譜寫著蒙古馬這一永恒的旋律。蒙古馬精神已深植于每位將蒙古馬作為情感寄托的造型藝術家內心,因此他們能夠創作出展現社會集體精神的優秀作品。在阿斯巴根老師的油畫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用極其精簡的造型表達蒙古馬,對色彩的應用也是大面積的純色,由此表現對馬直白的喜愛。不加修飾的直馬腿,讓人一眼就可以認出這是阿斯巴根老師筆下的馬。他在構圖上的新穎表達方式展現出其對草原與蒙古馬的強烈熱愛。
在中國北方寬廣美麗的內蒙古,無數造型藝術家用畫筆、用刻刀、用極為豐富的現代創作材料,來表達蒙古馬的造型藝術,表現出他們對草原上蒙古馬的熱愛。
內蒙古師范大學雕塑系主任陳栓柱老師對蒙古馬的雕塑造型表達也讓人很著迷。他的作品《疾馳》通過結構、線條與整體輪廓讓馬呈現出飛奔的狀態,活靈活現。這幅作品只雕了人物與馬的前半段,即馬蹄、人物離開地面的瞬間,全身肌肉緊繃,人物幾乎與馬平行趴在馬背上,手死死拽住韁繩。騎手與馬的結合讓觀者感受到那種馳騁草原的狀態,即風馳電掣般地飛奔,偶爾還會發出幾聲尖利的嘶吼,讓人精神一振。這就是草原人民的質樸情懷,通過造型藝術實現了完美重塑。
我們沉浸在對廣袤草原的幻想中時,就會想到那一匹屬于自己的蒙古馬,帶著我們遠走他方,尋覓那未知的旅程。而藝術的表達就是帶著那一股濃烈的情懷,讓人們感知蒙古馬精神。這種吃苦耐勞、不畏艱險和一往無前的偉大精神一直鼓舞著草原人民。
在藝術創作的路上,藝術家們依然秉持這樣的精神服務著人民。當今,以蒙古馬為主題的造型藝術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是我們精神世界的燈塔,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的指路人。這是一種為人民奉獻一切的精神,而造型藝術也是要服務于人民,此外,創作者應像蒙古馬一樣,用堅強的意志披荊斬棘,踏實苦干,樹立為偉大的民族復興和繁榮昌盛奉獻的精神。中國造型藝術以其獨特的文化視角,正在為民族精神的傳承做出巨大的努力,同時蒙古馬精神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優秀的造型藝術創作者,促進中華民族文明不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