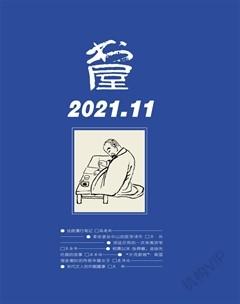弘一大師對朋友、學生及眾生的關愛
鐘書林
據亦幻《弘一大師在白湖》記載,弘一大師在聽靜權法師宣講《地藏菩薩本愿經》時,忽然當眾哽咽起來,“泣涕如雨”,原因是弘一大師聽到經文,想起了母親的慈愛。大師難得的天性流露,感動了眾僧,對亦幻法師觸動尤其大。他說:“我平生硬性怕俗累,對于母親從不關心,迨至受到這種感動,始稍稍注意到她的暮年生活。中間我還曾替亡師月祥上人撫慰了一次他的八十三歲煢獨無依、晚景蕭條到極點的老母。弘師對我做過這樣浩大的功德,他從沒有知道。……我想天下必定有許多如我之逆子,會被這部通俗注解感化轉來,對于劬勞的母親孝敬備至。”以往人們普遍認為“出家無家”,了無牽掛,甚至誤認為出家人對俗世人多半薄情寡義。但弘一大師用事理告訴世人:出家并非絕情。佛家的慈悲萬物、平等救度眾生,與儒家寬厚仁愛,在弘一大師的精神世界中得到很好的融合、升華。
1918年,三十九歲的李叔同決定出家,號弘一。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一文中回憶靈隱寺高僧慧明法師:
曾記得,在民國十二年夏天的時候,我曾到杭州去過一回。那時正是慧明法師在靈隱寺講《楞嚴經》的時候。開講的那一天,我去聽他說法。因為好幾年沒有看到他,覺得他已蒼老了不少,頭發且已斑白,牙齒也大半脫落。我當時大為感動。于是拜他的時候,不由淚落不止。聽說以后沒有經過幾年工夫,慧明法師就圓寂了。
民國十二年(1923),李叔同出家已五年,他猛然間看到慧明法師數年間蒼老了不少,不由淚落。
劉質平是李叔同出家前后傾心關愛的學生。今《弘一大師全集》(修訂本)中收錄有李叔同致劉質平書信一百一十五封,是現存李叔同致學生書信作品中數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1915年,李叔同在劉質平人生最艱難的時候千方百計設法相助其完成學業,兩人因此結下了深厚的感情。今存兩人最早通信即從這時開始:1915年9月3日。在這封書信中,李叔同安慰在老家養病的劉質平,并給予他百般鼓勵。他說:
質平仁弟足下:頃奉手書,敬悉。尊狀近若何,至以為念!人生多艱,不如意事常八九,吾人于此,當鎮定精神,勉于苦中尋樂;若處處拘泥,徒勞腦力,無濟于事,適自苦耳。吾弟臥病多暇,可取古人修養格言(如《論語》之類)讀之,胸中必另有一番境界。
不到半月,李叔同又隨即回信說:“頃接手書,誦悉。吾弟病勢未減,似宜另擇一靜僻之地療養為佳。家庭瑣事,萬勿介意。”在李叔同的鼓勵下,劉質平逐漸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并計劃往日本留學,而李叔同又主動資助其留學費用,并在通信中對他百般寬慰和教導。以1916年8月19日李叔同給劉質平來信為例:
質平仁弟:
來函誦悉。日本留學生向來如是。雖亦有成績佳良者,然大半為日人作殿軍,或并殿軍之資格而無之。故日人說起留學生輒作滑稽訕笑之態。
不佞居東八年,固習見不鮮矣。君之志氣甚佳,將來必可為國人吐一口氣。但現在宜注意者如下:
(一)宜重衛生,俾免中途輟學。(習音樂者,非身體健壯之人,不易進步。故每日宜為適當之休息,及應有之娛樂,適度之運動。又宜早眠早起。)
(二)宜慎出場演奏,免受人之忌妒。(能不演奏最妥,抱璞而藏,君子之行也。)
(三)宜慎交游,免生無謂之是非。(留學界品類尤雜,最宜謹慎。)
(四)勿躍等急進。(吾人求學,須從常軌,循序漸進,欲速則不達矣。)
(五)勿心浮氣躁。(學稍有得,即深自矜夸;或學而不進,即生厭煩心;或抱悲觀,皆不可。必須心氣平定,不急進,不間斷。日久自有適合之成績。)
(六)宜信仰宗教,求精神上之安樂。(據余一人之所見,確系如此,未知君以為何如?)
李叔同在出家前后,設法籌集資金,幫助劉質平完成學業,不使其輟學。其1917年3月書信說:“質平仁弟:來書誦悉。借假無覆音,想無可希望矣。(某君昔年留學,曾受不佞補助。今某君任某官立銀行副經理,故以借款商量,雖非冒昧,然不佞實自志為窶人,于人何尤!)……不佞即擬宣布辭職,暑假后不再任事矣。……秋初即入山習靜,不再輕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從這封書信來看,李叔同早年也曾資助“某君”留學,此次為了不使劉質平輟學,他不得不向“某君”冒昧以求借款,最后卻碰壁遭拒,李叔同卻以“不佞實自志為窶人,于人何尤”自責,足見其博大寬仁的心胸。
1918年3月9日給劉質平書信說:“兩次托上海家人匯上之款,計已收入。”1918年3月25日又去信說:“君所需至畢業為止之學費,約日金千余圓。頃已設法借華金千元,以供此費。余雖修道心切,然絕不忍置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職至君畢業時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學,勿再過慮。至要至要!”
如此這般的仁者赤子深情,李叔同在出家之后一以貫之。他臨終前依然不忘諄諄教誨后學僧眾。律華法師是一名幼年學僧。弘一大師臨終前給他書信一封:“朽人與仁者多生有緣,故能長久同住,彼此均獲利益。朽人對仁者之善根道念十分欽佩。朽人撫心自問,實萬分不及其一。故朽人與仁者長久同住,能自獲甚大利益也。妙蓮法師行持精勤,悲愿深切,為當代僧眾中所罕見者。且如朽人心中敬彼如奉師長。但朽人在世之時,畏他人嫉妒疑議,不敢明言。今朽人已西歸矣。心中尚有懸念者,以仁者年齡太幼,若非親近老成有德之善知識,恐致退墮。故敢竭其愚誠,殷勤請于仁者。乞自今以后,與妙蓮法師同住。且發盡形承侍之心,奉之如師,自稱弟子。并乞彼時賜教誨,雖受惡辣之鉗錘,亦應如飲甘露,萬勿舍棄。至囑至囑!”信中對于律華法師今后的成長萬般叮囑。
1941年10月,弘一大師臨終前,給青年居士李芳遠書信一封,勉勵他“仁者慧根深厚,舉世無匹。深望自此用功,勇猛精進。朽人近來病態日甚,不久當即往生極樂,猶如西山落日,殷紅絢彩,瞬即西沉。故未圓滿之事,深盼仁者繼成之。則吾雖凋,復奚憾哉”。
1942年,最后又書信說:“惠書誦悉,至為欣慰!見來書有唐人詩“西樓望月幾回圓”句,知近境大進。音嬰年亦喜此詩,今老矣,尚復如是。所恨蹉跎歲月,無所成就,愧見故人耳。仁者春秋正富,而又聰明過人,望自此起,多種善根。精勤修持,當來為人類導師,圓成朽人遺愿。謹稽首祝禱焉!”
這前后兩封書信中,對李芳遠寄予了很深的期望。弘一大師以“當來為人類導師,圓成朽人遺愿”,勉勵李芳遠精勤修持,頗見其良苦用心及其對后學英才的精心培養。
李叔同早年攜家眷南下居于上海,以文會友,結交“天涯五好友”,其中有許幻園,以城南草堂安頓李叔同家眷。李叔同在這里度過了人生少有的歡樂時光。據李叔同學生豐子愷回憶說:“(李叔同)二十歲時陪了母親南遷上海,住在……城南草堂。他母親在他二十六歲的時候就死在這屋里。他自己說:‘我從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之間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時候。……而在城南草堂讀書奉母的‘最幸福的五六年,就成了他底永遠的思慕。”1901年,辭別天涯五友,離滬北上,他寫下《南浦月·將北行矣留別海上同人》:“楊柳無情,絲絲化作愁千縷。惺忪如許,縈起心頭緒。誰道銷魂,盡是無憑據。離亭外,一帆風雨,只有人歸去。”
十多年后,他因送別許幻園而創作了《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余歡,今宵別夢寒。”這首歌凄婉動人,道盡別離的傷感與惆悵。后來,隨著許家的家運衰沉,這房子也就換了主人。1926年夏天,李叔同到上海后,再次專程造訪這處城南草堂遺址,觸發無限感慨。豐子愷《法味》一文詳細描繪了當時的情形。而弘一大師出家后的專程造訪,體現了他對友情及生活的重視與留戀。舊地重游,物是人非,當面對出來招呼的精舍和尚時,弘一大師卻淡淡地表示“我們是看看的”,“這房子我曾住過,二十歲年以前”。而“那和尚打量了他一下說:‘哦,你住過的。”這番對話,盡顯弘一大師的淡雅、恬靜、從容,正恰如葉圣陶《兩法師》中所說:“他(弘一法師)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樹,毫不愧怍地欣欣向榮,卻沒有凌駕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氣概。”
葉圣陶先生還回憶說:“決定不坐人力車,弘一法師拔腳就走,我開始驚異他步履的輕捷。他的腳是赤著的,穿一雙布縷纏成的行腳鞋。這是獨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雙這樣的腳。……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處自得;似乎他以為這世間十分平和,十分寧靜,自己處身其間,甚而至于會把它淡忘。這因為他把所謂萬象萬事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著的一部分內之故。”在葉圣陶先生眼里,弘一大師對書法也如同其待人一般:“就全幅看,許多字互相親和的,好比一堂謙恭溫良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顏悅色,在那里從容論道。就一個字看,疏處不嫌其疏,密處不嫌其密,只覺得每一畫都落在最適當的位置,移動一絲一毫不得。”
劉質平回憶:“師入山初期,念佛誦經,中期宣講律學,晚期從事著述,對于佛學上之貢獻甚大。出家二十五年,不收徒眾,不主寺剎,云游各處,隨緣而止。”在李叔同出家以后,曹聚仁也見過老師幾次。有一次,他看到弘一大師吃黃米飯、蘿卜干,吃得津津有味。為此他大為感動,認為:“一個美術家出身的和尚,竟如我們祖父(老農夫)一樣懂得生活的意義呢!”由此可見在朋友、學生眼中弘一大師謙恭溫良的性情。
但也有例外的。夏丏尊《弘一法師之出家》回憶:“我和弘一法師相識,是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校任教的時候。這個學校有一個特別的地方,不輕易更換教職員。我前后擔任了十三年,他擔任了七年。在這七年中我們晨夕一堂,相處得很好。他比我長六歲,當時我們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氣息懺除將盡。想在教育上做些實際功夫,我擔任舍監職務,兼教修身課,時時感覺對于學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圖畫、音樂二科,這兩種科目,在他未來以前,是學生所忽視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視起來,幾乎把全校學生的注意力都牽引過去了。課余但聞琴聲歌聲,假日常見學生出外寫生。這原因一半當然是他對于這二科實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師生以及工役沒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誠敬中發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學他。舉一個實例來說,有一次寄宿舍里學生失少了財物了,大家猜測是某一個學生偷的,檢查起來,卻沒有得到證據。我身為舍監,深覺慚愧苦悶,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說也怕人,教我自殺!說:‘你肯自殺嗎?你若出一張布告,說做賊者速來自首,如三日內無自首者,足見舍監誠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這樣,一定可以感動人,一定會有人來自首——這話須說得誠實,三日后如沒有人自首,真非自殺不可。否則便無效力。這話在一般人看來是過分之辭,他說來的時候,卻是真心的流露,并無虛偽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謝,他當然也不責備我。我們那時頗有些道學氣,儼然以教育者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不夠。可是所想努力的,還是儒家式的修養,至于宗教方面簡直毫不關心的。”
為了感化學生,李叔同竟幫夏丏尊想出一個教他“自殺”的教育方式來。這樣的話,正如夏丏尊說:“這話在一般人看來是過分之辭,他說來的時候,卻是真心的流露,并無虛偽之意。”足見李叔同對待朋友的赤誠之心。
這份自然天性,在李叔同出家后有時也會悄然流露出來。他在1937年1月29日給高文顯寫信說:“昨日出外見聞者三事:一、余買價值一元余之橡皮鞋一雙,店員僅索價七角。二、在馬路中聞有人吹口琴,其曲為日本國歌。三、歸途凄風寒雨。”
弘一法師出家利益眾生,悲天憫人,慈愛有情。據豐子愷回憶說: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后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里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在弘一大師生命彌留之際,他對隨侍的妙蓮法師還特別叮囑:當我身體停龕時,要用四只小碗填龕四腳,再盛滿水,以免螞蟻爬上來,這樣也可在焚化時免得損傷螞蟻。
據徐悲鴻回憶,弘一大師出家后,他曾多次進山看望弘一大師。有一次,徐悲鴻突然發現,山上已經枯死多年的樹枝發出新嫩的綠芽,他很納悶,便對大師說:“此樹發芽,是因為您,一位高僧來到此山中,感動了這棵枯樹,它便起死回生。”弘一法師說:“不是的,是我每天為它澆水,它才慢慢活起來的。”還有一次,徐悲鴻先生又去看望弘一大師,他看見一只猛獸在法師跟前走來走去,沒有傷人的意思,徐先生覺得很奇怪,便問:“此獸乃山上野生猛獸,為何在此不傷人?”法師說:“早先它被別人擒住,而我又把它放了,因此它不會傷害我。”1935年12月,弘一大師病重,曾傳遺囑給傳貫法師說:“命終八小時后以隨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夾被,卷好,送往樓后之山凹中。歷三日有虎食則善,否則三日后,即就地焚化。”李叔同的仁者摯愛、佛家慈悲之心,惠及枯枝、猛獸,無不體現出他對眾生的多情。
李叔同自幼心底澄凈良善,長大后飽受儒家思想熏陶,憂國憂民,關心民生疾苦,在近代紛亂之世,滿懷“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熱忱,東渡日本,尋求強國富民之路,歷經坎坷,皈依佛教,在佛祖面前發下弘愿,愿以此身普度眾生。這份牽掛、憫憐眾生的情感,從幼年到辭世,一以貫之。
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弘一法師多次明志說:“吾人所食,中華之粟。吾人所飲,溫陵之水。我們身為佛子,不能共紓國難,為釋迦如來張些體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為主子守門,吾人一無所能,而猶靦顏受食,能無愧于心乎?”很多時候,他將這些誓愿更多地化作了壯舉。1939年,他寫信給印西和尚,吩咐將緇素弟子為自己祝賀六十大壽的酬資,“轉奉衛國將士,及避難同胞,庶乎有用”。1938年4月18日,他給豐子愷寫信說:“朽人出家以來,恒自韜晦,罕預講務。乃今歲正月至泉州后,法緣殊勝,昔所未有,幾如江流奔騰不可歇止。朽人亦發愿為法舍身。雖所居之處,飛機日至數次(大炮疊鳴,玻璃窗震動),又與軍隊同住,朽人亦安樂如恒,蓋已成習慣矣。幸在各地演講,聽者甚眾,皆悉歡喜。于兵戈擾攘時,朽人愿盡綿力,以安慰受諸痛苦驚惶憂惱諸眾生等,當為仁者所贊喜。”在炮火轟鳴中,弘一大師不懼艱險,泰然處之,“安樂如恒”。抗戰期間,凡是各方人士前來要求墨寶,弘一法師概書“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相贈。
1937年11月1日他給夏丏尊等書信說:“廈門近日情況,仁等當已知之。他方有勸余遷居避難者,皆已辭謝,決定居住廈門,為諸寺院護法,共其存亡。必俟廈門平靜,乃能往他處也。知勞遠念,謹以奉聞。”同一時期,他給蔡冠洛居士書信也說:“時事未平靖前,仍居廈門。倘直變亂,愿以身殉。古人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在給朋友的書信,他多次表示以身殉難,以詩明志的決心,與國人、友朋共赴國難、共渡艱險。也正是他的這番仁愛和勇氣,激勵著更多的僧眾、朋友、學生,砥礪前行,書寫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