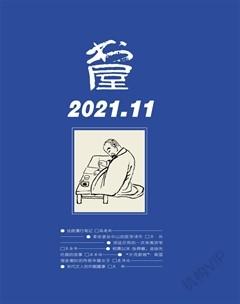李時珍與中醫學的“醫道”傳統
王淼 張雪亮
蘄春這個地方,地處“吳頭楚尾,荊揚交匯之區”,自古即以醫藥文化聞名于世。所謂“蘄”,在《爾雅》中指的是蘄茝,乃是蘼蕪的別稱,蘄茝,或者說蘼蕪,苗似芎藭,葉似當歸,香氣似白芷,在藥用上有祛風止眩、補肝明目、除涕止唾的功效。另據晉代劉伯莊的《地名記》記載,“蘄春以水隈多蘄菜”而廣為人知。蘄菜乃是水芹菜,除食用的價值之外,在藥用上有保血養精、益氣健胃、清火解毒之功效——可知蘄春乃是因藥得名,“蘄春”一詞,實際上蘊含著草藥繁茂、藥物昌盛的寓意。
蘄春有著深厚的醫藥文化傳統,早在唐代,這里已經設立醫館,設醫學博士和助教各一人,并向朝廷進貢各種名貴藥材,這在當時的州縣中已屬稀見。進入宋代,蘄春成為長江中游一帶最大的藥材貿易集散中心,南宋詩人陸游入蜀出任夔州通判,由江西隆興溯江而上,途徑蘄春,留下這樣的記錄:“是日,買熟藥于蘄口市,藥貼中皆有煎者所須,如薄荷、烏梅之類,此等皆客中不可倉促求者。藥肆用心于此,亦可嘉也!”可見宋代的蘄春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藥材市場。明代以降,蘄春的中醫藥文化進入鼎盛時期,一時間名醫輩出、人才濟濟,各種官辦和私辦的診所與藥店出現在大街小巷,蘄春人善識草藥,民間社會甚至達到了“指草皆為藥,路人皆知醫”的境地,而醫藥文化長期氤氳與積累的結果,就是“一代藥圣”李時珍的應運而生。
因為史料的缺失,李時珍祖上的家族譜系已不可知,如今我們大抵知道的是,李時珍(1518—1593)出生于一個世醫之家,他的祖父是一位鈴醫,也叫“走鄉醫”,亦即游走于江湖的民間醫生。他的父親李言聞乃是蘄春名醫,曾經考取貢生,做過太醫院吏目,后辭歸故里,設診于蘄春玄妙觀,著有《四診發明》《奇經八脈考》《蘄艾傳》《人參傳》《痘疹證治》等多種醫學著作。李時珍是李言聞的次子,他自幼習儒,年甫十四已然考中秀才,這讓將科舉視作正途的李言聞感到欣喜不已。但是,李時珍其后的科舉之路卻并不順遂,從嘉靖十三年(1534)到嘉靖十九年(1540)的六年間,他連續三次參加鄉試,卻“三試于鄉不售”,最終決定放棄舉業,子承父業,矢志做一名治病救人的醫者。
按說以當時李時珍二十三歲的青春年華,還是完全有可能在科舉方面做出一番作為的,而李時珍之所以毅然放棄舉業,走上從醫之路,首先是與他個人的志向分不開的。據《明史稿》記載,李時珍從小即“不治經生業,獨好醫書”,能夠把父親為人治病的藥方熟記于心。而在《本草綱目》中,李時珍自陳,他二十歲那年曾經得過一次重病,發病時“骨蒸發熱,膚如火燎,每日吐痰碗許,暑月煩渴,寢食幾廢,六脈浮洪”。李言聞親自為他配制了柴胡、麥門冬、荊瀝諸藥,李時珍服下后病情非但不見好轉,反而愈顯沉重,甚至連親友都以為再無恢復的可能。情急之下,李言聞突然想起金代名醫李東垣用過的一副藥方,他抱著試一試的心態讓李時珍服下,沒想到第二天兒子即“身熱盡退,而痰嗽皆愈”。李時珍由是感嘆道:“藥中肯綮,如鼓應桴,醫中之妙,有如此哉!”自此愈加堅定了從醫的決心。
一個對自然博物充滿興趣的人,其實是很難真正在呆板、空疏的八股文方面有所建樹的,這既需要性情的契合,又是興趣所然。李時珍從醫的選擇固然得益于他家族行醫的傳統,同時也與蘄春當地的地域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如前所述,蘄春本來即有著深厚的醫藥文化土壤和豐富的中醫藥資源,所謂“不知醫者為不孝”,一般民眾亦把識藥知醫作為“盡孝”的一種具體方式加以弘揚。當“醫者”的傳統與“儒者”的傳統聯系在一起時,從醫已不再局限于形而下的“醫術”層面,而是上升為一種形而上的“道統”:懸壺濟世既是中國“醫道”文化的核心價值,亦足以用來維系儒家道統的脈絡和系統——西漢名士賈誼所謂:“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居醫卜之間。”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所謂:“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實際上都是這種“醫道”傳統的一脈相承。
作為一介士子,李時珍起初或許的確曾將“學而優則仕”視作自己人生的歸依,但是,當這條路走不通時,他反而產生了一種全身放下的輕松感,他迅速調整目標,將自己的人生定位在濟世救人的“仁術”上。他向父親表明了這樣的心志:“身如逆流船,心比鐵石堅。望父全兒志,至死不怕難。”并終于獲得了父親的諒解。這當然也是李時珍自覺的選擇——時當明代中后期,經濟日益繁榮,文化漸趨多元,一般士子的人生之路已不再是單一的由士而仕,他們不必在科舉之路上一條道走到黑,他們有了更多的選擇——若從這個角度上說,李時珍既是不幸的,又是萬幸的,他雖然沒有獲得科舉的成功,卻因此成就了“一代藥圣”的名聲。
自嘉靖十九年(1540)以后,矢志從醫的李時珍開始發憤讀書,乃至“十年不出戶閾”,舉凡經傳、子史、聲律、農圃、星卜、佛老、稗說……可謂無所不窺,為他其后編撰《本草綱目》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發憤苦讀期間,李時珍也時常協助父親診治病人,積累了大量的臨床經驗和用藥知識,從而慢慢開始了獨立行醫的歷程,并初步產生了重修《本草》的想法。正式掛牌行醫的李時珍總是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以至經常有外地病人慕名前來,“千里就藥于門,立活不取值”,其高超的醫術和高尚的醫德逐漸傳遍鄉里。
嘉靖三十一年(1552),封藩于武昌的楚王聽聞到李時珍的名聲,派人聘請李時珍為楚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醫所日常事宜。適逢楚王世子驟得疾病,李時珍巧施妙手將其搶救過來,由此深得楚王信任。時隔不久,李時珍即被楚王推薦給設置在京城的太醫院,并被授予“太醫院判”一職,有機會出入太醫院的藥房及御藥庫,飽覽皇家珍藏的豐富典籍。盡管李時珍對太醫院的任職興趣不大,但太醫院的經歷卻讓他如入寶山、眼界大開,他不僅親眼看到各種珍貴的藥品實物,得以鑒別各地藥材,同時也搜集到大量難得的資料——他后來編撰《本草綱目》之所以能夠做到“上自墳典,下及傳奇,凡有相關,靡不備采”,他在太醫院任職的經歷無疑至關重要。
李時珍在太醫院任職不過一年的時間即辭職返鄉。這一方面是因為他與皇家拘謹壓抑、等級森嚴的環境格格不入,很難與那些庸醫同行們打成一片;另一方面,李時珍始終抱有“醫者仁心”的理想,他更愿意用自己的醫術服務大眾,讓更多的病人受惠。返鄉后的李時珍自創東壁堂,白天坐堂行醫,晚上著手準備編撰《本草綱目》。在此后的將近三十年間,李時珍一邊坐診出診,救死扶傷;一邊漁獵群書,搜羅百氏。為了搜集藥物標本,李時珍的足跡遍及廬山、茅山、武當山、牛首山及湖廣、河南、南直隸、北直隸等地;為了得到民間處方,李時珍曾經拜農夫、漁人、樵夫、車夫、藥工、捕蛇者為師。為了編撰《本草綱目》,李時珍一共記錄了上千萬字的筆記,前后不斷增刪,三易其稿,才終于完成了這部皇皇巨著。
《本草綱目》脫稿于萬歷六年(1578),此時的李時珍已經由翩翩少年變成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可以說這部巨著傾注了李時珍大半生的心血。盡管《四庫提要》評介《本草綱目》是“取神農以下諸家本草薈萃成書”,是一部“復者芟之,闕者補之,訛者糾之”的本草學的集大成之作。但在事實上,這部巨著的影響已經遠遠超越了本草學的界域,而囊括了人文、歷史、地理、天文、農圃、民俗等各個方面的價值——它不僅僅具有百科全書的性質,同時也傳遞了一種究天人之際、效法自然的“醫道”智慧;而這種“醫道”智慧,也不僅僅能夠“格藥之性,窮醫之理”,同時也蘊含著“醫者仁心”——亦即“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的“乃成蒼生大醫”的人格理想。
毫無疑問,李時珍被后世尊為“藥圣”,絕不僅僅是因為他的醫術高明——對于李時珍來說,行醫并不單純是一種糊口的職業,同時也是一種兼濟天下的方式,這曾經是他作為一介儒生的理想,也同樣是他后來成為一名醫者的理想。李時珍被后世尊為“藥圣”,是因為他象征著醫者的良心,正因為有了醫者的良心,中國的醫學文化才能夠超越商業利益,成為一種“醫道”傳統,從而源遠流長,生生不息——這既是傳統中醫藥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面對當下商業大潮沖擊下的醫療現狀,最值得我們反思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