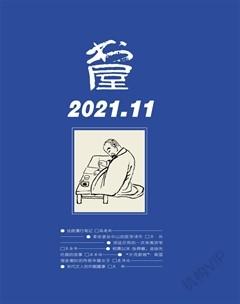《李澤厚劉綱紀美學通信》編后記
楊斌
《李澤厚劉綱紀美學通信》出版,作為編者,有必要向讀者作一些交代。
近十多年來,因為編撰《李澤厚學術年譜》的緣故,我和李澤厚先生的聯系是比較多的。見面交流多次,郵件數十封,更多的是電話請教。每次聯系,李先生很少主動講起什么,總是我有所求教,他有選擇地做些回答、解釋,聊到高興時,偶爾老先生也會宕開話題,作些與談話話題有關或無關的發揮。但是,李先生從未主動提起過和劉綱紀先生通信的事。
知道兩位先生有過許多通信的事,我是偶爾從《中國青年報》一篇報道中看到的。那篇訪談中,劉綱紀先生說:“我現在還保存著在寫《中國美學史》時李澤厚給我的七十多封信,每封信都充滿誠摯熱烈的友情,文筆也相當好。如果他同意,可以公開發表。作為老朋友,我們相互幫扶,走了一段不短的人生旅程。”訪談是2007年前后的事,而我在網上看到時已是2017年。其時,我正在張羅著修訂《李澤厚學術年譜》,四處搜尋資料。這個信息太重要了!我趕緊向李澤厚先生求證。李先生表示:“確有這回事,但不知道人家會不會接待你,愿不愿意讓你看。”我想,凡事總得試試,碰壁了也無所謂。于是,我求助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劉悅笛研究員,劉悅笛又通過武漢大學彭富春教授,輾轉拿到了劉府的聯系電話,這樣,我終于和劉綱紀先生建立了電話聯系,劉先生也頗為爽快地同意了我擇機去武漢看信的請求。
2017年12月初,我來到了位于珞珈山麓的劉先生寓所。劉先生很高興,向其夫人介紹道,這是李澤厚介紹來的,專門來看信的。敘談期間,劉先生回憶了兩人之間的一些交往,還特意拿出一本十分精美的《劉綱紀書畫集》,翻到其中一幅書法作品《唐杜甫詩·春日憶李白》,并且輕聲朗讀了起來:“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劉先生強調說:“我在寫這幅作品時,心里想的就是李澤厚!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啊!”劉先生還說:“李澤厚的性格像李白,而我和杜甫相似。”我當即向劉先生提出請求,希望能得到劉先生的墨寶,就是重寫這幅作品,并且題簽注明,是為了紀念和李澤厚先生友情而寫。劉先生答應了我,只是說時間要往后挪,當下手里還有七個博士生在讀,指導論文的任務很重,很忙。我當時縈繞心懷的主要是信件——那些至為寶貴的信件,同時初次見面也不敢造次,心想,來日方長,以后一定有機會的。誰知,這一極具紀念和象征雙重意義的書法佳構,永遠也無法再次重現了!2019年12月1日,劉綱紀先生走完了八十七年的人生征程。遠在大洋彼岸科羅拉多高原的李澤厚先生,第一時間通過劉悅笛的微信送了挽聯:“憶當年合作音容宛在,雖今朝分手友誼長存。”如今,那個深秋的午后,在劉府寬敞的客廳兼畫室和綱紀先生對話的情景,仍歷歷在目。寫出這一段故事,我似乎有了一種記錄和還原歷史的感覺。
那次拜見劉綱紀先生的聊天,不知不覺大約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傍晚,劉先生堅持親自送我到他家附近的武漢大學教工招待所,并安排入住。我就在招待所里安營扎寨,閱讀并整理起那厚厚一大袋子李先生的書信來。盡管我知道李先生的字跡辨認起來難度很大,盡管我事先對劉先生夸過海口,我說我辨認李先生的字跡還是比較厲害的,在我撰寫《李澤厚學術年譜》時,李先生在初稿上的修改和添加,許多地方可謂密密麻麻,但我基本都連認帶猜地讀出來了,為此還得到過李先生的贊揚,但是,這一次讀信過程中,仍然遇到很多“攔路虎”,因為對寫信時的一些具體情境不甚了解,有不少字怎么“猜”也無法“自圓其說”。我是答應劉先生幫助他將信的內容輸入電腦的,這有些地方“半通不通”連我自己也說服不了的通信,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就這樣交“作業”的。因此,電腦輸入的速度極慢,三天下來才做了不到三分之一。于是,我在征得劉先生同意后,只好將所有信件復印出來,帶回蘇州慢慢“考證”“破譯”。
回家之后的進展要順利得多。一方面,根據《李澤厚學術年譜》,另一方面,依據李先生的著作尤其是兩位合著的《中國美學史》,很多疑難問題便能迎刃而解。這樣,大約有兩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我完成了這批信件的電腦輸入,趕緊發給兩位老先生。令我驚喜的是,李澤厚先生看到我發去的電子稿之后不久,便也寄來一大包劉綱紀先生給他的信件。這可真是“天上掉下個林妹妹!”李先生糾正了我“破譯”的一些訛錯之處,有幾處我們倆意見不統一,李先生說“我不可能這么說,這么說也不通”,我說“白紙黑字,您就是這么寫的”。再后來,我學會了微信,有幾個字是微信拍照發過去請李先生確認的。當然,結果還是人家那位寫信的人說得對!
劉綱紀先生的信整理起來很快,這當然得益于劉先生字跡規范,那可是書法家的手筆;而且,寫得也很認真。僅從兩位先生的通信字跡,倒也部分印證了劉綱紀先生的說法,一位像李白,瀟灑奔放;一位像杜甫,恭謹合度。
接下來就是整理編排了,這涉及體例。我最初想法是,你來我往,一一對應,這樣閱讀起來會更加方便。誰知道,很難!一方面,信件本身不全,有缺漏,更重要的是,雙方寫信落款一般都是月、日,很少顧及年份,而信封上的郵戳,除少數幾封寄自新加坡的可以看得清楚,其他的都模模糊糊。于是,還得根據內容去做些“考證”,確定年份。應該說,這些“考證”工作花費了大量時間,但還是很難保證完全準確。若有訛錯,當然責任在我。不過,兩位學者圍繞《中國美學史》寫作交往、交流和磋商的大致線索脈絡,已經是十分清楚了。
最后,轉達李澤厚先生有關本書的兩點說明:一、因在國內外數次搬家,劉致李的信有不少遺失,不全。二、李澤厚為《中國美學史》寫的兩個后記,作為這本通信集子的附錄。
還要予以說明的是,征得李澤厚先生同意,編輯對個別內容作了技術處理,凡刪節處都予以說明。劉綱紀先生生前,筆者曾就此和劉先生商量過,他也表示贊成。
感謝浙江古籍出版社應允出版本書,感謝策劃編輯夏春錦先生、責任編輯孫科鏤先生為此付出的努力。尤其是孫科鏤老師,不僅為本書的編排提供了寶貴建議,同時在編校過程中,刨根問底、落水出石,糾正了原稿中的諸多疏漏,其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和審慎求精的編審功力,令我十分感佩。這是一份記錄《中國美學史》(第一、二卷)誕生過程和幕后故事的第一手資料,也是見證兩位著名學者為中國美學事業傾心合作的一段學術佳話!唯一遺憾的是,因為種種原因,這部極具開創性意義的美學巨構沒有能夠終篇,否則,這本學術通信集會因之而更加豐滿厚重。只能說,缺憾也是一種美。美好的事物總難免有遺憾,此事古難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