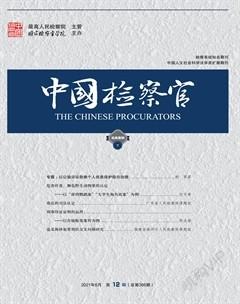刑事印證證明的運用
鄭法梁
摘 要:印證證明是刑事案件證明的基本方法。司法實踐中,印證證明有時未被正確地運用,出現印證證明模式化、粗濫化的現象。審查者對印證證明的認識模糊、運用混亂是沒有形成真正印證或形成虛假印證的內在原因。基于此,有必要厘清刑事印證證明的證成邏輯。從證據來源、印證的同一性、印證的程度判斷同向證據形成充分印證,并消除根本性的矛盾證據和進行必要的檢驗,進而準確把握刑事印證證明。
關鍵詞:印證證明 模式化 虛假印證 證成邏輯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毒品犯罪案件數量大,禁毒形式依然嚴峻。毒品犯罪人員經常采用“少量、多次、流動”的手段從事毒品犯罪交易活動,販毒活動的網絡化手段增多,利用網絡交易,利用虛假的身份信息郵寄毒品,并利用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毒資,交易趨于復雜化和隱蔽化,給毒品案件偵破帶來很多挑戰。毒品案件也不是偵破了就代表案子結束,更大的挑戰還在于證據的收集、審查和事實的認定。不少疑難毒品案件經過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審查者面對相同的證據并沒有得出一致的判斷結論,反而產生“證據夠不夠”“是否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否排除合理懷疑”“結論有沒有唯一性”的分歧意見。也許,審查者的司法經驗、業務能力高低對證據結論產生影響,但對刑事印證證明的不同理解與把握才是分歧意見的根源。
印證證明作為刑事案件證明的基本方法受到司法人員的熱捧和頻用,在司法實踐出現“簡單化甚至庸俗化的情況未能有效克服,甚至在某些方面成泛濫之勢,這是由于印證證明模式的弊端造成的”[1],那么,司法人員應當如何把握刑事印證證明,如何避免印證證明模式的弊端,從而精準認定犯罪事實。鑒此,以所任職檢察院近十年作存疑不捕的販賣毒品案件作為分析樣本,結合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等有關規定,對印證證明的運用經驗作粗淺的探討和總結,以期有助于司法實踐。
樣本的選擇是考慮到提請逮捕的案件由于偵查時間緊湊,一般圍繞基本犯罪事實偵查。所取的證據情況反映偵查人員內心對刑事印證證明的最真切理解與把握;存疑案件體現了檢察人員與偵查人員在事實和證據認定上的沖突與矛盾,亦直接反應檢察人員對印證證明運用邏輯。案例中不同思維的碰撞對比,能夠說明司法實踐中印證證明運用的具體問題。
二、印證證明的模式化
(一)偵查取證“點到為止”
印證證明的目的是認定犯罪事實。犯罪事實包括犯罪客觀要件事實和犯罪主觀要件事實。犯罪客觀要件事實則指犯罪結果事實、犯罪行為事實、因果關系事實以及罪責同一性事實。根據刑法第347條對販賣毒品罪的條文表述,販賣毒品不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說明販賣毒品罪是行為犯,無需有危害結果的發生,只要實行行為完畢,構成要件即已齊備。因此,在販毒案件中,犯罪行為事實和罪責同一性事實作為印證證明的必要證明對象,是偵查人員必須查明的要件事實。對樣本分析發現,兩證明對象在取證力度上受到明顯的區別對待,犯罪行為事實得到了偵查人員更多的“關心”。以林某林販賣毒品案為例,該案中偵查機關基本沒有對0596尾號的手機號碼是否為林某林使用事實進行偵查取證,未將微信語音進行聲紋比對、未對登記機主查詢核對,僅僅憑借在林某林身上查獲作案手機即完成罪責同一性事實的認定。
[案例一]林某林販賣毒品案
公安機關認定的事實:2017年6月1日16時、6月2日11時,犯罪嫌疑人林某林向吸毒人員張某福販賣海洛因,每次均通過微信收取毒資200元。
本案的證據主要包括:(1)證人張某福陳述6月1日16時、6月2日11時,使用6690尾號的手機號碼聯系0596尾號的手機號碼向“阿林”購買毒品海洛因,均通過手機微信向“阿林”轉賬200元;(2)通話詳單顯示6月1日16時、6月2日11時,張某福6690尾號的手機號碼與0596尾號的手機號碼均有通話記錄,且在5月27日至6月7日間通話頻繁;(3)張某福手機微信的轉賬記錄顯示6月1日16時1分,張某福的微信號向昵稱為“阿林”的微信號轉賬200元;6月2日11時11分,張某福的微信號向昵稱為“阿林”的微信號轉賬200元;(4)微信語音聊天記錄顯示6月1日16時、6月2日11時11分,張某福的微信號與備注為“阿林”進行毒品買賣及有關購買毒品質量的語音;(5)張某福的辨認筆錄辨認出林某某系“阿林”;(6)林某林陳述不認識購毒者張某福,以及0596尾號的手機是別人送的,不清楚手機的微信情況。(7)在林某林身上查獲到0596尾號的手機。
檢察機關審查認為,在案證據能證實張某福于6月1日16時、6月2日11時向“阿林”購買毒品海洛因。但“阿林”是否犯罪嫌疑人林某林本人尚缺少證據印證,僅有張某福指證“阿林”系林某某,罪體同一性的事實尚未查清,認定系林某林販賣毒品的證據不足。
(二)輕視當事人的辯解
通過現有的一些證據進行簡單的推論,欲套用相互印證的證明標準直接推翻當事人的辯解,不針對辯解進行取證核實,這是印證證明被模式化的另一表現。如林某祥販賣毒品案,當事人對微信接收的錢款辯解不是收取的毒資,該辯解直接影響到林某祥販賣毒品事實能否認定,偵查機關認為秦某冰關于林某祥販賣毒品的指控已得到其他證據的印證,林某祥的辯解明顯是為了躲避法律追究,不予采信,因此無需進一步核查。
[案例二]林某祥販賣毒品案
公安機關認定的事實:2019年3月15日18時,犯罪嫌疑人林某祥在某臭豆腐店旁以2400元價格向秦某冰販賣毒品K粉4克。
本案的證據主要包括:(1)秦某冰陳述,2019年3月15日18時,其通過電話向林某祥購買K粉,后林某祥開車接其到了一家臭豆腐店,之后不知去哪拿了一包K粉,里面4小包,每包1克,其通過手機轉給林某祥2400元;(2)電話詳單顯示3月15日18時,二人有多次通話;(3)微信轉賬記錄顯示,3月15日18時秦某冰轉給林某祥2400元,除此之外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30日林某祥有多筆轉給秦某冰的記錄,2019年3月有5筆共計1.2萬元;(4)林某祥否認販毒,陳述3月15日秦某冰轉的2400元是其之前將錢預存在秦某冰處便于向秦某冰購買毒品K粉,這筆2400元的轉賬匯款是因為當時秦某冰一直K粉斷貨,故其把之前的K粉預存款還給犯罪嫌疑人林某祥;(5)秦某冰的刑事判決書顯示,2019年1月至3月,秦某冰因多次向他人販賣K粉被判刑。
檢察機關審查認為,犯罪行為事實系犯罪基本事實的必要構成,本案僅秦某冰一人指證,林某祥的辯解合理,微信轉賬記錄不能佐證秦某冰的指證,在案證據無法證實3月15日2400元的轉賬記錄就是秦某冰向林某祥購買毒品K粉的毒資,亦無法證實林某祥有販賣毒品的行為。
(三)過分依賴言詞證據
言詞證據能夠直接反映案件情況,在證明事實時比客觀證據更為快捷、便利。當事人的口供在販毒案件的證據體系里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在證明主觀犯罪事實上,對言詞證據的依賴更是有過之無不及。如劉某芬販賣毒品案,偵查人員在無法突破劉某芬的口供情況下,仍著力于劉某芬關系人的言詞證據,意通過關系人的言詞證據以證明劉某芬明知是毒品而幫忙送貨,收效甚微。
[案例三]劉某芬販賣毒品案
公安機關認定的事實:2016年2月8日下午,林某岳在電話中約好將一包毒品冰毒以1300元價格出售給李某群,后犯罪嫌疑人劉某芬受林某岳指使將一包毒品送到李某群的暫住處。
本案的證據包括:(1)證人林某岳陳述,2月8日約好以1300元價格向李某群出售一包冰毒,由劉某芬送給李某群,自己沒有明確告知劉某芬系毒品,冰毒被紙巾包住;劉某芬此前還為其送過兩次毒品給李某群。后偵查人員重新取證,林某岳改變陳述稱劉某芬應該知道送的東西是毒品。(2)證人李某群陳述2月8日向林某岳以1300元購買冰毒,后由一大姐送毒品過來,之前有向林某岳購買過2次冰毒,也是該大姐送的,但記不起來具體日期。(3)李某群辨認出劉某芬系送毒品的大姐。(4)通話詳單顯示,林某岳與李某群在2月8日有多次通話,以及林某岳有聯系劉某芬。(5)微信交易記錄,證實2月8日林某岳收到李某群轉賬1300元。(6)劉某芬稱與林某岳系一般朋友,自己幫林某岳送過好幾次東西,林某岳告訴其送的是藥丸,沒有說毒品,沒有收取好處費。(7)劉某芬為文盲,沒有吸毒、販毒經歷。
檢察機關審查認為,在案證據能證實劉某芬客觀上實施幫林某岳送毒品的行為,但無法證實劉某芬主觀明知送的是毒品,一是在案證據無法直接證明劉某芬主觀明知,二是間接性證據無法形成證據鏈證明劉某芬主觀明知;三是劉某芬的基本情況及生活經歷難以推定。
三、印證證明的粗濫化
印證證明模式化的實質原因是印證證明方法的認識模糊和運用混亂,繼而才有了以證據相互印證即能認定相關事實的錯誤理念。換言之,這是對印證證明的粗濫化認知。在不同認知的支配下,印證證明在實踐中產生三種形態:形成充分印證證明、沒有形成印證證明、形成的印證是虛假的。后兩種情形通常是粗濫化運用印證證明導致的。
(一)沒有形成相互印證
行政訴訟法第55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這是證據補強規則的法律出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140條規定:“沒有直接證據,但間接證據已經查證屬實,證據之間相互印證,不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和無法解釋的疑問,全案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根據證據認定事實足以排除合理懷疑,結論具有唯一性,運用證據進行的推理符合邏輯和經驗”,創設了間接證據的印證規則。因此,沒有形成相互印證主要分為基礎證據沒有得到補強和間接證據鏈斷節的情形。
1.基礎證據沒有得到補強
補強證據應達到何種補強程度,才能實現補強證據規則的應有價值,涉及到對補強證據的證明要求問題,對此,理論上有“絕對說”與“相對說”之分。“絕對說”主張,補強證據應對案件事實具有較為充分的證明作用;“相對說”則主張被告人供述和補強證據“合二為一”能夠證明犯罪事實即可。實踐中一般采用“相對說”[2]。然而,知曉證據補強規則,實踐中卻還是出現用于補強的證據不能切中要點,無法印證待證事實的情形,如丁某強販賣毒品案。
[案例四]丁某強販賣毒品案
公安機關認定的事實為:2020年1月上旬,犯罪嫌疑人丁某強在某出租房內向張某鳳出售1100元冰毒。
本案的證據包括:(1)丁某強前2份筆錄否認販毒,后3份訊問筆錄供認2020年1、2月份,在出租房內向張某鳳出售過一次毒品冰毒,但關于是現金、還是微信收取毒資陳述反復,毒資數額是500元還是200元陳述反復;(2)丁某強辨認出張某鳳;(3)張某鳳前3份筆錄稱2020年1月上旬,在出租房內向丁某強的老婆涂某英購買冰毒,通過微信向涂秀英轉賬1100元毒資;第4份筆錄稱是向丁某強購買冰毒,通過微信向丁某強轉賬1100元毒資;第5份筆錄稱是以現金方式給丁某強;(4)涂某英零口供。
檢察機關審查認為,本案的丁某強在偵查階段后期供認向張某鳳販賣毒品一次,屬于直接性的基本證據。只要在案有其他證據能夠印證丁某強的口供,應當是可以定罪的。審查本案證據,張某鳳的證言能印證其向丁某強購買過冰毒,可在毒資交付方式、數額及購買時間等重要細節上無法印證,本案另無其他客觀性證據補強丁某強的口供,因此本案的證據沒有形成相互印證,無法認定犯罪事實。
此外,實踐中還存在證據堆積問題,偵查人員未有效區分具體的場景,對印證的不同類型沒有作精細化分析,盲目追求證據的數量,不對同一待證事實補取有效證據,導致大堆證據堆積閑置,無法達成印證的目的,如溫某玉販賣毒品案。
[案例五]溫某玉販賣毒品案
公安機關認定的事實: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間,犯罪嫌疑人溫某玉協助丁某元多次將毒品海洛因販賣給姚某鈺、陳某宇、阮某勝等人。
案件的證據包括:(1)姚某鈺陳述其向丁某元購買毒品多次,有時候溫某玉送毒品過來,有時候另一馬仔送毒品。溫某玉送的次數有十多次;(2)姚某鈺辨認出溫某玉;(3)陳某宇陳述丁某元和溫某玉共同販毒,有時候打電話是溫某玉接的,溫某玉在電話中說過買毒品可以直接找她;送毒品有時是丁某元和溫某玉一起送,有時候是溫某玉送,溫某玉送了6、7次;(4)陳某宇辨認出溫某玉;(5)阮某勝陳述丁某元和其說過要將毒品生意給溫某玉接手,其向丁某元電話購毒4、5次,都是溫某玉送的毒品;(6)陳某宇辨認出溫某玉;(7)溫某玉承認與丁某元為情人,同居,辯稱不知道丁某元販毒,自己沒有參與販毒;(8)丁某元承認自己有販毒,查獲毒品系用于販毒,但辯稱溫某玉沒有參與販毒,對查獲毒品不知情;(9)搜查筆錄、鑒定意見顯示在丁某元家中查獲190克冰毒;(10)銀行交易記錄顯示姚某鈺、陳某宇、阮某勝多次向丁某元銀行卡轉賬;(11)通話詳單顯示丁某元的手機號碼與姚某鈺、陳某宇、阮某勝手機均有多次聯系。
檢察機關審查認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溫某玉否認販賣毒品,證人姚某鈺、陳某宇、阮某勝分別陳述曾單獨向丁某元購買毒品,溫某玉有幫忙送毒品的情況,三人陳述分屬于不同的犯罪事實,彼此間沒有緊密的關聯性,三名證人間的證言不能就具體事實形成相互印證。
2.間接證據鏈的斷節
間接證據的印證邏輯是,通過間接證據的相互印證認定片段事實和連結點,再將各片段事實按常理接連在一起,形成閉合的證據鏈,進而完整地證明犯罪事實。但實踐中存在各片段事實間斷節的情形,如雷某兵販賣毒品案。
[案例六]雷某兵販賣毒品案
公安機關認定的事實:繆某浩受雇販毒上家丟包。2018年2月8日22時許,繆某浩被公安機關抓獲后,舉報當晚與上家約好拿取毒品。22時42分許,上家將毒品放置地點的照片發到繆某浩的微信,隨即民警使用繆某浩的微信以找不到毒品為由要求上家標明毒品的具體位置。之后,上家讓羅某澤到現場查看毒品,并在照片上圈出毒品的投放位置。羅某澤將該標明的照片發給上家后,離開現場時被抓獲。繆某浩手機隨即收到標注好的照片,民警在照片標注處查獲一包外用黑色塑料袋包裹,內用透明薄膜袋包裝的毒品冰毒,重98.7克。在透明薄膜袋上提取到犯罪嫌疑人雷某兵的汗液指紋。
案件的證據包括:(1)繆某浩陳述上述案發當晚的具體經過,但稱不認識羅某澤、雷某兵。繆某浩、羅某澤的手機微信聊天記錄證明毒品位置的照片接收及發送情況;(2)羅某澤否認販毒,稱案發當晚是他人請托讓其到現場看下東西在不在,其就去現場,稱雷某兵平時有到其出租房玩,案發當天雷某兵是先離開的;(3)通話記錄顯示,案發當晚羅某澤有接到繆某浩的上家電話;以及羅某澤被抓獲后,雷某兵多次呼叫羅某澤電話;(4)雷某兵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雷某兵與羅某澤就雷某兵弄丟50個東西發生爭吵,羅某澤要求雷某兵賠錢10000元,雷某兵發誓不小心弄丟;(5)勘驗、檢查筆錄、鑒定意見證實,查獲的毒品冰毒的透明薄膜包裝袋上有雷某兵的汗液指紋;(6)雷某兵稱平時有到羅某澤出租房玩,沒有參與販毒,羅某澤有用透明薄膜包裝袋裝茶葉,其有幫忙過。
檢察機關審查認為,毒品的內包裝上留有雷某兵的指印只能證實犯罪嫌疑人雷某兵接觸過毒品內包裝袋,但不能直接證實雷某兵在接觸內包裝袋時里面就已經裝有毒品或者雷某兵進行了毒品的分裝因而留下指印;結合本案的其他間接證據分析,微信聊天記錄里講到雷某兵被懷疑弄丟東西50個,但是該聊天記錄也并未明確里面的東西就是毒品,羅某澤、雷某兵討論的是共同販毒一事;雷某兵與羅某澤關系緊密、在事發后多次撥打羅某澤電話等情況,也無法推定二人系共同販賣毒品;各間接證據尚未就雷某兵參與販賣毒品事實形成一致性的證明效力,所能印證的事實非常有限,即使在毒品包裝袋上查到雷某兵的指紋,現有的間接證據也無法定罪。
(二)形成的印證是虛假的
1.據以定罪的證據不具有證據能力
證據必須具備合法性、客觀性、關聯性,才有證據能力。在運用印證證明方法時,審查者往往側重證據證明力強弱的考量,而忽視證據能力的審查。行政訴訟法第50條明確規定非法證據的幾種類型和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被排除后的非法證據不再具有證據能力。實踐中,通過指供、誘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不如實記錄筆錄的情況時有發生。如蔡某華、劉某義贖賣毒品案。
[案例七]蔡某華販賣毒品案
蔡某華的前2份筆錄均否認犯罪,第3份筆錄顯示其陳述犯罪事實。經查看同步錄音錄像,發現第3份筆錄里的蔡某華沒有陳述任何內容,系偵查人員自行制作筆錄交給犯罪嫌疑人簽字摁印。
[案例八]劉某義販賣毒品案
劉某義曾因販賣毒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存疑不捕,后偵查機關補充了上家指證劉某義受其指使丟包販毒的筆錄,并再次提請逮捕,經查看同步錄音錄像,發現上家的筆錄不屬實,訊問一開始仍是拒絕供述,后經過偵查人員5分鐘的思想教育(故意壓低聲音致同步錄音錄像無法聽清具體內容)而開始供述,表明偵查人員存在指供、誘供的可能。經審查認為,上述證據雖與其他證據能夠印證證明犯罪事實,但系非法證據或無法排除非法取證的可能,不具有證據能力,不能用于證明犯罪事實。
“在毒品案件中,技術偵查作為特殊偵查手段得到廣泛運用,而通過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材料在查明事實上有著獨特優勢。”[3]技術偵查材料被立法肯定具有證據資格,卻常因技偵部門不愿公開泄露偵查秘密或不愿提供技偵審批材料及通話監聽錄音等原始材料而喪失證據能力。如王某強販賣毒品案。
[案例九]王某強販賣毒品案
技偵摘要顯示王某強與販毒上家存在販毒事項交流的行跡,能有效印證王某強是上家販毒馬仔的事實,但公安機關未提供正式的技偵報告,也無其他原始材料,該摘要不具有證據能力,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2.存在合理懷疑
在案證據相互印證,一致指向犯罪事實,證明體系已然成型。若其中關鍵的當事人與證人陳述不符合常理,印證得出的結論可能就是虛假的。如鄧某文販賣毒品案,始終存在假立功的合理懷疑,不予認定鄧某文販賣毒品的犯罪事實。
[案例十]鄧某文販賣毒品案
公安機關認定的事實:2018年5月3日下午,犯罪嫌疑人鄧某文在某亭子里將一包0.37克毒品冰毒以200元的價格販賣給莫某兵,后被當場抓獲。
本案的證據為:(1)舉報人林某成的三次證言,稱其因犯罪被取保候審故積極尋找線索,第一次證言稱線索系其聯系朋友莫某兵獲得;第二次證言稱線索系去朋友黃某衡家玩的時候聽說莫某兵購買毒品;第三次證言稱第一次在黃某衡家玩時,莫某兵在場,并在打電話稱想購買冰毒,第二次去黃某衡家玩時,當場問莫某兵購買毒品事情,得知5月3日莫某兵要在某亭子交易;(2)莫某兵陳述其于5月3日下午向鄧某文購買毒品,后當場被抓獲,稱此前與鄧某文10年沒聯系,案發前1個月碰到面,聽鄧某文說毒品是專門從湖南老家帶過來的,自己買毒品一事沒有跟任何人說過,自己此前沒有吸過毒;(3)黃某衡陳述,其與莫某兵是表兄弟關系,和鄧某文是老鄉,不知道莫某兵說要買毒品,也不知道鄧某文有販毒;(4)鄧某文供認販毒,陳述莫某兵是電話聯系其買冰毒,后在5月3日下午交付200元的毒品時被當場抓獲,毒品是5月2日專門從湖南帶過來的,帶了1個毒品到瑞安賣是臨時起意,打算試試水,這是第一次販賣毒品;(5)稱量筆錄、鑒定意見,證實被查獲的毒品重0.37克,檢出甲基苯丙胺;(6)通話詳單:證實莫某兵與鄧某文5月2日、3日的通話情況顯示林某成與莫某兵及鄧某文沒有聯系。
檢察機關審查認為,在案證據能夠相互印證鄧某文向莫某兵販賣0.37克冰毒事實,但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不符合常理。從本案線索來源和檢舉動機看,檢舉人林某成的線索來源不明,檢舉動機可疑,未能說清楚線索的具體來源;從本案毒品交易環節的細節來看,鄧某文攜帶一包0.37克毒品從湖南于5月2日到達瑞安,5月3日將毒品販賣給莫某兵,犯罪嫌疑人鄧某文為何攜帶如此少量的毒品長途跋涉從湖南到瑞安販毒,不具有經濟性。鄧某文從未販賣過毒品,而購買毒品的莫某兵又從未吸食過毒品,莫某兵解釋此次交易是想要提神,而又稱其知道鄧某文以前有吸毒所以選擇向鄧某文購買毒品,可見莫某兵無法合理解釋為何要購買毒品?為何要向鄧某文購買毒品?莫某兵不具有真實毒品交易的動機。上述疑點表明此次交易不符合一般毒品買賣的習慣,存在為立功造假案的合理懷疑,故不予認定鄧某文的販毒事實。
四、印證證明的證成邏輯
應當明確,印證證明方法不等同于證明標準。證據的法定客觀證明標準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主觀證明標準要求司法者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證據得出的結論具有唯一性。證據認定歸根結底是自由心證的過程,法律又只是對證據的形式進行了分類,沒有對證據的證明力大小作出規定,故每個人不可能有完全一樣的衡量標準,也不存在一個確定的標準能夠合理闡述確實、充分所需達到的具體程度。退而求其次,立法者不再強求確定性的論證結論,轉而面向可靠性結論。印證作為數個同一指向證據的相互作用,對證明結論的高度蓋然性和可靠性,逐漸成為順手的證明方法,并演變成證據確實、充分標準的必要條件。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其中8個條文中印證出現了11次;在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的其中7個條文中印證出現了10次。[4]
印證證明方法讓審查者受益的同時,模式化的印證思維也讓審查者遺忘印證與證明標準的本質差異,從而將印證混同或直接代替證明標準錯誤地定罪。要知道印證始終是司法者為追求證明效率而選擇的快捷工具,而非法律規定的證明標準。故很有必要將審查者拉回到印證證明原有的證成邏輯,以正確地解決證據證明問題。
(一)同向證據的充分印證
1.印證的前提:非同一來源
“印證的核心是證明意蘊的重合增強了可信性,這種可信性來自于兩種(或多種)獨立渠道上各自所獲得的事實信息‘竟然出奇的一致,從不同路徑出發最終殊途同歸于一個結論,恰是印證的魅力所在。”[5]如果證據均來源于同一渠道,則無法驗證證據的真實性,印證可信性就大打折扣,證據間相互的作用力不復存在。實踐中,常見的同一來源證據是傳來證據。假設案例一林某林販賣毒品案,多了一份證人王某某的證言,內容為王某某聽張某福說,張某福在6月1日、6月2日向林某林各購買了一次冰毒,并給了0596尾號的手機號碼(就是林某林的號碼)微信轉賬。在審查過程中,該份證言能夠加強審查者對林某林有尾號為0596手機號碼的重復印象,卻無法對0596尾號手機號碼是林某林使用事實產生進一步的證明作用。又假設王某某另提供了一張林某林的身份證原件,稱是當面交易時林某林不小心丟下的,該物證系王某某直接提供,與張某福的證言來自于同一來源,雖然物證的客觀性較強,但該物證欲證明的客觀事實為張某福交易的販毒分子就是林某林,并非物證客觀記載的內容所能直接證明的,而是依托張某福的證言起到佐證。據此而言,物證的證明力依舊源于張某福的證言,實際未能形成對王某某證言的印證,沒有對張某福的證言起到證偽作用,故無法形成充分的印證。
2.印證的同一性
“在以印證為最基本要求的證明模式中,證明的關鍵是獲得相互支持的其他證據;單一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必須獲得更多具有內含信息同一性的證據來對其進行支持,突出表現為對相同或相似信息的證據數量的重視。”[6]印證的同一性要求證據對某一信息、事實具有共同指向,不要求證據必須是證明相同的內容。印證的相互性是相對“孤證不能定案”而言的,“法院在認定犯罪事實時,必須借助兩個以上具有獨立信息源的證據,使得這些證據包含的事實信息環環相扣,共同指向同一犯罪事實,從而形成較為完整的證明體系或證據鎖鏈。”[7]相互性代表著印證后產出的證明價值大于個體證據之和。
印證指向的同一性把握,是實踐的一大難題。如被告人陳述的內容能夠部分被印證,那么如何采信被告人陳述就存在爭議。案例四丁某強販賣毒品案中,丁某強陳述過向張某鳳販賣毒品一次,張某鳳也陳述過向丁某強購買過一次,只是雙方關于交易的時間、方式、數額存在較大分歧,偵查人員認為在丁某強向張某鳳販賣毒品這一事件上雙方的陳述具有共同指向,能夠互相支持,可以認定。但是,販賣毒品的時間、方式、數額是犯罪行為事實的重要構成要素。雙方陳述無法印證構成要素事實,卻直接得出印證犯罪行為事實的結論,必然無法令人信服。印證的最終目的是要證明犯罪客觀事實和犯罪主觀事實,可并不總有證據能直達這兩大待證事項,有時證據只能證明構成要素事實。犯罪事實清楚,則意味著構成要素事實的明晰。倘若多個構成要素事實都無法形成印證,很難說案件的犯罪事實已經成立。當然,實踐中存在著對個別構成要素事實模糊認定的情形,這也是法律所允許的。刑事訴訟規則就認為陳述的內容主要情節一致,個別情節不一致,不影響定罪的,就認定為犯罪事實已經查清。如時隔久遠,販毒者與購毒者對于販賣毒品的具體日期陳述有所差異,在事實認定時就會模糊表述犯罪時間。
3.印證的效力
并非形成印證,待證事實就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證據圍墻。印證的程度,與證據的證明力與證明內容直接相關,充分印證應當是同向證據在待證事實的細節上能相互吻合。案件中,有些證據可以證明部分事實,與同向證據在該部分事實上就形成佐證;有些證據可以證明全部事實,與同向證據就形成印證。印證和佐證就是印證效力強弱的表現形式。司法實踐中,實物證據往往是形成佐證。“實物證據不同于言詞證據能夠直接陳述事實具象,只能有限的視角內客觀反映分段事實的特征。實物證據更多體現為框架式支撐證明的作用,而真正串聯起各個證據、滿足相互印證需求、實現完整證據鏈的恰恰是言詞證據。語言可以構筑世界,自然也可以完成對犯罪事實的完整敘事。”[8]不過,言詞證據也并不總是印證關系,如案例二林某祥販賣毒品案中,臭豆腐店老板陳述見到林某祥將一包東西隱蔽的交給秦某某,實際是對林某祥交付毒品事實的佐證,還未到印證程度。
(二)矛盾證據的消解
同向證據決定了印證結論具有似真性,似真程度與印證程度成正比。同時,這種似真結論具有可廢止性,一旦出現更具說服力的反駁證據(或稱“矛盾證據”)足以推翻相互印證的先前證據,或者新證據顯示先前相互支持的證據之間印證關系瓦解,印證的階梯就會降級甚至退回零點。實踐中,矛盾證據對印證證成影響甚大,消解矛盾證據是通往真象的唯一道路。梳理相關規定,《解釋》第91條第2款規定“證人當庭作出的證言與其庭前證言矛盾,證人能夠作出合理解釋,并有其他證據印證的,應當采信其庭審證言;不能作出合理解釋,而其庭前證言有其他證據印證的,可以采信其庭前證言。”第96條“被告人庭審中翻供,但不能合理說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辯解與全案證據矛盾,而其庭前供述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存在反復,但庭審中供認,且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以采信其庭審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存在反復,庭審中不供認,且無其他證據與庭前供述印證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上述規定明確了自相矛盾證據的采信標準,然未涉及到不同證據的相互矛盾、沖突的消解、采信。
有學者認為,“證據間矛盾分為根本性矛盾與非根本性矛盾,前者是指影響基本事實認定的重大矛盾;后者是指不影響或基本不影響基本事實認定的非重大矛盾。遇到矛盾證據,需要分析矛盾的性質和類別,把握矛盾產生的原因,再以有效地排除、合理地解釋、充分地證明,以及適當地容忍等方式去排除矛盾。”[9]實踐中,個別偵查人員不能很好掌握矛盾的性質,基于繁忙的工作壓力等原因不愿對矛盾證據展開針對性的取證或認為矛盾通過解釋、容忍等方式即可排除,導致移送的案件證據還存在根本性矛盾。在販毒案件中,當事人的不認罪陳述與有罪指控證據是常見的證據矛盾,該矛盾無法通過合理解釋、適當容忍等方式進行排除,只能通過充分地證明、有效地排除予以解決。如案例一林某林販賣毒品案中,林某林的陳述與證人的陳述就基本事實認定上有著根本性的矛盾,特別是關于0596尾號手機是否為林某林使用的關鍵事實上有著嚴重分歧。這種情形下,就要充分提取、運用其他證據補強事實認定,以推翻矛盾證據,起到求真和證偽的作用。
(三)必要的驗證
1.證據能力的審查
審查判斷證據,證據能力和證明力是兩大要點。其實,證據能力的審查貫穿于犯罪事實認定的全過程,且從證據取得的那一刻就已開始。因此,證據能力的審查應先于證明力。實踐中,會有非法證據被當成合法證據運用的情形,證據間形成虛假的印證,此時就需要審查者深入分析證據,發現非法證據的蛛絲馬跡,精準審查證據能力。如案例七蔡某華販賣毒品案中,蔡某華此前2份筆錄都否認犯罪,而在第3份筆錄中突然供述犯罪事實,在審查逮捕階段又翻供,并提出了公安人員未如實記錄筆錄的情形,對于當事人提供的明確線索就要及時核查。又如案例八劉某義販賣毒品案,劉某義曾因販賣毒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存疑不捕,劉某義的上家此前均不供述,卻在劉某義不捕后突然指控,且在審查逮捕階段仍保持認罪筆錄的說法。盡管,當事人受利益權衡、偵查技巧、法律政策教育等影響,陳述經常會不穩定或認罪態度有反復,但必須重視其翻供、認罪的原因,從常理和經驗法則審查是否合理。
2.合理懷疑的驗證
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明標準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同時,還要足以排除合理懷疑,結論具有唯一性。在利用間接證據定罪時,還要求運用證據進行的推理符合邏輯和經驗。“因為證據印證,重在證據的外部性,而非證據的內省性。所謂內省,即求諸內心,看是否真誠的確信,或在自己的認識中是否已經排除合理懷疑。”[10]結論的唯一性和推理符合邏輯、經驗都表明證據間不存在其他結論的合理懷疑,是審查者已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就這點而言,驗證的本質還是在于檢驗合理懷疑是否存在。
合理懷疑的說法源于西方,它要求懷疑是建立在一定事實和證據基礎上的,這樣才具有合理性,而非審查者內心模糊的猜想,大概的懷疑。“在實踐中,最便利有效的方法,是訴諸經驗與常識,即依靠‘常識、常理、常情對合理懷疑產生證據判斷。”[11]如案例十鄧某文販賣毒品案,認定鄧某文販賣毒品的多個證據得到充分印證,亦沒有矛盾證據,若沒有認真的進行合理懷疑的內省驗證,是很難發現案件問題的。當然,這種藏于案件背后的隱性合理懷疑,十分考驗審查者的司法經驗和直覺。通過對鄧某文販毒動機、交易習慣、舉報線索來源等案件細節的探究,發現證據所印證的結論禁不起常理和常情的推敲,鄧某文與他人串通假立功的懷疑在審查者內心不斷強化,在案的證據始終無法將其排除。
(四)印證與主觀推定的關系
實踐中,證明犯罪客觀事實的證據相較于主觀事實的證據易于取得。販毒人員作為案發時主觀方面最有發言權的主體,為了逃避法律追究,往往不會交代或否認主觀明知是毒品以及辯解沒有販賣毒品的故意,導致司法證明的困難。為了不放縱犯罪,充分發揮刑法風險把控的作用,“決策者開始在刑事立法與司法中使用推定。很顯然,推定絕不只是單純的與證明相關的技術性問題,事實上,通過降低控方的證明負擔或改變需要證明的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推定具有使控方的指控與定罪變得容易的功能。”[12]在毒品案件中,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規定,判斷被告人對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僅憑被告人供述,而應當依據被告人實施毒品犯罪行為的過程、方式、毒品被查獲時的情形等依據,結合被告人的年齡、閱歷、智力等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判斷,并列舉了十種情形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釋的,可以認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證據證明確屬被蒙騙的除外。
在當事人供認主觀明知的場合,印證還是發揮著和證明客觀事實同樣的補強作用。而在當事人否認的場合,推定成了證明主觀事實的有力工具,印證的重心開始往證明推定成立的基礎客觀事實轉移。如案例三劉某芬販賣毒品案中,劉某芬有送毒品的客觀行為,一直否認主觀明知是毒品,故只能由客觀事實推定劉某芬的主觀。結合《紀要》里的規定,在案證據無法印證劉某芬具有推定明知的十種情形之一,故無法認定其主觀明知。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檢察院[325200]
[1] 龍宗智:《刑事印證證明新探》,《法學研究》2017年第2期。
[2] 參見黨建軍、楊立新:《死刑案件適用補強證據規則若干理論問題研究》,《政法論壇》2012年第5期。
[3] 薛振、李志恒:《技偵材料在毒品案件審理中的使用》,《人民司法(應用)》2018年第28期。
[4] 參見周洪波:《中國刑事印證理論批判》,《法學研究》2015年第6期。
[5] 栗崢:《印證的證明原理與理論塑造》,《中國法學》2019年第1期。
[6] 龍宗智:《印證與自由心證——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模式》,《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
[7] 陳瑞華:《刑事證據法的理論問題》,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頁。
[8] 同前注[5]。
[9] 龍宗智:《試論證據矛盾及矛盾分析法》,《中國法學》2007年第4期。
[10] 龍宗智:《中國法語境中的“排除合理懷疑”》,《中外法學》2012年第6期。
[11] 同前注[10]。
[12] 勞東燕:《認真對待刑事推定》,《法學研究》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