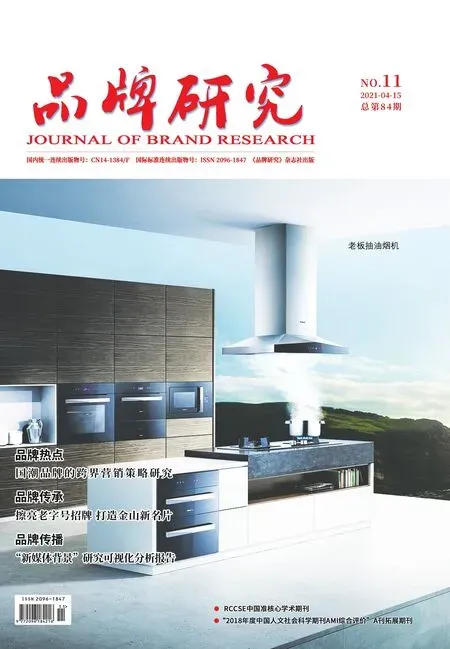社會風險視角下農村家庭的抗風險能力影響分析
——以云南省G村為例
文/劉琳(蘭州大學)
一、提出問題
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漢爆發后蔓延至其他省份,舉國上下為抗擊疫情,避免人口大規模流動與聚集,采取居家隔離、延長春節假期、封閉式管理、停產停工等一系列防控措施,不僅給城鄉居民的生活帶來巨大影響,更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較大的短期負面沖擊。數據顯示,2020年1~2月份,我國工業生產增加值同比下降13.5%;全國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下降1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5%;但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5.3%,食品煙酒價格同比上漲15.6%,其中豬肉價格上漲125.6%。這期間,疫情防控加大了物資運輸成本,導致食品價格上漲,大大增加人們的生活成本,加劇了城鄉居民的生活負擔。雖然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不同程度地波及農村,但相比之下,農村農業生產基本穩定,全國冬小麥播種面積3.31億畝,春耕備耕全面展開,受這次社會風險的影響較小。本文研究發現,城鄉在面對此次社會風險時展現出的較大差異,主要因素在于農村居民擁有土地,土地生產的相對穩定性使農民在面臨社會風險時,仍然可以依靠農作物度過短期風險。
自農耕社會至前工業時代,農地經營始終是農民謀生的主要方式,農民可以在自有土地或租借的土地上進行農業生產,由此獲得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當前對于農地保障功能的研究主要有三個方面:“功能替代論”“安全論”及“弱化論”。
“功能替代論”方面的研究認為,土地的保障功能替代對農戶轉出農地的意愿有一定影響。首先,勞動承載力功能替代程度及農地價值功能替代程度與農民轉出土地的意愿成正比(萬亞勝等,2017)。農地就業保障功能在個人和家庭兩個層面替代程度越高的農民,轉出農地的意愿越高,以新農保為代表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對農地養老保障功能的替代程度越高,農民轉出農地的意愿越高(聶建亮等,2015;唐焱等,2015)。其次,農地的社會保障功能使農村土地流轉與規模經營難以實現(何宏蓮等,2011)。土地是農民生活的基本保障,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有效替換農村土地對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閆文,2013)。
“安全論”方面的研究認為,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一時難以建立的條件下,農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功能實際上是由土地來承擔的,即所謂土地保障(李郁芳,2001)。土地保障是農民最后的一道生命安全保障,是農村家庭保障的核心(梁鴻,2000),土地作為就業崗位的功能已經十分微弱;而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則十分突出(徐琴,2003;鐘漲寶,2008;呂軍書等,2011;徐琴,2003;姚俊,2009),在土地各個功能中,其基本生活保障效用的平均值最大(王克強,2005)。耕地在農戶心目中所發揮的主要作用不是經濟功能,而是社會保障功能(陳美球等,2008)。社會保障功能是耕地資源社會功能的主體,其中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又是耕地社會保障功能的主體(孔祥斌等,2008)。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不完善強化了土地的保障功能(王銀梅,2009),欠發達地區農民偏好于土地的生產功能、保障功能,以家庭保障為主,保障水平較低,而發達地區則相反(徐美銀,2014)。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土地保障功能持續弱化。但是目前我國農村還不具備建立全面社會保障的現實基礎,農民社會保障還不能完全脫離土地保障,土地保障仍然是中國轉型期發展和穩定的需要(李南潔,2008)。
當然,也有學者關注到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在弱化。土地保障功能“弱化論”的學者認為,土地對農戶所承擔的福利保障功能已經大大下降,土地不再像歷史上任何時期那樣是農民的“命根子”(羅必良,2013)。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農戶從糧食市場獲得糧食的比例較大,參加非農就業的機會較多,農戶對耕地社會保障功能的依賴程度較低、被替代程度較大(張雪靚等,2013)。土地保障雖然仍是我國現階段農村社會保障的主體,但農地經營權的讓渡、我國農村人多地少及土地比較收益逐漸下降等原因,導致農地的生存保障功能不斷弱化(鄒寶玲等,2019;黎翠梅,2007;樊小鋼,2003)。同時,以土地作為農村人口生活保障的載體,也阻滯了農村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進程(樊小鋼,2003)。
上述三方面的研究雖然側重各異,但都基于農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可以看出,學術界對土地保障功能的研究已經很多,其中只有閆文指出土地在我國將長期承擔著由于政策性風險、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給農民帶來的生活水平的下降的保障責任(閆文,2013)。總體來說,對于土地保障功能的研究尚未從防范社會風險這一角度對農地保障功能進行研究。基于這一背景,本文以云南省G村為例,探討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社會風險時,土地的保障功能如何發揮作用,及其如何影響農村的抗風險能力。
二、當代鄉村社會下的土地功能
1978年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農民實際上占有土地的完整使用權和收益權,土地不僅承載著作為農民生產資料的功能,還承載著作為農民社會保障的功能。土地的保障功能,是指農戶以土地收獲物供給其基本生活資料或者以土地收入作為維持最低生活水平和抵御社會風險的主要手段。新冠肺炎疫情使社會經濟受到嚴重沖擊,農村家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土地的生產功能及集體互惠功能作為支持農村家庭防范社會風險的后盾,發揮了主要作用。
(一)土地的生產功能
土地是人類安身立命之本,是一切生產和生存的基礎,不僅給農民帶來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資,也承擔著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基本職能。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更多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從而形成當前占絕對主導地位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造成不同階層的農村家庭對農地生產功能的依賴性也不同(賀雪峰,2018)。
現有農村家庭的普遍情況有兩種:第一種是亦工亦農,主要有“代際分工”和“男女分工”兩種(趙曉峰,2012),分別為青壯年進城打工,中老年人從事農地生產經營;或者女主人在家從事農業生產、照顧父母及撫養孩子,男主人進城打工。這種農民家庭的收入有務工收入和農作收入,其中務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對農地生產功能的訴求以維持家庭糧食供給、維系基本開支為主。由于非農產業收入是波動的、不穩定的,多種因素致使農民的非農收入只能是暫時性收入,對于這類農村家庭來說,土地仍然是家庭必需的生產資料,通過土地經營一定數量的較為穩定的收入,作為家庭收入的底線。第二種是普通的農業經營者,這種農民家庭基本沒有非農收入來源,可供其生產經營的土地有限。農戶主要從事生產經營種植,但土地主要局限于自家承包地,部分農戶也通過土地流轉等形式耕種著其他農戶的少量土地,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力從事日常經營管理活動。這種家庭的收入幾乎全部來自土地經營收入,對土地的生產功能依賴性較強。
(二)集體互惠功能
農村社區的熟人關系網絡資本能夠將農地的其他功能轉換為互助性的社區保障。基于血緣與地緣雙重構建的自然村落及宗族,因天然信任與地緣認同形成的集體行動與合作互惠,成為個人力量不足以對抗天災人禍時候的重要補充。農村的熟人社會性質促使農民在同一村落中形成認同感、歸屬感,并不斷強化這一功能。即使傳統社會關系網絡不斷解構,農地的集體互惠功能呈現減弱趨勢,但當較大的社會風險來臨時,這一功能也顯得尤為重要。
盡管土地對于亦工亦農及普通農民的家庭來說都是生產功能,但其發揮的效用不一樣。熟人社會的網絡使得農村家庭土地經營生產出來的農作物在村莊中作為禮物相互流動,在新冠肺炎期間成為農村家庭防范風險的一個重要因素。需要強調的是,土地的生產功能與互惠功能二者是同時發揮效用的,其中互惠功能建立在土地的生產功能基礎上,只有農戶進行土地生產,才有農產品作為禮物相互流動。總而言之,只有土地生產滿足了亦工亦農的家庭的基本供給,及普通農戶家庭的預期收入,土地的互惠功能才能進行。
因此,形成了本文的分析框架。此外,賀雪峰指出,從全國普遍情況看,“亦工亦農”模式的家庭占比為70%,普通農戶占比為10%,全家進城的農戶占比約為20%,這類農戶已經完全脫離土地,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不僅如此,大規模種植農戶在本文的田野點只有一戶,且根據賀雪峰的研究,這類農戶在全國占比較小,因此本文也不做討論。
三、疫情下的土地功能對家庭的影響
本文田野點G村位于云南滇中地區,壩區、臨山,屬于自然村,共95戶。G村的耕地以壩區平底為主,其耕地面積240,000平方米。G村臨山,山里有私人企業開的采石場、水泥廠,這兩個企業為村民提供了就業機會。此外,距離鎮政府及縣城各5公里。因此,在G村88%的農戶都為“亦工亦農”家庭,這些家庭的男主人在采石場或其他地方打工,而女主人則照顧自家的地。對于這種“亦工亦農”家庭來說,家庭收入主要依靠男主人,而女主人耕種的作物則支持家庭基本生活,如大米、菜籽油等,都用于自家。此外,“亦工亦農”家庭還有夫妻都在打工,老人種植耕地的模式。在面對疫情期間停產停工及由于防控疫情造成的物價上漲,G村村民家庭能夠依靠自耕地的生產經營度過暫時的短期經濟危機。
(一)家庭基本供給:戰時防范狀態下的重要支撐
風險社會中的風險具有不可感知性、不可計算性、不可控性、不可逆性及全球性。而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和個體化極大地加重了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風險性。在新的時空環境下,時間的易逝性和空間的可變性極大地增強了社會的流動性,由于流動性使疫情暴發風險的規模和范圍發生了重大變化,使得原來局部的、地方性的風險越來越擴散成為一種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風險與危機(文軍,2020),從而導致鄉村內外道路封閉,基層實行閉環式管理嚴禁人員外出。面對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加大道路管控,從而增加物流運輸成本,并帶來生活物價上漲的情況時,土地生產經營的農作物成為村莊社會風險戰時防范下的重要支撐,土地生長的蔬菜能夠支持農村家庭度過這種短期的經濟社會風險,免遭物價上漲之災。
與傳統村莊一樣,G村一直處于原子化、碎片化的分散農業生產經營狀態,每個農戶家庭都擁有自耕地,對于“亦工亦農”家庭來說,女主人或者老人在照看家的同時自己經營少許耕地,種植農作物隨季節變化而變化,但農作物基本用于維持家庭生活,不對外出售;而對于普通農戶來說,自家便是種植蔬菜,更不會缺乏蔬菜食用。“新冠”來臨時,大米等谷物在G村農戶家里均有屯糧。首先,G村的“亦工亦農”家庭表現為女主人在家進行土地經營生產,維持家庭基本生活以及年輕夫妻在外打工,父母在家種植土地。由于家庭平時有人照看,G村的“亦工亦農”家庭均有養殖少許禽畜供家庭內部實用,此外,土地中日常蔬菜均成熟可正常食用。
風險社會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狀態,它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并讓我們意識到風險無處不在,而且,風險的形式多到使我們無法預計(張康之,2020)。在短期的沖擊較大的短期社會風險面前,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并不能及時發揮作用。而對于農村家庭來說,使他們心里“有底”的,是自家土地里有暫時充足的能夠維持家庭生活的食物供給,并且即使不夠,也能通過播種的形式補充家庭供給。由此可見,在面對短期的社會風險時,土地的生產經營功能可以轉變為保障功能,維持農村家庭的生活。
(二)家庭收入:社會風險下基本正常的農業生產
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提高了農業生產力,農民可以用自己多余的糧食換取其他的生產生活資料,這是封建社會以來土地生產實現農民生存以外的更多經濟功能的突破,也充分體現了土地對于農村家庭的保障功能。“新冠”肺炎疫情給餐飲業、旅游業等服務業帶來了較大沖擊,并影響著這些行業的每個家庭的經濟收入。與此相比,土地生產的穩定性則大大減輕了農村普通農戶所遭受的經濟風險。貝克認為,當危險伴隨著政治無為而增長的時候,風險社會就包含著一種固有的成為替罪羊社會(scapegoat society)的傾向:突然間不是危險,而是那些指出危險的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這種來自健康、經濟的不安全感深刻影響著風險社會中的每個人,而對于農村家庭來說,這種不安全感則要少很多。
G村的普通農戶正常從事農業經營活動,而由于疫情影響帶來物價上漲,蔬菜的收購一直在正常進行,并沒有受到較大影響。李家、劉家等在G村是全家從事農業經營活動的農戶,主要種植西葫蘆、茄子、白菜、西紅柿等。其中,李家自己搭建了大棚,棚內種植西葫蘆和西紅柿,正值成熟時期;劉家規模稍大,種植應季蔬菜,如茄子、白菜等,在蔬菜成熟時也請村里人幫忙收摘。其中李家的蔬菜一直送到私營老板那,于是每天采摘回來便送過去,未受疫情影響,而劉家的蔬菜則售賣到縣城,由于距離縣城較近,同樣未受影響。
與城市相比,鄉村人口密度底,人員流動性小,在面對突如其來的社會風險時,受到的沖擊更小,這一因素使農村家庭在面對社會風險時仍然可以從事勞動。貝爾指出,與財富一樣,風險是附著在階級模式上的,只不過以顛倒的方式:財富在上層聚集,而風險在下層聚集。然而對于這種短期壓縮式的社會風險來說,農村獨具優勢的地理位置能夠延緩這種社會風險的沖擊性,促使農業生產在一定程度上是穩定的,因而土地的經濟功能與保障功能都是發揮作用的。
(三)互惠功能:熟人社會下的集體防范風險
中國社會結構中尤以農村地區最為顯著,實行的是特殊的家族制度,并以家為社會“核心”構成一個“緊密的團體”,而社會價值系統都是由傳遞給個人,即使如今血緣關系已經不再是個人社會關系的關系,但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熟人社會”在中國鄉村仍然存在,并形成以“己”為中心的“差序格局”社會環境下的關系取向,進一步促使熟人社會中信任、互惠的“差序格局”(趙泉民等,2007)。在這樣的村落結構下,村民之間的互惠隨著村莊的封閉性而強化,并具有排他性、組織性與規范性特征,熟人之間的互惠合作成為在面對社會風險時的重要力量補充(鄒寶玲等,2019)。相對于危險,風險的不確定性更強,盡管科學手段能夠對風險進行評估,但人類認識能力的本質缺陷以及風險的客觀特性,使得風險仍然是不確定的(黃新華,2016)。風險呈現出一種蠶食關系。它們使實質上和時空上不能相提并論的東西建立了一種直接的和危險的關聯。因此,風險社會里,人們比以往都更加團結為一體,而具有深遠互惠合作文化的鄉村則在應對某些社會風險時更具優勢。G村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互惠在面對此次經濟社會風險時便表現得尤為重要。
閻云翔指出,關系緊密的鄉村中,在許多情況下,私人網絡比物質或金錢更珍貴,食物作為村民之間的禮物不僅是關系網絡的體現,也是社會援助體系。這一體系使個人在遭遇諸如食物和避難處等基本需求的非常情況時,道德義務連同先前的社會交換所造成的人情債務,創造了一種高度可靠的緊急援助機制(閻云翔,2000年)。由于G村的村民平時均種植家庭食用的蔬菜,加上李家和劉家為蔬菜種植戶,其他農戶可低價從這兩家農戶中購買蔬菜,也有相互贈送者。而對于熟人社會的鄉村來說,互惠合作是一件平常的事情,這種更多來自物質上的支持在鄉村面臨社會風險時能夠成為抵抗社會風險的重要力量。
四、總結
貝克與吉登斯都認為風險是無處不在的,風險的不被感知性、難以預計性使人們無時無刻不在面對風險。此外,風險的威脅是全球性(人類、動物和植物)以及它們的現代性起因,是現代化的風險,是工業化的一種大規模產品,而且系統地隨著它的全球化而加劇。人類社會存在于自然結束之后,自然的結束并不是指物質世界或物理過程不再存在,而是指人類周圍的物質環境沒有什么方面不受人類干擾的某種方式的影響。過去曾經是自然的許多東西,現在都不再完全是自然的了。被制造出來的風險并不止涉及自然——過去所涉及的多是自然,如婚姻家庭的變革為人們帶來各種機會與風險。當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擴展時,風險也變得危險重重,如在將來的某個時候,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威脅健康的潛在的災難。
在面對“新冠”疫情這樣突如其來的社會風險時,在經濟方面,由于農村擁有土地,當農民缺乏充足的財富積累及足夠的非農就業機會和非農收入時,依靠土地生產經營能夠獲取糧食供給維持家庭基本生活。在這一過程中,對于“亦工亦農”家庭來說,土地在留家“照顧”的家庭成員經營下,生產出的大米、蔬菜能夠支持家庭應對突如其來的社會風險;對于普通農戶來說,全部家庭成員都從事土地種植,由于農村土地面積廣闊,在面對這樣的社會風險下,他們的生產、生活計劃受到的影響較小。此外,農村熟人社會的性質所構成的以“已”為中心互惠的結構圈層也在強有力地支持著農村家庭對抗社會的風險。如上文所言,由于種植的蔬菜較少,隔壁的嬸嬸便將自家蔬菜送到門口。實際上,這種互惠互利的合作在農村較為常見,但是當面對重大社會風險時,土地的互惠功能便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在面對社會風險時,農村的土地發揮著重要的保障功能,并且在特殊時期,土地的生產功能可以轉變為保障功能及集體互惠功能,維持農村家庭的生活。
注釋
①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index_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