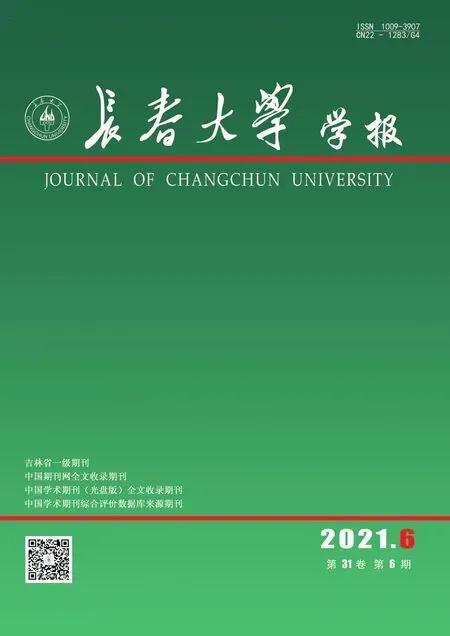高等院校美育改革與外國文學課堂對接相關問題及對策研究
符 曉
(長春理工大學 文學院,長春 130022)
2019年,教育部印發《關于切實加強新時代高等學校美育工作的意見》,指出要“推進美育教學改革與創新”,并強調要“提升高校美育科學研究水平,打造一批美育綜合研究的高地和決策咨詢的重地,建設一批美育高端智庫,重點研究高校美育的課程和教材體系、教學規律和模式、考核評價標準、教師隊伍建設等,深入研究中華美育精神。”;可見國家對高校美育改革問題的重視。美育改革和其他教學改革最重要的區別在于,美育本身的內涵決定“推進美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內外兼修、美善統一的完美人格,而不是學習藝術、欣賞藝術或體驗藝術情境。”[1]所以改革的目標更強調形而上層面的“樹人”,而不是單純的“技藝”。將高校美育改革落到實處的方法之一是在非美學課上介入美育的功能和方法,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力圖使學生得到美的教育和熏陶。基于此,筆者選取外國文學課堂介入美育教學這一問題為研究對象,通過統計學考查的方式嘗試厘清當下外國文學課堂美育教學的問題與缺失,并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進策略,以推動高等院校美育改革和外國文學課程改革。
1 對外國文學課堂介入美育教學情況的統計學考查
為了考查高等院校外國文學課堂介入美育教學的情況,筆者對吉林省某高校文學院已經修習過外國文學(史)課程的學生進行了抽樣調查。調查的方式是選擇式調查問卷,即“從多種答案中挑選最適宜的一個或幾個答案,然后作上記號”[2],利用問卷網統計,總瀏覽量170次,回收問卷165份,其中有效問卷165份,可以作為研究的基礎指標。調查問卷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調查學生對美育的熟悉和理解程度,二是調查學生對外國文學課堂介入美育教學的認識和理解。
問卷的第一部分涉及學生對美育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共6個問題。對于“您了解美育嗎”,選擇“非常了解”的占0.61%,選擇“了解”的占22.42%,選擇“不了解”的占24.85%,選擇“一知半解”的占52.12%,說明大部分學生對美育并不是很了解。對于“您覺得在高等院校范圍內美育已經普及了嗎”,認為“已經普及”者占4.24%,認為“尚未普及”者占29.70%,認為“在普及的過程中”者占61.82%,認為“完全未普及”者占4.24%,從中可見,美育在高等院校的普及尚需一個時間階段。對于“您了解美育的方式是什么”,67.88%的學生選擇“美學老師上課所講”,27.88%的學生選擇“平時的課內外閱讀”,2.42%的學生選擇“相關文件政策的學習”,1.82%的學生選擇“其他”(填寫的都是“不了解”),這反映出學生獲取美育知識和思想的途徑事實上是很單一的,學校美育教學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對于“您覺得美育的基本內涵是什么”(多選),61位學生選擇“藝術教育”,107位學生選擇“關于美的教育”,118位學生選擇“是人的全面發展的部分”,1位學生選擇“其他”(填寫的是“以上都”),可見,學生對美育內涵的理解不盡相同。對于“您讀過他們關于美育的著作嗎”(多選),選擇“席勒”69人,選擇“蔡元培”80人,選擇“曾繁仁”18人,選擇“其他”28人,其中大部分填寫的是朱光潛和李澤厚,由此可見,實際上了解作為新時期美育領軍人物的曾繁仁并不被大多數學生所了解。
問卷的第二部分涉及學生對外國文學課堂介入美育教學的認識和理解,共6個問題。對于“您讀過多少部外國文學作品”,選擇“10部以下”的占36.97%,選擇“10~30部”的占40.00%,選擇“30~50部”的占15.76%,選擇“50部以上”的占7.27%,大部分學生閱讀了至多30部外國文學作品。對于“您覺得外國文學學習的精髓是什么”(多選),選擇“了解世界文化與文學思潮”的149人,選擇“文學作品的文學性”的115人,選擇“作為中國文學的有效補充”的91人,選擇“文學的教育意義與教化功能”的106人,學生對這一問題答案的選擇比較平均,但能夠看出學生比較重視“文學的教育意義與教化功能”。
2 外國文學課堂美育教學的問題及缺失
無論是從上述調查問卷還是從日常的外國文學課堂教學中都可以發現外國文學課堂教學美育教學的缺失問題,這既存在美育自身受重視程度不夠和普及性差的原因,也存在學科之間邊界壁壘的問題,同時又不得不考慮到美育教學無法滿足外國文學課堂課程計劃和課程設計的原因。結合調查問卷和目前的外國文學課堂教學,外國文學課堂美育教學的問題及缺失大致如下。
首先,是學生對于美育的把握普遍存在不準確、不全面、不深刻的現象。從調查問卷就可以反映出一系列問題:一是學生雖然已經學習過美學課程或美學概論課程,但是對美育的了解并不是十分深入,很多學生對這個概念和概念所衍生出來的意義一知半解,或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其中既有學生“學”的問題,實際上也存在著老師“教”的問題。二是高等院校的美育教學尚未普及,無論是從調查問卷分析還是從當前美育普及的程度上看,美育在基層院校的普及工作剛剛展開,但由于沒有統一地配套落實美育措施,又容易將美育和藝術教育混用,導致美育的落實和普及工作并不理想。三是學生的美育理論來源過于單一,絕大部分來自老師上課所講,而少有通過閱讀習得,只有約2.5%的學生涉獵過與美育相關的政策和文件,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美育文件的普及性和傳播性及其產生的影響尚有限。四是對美育相關文獻的閱讀停留在教材介紹階段,學生雖然對席勒、蔡元培、朱光潛等傳統美學家的美育思想有所涉獵,但對如曾繁仁這種當下活躍在美育建設一線并為美育的實施和落實建言獻策起到領軍作用的美學家不太熟悉,更談不上深入閱讀,這也反映出了學生對美育的動態變化過程把握不足。這樣一來,美育教學存在的問題就與當下高等院校美育改革尤其是美育與外國文學課堂的對接存在著某種悖論,美育改革的中心目的和立足點在于使學生了解、理解美育并在此基礎上提升人格而全面發展,所以只有解決好上述問題,美育改革才能行之有效。
其次,是在外國文學課堂介入美育教學的缺失。據調查問卷反映,已經修習過外國文學課程的學生多數閱讀過外國文學作品,具有一定的外國文學素養積淀,他們也比較重視外國文學的教育與教化意義,但對于外國文學任課教師是否在課上介入美育教學,仍有學生選擇“記不清”(35.76%)或“不強調”(11.52%),這說明現在的外國文學課堂教學在介入美育教學方面還是存在著一些缺失的。表現之一是學科之間的壁壘本身沒有被打破,外國文學和美育之間存在著一些交集,但出于現代教學的需要,學科門類精細化使得這種交集呈現出隱性狀態而不是顯性狀態,比如莎士比亞、席勒、盧梭、雨果、波德萊爾等人作品中顯在的美學和美育精神因為其文學地位的重要性而被學科疆界遮蔽,換句話說,他們的美育思想并沒有在外國文學教學環節體現出來。表現之二是外國文學課堂任課教師對介入美育教學尚缺乏認識,在課堂上只強調作為知識的外國文學而忽略作為精神的美育教學,只強調授課的“技”而忽略了“道”,只強調作為文學家的席勒等人而忽略了他們作為美學家的身份。這兩方面的表現表明,目前的外國文學課堂教學并沒有開始重視課堂內部涉獵美育思想的問題。
再次,在目前外國文學教學的過程中太過重視外國文學的知識目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外國文學是應該重視知識目標的,因為當時受眾接觸外國文學的機會有限,外國文學課堂起到了知識講授和傳播的作用,并且具有普遍性。如今,信息爆炸,學生得到知識的途徑可謂多種多樣,所以在教學過程中太過強調知識目標意義不大。遺憾的是,這個問題普遍存在。表現在教學中,目前的教學過于強調學生對基礎知識準確性的把握,但實際上這種準確性已經與注重培養學生方法論和發散性思維的教學目標存在某種間接的沖突。在進行這種基礎知識準確性考查的同時,勢必忽略了對知識所引起的思維增量的考查。可見,無論是在教學還是在考試的過程中,知識目標都處于中心位置,這既會影響到外國文學課堂的教學效果,又和美育的中心目標有所偏離,亟待進行教學改革。
3 開展外國文學課堂美育教學的對策
基于外國文學課堂與美育教學對接過程存在的問題,如何彌補上述缺失就成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只有不斷地在外國文學教學過程中重視美育改革并展開實踐,只有在新的外國文學教學過程中揚棄一些陳舊的教學方式并努力嘗試探索新范式,才能不斷推動外國文學教學改革,才能不斷推動美學教育落到實處。具體言之,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開展外國文學課堂美育教學。
(1)在教學的過程中加強對美育及其周邊概念和思想的普及。如果學生不理解美育甚至不了解美育,那么外國文學課堂無論如何調動學生關于美育的積極性或興趣點,都是徒勞的,所以需要學生全面掌握美育相關知識和基本內涵,調查問卷顯示,這種思路是必要的。首先,在外國文學課堂內外組織學生漸漸形成美育知識習得的習慣,學生通過美學課程的學習、日常課外閱讀和學習相關政策文件已經對美育有一定的了解,這時需要通過推薦閱讀書目、推送公眾號相關文章、組織業余小組討論等形式強化這種了解。其次,在外國文學課堂也要有計劃地、有針對性地對美育常識進行再講述、再強調,只有不間斷地甚至壓迫式地向學生進行灌輸,“美育”才能深深嵌入到學生的內心世界,因此這種在外國文學教學中穿插美育的教學方式對美育改革和外國文學教學具有雙重意義。再次,在教學過程中要以動態的眼光和視角認識美育并培養學生具有這種態度,只有理解好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美學思想和政策,才能更好地使學生理解美育的動態內涵。
(2)在外國文學課堂加強對外國文學與美育教學通約性的講述與強調。這種通約性首先表現在,講述或分析文學作品文學性的同時,從更深的維度分析其中涵蓋的教育意義尤其是美育意義。在外國文學史中,有一部分小說的創作初衷就基于教育的功能,以至于在文學史上將之稱為是“教育小說”,如《威廉·邁斯特的漫游年代》(歌德)、《借方與貸方》(古斯塔夫·弗雷塔克)和《大衛·科波菲爾》(狄更斯)等,盧梭的《愛彌兒》甚至在教育史上掀起來“哥白尼式的革命”,這既說明文學本身的教育意義,也說明外國文學與美育教學的通約性。另有一部分小說的創作教育或美育動機似無那么明顯,但是卻具有相當深遠的教育學和美學教育意義,如在中世紀末期和文藝復興早期人文主義作品提倡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在人是全面發展的意義上也具有某種美育的功能。同時,在外國文學史講述的過程中也需要旁及美育知識。雖然美學和美育相對于漫長的西方思想史而言都是比較晚近的概念,但自古希臘以來文學作品中無不浸潤著美育思想,亞里士多德所謂悲劇的“凈化”功能、莎士比亞戲劇中對“人”的關照、盧梭和伏爾泰等人關于“人”的啟蒙都在人類進步的意義上作出了規范和度量,其中更有如席勒本身就是美育概念的倡導者,所以在講述外國文學時適當滲透美育的知識和思想,既是可能的,又是有益的。實際上,以上兩點原則的中心意旨都在于尋找出外國文學和美育思想之間的通約性,建立兩種看似不相關的學科邊界之聯系,在解構學科壁壘的同時使學生發現二者之間的自洽性甚至互文性。
(3)在外國文學課堂有計劃地從知識目標向修養目標過渡。隨著信息化和智能時代的到來,包括外國文學在內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漸漸呈現出一種“祛魅”的趨勢,學生的知識增量及其來源變得多元化,作為知識或者作為“技”的外國文學傳統教學也逐漸變得捉襟見肘,從另一個角度推動一線教師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教師上課所講述的具有知識性的內容既超越不了新興檢索引擎的廣度又滿足不了學生對知識寬度的渴求,這樣一來,知識目標在教學中就存在著一些問題甚至弊端,而修養目標變得重要起來。實際上,修養目標也是美育的重要核心之一,席勒曾指出,“近代人要做的,就是通過更高的藝術即審美教育來恢復他們天性中的這種完整性。”[3]言說的就是人的精神和修養等相關問題,也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問題。這樣一來,外國文學課堂所重新建構的目標恰恰和美育的終極目標相同,所以在教學的過程中,要更多地關注修養目標的教學途徑而從知識目標的傳統方法當中解放出來。
在談及新時期“金課”建設時,有學者指出,要“全面優化課程質量,全面梳理課程教學內容,合理增加課程難度,拓展課程深度,打造具有高階性、創新性與挑戰度的‘金課’”,[4]實際上,所謂“高階性、創新性與挑戰度”也是對外國文學課堂與美育改革對接的要求,只有二者有機結合為一個整體,才能產生最好的“金課”效果。早在1980年代,第一次全國美學會議就將美育作為美學發展的重要方面加以強調,在那之后,“美育思想和美育制度可以稱為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催化劑,但是實踐中美育制度的落實情況并不像人們最初設想的那樣順利。”[5]因此,落實美育制度和美育政策就成為現實中非常重要的問題,尤其是對于高等院校文學教學而言,如此一來,對高等院校美育改革與外國文學課堂對接等問題的研究就具有很強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也存在著更豐富的闡釋和實踐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