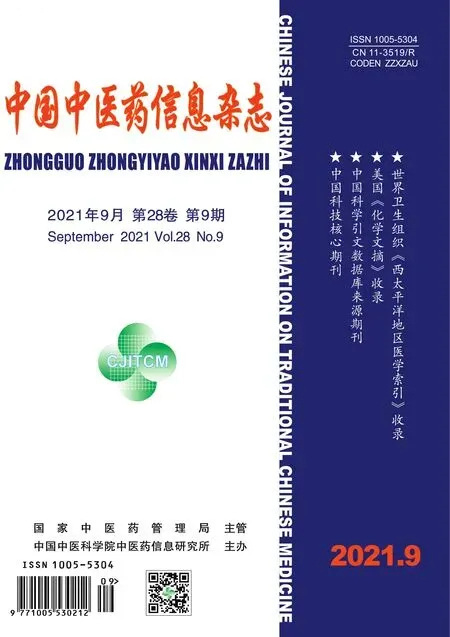國醫大師劉志明“表里雙解治溫病”理論與實踐
姚舜宇,劉金鳳,汪艷麗,郭艷瓊,常興,劉如秀,指導:劉志明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北京 100053
國醫大師劉志明出身于中醫世家,從事中醫工作80 余年,自1954 年參加中國中醫研究院(今中國中醫科學院)建院籌備工作并負責“傳染病組”的創立和建設,曾多次主導或參與流行性乙型腦炎、病毒性肺炎、麻疹、血吸蟲病等傳染病的中醫防治工作,均 取得良好成效[1-3]。2019 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劉老心系桑梓,雖已96 歲高齡,仍參與遠程會診,為重癥和危重癥患者診治,最終全部治愈出院,且回訪無一復發[4]。在多年防治傳染病實踐中,劉老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并形成獨特見解,提出“表里雙解治溫病”的觀點。茲結合案例闡述如下。
1 理論溯源
《內經》明確提出“表里”一詞,奠定了表里辨證的理論基礎[5-6]。一方面劃分人體為表里兩部分,提出一些診斷、治療的基本方法,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以表知里”,《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篇》“發表不遠熱,攻里不遠寒”;另一方面,用表里區分臟腑、經絡屬性,如《靈樞?官能》“用針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里”,《素問?血氣形志篇》“足,太陽與少陰為表里,少陽與厥陰為表里,陽明與太陰為表里,是為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為表里,少陽與心主為表里,陽明與太陰為表里,是為手之陰陽也”。總體而言,《內經》對表里辨證的闡釋,長于理論與針灸,略于方藥。其后,張仲景結合大量實踐,對表里辨證作出許多補充和提升。《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不少條文從“表里”出發,闡述病機、辨證思路,以及指導臨床用藥、施針[7-10],如《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里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雖然后世醫家總結“表里”的內涵略有出入,但一般認為太陽病的麻黃湯、桂枝湯證等屬表,陽明病的承氣湯、四逆湯證等屬里[11-12]。發展至今,表里辨證作為八綱辨證的一部分,其內容更加細致、豐富。表證常因自然界環境異常而人避護不慎,感受觸冒外邪,侵襲肌腠所致,主要表現為發熱、惡風寒、咳嗽、鼻塞、舌苔薄白、脈浮等;里證則常因七情、飲食、勞倦所傷,臟腑經絡正虛邪盛,表現變化多端,但一般無惡風寒、脈浮[13-14]。
當然,理論上表里辨證層次分明,臨證只需按圖索驥即可,但患者的外在表現常與內在本質并不一致,或因邪氣過盛而迅速入里,或因正氣虧虛而不能御邪,表里的劃分并非總是界限清晰。對此,仲景提出“合病”“并病”概念[15],如《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仲景提出了“太陽與陽明合病”“太陽與少陽合病”“陽明少陽合病”“三陽合病”“太陽與少陽并病”“二陽并病”等若干特殊情況,隨著實踐探索不斷深入,后世醫家又提出少陽為“半表半里”[16],并擴大“合病”“并病”范圍至六經,以適應臨床診治的需要。
作為外感病,傷寒與溫病具有許多共性[17]。不僅傷寒存在“表里同病”,溫病更是如此。葉天士《溫熱論》有“蓋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后化熱入里,溫邪則熱變最速”,“前言辛涼散風、甘淡驅濕,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劉老對此深有體會,指出若拘泥“開門揖盜,引邪入里”之說,則溫邪傳變迅速,必致表里俱實,熱盛陰傷,甚或由輕轉重,由重至危,終至無法挽救[1]。“表里雙解”法正為“表里同病”而設,尤其對變化迅速的溫病,臨證應高度重視。所謂“表里雙解”,即溫病初起就應在辛涼透表同時,配合清氣透營、涼血散血或通腑之法,并應貫穿整個病程。
2 臨床運用
2.1 溫病“表里同病”特點
溫病學最經典和最主要的辨證方法是衛氣營血辨證和三焦辨證[18],兩者均將溫病發生演變過程按由表入里、由淺入深、由輕而重順序劃分為不同階段,但彼此有許多交集,形象上可比喻為經線和緯線,共同對溫病進行定位、定性,以指導臨床;其所不同的是,衛氣營血辨證更強調圍繞經脈的橫向表里維度,而三焦辨證更突出上下部位、不同臟腑的縱向表里發展。
劉老臨證更強調“表里”的相對關系,而非獨立、絕對的定位。衛氣營血是一個由表及里的層次,氣分相對于衛分屬于里,相對于營分則屬于表,衛與氣、氣與營都可視為表里,但獨立地看,一般衛屬表,氣、營、血屬里,更加局限;三焦辨證,從上焦到中焦、再到下焦是一個病邪由表入里、逐漸深入的過程,如中焦與下焦可視為表里。值得注意的是,上焦自身內部尚存在一個由表及里的關系,即從皮毛到肺、再到心包,也是逐漸從表入里、病情深入的演變過程。若獨立分析,一般上焦的肺可以為表或里,心包為里;中焦脾胃,下焦的大小腸、肝腎均為里。總之,從相對關系出發,其內涵更加廣泛,臨床應用價值也更高。
溫病初起一般被合稱為“肺衛表證”,即將三焦辨證所論溫熱邪氣在上焦之肺,與衛氣營血辨證認為的病在衛分結合起來。正如《溫熱論》從衛氣營血論述:“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而《溫病條辨?上焦篇》則從三焦辨證指出“凡病溫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陰”。
除了溫病學自身的特殊辨證體系,作為中醫學的一部分,“肺與大腸相表里”等理論也適用于溫病的表里分類,這些分類方法更強調臟腑經絡之間關系。
以上是從理論角度分析,而臨床上溫病患者卻常呈現“表里同病”,如衛營同病、氣營同病,或上中二焦同病、上下二焦同病等復雜情況,尤其溫疫類溫病,邪氣猛烈,同時侵襲表里。因此,雖然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對臨床表現的劃分單純、清晰,易于初學者理解掌握,但也有不盡完善之處。最主要的不足是忽視了溫病常見的“表里同病”復雜情形,進階學習或臨床應用時需要留心,“表里雙解”法也應運而生。
2.2 治療
肺衛表證是溫病的最早階段,主要表現為發熱惡寒較輕,或暫未發熱,或見咳嗽、胸悶氣促、少痰(多為白痰)、納眠及二便均尚可等,治當發汗解表、辛涼透邪。一般而言,溫病忌用麻黃、桂枝等辛溫解表之品,以免“熱而溫之”(《大醫精誠》),《溫病條辨?上焦篇》亦強調“太陰溫病,不可發汗。發汗而汗不出者,必發斑疹。汗出過多者,必神昏譫語”。而辛涼解表之法,辛可散邪、涼可解熱,于病為正治,常用銀翹散加減。根據劉老經驗,流行性乙型腦炎高熱期患者服用辛涼解表劑后往往出一種黏汗或臭汗,同時體溫逐漸下降,病情也隨之好轉[2]。
里證病機更為多樣,病邪入里迅速,多在初期即兼有里證,常辨證使用清氣透營、涼血或通腑之法。清氣透營、涼血活血是《溫熱論》所倡經典治法,“在衛汗之可也,到氣才可清氣,入營猶可透熱轉氣,如犀角、玄參、羚羊等,入血就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膠、赤芍等物”,并根據衛氣營血辨證,在4 個階段分別使用辛涼發汗、清氣分熱、清營透熱、涼血活血之劑。辛涼發汗常用銀翹散加減;清氣分熱常用白虎湯加減;清營透熱常用清營湯;涼血活血除原文提及的藥物外,也常用丹參、玄參。對此,劉老結合臨床實踐,認為“若按葉氏衛氣營血四層來治療,病輕者尚可有效,病重者則今日治在‘衛’,而明日已入‘氣’。等你治在‘氣’,而又入‘營’、入‘血’矣”[1]。對于這種臨床現象,葉氏亦有“前言辛涼散風、甘淡驅濕,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溫熱論》)。故溫病早期雖必見表證,治療亦當解表,但須佐以清營解毒等之品,衛營雙解,奏效乃捷[1],這是“表里雙解”最典型的情況。若舉一反三,其他不同層次也常出現同時發病的情況。正如上文所說,獨立地看2 個同病層次,雖可能均屬于“里”,但在相互關系上互為“表里”,也需治以“表里雙解”之法,不可偏于一隅。
此外,還須強調“通腑法”,即通利大腸、小腸等六腑,使二便通暢。此法源自《內經》“肺與大腸相表里”“心與小腸相表里”諸論、仲景承氣湯類方及后世導赤散等,結合溫邪“首先犯肺”、中焦亦可見腑實證的臨床實際,可衍用于溫病治療。不過,溫病通腑常用大黃等,但需辨證選方,其中以吳鞠通所創系列承氣湯最值得重視。如牛黃承氣湯開竅通下,用于治療熱閉便秘,兼言語不利、飲不解渴;增液承氣湯潤燥通下,多用于老年或素體陰虛所致便秘者;新加黃龍湯扶正通下,用于溫病氣血虧虛、乏力明顯、口干唇裂者;導赤承氣湯不僅通大腸腑,且通小腸腑,治療溫病左尺脈牢堅,小便不暢兼痛、甚至尿血者;護胃承氣湯治療下后數日熱不退、口燥咽干、舌苔干黑或金黃色、脈沉而有力者。理論上,大便秘結屬溫病學中焦胃腑病(陽明腑實),而在臟腑辨證中又屬下焦病(大腸不通),這是不同辨證體系不同角度分類的結果。但其治療實質仍是“表里雙解”,如上中二焦雙解、肺與大腸雙解,用詞不同,內涵則一。需注意的是,兼顧通腑法雖也屬“表里雙解”,但并非必用之法,而應辨證施用。
3 典型病例
案例1:患兒,男,6 歲,1956 年7 月30 日入院。3 d 前突然頭痛發熱,繼而高熱,譫妄,煩躁不安,抽搐,神智不清。曾在西醫診所注射青霉素、復方奎寧。刻下:患兒狂躁不安,高呼大叫,周身灼熱(體溫40.0 ℃),小便利,大便秘結,舌苔白,脈沉數。查:心率128 次/min,呼吸40 次/min,神智半昏迷,譫妄,頸項強直,瞳孔縮小,對光反射遲鈍,膝反射消失,腹壁、提睪反射皆消失,巴賓斯基征及克尼格征皆陽性。西醫診斷:流行性乙型腦炎。中醫診斷:暑溫,證屬熱閉心包、肺胃熱盛、氣營同病。治法:清熱開竅、清解肺胃、清氣涼營。處方:石膏(先煎)200 g,知母9 g,甘草9 g,金銀花15 g,連翹15 g,安宮牛黃丸(兌)1 丸。1 劑,水煎,鼻飼,1 次/2 h。
1956 年7 月31 日二診:體溫39.4 ℃,狂躁稍安,驚厥減少,小便利,大便仍未解,舌脈同前,守方續服1 劑,煎服法同前。
1956 年8 月1 日三診:體溫38 ℃,無驚厥,仍譫妄不識人,能自進飲食,大便未解,苔白,脈沉數有力。乃暑稽陽明,肺熱未清,大腸里實。治當解暑清肺,釜底抽薪。改方:石膏(先煎)100 g,玄參9 g,甘草5 g,酒大黃9 g,芒硝5 g,連翹12 g,忍冬藤15 g,蓮子心9 g,紫雪丹(兌)1 g。1 劑,水煎,溫服,1 次/2 h。
1956 年8 月2 日四診:體溫37.5 ℃,神識較清,大便已解,守方續服1 劑后體溫正常,但出現陰虛證候。守方加養陰藥,續服7 劑后痊愈出院。
按:本案是流行性乙型腦炎病例,結合臨床表現按暑溫論治。初診高熱、神昏肢厥,乃典型氣營同病:氣分為肺胃熱盛證,營分則是熱閉心包證。方用辛涼重劑白虎湯,佐以安宮牛黃丸。二診時,病情略有好轉,效不更方。三診出現的變化為暑邪稽于陽明,肺熱未清,大腸里氣仍實,上中二焦同病,肺與大腸表里同病,故用釜底抽薪法。四診則逐漸進入溫病后期,熱勢漸弱,陰傷愈顯,遂加養陰之品善后。本案共服藥10 劑,石膏總用量達1 200 g,因患兒氣分熱盛最為嚴重,乃病之“本”,且其他熱閉心包、中焦腑實、營陰損傷等均由氣熱所致,屬于“標”,重用石膏可謂治病求本,故能力挽沉疴。可見,前期清熱與開竅并用,中期肺與大腸雙解,后期清解氣熱配合滋陰養營,“表里雙解”之法均得到充分體現。
案例2(遠程會診):患者,女,67 歲,2020 年2月4日入院。5 d前密切接觸有武漢居住史的兒媳后,出現咳黃綠色濃痰、動則氣促、乏力、納差、頭昏,無畏寒發熱,昨日在當地人民醫院住院,以克力芝、利巴韋林及降糖治療,今日至湘潭市中心醫院住院。既往史:2 型糖尿病、高血壓病、冠心病、糖尿病腎病、腎功能不全。刻下:咳黃綠色濃痰,胸悶氣促,乏力,納少,眠差,小便少,大便正常,舌紅,少苔而干。雙下肢浮腫,雙足趾膿皰、有波動感、顏色渾濁、皮溫稍高。查:體溫36.6 ℃,心率92 次/min,呼吸20 次/min,血壓126/86 mm Hg(1 mm Hg=0.133 kPa),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陽性。CT 示“雙肺各葉多發散在病灶,心臟稍增大,主動脈及冠脈部分鈣化”。其他檢查提示心力衰竭、腎功能不全、血糖控制不良等。入院后逐漸出現氣促加重、尿量減少、下肢浮腫,已下病危通知。西醫診斷: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危重型;呼吸衰竭1 型;2 型糖尿病,糖尿病腎病,腎功能不全;低蛋白血癥;皮膚軟組織感染;高血壓病3 級,極高危;冠心病,心衰2級。中醫診斷:咳嗽,證屬心腎陰脫、痰熱阻肺、氣營同病。治法:滋陰固脫、清肺化痰、清氣涼營。處方:西洋參6 g,麥冬9 g,五味子6 g,黃芪30 g,生地黃10 g,丹參10 g,炒麥芽10 g,橘紅10 g,豬苓15 g,茯苓15 g,蘆根30 g,薏苡仁30 g,苦杏仁9 g,甘草6 g,黃芩10 g。5 劑,每日1 劑,水煎服。
2020 年2 月13 日二診:靜息時無胸悶氣促,但不耐活動,納差、無惡心反胃,略口干口苦,無下肢水腫,今日3 次稀便,小便量可,舌淡紅,舌根苔黃黑厚膩。乃心腎陰虛、痰熱阻肺、氣營同病、疫穢未盡。治法:滋腎養心、清肺化痰、清氣涼營、辟疫除穢。改方:太子參15 g,麥冬10 g,五味子5 g,黃芪30 g,竹茹10 g,丹參30 g,葶藶子15 g,橘紅10 g,枇杷葉15 g,茯苓15 g,蘆根40 g,薏苡仁30 g,苦杏仁10 g,甘草6 g,檳榔10 g,草果6 g。繼服3 劑。
2020 年2 月15 日三診:氣促好轉,精神改善,淡紅舌,舌根苔白厚膩、有中裂。辨證:痰熱阻肺、營陰耗傷。治法:清肺化痰、涼營養陰。西醫診斷由危重型調整為重型。改方:蘆根30 g,薏苡仁18 g,苦杏仁9 g,茯苓12 g,甘草6 g,法半夏9 g,橘紅6 g,川貝母12 g,黃芪30 g,黃連6 g,西洋參10 g,黃芩12 g,厚樸9 g,瓜蔞9 g,前胡9 g。繼服3 劑后乏力、氣促明顯改善,偶有干咳。至2020 年2 月23日已連續多次復查新型冠狀病毒核酸陰性,符合出院標準。
按:本案為老年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患者,屬溫病學“溫疫”“冬溫”“濕溫”范疇。初診為典型的上下焦同病、氣營同病、虛實錯雜。具體而言,上焦心、肺與下焦肝、腎同病;與案例1 有所不同,本案氣營同病存在營分閉證、脫證,以及氣分肺胃無形熱盛與氣虛有形痰熱差異。本案患者氣分證見肺氣虛兼有痰熱阻肺,營分證則屬心腎氣虛、營陰欲脫。故以治療上焦氣分之《千金》葦莖湯、《金匱》茯苓杏仁甘草湯,治療下焦營分之生脈散、清營湯、豬苓湯合方,另加黃芪扶正、橘紅止咳化痰。二診時明顯好轉,但疫氣穢濕仍在,故見口干口苦、便溏、舌根苔膩等,遂加利濕、化濕、燥濕、辟穢之品。三診時病情繼續好轉,遂去生脈散、豬苓湯及祛濕藥,而保持清解肺中痰熱,輔以益氣扶正,幫助后期康復。本案提示,老年人素體虛弱、既往有多種基礎病者,患溫病(溫疫)后更易出現表里同病,且病情危重,證型多為氣營、上下二焦同病,治療不可拘泥某一方面,而應統籌兼顧,攻補兼施,適時采用“表里雙解”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