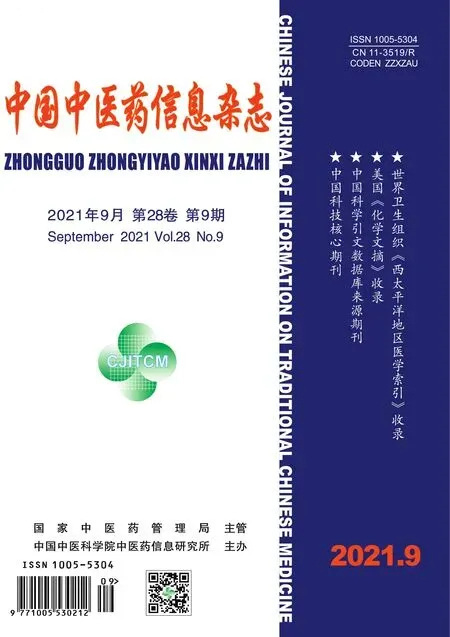基于伏邪理論探討遲脈癥的辨治思路
梁津煥,蔡銀河,林莉雯,褚慶民,趙新軍,李榮
1.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 廣州 510405;2.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廣東 廣州 510120
臨床上,遲脈癥以成人心室率低于60 次/min 為特征[1],《脈經》所謂“遲脈,一息三至,去來極慢”,現代醫學的緩慢性心律失常即屬其范疇。遲脈癥早期患者心率在40~60 次/min 時可無明顯癥狀,隨著病情加重,尤其心率低于40 次/min 時出現較明顯的臨床癥狀,如心悸、胸悶、氣短、乏力、頭暈,甚則黑矇、暈厥等[1],與伏邪致病具有高度一致性。茲從伏邪理論尤其少陰心腎伏邪方面探討遲脈癥辨治,為中醫治療遲脈癥提供參考。
1 伏邪理論溯源
有關伏邪理論的闡述,《靈樞?賊風》“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即指出邪氣侵襲人體未即發,可留而 不發,過時而發;《素問?瘧論篇》“此病藏于腎,其氣先從內出之于外也……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也”,指出伏邪有一定的潛藏部位,且易傷陽氣;此外,《素問?金匱真言論篇》“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溫”,指出腎氣虧虛是伏邪發病的決定因素。在之后的發展中,伏邪理論的重點多屬伏氣溫病范疇。至清代擴展到外感“六淫伏邪”,王燕昌《王氏醫存》將伏邪進一步擴展為“一切不即發的邪氣”,所謂“伏匿諸病,六淫、諸郁、飲食、瘀血、結痰、積氣、蓄水、諸蟲皆有之”,豐富了伏邪理論的應用范圍。至現代,任繼學教授[2]認為,伏邪即隱藏于人體正虛之處之邪,且有外感、內傷、先天、后天之分。
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入,目前有學者提出伏邪涵蓋伏風、伏寒、伏痰、伏瘀、伏毒等,其致病具有動態時空、隱匿潛藏、自我積聚、潛證導向等特點[3]。其中,動態時空是指隨著時間推移或機體正邪斗爭,伏邪位置發生由淺入深或由深入淺的變化,具體體現于伏邪系統的“隱匿”和“積聚”兩方面;隱匿潛藏是伏邪致病最本質的特征,體現伏邪在時間上的遲發性及空間上的隱匿性[4]。隱匿潛藏反映伏邪在機體的2種狀態:一是邪氣侵襲時,或因邪氣式微,或因同氣相求,邪氣直接深入潛藏,導致機體出現潛證狀態而無不適癥狀,臨床無證可辨;二是邪氣潛藏后,正邪交爭態勢的伏匿,其暗中消耗正氣,而無外在癥狀或無典型癥狀可查。自我積聚反映機體正邪勝卻的態勢,伏邪潛藏和損害部位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當伏邪積聚到一定程度,超出正氣控制范圍,即可發病,表現出一種突然從無明顯癥狀到嚴重且典型癥狀的爆發性轉變。
目前伏邪理論已用于指導腎病綜合征[5]、類風濕關節炎[6]、冠心病術后[7]等辨治,并取得滿意療效。
2 對遲脈癥的病機認識
關于遲脈癥的病機,《診家樞要》有“遲為陰勝陽虧之候,為寒,為不足”,《難經?經脈診候》“遲者藏也”“遲則為寒”,《瀕湖脈學》“遲來一息至惟三,陽不勝陰氣血寒”,可見,心腎陽虛是遲脈癥的重要病機。
心主陽氣,心賴陽氣以維持其正常生理功能,鼓動血液運行。若心陽不振,鼓動血脈乏力,故見脈遲。當病程較淺或正氣尚足時,僅表現為心動過緩,即心率<60 次/min。隨著病程進展,當心率<40 次/min,此時心陽愈虧,胸陽不振,陰寒諸邪趁虛而入,心悸、胸悶痛等出現。心陽虧虛,以致血行遲澀,或寒邪侵襲,寒凝血脈,使血脈閉阻而見胸痛、心悸。心主血脈,居上屬陽;腎主水、藏精,居下屬陰。腎陽為諸陽之本,腎陽虛衰,開闔失司,膀胱氣化不利,飲停濕聚,寒飲上逆,加之心陽失于溫煦,氣化失利,水液不得下行,停于心下,上逆以致心悸。心腎陽虛日久損及脾陽,脾失健運,傳輸失權,以致痰濕聚生,痰濁水濕閉阻心脈,導致心悸,《血證論?怔忡》所謂“心中有痰者,痰入心中,阻其心氣,是以心跳不安”,又脾為后天之本,脾陽虧虛,氣血生化乏源終可致氣血陰陽失衡。可見,遲脈癥病機宜從虛、痰、瘀立論,陽(氣)虛、痰阻、血瘀是其基本病理因素,病屬本虛標實、虛實夾雜之證,以氣血陰陽虧虛為本,血瘀、痰濁為標,其病位在心,病本在腎,以心腎陽虛為首要病機[8]。
3 遲脈癥具有伏邪致病特點
3.1 腎氣不足是伏邪內藏的先決條件
伏邪致病有其內因,《素問?金匱真言論篇》所謂“藏于精者,春不病溫”,《溫熱逢源》“伏溫之邪,冬時之寒也。其傷人也,本因腎氣之虛,始得入而據之”,指出伏邪致病與體質相關,腎氣不足是伏邪內藏的先決條件,“若腎虛不能托邪,則伏于臟而不得外出”。此外,少陰心腎是邪氣伏藏的主要位置。心本乎腎,腎本乎心,二者同為少陰,故《傷寒總病論?解仲景脈說》有“伏氣之病,謂非時有暴寒而中人,伏毒氣于少陰經,旬月乃發”,《溫熱逢源》所謂“寒邪之內伏者,必因腎氣之虛而入,故其伏也每在少陰”。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有“年四十,而陰氣自半”,其陰氣即腎氣,包括腎精、腎陰、腎陽,人到中年以后,腎氣漸虧,猶以腎陽虧虛為甚。《素問?五臟生成篇》“脈者,源于腎而主于心”,指出心陽根于腎陽,五臟之陽氣非此不能發,腎陽不足以致心陽日損,心腎陽氣偏虛。因此,若素體腎氣不足,中年以后,心腎陽氣愈虛,感邪時寒邪更易直中,竄伏少陰,其對伏邪具有易感性,且既病后,有從寒而化的演變趨勢,故《溫熱經緯?仲景伏氣溫病篇》有“少陰為陰,寒邪亦為陰,以陰遇陰,故得藏而不發也”。
3.2 少陰心腎伏寒是始動因素
素體腎氣不足,中年后心腎陽氣愈虛,寒邪直中,伏于少陰心腎,待時而發。寒為陰邪,易傷陽氣,少陰伏寒不斷損耗機體心腎陽氣而心率愈緩。此外,“寒氣生濁,熱氣生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心腎陽虛致機體寒濕濁邪內生;又“濁者其氣澀”(《靈樞?陰陽清濁》),濁邪內生,氣機不利,致水谷精微代謝失常,日久產生痰濕瘀積,所謂“陽虛生寒,停痰留飲”。心腎陽虛,一者血脈鼓動日漸乏力,血行遲緩而瘀滯叢生;二者陰寒諸邪逐漸累積。日久損及脾陽,氣血生化乏源,機體氣血陰陽失衡,致血瘀、濕阻、痰凝、濁毒等病理產物蓄積機體,形成伏寒、伏瘀、伏痰之象,為遲脈癥提供了發病條件。
3.3 伏寒、伏痰、伏瘀內動是根本原因
《醫述》“伏邪甚則病甚,伏邪微則病微”。一般而言,伏邪處于隱匿狀態,當積聚到一定程度,超出正氣控制即發病。此時若“外邪乘之,觸動伏邪”,則伏寒、伏瘀、伏痰諸邪內動,可驟然出現心悸、胸悶痛等癥。伏寒暴動,寒性凝滯,血行瘀阻,而見心悸、胸悶痛;伏痰、伏瘀內動,致脈絡瘀阻,血行澀滯,則胸悶不舒;伏痰內動,痰入心中,阻其心氣,則見心悸。更有甚者黑矇、暈厥等,蓋因陽氣虛甚,陰寒獨勝,瞬時陰陽之氣不相順接所致,《素問?厥論篇》所謂“陽氣衰于下則為寒厥”。可見,伏寒、伏痰、伏瘀隱匿潛藏,積聚日久,暴而內動,是遲脈癥發病的根本原因。
4 伏邪理論在遲脈癥辨治中的運用
遲脈癥病機以心腎陽虛為主,兼夾血瘀、痰濕、寒凝、氣滯等,故多采用溫補心腎為基本治法,佐以行氣、逐瘀、化痰之品,正如《素問?至真要大論篇》所言“寒者熱之”“勞者溫之”“損者溫之”。
鑒于伏邪深藏,不易且不宜攻伐,“非透不盡”,當以“透邪”為要,使邪有出路。故其治療原則在于“扶正”和“透邪”[9];又正氣及腎氣狀態在伏邪致病中起決定作用,故扶正是關鍵,通過滋陰、助陽、益氣以扶正,助機體透邪外出。
由于伏邪隱匿潛藏,“發則有證可辨,伏則無機可循”,故在隱匿階段“先證而治”有現實意義[7]。若患者除心動過緩,尚有喜暖畏寒、四肢不溫、夜尿頻多等心腎陽虛之象,即應溫補心腎,酌以逐瘀化痰之品。而當遲脈癥凸顯,須助陽透邪,亦可寓透邪于養陰、助陽并舉,使正氣復而邪自除。
4.1 助陽透邪法
《醫門法律?痢疾門》“邪陷入里,雖百日之久,仍當引邪由里出表,若但從里去,不死不休”,強調對深陷于里的邪氣,不論久遠,當引邪出表,不可瀉下攻邪。可見,對伏邪久郁少陰的遲脈癥,宜先用藥深入腎中,領邪外出,方選麻黃附子細辛湯。本方出自《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原為治療陽虛外感風寒之證,既助陽以扶正,又透邪外出,是扶正透邪并重的常用方。臨床觀察發現,麻黃附子細辛湯治療遲脈癥效果滿意[10]。
4.2 養陰助陽透邪并舉
針對伏邪久郁少陰致陰陽俱虛,不能鼓邪外出,治療“若惟取其陰而不鼓動其陰中之陽,恐邪機仍冰伏不出”,《溫熱逢源》主張“擬于大劑養陰托邪之中,佐以鼓蕩陽氣之意,俾邪機得以外達三陽為吉”,即養陰、助陽并舉以托邪外出。
炙甘草湯又名復脈湯,是《傷寒論》養陰助陽并舉以托邪外出的代表方。本方寒熱并用,益陰扶陽,所謂“善補陽者,必于陰中求陽,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景岳全書》)。遲脈癥患者多有素體心腎陽虛,單純溫陽通脈難以顯效,故佐以益氣養陰之品,陰中求陽,陽氣生化,陰陽既得,邪祛正復。資料顯示,炙甘草湯治療緩慢性心律失常[11-12]療效滿意。
5 小結
在伏邪理論看來,遲脈癥乃素體腎氣不足,中年后陽氣更虛,以致寒邪直中,竄伏少陰心腎,日久促成機體伏寒、伏瘀、伏痰內生,若超出正氣控制,“外邪乘之,觸動伏邪”,則伏寒、伏痰、伏瘀內動,驟然出現心悸、胸悶痛、氣短,甚則黑矇、暈厥等遲脈癥相關癥候群。因此,從少陰心腎伏邪與遲脈證的相關性著手,運用伏邪理論指導遲脈癥辨治,在遲脈癥隱匿潛藏階段“先證治之”,突破“依證而治”限制;一旦遲脈癥病發,則通過辨證論治,靈活用藥,既可助陽透邪,又寓透邪于養陰、助陽并舉,同時佐以逐瘀化痰之品。這對本病治療有積極的臨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