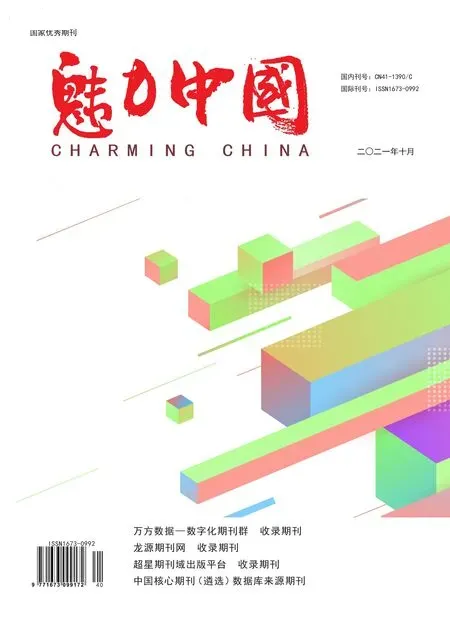漢語古代小說《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蒙譯本傳播研究
薩日郎
(內蒙古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文學傳播研究屬于文學作品的外圍研究。文學傳播的傳播場域、文學創作、文學作品的傳播渠道、受眾欣賞、傳播影響等環節都是文學傳播的研究對象。研究明清漢語小說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情況對研究漢族與少數民族地區文學的相互交融與交流,漢族文學對少數民族地區文學的關系能夠提供重要的研究視角和史料。
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蒙譯本文獻來源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蒙譯本以入選《今古奇觀》小說集蒙譯本和單行蒙譯本兩種形式流傳下來。《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入選為《今古奇觀》小說集的第23 章小說。《今古奇觀》小說集大約成書于明末1632 至1644 年,由抱甕老人從《三言二拍》選取了40 篇小說,其中大部分小說主要描寫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與喜怒哀樂,有非常高的可讀性,故事情節豐富,引人入勝。
自19 世紀初以來,《今古奇觀》曾數次被譯成蒙古文,在蒙古地區廣泛傳播。據初步統計,目前分藏于國內外圖書館的《今古奇觀》清代蒙古文譯本至少有200 余冊。
《今古奇觀》小說集現有兩種譯本流傳于內蒙古和蒙古國地區。即1816 年附有《今古奇觀,譯者補序》的東部蒙古地區的卓索圖盟人哈斯寶譯本和蒙古國烏蘭巴托譯本。烏蘭巴托譯本是19 世紀末到20 是世紀初在喀爾喀蒙古地區庫倫翻譯,譯者不詳,從多個章節的翻譯風格與翻譯策略各有差異來看,可以斷定多人參與到該小說集的翻譯工作中。
在蒙古地區《今古奇觀》詩集中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灌園叟晚逢仙女》《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單篇小說的蒙古文單行本譯本也有傳播和流傳。其中《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對蒙古族文學創作與手中審美方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今古奇觀》小說集的哈斯寶蒙譯本和烏蘭巴托蒙譯本兩種譯本均編入了《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小說之外,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蒙古語文工作辦公室藏有《蔣興哥故事》冊頁式蒙古文抄本。《蒙古文抄本〈蔣興哥故事〉和哈斯寶譯本卷二十〈蔣興哥重回珍珠衫〉在個別字詞的寫法上略存差異,其余的大體內容完全一致,而與烏蘭巴托譯本的對應內容卻存在諸多歧異。故可以推斷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蒙古語言文工作辦公室所藏蒙古文抄本〈蔣興哥故事〉實則哈斯寶譯本卷二十三章〈蔣興哥重回珍珠衫〉中以單篇形式謄錄出來的獨立文本,它是哈斯寶譯本的一種特殊傳播形式。》[1]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以蔣興哥和王三巧兒夫妻為主要人物,講述了他們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蔣興哥與妻子三巧兒婚后恩愛有加,但因為生計所迫,他留下妻子獨自赴外地做買賣。在此期間三巧兒由于受到陳大郎與薛婆的誘惑和欺騙,做出違背丈夫的不貞之事,后被蔣興哥休棄。但在蔣興哥遭遇之難時,她又出手相助幫他擺脫了冤案。最后蔣興哥不忘舊情,與三巧兒重歸于好。作品的故事情節扣人心弦、一波三折、人物形象豐滿有趣、生活細節描寫細膩生動。
小說中不僅塑造了豐滿生動的普通市民的形象,也不乏漢族市民的生活環境、思想觀念、行為習慣、習俗禮節、審美標準、飲食服飾等文化符號的體現。當然這些文化符號通過蒙譯本傳播到蒙古族地區后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誤讀、創造性叛逆等跨文化傳播的現象。
二、《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蒙譯本的傳播場域
文學傳播的傳播場域不是一個獨立的空間,他與文學傳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時代背景因素密切相關,并且與文學傳播內部系統的的作者、編輯、傳播者、受眾等多重因素有密切的關聯。
清代蒙漢文學關系是中國多民族文學關系史上非常重要的時段。據統計,清代至民國早期,蒙古族文人曾翻譯百余部漢族古代小說,大多以抄本的形式流傳于蒙古族地區,且有多種版本。清朝時期,隨著蒙漢族地區在整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多方面的關系日益密切。譯本傳播的傳播者和受眾需求兩個傳播因素的逐漸形成直接推動了對漢族文學的喜愛與認可,隨之出現了多部文學作品的蒙譯本陸續出現。現在搜集到的最早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譯本是1816 年哈斯寶的譯本。在清朝嘉慶丙子年間該小說被翻譯成蒙古文,供廣大蒙古族受眾并非是一個偶然現象。
清代漢文小說蒙譯活動前后延續了兩百年,大致分為17 世紀初至18世紀中葉、18 世紀后半葉至19 世紀初、19 世紀初至20 世紀初等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的翻譯活動的內容與地點略有不同。第一階段的翻譯中心為北京,第三階段是翻譯中心轉移至東部蒙古地區的卓索圖盟和喀爾喀蒙古族地區的庫倫。《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兩種蒙譯本翻譯地點正在這個時期的翻譯中心卓索圖盟和喀爾喀蒙古族地區。
文學傳播場域里文學傳播者和受眾是最重要的兩個影響因素。19 世紀初期在蒙古族地區有不僅蒙漢兼通,并且認同漢族文化的蒙古族文化人的出現,直接推動了漢族古代文學經典作品的翻譯和傳播。與之前只有官方組織翻譯活動的情況相比,沒有官方背景的文化人員的參與,文學作品的蒙譯活動在翻譯作品的內容選擇與審美趣味都有了明顯的變化。《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蒙譯本譯者《哈斯寶飽讀中國古籍,精通文史。哈斯寶的文學思想和文化理想中就具有深刻的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2]蒙古文學的發展歷史與漢族文學發展歷史有較大不同。
19 世紀開始,清朝時期漢族小說里描寫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和的現實關懷都都是蒙古族受眾更加接近生活,接近現實的一種文學審美的需求。讀者的需求是推動文學創作的有力影響因素。小說里出現的情感恩怨、日常起居、飲食服飾等細節更加拉近了文學作品與受眾的日常生活。描寫普通市民生活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蒙譯本深受受眾的歡迎的原因所在了。
三、《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蒙譯本的翻譯特色
清代蒙古族翻譯者因為對漢語文化的理解與認同的差異、個人審美取向的不同對古代漢語小說采取了不同的翻譯策略。有對原文逐字逐句的對等翻譯,也有創造性的叛逆,更有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對原文進行大量的刪節等情況。原文在翻譯過程中出現了多種文本變異。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哈斯寶譯本和烏蘭巴托譯本在翻譯地點和翻譯翻譯策略上采取兩種不同的方法,差異明顯。
(一)忠于原文的對等翻譯
哈斯寶忠實于原文,對《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原文小說中出現的人名和地名等信息進行了對等的符號轉碼、對人物對話、細節描寫、情節發展等所有的內容未加修改與刪減,也沒有夾述評語,在譯文里都能夠找到相對的語句,進行了嚴謹貼切地表達。哈斯寶譯本對原文的詩詞部分也是做到了完整的翻譯。原文共有行數不同的24 首詩詞,譯文中也沒有夾述自己的評語。哈斯寶在翻譯詩詞與諺語時遵守了蒙古族文化的表達思維與詩歌的首尾押韻。
(二)跨語際轉碼的創造性叛逆
烏蘭巴托譯本更加考慮到了受眾的閱讀期待,便于受眾理解與通過小說來教化和感染受眾,一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刪節、節譯和改編,進行了跨語際傳播的創造性叛逆。在必要之處改編了原文的敘述模式,將原文中的認讀對話直接安變成了敘述形式。烏蘭巴托譯本對刪節故事情節不強、或者與故事主干聯系不深緊密的部分。對人物對話和細節描寫進行了節譯與刪譯。有事簡略了故事情節,便于受眾更好地理解,譯者夾述了自己的理解和對故事情節的評論。《原著中共有24 首詩歌,翻譯時改寫了13 首詩歌,增加了3 首詩歌。沒有嚴格遵守字句或段落的原有形式進行翻譯,譯文中的詩句都遵循了蒙古族詩歌的押韻方式和原則》[3]86。
(三)文化誤讀的誤譯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兩種譯本因為對漢語文化的理解不準都存在不同成的文化誤譯。
例如哈斯寶譯本對原文中一些重要信息漏譯之外,還由于不諳漢語文化意境、用詞習慣、難辨細微等原因而出現誤譯的現象。對一個完全嶄新的文化及美學體系進行詮釋,如果對原文的語言內涵或文化背景缺乏足夠的了解,理解有失偏頗,就會導致傳情達意受限。蒙古文抄本《蔣興哥故事》的誤譯中,對古代禮制、相關習俗的誤譯現象占據較大比重。
例如原文中的有一句《只推制中、不繁外事》,在漢族文化中“制中”一詞也叫“守制”,指父母喪后,子女在居喪期間不能飲酒、聽樂、外出參加各種娛樂活動。蒙古文抄本《蔣興哥故事》將其譯為“不理會無關的事情”,沒有譯出“制中”一詞的完整意義。又如原文中的蔣興哥給三巧兒的休書中寫道“過門之后本婦多有過失,正合七出之條,因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其中“七出之條”為封建社會,妻子有下列情況之一,丈夫就可單方面休妻的七種理由,即指無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盜竊,妒忌,惡疾等。蒙古文抄本《蔣興哥故事》將“七出之條”譯為法律,對其進行了模糊處理,未能準確表達原文意義。
四、《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蒙譯本的傳播影響
(一)推動蒙古族文學的敘述內容的變革
清代漢語古代小說的蒙譯本傳播,推動了文學作品開始關注現實生活,滿足受眾期待。
古代蒙古族文學植根古老的游牧民族的文化熏陶,口語文學和英雄崇拜一直是蒙古族文學的主要特色。翻譯和接收漢族文學史也是熱衷于翻譯和傳播《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游記》等充滿英雄傳奇色彩的作品。上述作品的故事情節、敘述風格與蒙古族文學的文化特色和變現形式有諸多的相似之處。
但是《今古奇觀》里的家長里短的故事、細膩的生活場景描寫、普通市民的人生體驗等都是之前蒙古族文學作品中特別少見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廣泛傳播不僅推動了蒙古族受眾審美趣味的逐漸改變,也使得文學創造中開始描寫普通人生活場景、塑造普通的形象,展現普通人的喜怒哀樂。
(二)直接影響文學創作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蒙譯本對蒙古族文學的發展和創作產生過深遠的影響,《曾經數次從漢文譯為蒙古文,這不僅是蒙古族讀者非常喜愛它的證明,也的確充分顯示出蒙古語語言詞匯之美妙豐富性。這些故事的譯文由書面滲透至民間,不僅有蒙古族烏力格爾齊增補講述,而且自蒙古國建國初期,還在烏力雅蘇臺、阿拉坦寶力格以及首都大庫倫等地搬上戲劇舞臺,編成歌舞劇進行演出》[4]290。蒙古文譯本《蒙古國現代著名作家達·寶德瓦的〈美麗的故事〉(wujimjitewugulel)也是模仿〈今古奇觀〉中〈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而創作的。他以蒙古國社會生活為背景,以〈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故事為框架,講述了一個蒙古族生意人家庭類似于〈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故事。〈美麗的故事〉于1990 年由蒙古國政府出版社出版發行,該小說在蒙古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5]12。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蒙譯本的傳播是清代蒙漢文學跨文化傳播的經典個案,對研究蒙漢文學關系,民族文學相互交融與交流有非常高的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