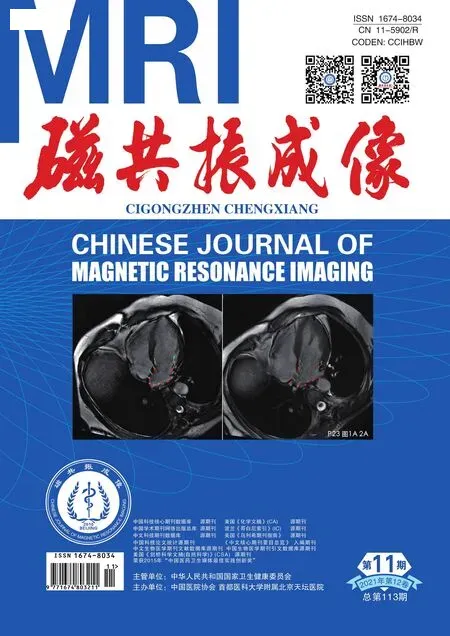兒童孤獨癥的神經影像學研究進展
胡爽,李紅,張雅清,王曦
孤獨癥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幼兒時期一種異質的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1],核心癥狀主要為語言及社會交往障礙、參與度和溝通度降低以及活動受限的重復刻板行為[2-3],其高發病率及高致殘率成為全球重大公共衛生健康問題[4-6]。研究證實ASD患兒早期神經結構具有可塑性,及早診斷并行有效的干預治療對患兒的預后具有深遠的影響。神經影像學技術因其在探索大腦結構和功能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被廣大學者用于ASD診斷中,通過評估腦結構形態、腦白質纖維束的完整性、物質代謝等方面來顯示ASD病理生理學的改變,為臨床對ASD的早期診斷提供了更可靠、更客觀的依據。筆者就兒童孤獨癥的神經影像學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ASD概述
ASD的病因復雜,發病機制尚不完全明確,其可能的假說涵蓋遺傳學、代謝組學、免疫學、神經生物學等多方面,有研究表明遺傳和環境因素共同作用[7]影響大腦神經發育,導致神經元連接不足。研究證實CYFIP1基因的缺失與ASD患者的腦功能和結構連接障礙息息相關[8]。陳永紅等[9]認為結構連接和功能連接的神經環路異常導致ASD臨床核心癥狀的重復行為增加及社交行為障礙,推測神經環路異常可能與ASD發病機制相關。這些研究結果有助于理解ASD的發病機制,更好地認識疾病并為臨床診斷及早期干預治療提供可行的方案。
2 臨床評估ASD的手段
臨床對ASD的診斷主要依靠患兒的行為表現和癥狀分析,評估ASD兒童行為特征的方法是基于各種量表工具以及對影響因素復雜性的定性分析,臨床應用較廣泛的篩查量表主要包括孤獨癥行為檢查量表、兒童孤獨癥評定量表以及兒童孤獨癥量表;診斷量表包括孤獨癥診斷觀察量表診斷量表和孤獨癥診斷訪談問卷修訂版[10]。這些量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ASD的陽性診斷率,但因其主要依賴于臨床癥狀的觀察和醫生的臨床經驗,存在一定的主觀性,缺乏客觀的神經解剖學及功能方面的依據。神經影像學技術可減少主觀影響因素,以更客觀的影像學證據提高ASD的診斷符合率。
3 神經影像學評估ASD
近年來神經影像學飛速發展,結構磁共振成像(struc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sMRI)、擴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磁共振波譜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血氧水平依賴功能磁共振成像(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BOLD-fMRI)及功能性近紅外光譜(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技術的應用,能夠安全無創、客觀地檢測ASD患兒腦結構和功能的改變,對臨床ASD診斷有十分廣泛的應用前景。神經影像學研究表明,孤獨癥患兒存在腦結構和功能異常,包括腦體積異常、腦白質纖維束連接異常、腦組織代謝物質紊亂等神經病理學變化。
3.1 sMRI
sMRI采集高分辨率的3D T1圖像,通過后處理技術對腦體積測量、腦表面皺褶等進行研究。常用分析方法包括基于體素的形態學分析和基于表層的形態學分析[11]。
基于體素的形態學分析可反映孤獨癥患兒腦體積的變化,ASD兒童的神經生長軌跡存在早期差異,他們的大腦似乎比正常發育大腦增長得更快,腦體積增加約10%[12]。儲康康等[13]通過縱向對比分析發現ASD患兒額葉和顳葉的腦白質體積增大,而這些腦區主要與社交情感、語言表達等相關,推測這些區域的變化可能是ASD兒童社交和認知障礙的潛在病理基礎[14]。一項Meta分析提出,ASD患兒中央后回和顳上回等多個腦區灰質體積增大,且灰質體積的變化與患者的平均智商顯著相關,推測這些變化可能是導致ASD患兒智力低下因素[15]。
基于表層的形態學分析主要反映微結構的改變,例如腦表面皺褶程度、皮層厚度等。Kohli等[16]研究發現,ASD患兒某些皮質區域的皮層折疊數量趨向于升高,但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減少,這可能與ASD患兒早期腦過度發育所致。研究發現ASD患兒的紋狀體、額葉皮層和顳葉皮層等情感與認知相關腦區的皮層較正常兒童增厚[17-18],提示腦皮質的增厚或許與ASD的發生有一定的關系。綜上所述,sMRI主要通過腦體積和腦表面皺褶細微結構改變觀察ASD患兒腦結構的變化,進而輔助臨床診斷ASD。
3.2 DTI
DTI技術是目前唯一能夠無創性在活體內定量評估腦白質纖維束的完整性和方向性的檢測方法,對生物組織內水分子的擴散十分敏感,能夠直觀地顯示腦白質纖維束的宏觀和微觀結構以及白質纖維束的傳導通路及其發育變化情況[11,19],是當前研究大腦白質結構性連接的最為有效的方法之一。
Steinbrink等[20]首次對ASD兒童行DTI研究發現ASD組腹側前額葉皮層附近、扣帶回前部以及顳頂交界處的白質中部分各向異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降低,在雙側靠近杏仁核的顳葉、胼胝體和雙側鄰近顳上溝附近也可見FA降低的其他簇。近年來許多學者[21-24]的研究也發現ASD患兒腦白質FA降低,包括弓狀束、扣帶束、上縱束、內囊和胼胝體壓部等,推測ASD相關神經通路的髓鞘和軸突體積較小及密度降低,導致軸突完整性缺陷和髓磷脂存在受限,進而引起ASD患兒相應臨床癥狀的出現,眾多研究結果提示白質結構在ASD患兒發育中似乎特別受影響,表現出髓鞘形成減少,FA值降低,這都表明ASD有一種獨特的神經發育模式,并且這種潛在的結構差異可能影響學習和社交溝通能力。DTI通過評估腦白質纖維束的完整性及相關參數變化,可觀察纖維束是否損傷及損傷程度,或可為ASD的診斷提供新的見解。
3.3 MRS
MRS利用磁共振現象和化學位移作用,以非侵入性技術測量活體腦組織內特定神經化學產物的穩態濃度及其代謝活性,間接反映腦功能狀態。目前應用最廣泛的是1H-MRS成像,其主要檢測的代謝產物包括N-乙酰天冬氨酸(N-acetyl aspartate,NAA)、谷氨酸(glutamate,Glu)、γ-氨基酸(gammaaminobutyric acid,GABA)等。NAA僅存在中樞神經系統的神經元中,是衡量神經密度、完整性及靈敏度的指標,NAA濃度的降低提示中樞神經元結構的完整性及功能的損傷[11]。有學者[25]發現ASD患者丘腦、扣帶回前部區域的NAA濃度降低,且NAA濃度越低,核心癥狀越嚴重,推測神經元的損傷可能與ASD的臨床癥狀相關。而Glu、GABA分別是中樞神經系統重要的抑制性和興奮性神經遞質,Puts等[26]研究發現ASD患兒感覺運動區GABA水平降低,并認為這可能是ASD患兒觸覺功能改變的基礎。而Umesawa等[27]發現ASD患者較對照組患者有更嚴重的感覺超反應性,ASD患者左側輔助運動區和左側腹側前運動皮層的GABA濃度降低,與感覺超反應的嚴重程度呈負相關,表明高階運動區抑制性神經傳遞GABA減少可能是ASD感覺超反應的基礎。另有學者[28]發現ASD兒童雙側視皮層中的GABA濃度與更有效的視覺搜索能力相關,GABA值降低會導致ASD患兒社交障礙癥狀加重。他們還發現在右顳頂葉交界處的GABA、Glu、GABA/Glu均減少,提示關鍵網絡中樞的神經元功能受損。MRS通過分析中樞神經系統代謝產物含量的變化來反映腦組織損傷程度,在探測ASD患兒神經元發育及損傷情況具有獨特的優勢。
3.4 BOLD-fMRI
BOLD-fMRI是最基本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其原理是腦組織在執行任務時,相應腦功能區神經元被激活,組織血流量和耗氧量增多,氧合血紅蛋白/脫氧血紅蛋白比值變化,其T2縮短效應減弱,在加權像上表現為信號增強,形成BOLD-fMRI信號。BOLD-fMRI包括靜息態及任務態,在ASD患兒的診療中研究較多的是靜息態,主要通過患兒腦功能連接情況反映相關腦功能的變化。大量研究顯示ASD患兒的神經活動存在異常,他們在認知、語言等區域的腦功能連接較正常兒童減少[29-33]。在一項基于局部一致性(regionalhomogeneity,ReHo)的研究中,學者發現ASD患兒存在多個腦區的自發活動改變,特別是ASD的視覺和語言相關區域的改變[30]。Chen等[31]發現ASD默認網絡的影像學標志物與社會反應度的原始評分和模型因子呈負相關。Borras-Ferris等[32]發現ASD兒童默認網絡區域之間的低連接性,并且左側顳中回與右側顳極之間、左側眶額前額皮質與右側額上回之間的腦功能連接降低程度往往與患者社交溝通能力呈正相關。Kim等[33]研究ASD患兒對日常用語的理解能力時發現,患兒右側額下回的腦激活程度較對照組明顯減少,提示語言功能相關的額葉受損。最近一項研究發現杏仁核-背側前扣帶回/內側前額葉皮層連通性降低與ASD社交障礙嚴重程度相關,而杏仁核紋狀體連接與ASD個體的限制性、重復性行為癥狀嚴重程度相關[34]。由上可知,BOLD-fMRI可發現ASD患兒腦功能連接中的異常,推測相關區域之間的低連接性與ASD的發病有關。
3.5 fNIRS
fNIRS是一種新興的非侵入性腦功能神經影像學技術,通過向特定腦功能區照射近紅外光(650~950 nm),利用近紅外光窗口內生物組織的相對透明度,以神經元激活后局部血氧濃度的變化觀察神經活動,進而探測大腦功能[35-36]。fNIRS具有設備便攜、可移動的優點,可在更自然的環境中研究大腦活動,這意味著fNISR可以更準確地探索ASD的社交溝通障礙[37]。Mazzoni等[37]發現與對照組相比,ASD兒童具有更高的半球間連通性,兩側血流動力學活動有0.02 Hz的波動。有學者[38]發現ASD兒童在額中下回及顳上中回皮質激活與ASD嚴重程度相關,與對照組兒童顯示雙側對稱激活不同,ASD的兒童在額中下回顯示出更多的左側激活,在顳上中回顯示右側化激活。此外,左額中下回較低的激活和更嚴重的重復的行為相關聯。另有學者[39]發現右半球的血流動力學信號在ASD和正常兒童之間的差異性比左半球更高。Haweel等[40]也發現ASD幼兒的血氧飽和水平檢測信號呈偏側化,在左側前側的顳上葉皮層出現低活化,并且這種異常偏側性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fNIRS可探測神經活動引起的局部腦血流變化評估大腦活動狀態,因其具有便攜和較低的環境要求,在嬰幼兒ASD中的應用十分廣泛。
4 總結與展望
ASD是一種復雜的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其病因及發病機制至今尚不明確,對它的研究也一直是熱點及難點。目前廣大學者公認早期對ASD患者行干預治療對他們的預后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臨床亟待各種更加有效的方法對ASD患者進行早期診斷。目前,神經影像學在反映ASD神經病理學改變的研究中取得較好的成果,但與臨床癥狀、基因學的相關性研究仍有不足,單純的神經影像學表現作為診斷ASD的依據尚不能令人信服。未來需要影像組學、基因組學以及人工智能從宏觀、微觀水平為臨床ASD的診斷提供更可靠、更客觀的依據。
作者利益沖突聲明:全體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