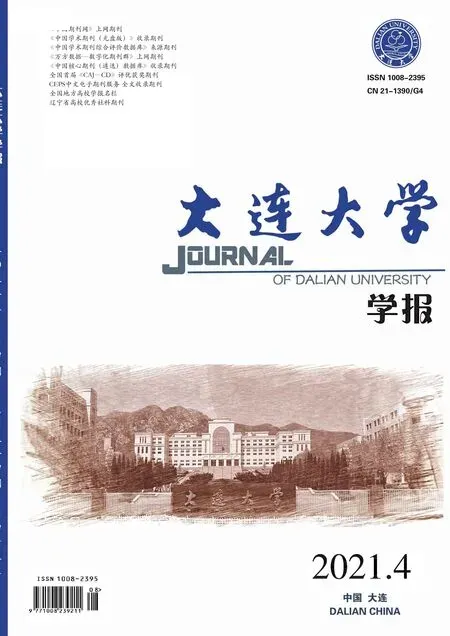論朱自清的文學批評藝術
李 賢
(蚌埠學院 文學與教育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朱自清是散文家、詩人和學者。他既有大量的文學作品又有文學批評理論著作,目前關于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詩歌與詩論研究,如孫玉石的《朱自清現代解詩學思想的理論資源—四談重建中國現代解詩學思想》;二是散文研究,如孫紹振的《背影的美學問題》;三是學術思想和史料研究,如王曉東的《朱自清學術思想研究》、朱金順的《朱自清研究資料》。相比較而言,對他文論整體風格的研究較少,本文把他的文學批評著作視為一個整體,探討他的文學批評藝術。他的文論既強調文學作品對現實、人生的關照,又重視純正的文學趣味;既注重人的主觀意志的表達又注重時代精神的充分表現。他的這一文學批評觀念更多受中國傳統文化與文論的影響,體現了中國哲學重倫理的特征,也體現了現代文學批評對古典文化的繼承。概括來看,朱自清的文學批評藝術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特征。
一、“剎那趣味”的文學審美觀
在朱自清的文論中,出現頻率較高的詞是“趣味”,既有對“一剎那”的捕捉,又有對達到“圓滿剎那” 的追求,這一特征暗含了作家的文學審美觀。前者是就創作主體而言,突出靈感在創作中的意義,認為靈感的瞬間以文字藝術的方式永恒;后者著重于文學價值的實現,在“圓滿剎那”中實現“文學里的美也是一種力”[1]237。這種力既是源于文學的美,又是通過對現實人生的反映引起讀者共鳴的“力之美”。這一特征在朱自清散文中表現的最為明顯,他作品中經典的“一剎那”有“背影”“荷塘”“秦淮河”“春”“匆匆”等。他對自己散文的評價是“雖只一言一動之微,卻包蘊著全個的性格,最要緊的,包蘊著與眾不同的趣味”[2]。他的詩歌大多追求一種“圓滿的剎那”,如《雪朝》中一些清新明快的小詩。“剎那趣味”同樣表現在他的文學批評中,在對新文學第一個十年作家的評論中,他具有中國傳統文論風格的文字既見古典文學文論的蘊藉又見隨時代而增的學術眼界,對茅盾著作的評論不同于阿英等側重社會歷史的批評,他著眼于文學在反映現實生活時所達到的藝術成就,語言美、篇章布局的和諧等也是他評價作品時的標準。朱光潛以“情趣”論詩歌,他的“趣味”中包括“情趣”的美學意義也包括人間煙火,這就是對“味”的把握。“只從一般的所謂時代思潮的順流的趨勢或文藝思想的表面的發展順序,去解釋文藝發展的趨勢。”[3]238這一特征的形成與他的審美觀分不開,他的“趣味”是一個整體同時又代表了文學的審美與實用兩個方面,與阿英在《文學百題》中提出“文學的趣味”意義不同,阿英的“趣味”與梁啟超的“趣味”一致,朱自清是綜合這兩人的智慧并加以藝術的審美。哲學專業的他熱愛中國古典文學,趣味是古典文論中常用的詞語,源自道家的智慧,但不包括其中超然獨立的人生趣味。他的“剎那趣味”是哲學與古典文論的凝練,體現了他對新文學發展的思考,把傳統的詩文評納入現代文學批評體系中。如《論誦讀》《魯迅先生的中國語文觀》等強調音節在文學發展與創作中的意義,與聞一多的“音樂美”相似,他對聞一多作品的評論借鑒并概括了自有《詩經》以來的詩歌理論發展脈絡,是他“趣味”的實踐和整體表現。他自己也曾說過“不擅長做小說”,小說中“剎那”因素遠不如詩歌、散文來的自然,當他以這一審美觀來評價小說時就顯示出局限來。在《什么是文學》《文學的標準與尺度》中提出“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一時代還給一時代”的觀點,一如他散文的溫柔敦厚與平淡從容,這一美學風格也是他文學批評的總體風格。他是以創作和批評兩個方面致力于現代文學詩歌和散文這兩種文體藝術的探索,“文學批評史不止可以闡明過去,并且可以闡明現在,指引將來的路,這也增高了它的地位與趣味。”[1]26朱自清明確指出文學批評要有“趣味”,在三十年代的文學批評中,持這一觀點的并不多,而這恰好是他的文論風格并在文本內部矛盾的呈現,這一特點貫串于他的批評體系中。
他一面強調“剎那”的體驗在創作中的作用,一面要求以這“剎那”的感覺載道,并以美國詩人麥克里希為例論證了“詩以載道”在創作中的普遍性,“這個道是社會的使命。”[4]49朱自清的“道”是儒家的思想,他的創作與批評之路是尋求藝術與思想融合的過程,在強調文學“美”的“五四”時期,他有“道”;在強調文學“責任”的三十年代,他有“趣味”。曾撰文論述“逼真與如畫”作為傳統批評常用語的矛盾感,深感“真與好”兼得不易。從本質上看,他的審美觀也是矛盾的一體,“剎那趣味”的獲得要求較高的藝術敏感,從虛境到實境上偏于虛境的營造,從藝術到人生上偏于藝術對人生的價值,他注重趣味而不是意境,但又強調文學趣味還在于對人生的反映,是傳統的“逼真與如畫”在現代文學批評中的變體。如果按照王富仁對現代文學批評分類來看,朱自清的文學批評既是“學院派”又屬于“為人生派”。與同時代的批評家相比,他更著重于從文學內部發展規律評論作家作品,不因“為人生”而輕視文學的趣味,不輕易相信任何一個“標語和口號”,將文學批評當成一件“嚴肅”的事情去做,這嚴肅中有“趣味”。強調批評主體的情感介入,他的“剎那”離不開想象的參與,“詩也許比別的文藝形式更依靠想象,所謂遠,所謂深,所謂近,所謂妙,都是就想象的范圍和程度而言。想象的素材是感覺,怎樣玲瓏縹緲的空中樓閣都建筑在感覺上。”[5]36其實就正指的是作者在寫評論文章時要有真切的感受,這種真切的感受是自我的經驗,是“有我之境”,這種批評適合篇幅不長的作品,比如詩歌和散文,這也可能就是他寫的小說評論有某種意猶未盡之感的原因。“趣味”是他的審美觀,也是他批評文學作品時的一個標準,他的“趣味”不是無功利的純審美,是文學反映時代與人生的藝術呈現,這兩方面一個是主觀感性的,一個是客觀理性的,這種以感性表現理性、以理性滲透感性的方式與徽州樸學中的“情感哲學”一致。強調直覺感悟也看重內在邏輯的一致;強調批評者情感的主動性也注意創作的時代背景與寫作目的;強調中國傳統文論批評在現代文學批評中的延續性也注重西方文藝理論的介入與影響,這三個方面成為朱自清批評方法的基本特征。
二、“尊情崇志”的文學價值觀
從現代文學思潮變化的角度綜觀朱自清的文學作品,可以發現他對文學與人生、文學與時代關系的演繹始終不脫離文學藝術這一范圍,以“剎那”的靈感尋求文學與人生、文學與時代的契合。從文學價值觀的類型來看,朱自清屬于“尊情崇志”類,“是以人的主觀意志的充分表達和情感的宣泄為取向的文學價值觀念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是把人的意志力量、情感意向及時代精神、人民情緒的表現作為具體的文學價值目標。”[6]165尊情崇志是理解朱自清創作和批評的關鍵,他的創作和批評注重主體情感的融入與再建構,在時代文學之中但又不在主流之內;反映社會現實但又是別樣的視角;以文學的輕柔之美反觀人生中那些不能承受之重。他以兼容并包的態度看待現代文學批評方法與現象,他的詩歌和散文評論具有鮮明的個性化特征,對藝術與美的探討大多集中在這一類作品中。尊情崇志的文學價值觀在創作中有利于充分展現文學自身的屬性,在文學批評中有其自身的局限,有時會限制觀察的視野,比如不能很好地概括現代文學中宏大的時代主題,不能準確地解釋外部環境在文學發展規律中的作用。這一特點在朱自清文論中有明顯的體現,他對聞一多、茅盾等作家作品的評論細致入微,更多是從文學藝術表現的層面論述“趣味”。他很少從社會時代思潮的角度解讀文學,或者說他是透過這些文學表象直接正視文學發展中屬于本質性的因素,即文學以怎樣的方式表達現實生活中的“情、志”,文學批評應該如何發現這其中的“情、志”與“美”。“文學是文字的藝術,文學是人生的語言”“文學最重要的是思想,是默喻的經驗,那是文學的材料”[1]161。與緊密關注時代環境變化的文學批評不同,這里“文字的藝術”“人生的語言”無疑是在強調“美與志”及由此而來“情”,朱自清更偏向于志、情,“志”是有內涵的客觀存在,不是小品文中的“志”,與他的“道”契合。“情”是他的審美,他能將沉重的現實生活在作品中化為淡然、淡泊的心境,蘊蓄成詩意的空靈。而“默喻的經驗”源于既成的文學價值觀和既有的認知體系,與杜威的“藝術經驗”相通,“經驗本身具有令人滿意的情感性質,因為它擁有內在的、通過有規則和有組織的運動而思想的完整性和完滿性。”[7]40朱自清的文學經驗一是源自中國傳統文學與文化,二是新文學發生后中西文化對比下產生的自我判斷,內在的情感性質和審美經驗還是受數千年延續而來的儒家倫理的影響。在現代文學的第一個十年,是對中國傳統文論及文化比較重視的學者之一,特別是在新詩發展道路上,他以嚴謹的學風、深厚的學養在新詩與古典詩詞之間建立橋梁。尊情崇志的文學價值觀在中國文學發展不同時期都有存在,融“詩言志”的儒家內涵與“詩緣情”的審美追求于一體,朱自清的創作和批評是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平衡點。
作為一個經受過“五四”時代思想沖擊的中國傳統學者,他在三十年代的反思與審視似乎更為直觀,早期作品中的迷茫(《毀滅》)焦灼逐漸化為平和從容(《荷塘月色》)。文學凈化心靈的作用是文學性的體現,文學表達人生現實的層面是社會性的訴求,朱自清以“尊情崇志”實現了文本的內在和諧與個人的內心沖突。“五四”新文學階段的“西方”作為“現代”的象征,與他既有的傳統文化理念不斷碰撞,在他創作中體現了“概念”的抽象意義,與其說他受到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不如說他是在時代思潮中重新認識了中國傳統文化與文學的“力之美”。“1921年到1925年的江南時期和1925年到1937年的北京時期。他在這兩個階段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態度,可以概括為三個特征:充滿矛盾的,緩慢發展的,穩健向前的。”[3]89這兩個時期的三個特征是他文學探索與文學價值觀形成的過程,一是在中西、新舊對比中對思考文學的本質屬性;一是在外部環境的變化中探討文學的社會性,對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的推崇,對“情與美”的偏愛,對作家時代責任感的認識,構成了他矛盾糾結的心境。“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就得認識傳統里的種種價值,以及種種評價標準”[1]26,重新認識傳統里的價值是作家們反思“五四”文學時的群體特征,胡適于1923年提出的“整理國故”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文壇表現為集體心理。相比較而言,朱自清的“矛盾”有內在的清醒和堅持,面對“新”不自覺地憶“舊”,思考并直面如何賦予“舊”以“新”的品質,最終在的“尊情崇志”中調和,并貫串于他之后的創作。他的作品大多是從自然中尋找意象,在情與志的統一中呈現溫柔敦厚之美,體現出中國傳統哲學重倫理并尋求倫理和諧的關系,而非西方哲學思想。他的“尊情崇志”不是逸世高蹈,是在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中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不排斥西方文藝思想,是在對比中尋求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共通之處,比如,他認為“文以載道”并非中國獨有,從本質上看“尊情”是遵循文學審美的一面,“崇志”是“載道”,他的“道”是“社會使命”,也就是作家的責任。這可歸因于作家內心的歷史感(historical sense),“它迫使一個人不僅僅以骨子里的他自身一代的感受來寫作……這種歷史感可以使作家變得傳統,同時也會使得他精確地意識到在自己時代所處的位置。”[8]49朱自清兩個階段的變化以及創作時的矛盾心態就是這種意識的反映,他的文學批評也呈現這樣一個階段性特征,早期的“為人生”批評是自我知識體系的碰撞整合,之后專注于“文學的美也是一種力”的批評。
三、“融情入理”的文學批評觀
朱自清文學批評自成系統始于三十年代,“五四”時期“為人生”的批評是他嘗試階段,是以詩歌相關的理論探討為主。盡管執著于“趣味”的實踐,但不能否認社會思潮的變化是促成他文學批評觀形成的重要原因,有研究者指出“三十年代是一個文學批評很盛的時期,這里所謂的盛是指三十年代幾乎所有的文學理論家、作家甚至是文學圈外的都在操文學批評之業”[9]149。這種盛況之下的文學批評一方面激發了文學的多樣性,一方面削弱了文學的獨立性,同時也是文學批評理論迅速成長的時期。在強調文學參與時代變革的社會責任階段,文學的政治批評、社會批評、價值批評等文學的外部批評成為主流,朱自清提出“文學的美也是一種力”是從文本內部批評出發,不同于康德哲學中“力學的壯美”[10]232,他文學的“美之力”首先源于“趣味”,這一“趣味”不是純藝術無功利的,是源于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儒家思想以及和諧美。這是他的美學觀念,自身的性格因素以及中國哲學對他的影響促使他形成“溫柔敦厚”的“實用”思想。因此,他的文學批評不是反功利的,是既要求文學的“情”又要求文學的“理”,這里的“情”是指文學反映表達社會人生時所蘊含的作者情感與文本內部情感,這里的“理”不是哲學意義上的,是指作品中所表現的“道理、事理”,也就是朱自清的“道”,依然不脫儒家倫理的影響,他很少從哲學的角度或者用哲學術語評價文學作品,衡量的標準是“表情和達意”,也很少化用西方的文藝思想。“朱自清僅僅一般地承認異域學殖對于重建中國文學批評的助力……但是寬闊的眼光驅使朱自清專攻傳統的文學批評。”[11]213發現并建立傳統文論與現代文學批評之間的關系,客觀地看待異域學殖在本土學科發展中的作用,這一學術視野不是民族主義,而是在比較中看到了文學的世界性與民族性,以及審美心理的本土化在文學批評中的潛在制約。審美心理有時也是一種傳統文化心理,早在《論語》中就有“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論述,表達的道理就是如何“在情與理的融合中實現語言的力量”。朱自清“文學的美也是一種力”要求批評者具有“融情入理”的能力。
在各類文體中,朱自清的“詩論”卓著,然而他并不是單一的論詩,他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這一學科的發展有系統性論述。史料中有關于他在大學任教時講授“中國文學批評”這門課的記錄,其中對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進行溯源式的研究,對現代文學批評既有個案的分析,也有宏觀整體的概述。“在文學批評里,理論也罷,裁判也罷,似乎都在一面求真,同時求好。”[1]29這里的“真和好”與“逼真和如畫”是一個意思,也是他在不同篇章中經常提及的話題,并且在思考和討論這一問題時常常陷入自我矛盾的漩渦,最終又在“道”與“趣味”的和諧中圓滿,即藝術的真與生活的真以及文學表現“真”時所取得的審美效果和實現的社會價值是衡量作品的標準。這些理論觀點即是他文學價值觀的反映又是他文學批評觀的直接運用,適合于各種文體,與“尊情崇志”相對應,“融情入理”既是文學批評觀又是他文論的風格之一。他不是社會歷史批評者,但他注重文學如何表現“社會的使命”;也不是帶有印象主義的審美批評,強調作品中的情感的體驗,“文學作品之吸引人最大因卻在情感的濃厚”[3]117,但有別于王國維、朱光潛的“審美非功利性”。比如 “文字的藝術,材料便是人生”“文字里的思想是文學的實質,文學之所以佳勝,正在他們所含的思想”[1]237-238。類似的論斷還有不少,表達的是文學的無功利性與功利性兩個方面,也是他作文學批評時的依據。《標準和尺度》一書是他文學批評觀的系統體現,提出了“標準是不自覺地接受了傳統的”“尺度是自覺的修正了傳統的”。他參照的對象是“傳統”,是受文化心理習慣影響的無意識,尺度是隨時代思潮而變化并且不斷擴展自身的內涵。“標準和尺度的分別,在一個變得快的時代最容易覺得出,在道德方面在學術方面如此,在文學方面也如此”[4]16。朱自清從紛繁的文學批評流派中看到關鍵性因素,無論在哪個時代,無論哪一種方法,文學批評的區別在于“標準和尺度”的不同。如果從這一角度考察文學批評方法的差異,可以發現幾乎是一個真理性的判斷。如果說深厚的英文功底是他博覽外國文學書籍時的工具,哲學專業對他的影響則是認識到“文學、文學批評”和“哲學”的不同。無論是作品還是文論,都不是晦澀的文風,也不求深奧的境界,他在《什么是文學》中把胡適的文學三性“懂得性、逼人性、美”概括為 “達意和表情” 兩重性。但不能因此否認哲學在他文學批評中的作用,他的審美觀、文學價值觀、批評觀都是矛盾的統一體,也就是說他以哲學的“矛盾”概觀文學意義上的“矛盾”,并以此解決文學創作、批評中的自我矛盾。哲學的矛盾觀與考據的學術方法是他“融情入理”的途徑,在“文學的考證和批評”中認為“絕對的超然客觀,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須和批評聯系起來”[3]35。他看出絕對超然的客觀與超然的美學在現代文學批評中都是不可能永存的,考證是實事求是,文學批評是否如實反映了“道”。考據法在晚清以前是有影響力的學術方法,是清代徽州樸學這一學派的治學之道,西方學者對中國明清社會歷史的研究中,稱徽州樸學為 “江南學術共同體”,對學者們的辯證思維給予很高的評價。就這一學派的著作來看,他們在對古典文論的考據考證中有不少關于“詩文”的經典論段,是對“詩文評”地再判斷。朱自清的文論以及他對現代文學批評理論的思考呈現出相似的特征,在他的文學世界里,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學術方法、古典文學、儒家倫理占有重要地位,歐洲游學經歷堅定了從“國故”中建設現代文學批評理論的想法,與“拿來主義”相比,他是謹慎的比較、借鑒。
四、結語
把考證和具體的文學批評相聯系,以學術考證的方法考察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以及現代文學批評作為一門學科的建設,對引進的西方批評術語進行追根究底的探討,并結合具體特征思考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的關系或獨特之處。作家的朱自清和學者的他有著不同的風格,前者是寓濃郁于淡然的情感表現、寓深沉于清淺的語言表達;后者是不厭其煩的考證、舉例論證,是清晰、簡潔的理性分析。在朱自清的作品、文論中,“情”以多種形式存在,但都要求“情”中有時代的生活,他認為只表現個人情感、情緒的作品不是好作品,詩文評中強調“獨抒性靈”的論述是不全面的。這是他緣情而文,隱理而深的成就之一。其二,善于運用哲學方法,這種哲學方法調和了他文學批評體系中的自我矛盾,他認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是“相反相成,矛盾的發展”[4]27,而他個人的批評理論也呈現這樣的特征。他的審美觀、文學價值觀、文學批評觀都是矛盾的整體,他講“趣味”但反對“無意義的幽默”,他的很多論述都在表明“文學是情感的,文學也是歷史的”這一觀點。如果單看他的這一“標準”很容易想到社會歷史批評,然而他的這一主張并不是獨立存在,他的另一個 “尺度”是“一切偉大的藝術都是凈化的,安慰人的。”[1]246他的“標準和尺度”總是同時規范著批評的方向,文學凈化心靈是以“動之以情”,文學研究參考“別的學科做根據”是為了“曉之以理”。緣情而文似乎是他所有文學作品、文學批評的最初動機,隱理而深則既關學術視野又關語言的藝術,這個“理”是他的“道”,是他學者的理性思維,有時會借鑒英文的語法書寫中國的語言,用簡明的句子表達繁復的內涵,直白中經得起品味。批評家的審美自覺與學者的嚴謹構成他文論的整體風格。
朱自清的文論在現代文學批評中自成一家,經歷了從嘗試的探索到穩健的糾結兩個階段,同時代學者和后來的研究者都關注于中國文學批評對他的影響,很少關注傳統學術方法對他的影響,他的哲學專業知識很少被提及。而這兩點在他批評中都至關重要,前者形成了視野,后者形成學術特征。“剎那的趣味”在“社會的使命”中尋找;情之所鐘,道之所存;在傳統文論與學術方法中飄逸始終未能超脫。他以實事求是做學問的方法建設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他提出的“標準和尺度”是哲學的矛盾統一,他文論中的“緣情就理”是內在情感哲學的調和,他的文論是現代文學批評對傳統文論的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