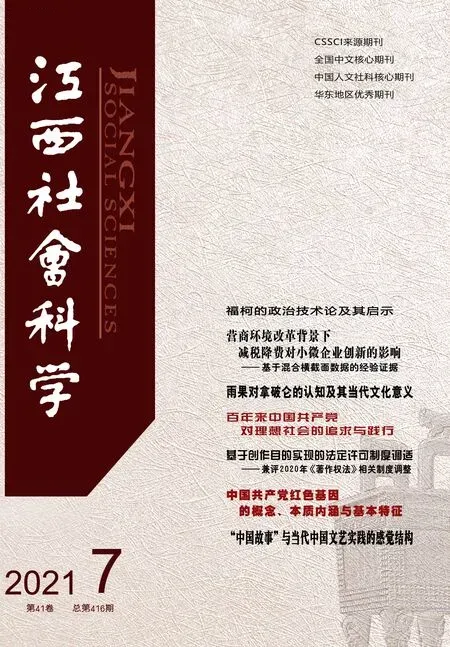福柯的政治技術(shù)論及其啟示
■李福巖
揭示并批判政治技術(shù)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國家的演變及其未來走向,是福柯后現(xiàn)代微觀政治哲學(xué)富有創(chuàng)見性的重要內(nèi)容。通過對(duì)權(quán)力統(tǒng)治方式的獨(dú)特微觀歷史考古與譜系學(xué)研究,福柯提出政治技術(shù)的相關(guān)概念,認(rèn)為權(quán)力對(duì)社會(huì)和個(gè)人統(tǒng)治的方式是一種傳統(tǒng)政治技術(shù)。他把現(xiàn)代國家的本質(zhì)視為日益工具化的政治技術(shù),認(rèn)為現(xiàn)代性政治技術(shù)的日益普遍與強(qiáng)化形成了新的全景敞視與統(tǒng)治,也造成針對(duì)個(gè)人的“全景敞視主義”,走向啟蒙理性自由的反面,還提出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缺乏一套自主的政治技術(shù)。為克服現(xiàn)代性國家治理的困境,福柯提出政治技術(shù)未來發(fā)展要走向政治藝術(shù),形成了政治美學(xué)的自由主義烏托邦。福柯政治技術(shù)論對(duì)深刻認(rèn)識(shí)當(dāng)代西方國家治理的本質(zhì)及問題,深入挖掘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國家治理思想資源,開創(chuàng)性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道路,都具有一定啟示意義。
伴隨政治國家的誕生以及歷史演進(jìn),為實(shí)現(xiàn)政治權(quán)力的現(xiàn)實(shí)有效統(tǒng)治及理想中的運(yùn)行,政治家和思想家們就對(duì)政治技術(shù)開始了從不自覺到自覺的持續(xù)思考,提出了性質(zhì)各異、類型不同的政治技術(shù)方案,即國家治理策略。當(dāng)國家治理實(shí)踐發(fā)展到資產(chǎn)階級(jí)統(tǒng)治的現(xiàn)代國家的時(shí)候,在現(xiàn)代科技的助推下,思想家們對(duì)政治技術(shù)的思考以更加自覺的理論形態(tài)展現(xiàn)出來,并達(dá)到政治理智的時(shí)代頂點(diǎn)。在對(duì)政治技術(shù)自覺思考的長河中,法國后現(xiàn)代政治哲學(xué)家福柯的批判性反思深刻而獨(dú)特,對(duì)進(jìn)一步思考政治技術(shù)的基礎(chǔ)理論性問題、政治技術(shù)的歷史與實(shí)踐,正確批判分析現(xiàn)代自由主義國家治理,建構(gòu)性地思考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等問題,都具有基礎(chǔ)理論意義與一定現(xiàn)實(shí)價(jià)值。
一、政治技術(shù)是權(quán)力對(duì)社會(huì)和個(gè)人統(tǒng)治的傳統(tǒng)方式
在福柯之前,思考如何實(shí)現(xiàn)最好的統(tǒng)治與治理,即實(shí)現(xiàn)善治,是歷史上的統(tǒng)治者及其理論家的必修課程。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xué)提出多種類型的國家善治方案,典型的有道家的“無為而治”、儒家隆禮重法的“中庸之治”以及法家的“以術(shù)治國”等。就曾熏陶與滋養(yǎng)福柯政治技術(shù)思想成長的西方治國思想方案的背景與前提來說,從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的中庸之治,到古羅馬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中世紀(jì)阿奎那的神權(quán)政治統(tǒng)治論,再到近代以馬基雅維利等為代表的歐洲啟蒙思想家們對(duì)現(xiàn)代國家治理理性思考先河的開啟等,都在以不同方式整體思考國家統(tǒng)治與治理的道與術(shù)。
從古代傳統(tǒng)國家統(tǒng)治方案到現(xiàn)代國家治理方案的變遷,首先折射出建筑在人類社會(huì)之上的國家統(tǒng)治形式的歷史演進(jìn)過程,借用并改造韋伯的解釋來說,這是國家施行統(tǒng)治的方案開始以家族和宗教為典型形式的魅力型統(tǒng)治為主,到以宗主、父權(quán)、封建制度為典型形式的傳統(tǒng)型統(tǒng)治為主,再到以科層制為典型形式的現(xiàn)代法理型統(tǒng)治為主的發(fā)展過程。深入理解國家治理方案、策略的歷史變遷,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gè)從思考如何實(shí)現(xiàn)君主的更好統(tǒng)治、權(quán)術(shù)的有效運(yùn)用,到思考如何實(shí)現(xiàn)更好的治理、實(shí)現(xiàn)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的劃界分治的政治智慧發(fā)展過程。這也是治理主體從神到人、從政治理性的迷誤到政治理性啟蒙的歷史發(fā)展過程。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差不多和哥白尼的偉大發(fā)現(xiàn)同時(shí),國家的引力定律也被發(fā)現(xiàn)了:國家的重心是在它本身中找到的……先是馬基雅維利、康帕內(nèi)拉,后是霍布斯、斯賓諾莎、許霍·格勞秀斯,直至盧梭、費(fèi)希特、黑格爾則已經(jīng)開始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了,他們從理性和經(jīng)驗(yàn)出發(fā),而不是從神學(xué)出發(fā)來闡明國家的自然規(guī)律。”[1](P227)
深受馬克思?xì)v史分析方法論的啟發(fā),福柯逐漸開始對(duì)國家治理技術(shù)、政治技術(shù)的微觀探索。福柯說自己是個(gè)不帶引號(hào)的馬克思主義者,直言自己繼承馬克思的歷史分析方法。馬克思的現(xiàn)代性政治批判及其歷史主義方法論深深影響了福柯,并為他所借用來深入考察精神病院、監(jiān)獄、學(xué)校、工廠等現(xiàn)代性政治權(quán)力的微觀運(yùn)行管道,揭露與批判權(quán)力對(duì)社會(huì)、個(gè)人權(quán)利的日益加強(qiáng)的、無孔不入的監(jiān)控與宰治。尤其需要注意,福柯從張揚(yáng)個(gè)體主體多樣性權(quán)利和自由的視角與價(jià)值觀念的理論旨趣出發(fā),展開對(duì)國家權(quán)力的譜系學(xué)研究與知識(shí)考古,即對(duì)政治權(quán)力的微觀歷史反思與現(xiàn)代性批判,逐步提出“權(quán)力技術(shù)學(xué)”“政府統(tǒng)管術(shù)”“政治技術(shù)”等概念,將研究重心逐漸轉(zhuǎn)向了國家治理問題。正如有論者所說:“探討西方治理史和治理技藝是福柯后期政治哲學(xué)的重要學(xué)術(shù)使命。”[2]
在1975年的《規(guī)訓(xùn)與懲罰》一書中,福柯提出“把懲罰視為一種政治策略”,“把權(quán)力技術(shù)學(xué)變成刑罰體系人道化和對(duì)人的認(rèn)識(shí)這二者的共同原則”。[3](P25)在1976年的《必須保衛(wèi)社會(huì)》一書中,福柯提出:“在馬基雅維里那里,力量關(guān)系主要被描述為統(tǒng)治者手中的政治技術(shù)。”[4](P154)從1977年起,福柯將研究重點(diǎn)轉(zhuǎn)向“政府統(tǒng)管術(shù)”,在法蘭西學(xué)院的系列演講中提出“我們生活在政府統(tǒng)管術(shù)的新時(shí)代”[5](P656)。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中,福柯詳細(xì)考察古希臘羅馬執(zhí)政官、基督教牧領(lǐng)、近代以來的管治、自由主義的節(jié)制性等西方治理史及其技藝問題。1982年10月,福柯在美國的學(xué)術(shù)演講會(huì)上宣讀《統(tǒng)治個(gè)人的政治技術(shù)》一文,進(jìn)一步明確闡發(fā)“統(tǒng)治個(gè)人的政治技術(shù)”[6](P92)概念。
理解福柯的政治技術(shù)及其相關(guān)概念,首先應(yīng)看到它來自于對(duì)權(quán)力統(tǒng)治、政府統(tǒng)管的歷史分析,又止步于對(duì)歷史上的權(quán)力技術(shù)、政府統(tǒng)管術(shù)的微觀分析,把政治技術(shù)看成權(quán)力對(duì)個(gè)人統(tǒng)治的傳統(tǒng)方式基礎(chǔ)上的永恒方式。通過對(duì)權(quán)力統(tǒng)治、政府管制的歷史分析,福柯得出的觀念是,各種統(tǒng)治類型的變遷只不過是一種以暴易暴、以一種統(tǒng)治取代另一種統(tǒng)治而已,進(jìn)而提出“我們不能擺脫統(tǒng)治,正如我們不能擺脫歷史”[4](P99)。即是說,人類不能擺脫權(quán)力統(tǒng)治的歷史,這是永恒的。在此前提下,人類對(duì)國家的理性反思就像馬基雅維利那樣,不必反思權(quán)力的合法性問題及其道義論、目的論的未來,只需反思實(shí)現(xiàn)更好統(tǒng)治的技術(shù)問題,或許能逐漸增進(jìn)個(gè)人的自由與權(quán)利。這種對(duì)權(quán)力的微觀分析方法,從馬克思的歷史分析方法論起步后又有意避開,試圖開辟現(xiàn)代性政治分析的新視域與新方法,走出自由的新路徑來,然而卻因陶醉于個(gè)體多樣性權(quán)利與自由的迷宮,故而從根本上迷失了人類解放歷史前行的大方向。
其次,應(yīng)看到它來自于結(jié)構(gòu)主義的權(quán)力分析模式,福柯以此看到國家機(jī)器對(duì)社會(huì)、個(gè)人權(quán)利的壓制,但因其審視權(quán)力的目光過于專注解剖政治權(quán)力的“細(xì)微管道”、微觀運(yùn)行技術(shù),又有意拋開政治上層建筑的變革源于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根本性變革,進(jìn)而異質(zhì)于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解放與人類解放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xué)與歷史唯物主義科學(xué)方法論。用福柯的話說:“我們有關(guān)權(quán)力本質(zhì)的研究,不應(yīng)該指向統(tǒng)治權(quán)的法律大廈、國家機(jī)器和與之相伴的意識(shí)形態(tài),而應(yīng)該指向權(quán)力的支配和具體操作者,指向臣服的形式和在局部系統(tǒng)的運(yùn)用及變化,指向戰(zhàn)略的機(jī)器。在權(quán)力的研究中,我們應(yīng)該避開利維坦的模式。我們應(yīng)該避開法定的統(tǒng)治權(quán)和國家機(jī)構(gòu)的有限領(lǐng)域,并把我們對(duì)權(quán)力的分析建立在對(duì)支配的技術(shù)和戰(zhàn)術(shù)的研究之上。”[7](P236)“我們并不是要使國家—市民社會(huì)的區(qū)分成為一種歷史的和政治的普遍,該普遍能夠使人們審問所有的具體系統(tǒng),而是要從中看到一種特殊的治理技術(shù)學(xué)自身所特有的一種圖式化樣式。”[8](P282)
借助于結(jié)構(gòu)主義的權(quán)力分析,福柯也看到建筑在社會(huì)之上的各類型國家權(quán)力對(duì)社會(huì)和個(gè)人的統(tǒng)治,因此,他把近現(xiàn)代自由主義的權(quán)利主張變換為必須保衛(wèi)社會(huì)、個(gè)人權(quán)利,但不能推翻凌駕于社會(huì)之上并對(duì)社會(huì)進(jìn)行壓迫的國家權(quán)力及其制度、體制與機(jī)構(gòu),只能對(duì)國家或政府權(quán)力運(yùn)行的細(xì)微技術(shù)管道進(jìn)行干預(yù)與調(diào)整。這也即是只能對(duì)規(guī)訓(xùn)與懲罰這類權(quán)力技術(shù)進(jìn)行解剖、批判與調(diào)整。所謂權(quán)力技術(shù),“包括一系列手段、技術(shù)、程序、應(yīng)用層次、目標(biāo)。它是一種權(quán)力‘物理學(xué)’或權(quán)力‘解剖學(xué)’,一種技術(shù)學(xué)”[3](P242)。所謂政府統(tǒng)管術(shù),就是建立在政府機(jī)構(gòu)制度的基礎(chǔ)上,由把人遷來引去的程序、技術(shù)和方法所構(gòu)成的整體。[6](P93)權(quán)力技術(shù)、政府統(tǒng)管術(shù)都屬于國家維護(hù)與施行統(tǒng)治的政治技術(shù),現(xiàn)代政治技術(shù)更加注重對(duì)個(gè)人的統(tǒng)治。
最后,還應(yīng)看到它是福柯對(duì)現(xiàn)代性政治展開理論批判的新話語方式。政治技術(shù)概念是解釋傳統(tǒng)政治統(tǒng)治方式的新話語。有人就有技術(shù),有人類社會(huì)就有社會(huì)技術(shù),有政治就有政治技術(shù)。古代傳統(tǒng)國家曾使用王霸之道、權(quán)術(shù)、治國術(shù)、御人術(shù)、統(tǒng)治技藝等類似政治技術(shù)的概念,只是在統(tǒng)治者如何治吏、治民等意義上使用政治技術(shù)概念的部分內(nèi)涵,并未明確自覺提出政治技術(shù)的概念。隨著國家統(tǒng)治方式的歷史變遷,以及現(xiàn)代科技的快速發(fā)展與應(yīng)用,出現(xiàn)了政治化的技術(shù)與技術(shù)化的政治日益互為工具的融合發(fā)展態(tài)勢(shì)。在此時(shí)代發(fā)展背景之下,福柯從科學(xué)技術(shù)與政治的關(guān)系、政治御用的技術(shù)兩個(gè)維度,即從技術(shù)哲學(xué)、政治哲學(xué)兩個(gè)維度展開反思、“從后思索”,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政治技術(shù)概念,進(jìn)而給政治統(tǒng)治方式的闡釋注入新的話語方式。
政治技術(shù)概念是微觀政治權(quán)力批判的新話語。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續(xù)了馬克思的現(xiàn)代性政治批判精神,但又不同于馬克思對(duì)現(xiàn)代性政治完整而徹底的、從宏觀整體到微觀局部的激烈批判,福柯以政治技術(shù)的新話語揭露政治權(quán)力對(duì)個(gè)人權(quán)利的微觀宰制,希望人們以警惕的目光、多一雙慧眼去發(fā)現(xiàn)那些無時(shí)不在、無處不在、運(yùn)行隱蔽的權(quán)力詭計(jì)與陰謀。不同于對(duì)政治權(quán)力的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追問,不同于純粹思辨科學(xué)的旁觀態(tài)度,類似于杜威提出的指導(dǎo)社會(huì)學(xué)與政治學(xué)的技術(shù)之學(xué),“這是工具主義的態(tài)度,便是實(shí)驗(yàn)的態(tài)度”[9](P9)。福柯的政治技術(shù)概念也是對(duì)社會(huì)政治問題進(jìn)行改良的、零碎的解決觀念策略,更希望給出政治技術(shù)的合理使用界限與陽謀。他也曾把這種政治技術(shù)的“微觀分析”“地圖繪制術(shù)”稱為“權(quán)力的微觀物理學(xué)”[10](P100),是一種不尋找原點(diǎn)、不尋找永恒、不探求本質(zhì),只是探尋政治的皮膚與褶皺之學(xué)。
二、現(xiàn)代國家治理的政治技術(shù)發(fā)展日益普遍與強(qiáng)化
福柯探討西方國家治理技術(shù)從古代到現(xiàn)代的發(fā)展歷史,把政治哲學(xué)研究的重心從宏觀問題轉(zhuǎn)向微觀問題,從政治國家的合法性問題轉(zhuǎn)向國家治理的政治技術(shù)的合理性問題,實(shí)現(xiàn)了一次政治哲學(xué)研究視域的轉(zhuǎn)換與話語方式的創(chuàng)新,為其深刻反思現(xiàn)代國家治理的政治技術(shù)奠定了價(jià)值觀與方法論基礎(chǔ)。由此出發(fā),福柯把現(xiàn)代國家治理的本質(zhì)理解為現(xiàn)代性政治技術(shù),并對(duì)其進(jìn)行了更加深刻的政治解剖與刻畫。
首先,福柯從治理工具的視角出發(fā)對(duì)現(xiàn)代國家的本質(zhì)進(jìn)行了新界定,把國家視為日益工具化的治理技術(shù)、政治技術(shù)。通過深入解剖與微觀分析國家治理的運(yùn)行,尤其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國家統(tǒng)治從建立管治到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再到新自由主義的運(yùn)行演變,福柯以治理技術(shù)為中心觀測(cè)點(diǎn),察看國家統(tǒng)治的合法性變遷,將國家統(tǒng)治類型與理由等的演變視為治理技術(shù)、政治技術(shù)的工具化變遷過程。進(jìn)而,福柯把現(xiàn)代性國家本質(zhì)視為現(xiàn)代性的治理技術(shù)、政治技術(shù)。由此加以放大,現(xiàn)代性在福柯的理論視野中觀測(cè)到的重要景觀,不再是抽象的“社會(huì)的國家化”,即政治國家公權(quán)力對(duì)社會(huì)私權(quán)利領(lǐng)域日益彌漫性的統(tǒng)治,而是具體的“國家的‘治理化’”[11](P92),即政治技術(shù)對(duì)社會(huì)私權(quán)利領(lǐng)域日益微觀的治理。正如英國學(xué)者萊姆克等所說:“對(duì)福柯而言,國家本身就是一種‘治理技術(shù)’。”“與其說福柯把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技術(shù)視為社會(huì)的一種轉(zhuǎn)變,倒不如說視為社會(huì)的終極目的。”[12](P10-11)
把國家的本質(zhì)視為政治技術(shù),把國家的變遷視為治理技術(shù)的變遷,把現(xiàn)代國家視為日益強(qiáng)化的現(xiàn)代理性政治技術(shù),這是福柯在國家觀念上的新表達(dá)。這不同于把國家定義為倫理共同體、政治組織、政治機(jī)構(gòu)、政治地理等的傳統(tǒng)概念表達(dá)方式,也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概念,但又受到馬克思主義國家概念的影響且與其有相似之處。與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概念一樣,福柯也認(rèn)為國家是統(tǒng)治工具。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概念是從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與上層建筑的角度、階級(jí)分析的角度得出的統(tǒng)治工具概念,即國家在本質(zhì)上是階級(jí)壓迫的暴力工具,是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和利益的表現(xiàn)。而福柯的國家概念既拋棄了近現(xiàn)代西方自由主義的契約論分析模式,即“把契約作為政治權(quán)力的模型”——“契約-壓迫的圖式”,又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對(duì)權(quán)力的經(jīng)濟(jì)分析”模式,吸收了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賴希呼喚性解放的權(quán)力壓抑分析模式與尼采的生命-權(quán)力意志分析模式,把國家權(quán)力統(tǒng)治看成對(duì)外進(jìn)行征服戰(zhàn)爭(zhēng)的技術(shù)工具、對(duì)內(nèi)進(jìn)行壓抑與鎮(zhèn)壓的技術(shù)工具的政治技術(shù)總和。對(duì)于福柯的現(xiàn)代國家治理而言,這是從契約統(tǒng)治論走向統(tǒng)治階級(jí)壓迫論,再到戰(zhàn)爭(zhēng)-壓抑的政治技術(shù)論的轉(zhuǎn)變過程,正如福柯所說:“它不試圖根據(jù)契約-壓迫的圖式來分析政治權(quán)力,而是根據(jù)戰(zhàn)爭(zhēng)-鎮(zhèn)壓的圖式。”[4](P15)“近年來我所有的工作都圍繞著戰(zhàn)爭(zhēng)-壓抑的方案,我一直都在運(yùn)用這種方案。”[7](P227)
其次,現(xiàn)代國家治理的政治技術(shù)日益普遍廣泛,形成了新的“全景式統(tǒng)治”。通過對(duì)社會(huì)生活、日益國家治理化的現(xiàn)代性社會(huì)政治生活的鄉(xiāng)野胡同、微觀領(lǐng)域的細(xì)致考察,福柯指認(rèn)現(xiàn)代性政治技術(shù)日益普遍廣泛滲透到經(jīng)濟(jì)、教育、醫(yī)療、家庭等社會(huì)生活各領(lǐng)域。就是說,現(xiàn)代性政治技術(shù)對(duì)社會(huì)的控制與統(tǒng)治已無孔不入,形成新的“全景敞視主義”。在福柯看來,在古代傳統(tǒng)國家中,最古老的君主最古老的夢(mèng)想是“全景式統(tǒng)治”,君主是全景的中心。就是說,古老的統(tǒng)治者希望像上帝那樣成為洞察官吏與全民秋毫的全聽全視者,而非相信、依靠、為了人民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對(duì)于政治、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關(guān)系相對(duì)簡(jiǎn)單、君權(quán)一統(tǒng)天下的傳統(tǒng)封閉國家治理來說,“全景式統(tǒng)治”的實(shí)現(xiàn)尚且是君主理想中的統(tǒng)治圖景,那么,對(duì)領(lǐng)域日益分離獨(dú)立、市場(chǎng)日益開放、資本加速全球流動(dòng)的現(xiàn)代國家,權(quán)力的新全景敞視與統(tǒng)治又是怎樣可能的呢?
福柯認(rèn)為,如果人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到國家宏觀政治權(quán)力的運(yùn)行上,或者只把注意力集中到政府政治法律的組織機(jī)構(gòu)的運(yùn)行上,或者只以審視傳統(tǒng)國家治理術(shù)的慣性思維和老眼光來審視現(xiàn)代資本主義政治技術(shù)發(fā)展的新時(shí)代,那都是看不到權(quán)力的新全景敞視與統(tǒng)治的。因此,人們要把審視權(quán)力的目光進(jìn)一步收攏并聚焦到權(quán)力的細(xì)微運(yùn)行管道、技術(shù)上來,從而以此來審視權(quán)力技術(shù)在工廠、學(xué)校、醫(yī)院、媒體、家庭等社會(huì)及私人生活領(lǐng)域中的細(xì)微運(yùn)行,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這種權(quán)力的新全景敞視與統(tǒng)治的微觀具體運(yùn)行新軌跡。他認(rèn)為:“在整個(gè)古典時(shí)代有一種全面的規(guī)訓(xùn)普及趨勢(shì)。”[3](P235)這種新的全面規(guī)訓(xùn)吸收教育、軍隊(duì)、醫(yī)學(xué)、精神病學(xué)、心理學(xué)等的規(guī)訓(xùn)模式,使社會(huì)在總體上變成“一個(gè)規(guī)訓(xùn)社會(huì)”“一個(gè)監(jiān)視社會(huì)”,“個(gè)人被按照一種完整的關(guān)于力量與肉體的技術(shù)而小心地編織在社會(huì)秩序中。……處于全景敞視機(jī)器中,受到其權(quán)力效應(yīng)的干預(yù)。這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因?yàn)槲覀兪瞧錂C(jī)制的一部分”。[3](P243)他還借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3章的話語分析證明,伴隨西方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的飛速發(fā)展,資本積累技術(shù)與人員積聚技術(shù)也很快擺脫傳統(tǒng)的粗暴的權(quán)力形式,形成“一種巧妙的、精致的征服技巧”,“即‘政治解剖學(xué)’能夠運(yùn)用于極其多樣化的政治制度、機(jī)構(gòu)和體制中。……權(quán)力的全景敞視方式——它處于基礎(chǔ)的、技術(shù)的、純物理的層次上——并不是直接依賴于一個(gè)社會(huì)的重大法律—政治機(jī)構(gòu),也不是它們的直接延伸。但它也不是完全獨(dú)立的”。[3](P247-248)當(dāng)然,這種權(quán)力的新全景敞視與統(tǒng)治是“在建構(gòu)知識(shí)的條件下才能運(yùn)轉(zhuǎn),知識(shí)的建構(gòu)對(duì)于它來說既是后果也是得以發(fā)揮作用的條件”[13](P40)。就是說,現(xiàn)代科技發(fā)展與現(xiàn)代權(quán)力運(yùn)行相互助力、共謀,從而使權(quán)力的新全景敞視與統(tǒng)治從具體微觀到宏觀總體上的順暢運(yùn)行成為現(xiàn)實(shí)。
再次,現(xiàn)代國家治理的政治技術(shù)日益強(qiáng)化,形成“全景敞視主義”,走向啟蒙理性自由的反面。在福柯看來,現(xiàn)代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統(tǒng)治的確立和發(fā)展過程,是標(biāo)志性的宏觀政治法律制度與陰影中的“微觀權(quán)力”“細(xì)小的、日常物理機(jī)制”相輔相成,也就是明暗兩方面的政治技術(shù)日益普遍化和強(qiáng)化的過程,形成“全景敞視主義”。“全景敞視主義是一種新的‘政治解剖學(xué)’的基本原則。其對(duì)象和目標(biāo)不是君權(quán)的各種關(guān)系,而是規(guī)訓(xùn)(紀(jì)律)的各種關(guān)系。”[3](P234)現(xiàn)代社會(huì)的規(guī)訓(xùn)以狡猾的政治技術(shù)把權(quán)力隱蔽起來運(yùn)行,而使權(quán)力統(tǒng)治以退為進(jìn)、無形而無處不在,看似放松,實(shí)則加強(qiáng)對(duì)人的肉體與精神的控制,以法律、紀(jì)律、規(guī)則、效率等各種形式加強(qiáng)對(duì)個(gè)人的馴服,是一個(gè)以自由和正義之諸名義樹立權(quán)力新威嚴(yán)的過程。“這是一個(gè)從封閉的規(guī)訓(xùn)、某種社會(huì)‘隔離區(qū)’擴(kuò)展到一種五線譜變化的‘全景敞視主義’機(jī)制的運(yùn)動(dòng)。”[3](P242)
一方面,現(xiàn)代政治技術(shù)的日益強(qiáng)化對(duì)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huì)走上穩(wěn)定發(fā)展道路以及形式自由的實(shí)現(xiàn),都具有重要功能和積極效果。福柯對(duì)現(xiàn)代政治技術(shù)的肯定類似于托克維爾對(duì)現(xiàn)代法國、美國革命后的政治哲學(xué)反思,法國之所以沒有像美國那樣很快走上穩(wěn)定繁榮的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是因?yàn)榉▏挥泻暧^抽象政治哲學(xué)理論的“大砍刀”,沒有美國那樣微觀具體政治技術(shù)的“針線活”。
另一方面,現(xiàn)代政治技術(shù)的日益強(qiáng)化造成針對(duì)個(gè)人規(guī)訓(xùn)日益強(qiáng)化的“全景敞視主義”,走向了啟蒙理性自由的反面。“全景敞視主義則是具有普遍性的強(qiáng)制技術(shù)。……‘啟蒙運(yùn)動(dòng)’既發(fā)現(xiàn)了自由權(quán)利,也發(fā)明了紀(jì)律。”[3](P249)受到邊沁設(shè)計(jì)的圓形監(jiān)獄監(jiān)視系統(tǒng)的啟發(fā),福柯深入反思現(xiàn)代資本主義從吶喊自由、平等、人權(quán)起步,卻日趨走向政治權(quán)力技術(shù)對(duì)個(gè)人生活與自由的全面監(jiān)視、規(guī)訓(xùn),走向了18世紀(jì)啟蒙理性自由的反面。因此,他把現(xiàn)代資本主義試圖監(jiān)視、規(guī)訓(xùn)整個(gè)社會(huì)及個(gè)人的烏托邦稱為“全景敞視主義”。在此規(guī)范性無所不在的現(xiàn)代社會(huì)生活中,教師、醫(yī)生等社會(huì)工作者統(tǒng)統(tǒng)都變成了“警察”“法官”,形成以新規(guī)范權(quán)力為主要支柱的社會(huì)“監(jiān)獄網(wǎng)絡(luò)”,現(xiàn)代性政治技術(shù)規(guī)訓(xùn)下的個(gè)人既是完全自由的,又完全被排除在自由之外。
最后,福柯認(rèn)為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缺乏一套自主的政治技術(shù)。福柯的政治哲學(xué)主要以現(xiàn)代性資本主義社會(huì)政治為批判研究對(duì)象,其政治技術(shù)論的宗旨是在承認(rèn)現(xiàn)代資本主義國家政權(quán)合理性的前提下,批判與反思現(xiàn)代自由主義治理技術(shù)的改良與發(fā)展問題。在此理論批判反思的過程中,雖然他對(duì)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沒有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但也對(duì)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接受,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歷史與實(shí)踐也有過一些零星思考。在他看來,與現(xiàn)代資本主義國家政權(quán)相比較,現(xiàn)代社會(huì)主義國家政權(quán)同樣具有歷史合理性、經(jīng)濟(jì)合理性、行政合理性,但是,現(xiàn)代社會(huì)主義國家缺少與其國家理論相配套的治理理由、治理合理性的界定,尤其缺乏一套自主的政治技術(shù):“社會(huì)主義所缺少的不是一套國家理論而是一個(gè)治理理由……我認(rèn)為并不存在自主的社會(huì)主義治理術(shù)。不存在社會(huì)主義的治理合理性。”[8](P76)福柯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社會(huì)主義國家早期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并且期望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的政治技術(shù)與其國家理論匹配,在總結(jié)與反思現(xiàn)代性國家治理歷史、實(shí)踐與技術(shù)的基礎(chǔ)上,找到一套面向社會(huì)與人的未來發(fā)展的、更加合理的自主創(chuàng)新的政治技術(shù)。
三、政治技術(shù)未來發(fā)展的走向是政治藝術(shù)
在深入具體考察與分析權(quán)力對(duì)社會(huì)和個(gè)人統(tǒng)治的政治技術(shù)發(fā)展歷史的基礎(chǔ)上,福柯看到現(xiàn)代國家治理的政治技術(shù)對(duì)個(gè)人日益普遍和強(qiáng)化的新全景敞視與統(tǒng)治,現(xiàn)代性政治技術(shù)雙刃劍的另一面存在著針對(duì)個(gè)人權(quán)利和自由的新宰治,面臨走向啟蒙理性自由反面的新歧途。為走出現(xiàn)代政治技術(shù)發(fā)展面臨的新危機(jī)、新困境,福柯從改良自由主義的立場(chǎng)出發(fā),試圖以治理藝術(shù)、政治藝術(shù)來矯正政治技術(shù)的陰暗面,并把政治藝術(shù)看作政治技術(shù)發(fā)展的最高境界與未來,走向政治美學(xué)的自由主義烏托邦。
首先,政治有其美學(xué)之維,政治技術(shù)有其藝術(shù)之維,這是從政治技術(shù)走向政治藝術(shù)的理論與現(xiàn)實(shí)邏輯前提。從理論邏輯上說,事物都有真、善、美三個(gè)基本維度,都可以用這三個(gè)基本維度加以考量。也就是說,政治可以有美學(xué)之維,技術(shù)可以有藝術(shù)之維,而且在歷史和現(xiàn)實(shí)中政治也有崇高、偉大之處,政治技術(shù)也有高超政治藝術(shù)之境界。人們應(yīng)該能夠從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與理性邏輯上發(fā)現(xiàn)政治之美。正如近代法國政治哲學(xué)家貢斯當(dāng)所說:“政治應(yīng)該是美的,也可以是美的。”華裔法國學(xué)者高宣揚(yáng)還對(duì)福柯的生存美學(xué)與“治理的藝術(shù)及政治的審美性”[14](P893-894)進(jìn)行了專門探討。然而,政治、政治技術(shù)的諸多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發(fā)展的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也呈現(xiàn)更多政治之丑惡、政治技術(shù)之陰謀詭計(jì),進(jìn)而形成大多數(shù)人的政治常識(shí)與偏見。直面政治之丑惡、政治技術(shù)之陰謀,福柯從政治、政治技術(shù)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發(fā)展中尋找政治之美好、政治技術(shù)之陽謀。因此,他說:“‘治理術(shù)’這個(gè)邪惡的名詞”[11](P100),“‘政治’這個(gè)詞總是用作貶義”,但來源于《圣經(jīng)》的政治概念“已經(jīng)變?yōu)槟撤N去掉貶義的東西”。[11](P216-217)由惡向善,丑中尋美,從政治技術(shù)走向政治藝術(shù),福柯面向未來的自由主義烏托邦賦予政治及政治技術(shù)發(fā)展的積極內(nèi)涵。他說:“政治類似于數(shù)學(xué),類似于治理藝術(shù)的理性形式”[11](P256),“對(duì)人進(jìn)行治理的藝術(shù)”是真正的科學(xué)反思、一切知識(shí)的知識(shí),“一切藝術(shù)的藝術(shù),治理人的藝術(shù)”[11](P130)。就是說,政治美學(xué)是大寫的美學(xué),政治藝術(shù)是大寫的藝術(shù),政治美學(xué)、政治藝術(shù)才是政治的靈魂與真諦,更是與人的生存美學(xué)相匹配的政治未來發(fā)展的走向與旨?xì)w。
其次,從政治技術(shù)走向政治藝術(shù),是對(duì)傳統(tǒng)國家治理的政治藝術(shù)根脈的接續(xù)與現(xiàn)代性政治技術(shù)的新啟蒙。中國先秦時(shí)期的“天下大同”“禮樂教化”“仁政藝術(shù)”等傳統(tǒng)政治智慧中,就蘊(yùn)涵著國家治理的政治藝術(shù)根脈,有學(xué)者將其稱為“一種最徹底的政治美學(xué)”[15](P157)。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家勾畫的完美政治圖景也屬于政治美學(xué),而且首次指明政治作為統(tǒng)治者的技藝是“真正科學(xué)地理解的統(tǒng)治技藝”[16](P144),蘊(yùn)涵著西方傳統(tǒng)國家治理的政治藝術(shù)根脈。中世紀(jì)阿奎那借助古希臘政治智慧,以信仰、希望和愛的原則超驗(yàn)虛幻地把政治藝術(shù)的頂點(diǎn)推向了天國上帝,塵世王國所追求的政治藝術(shù)境界要遵循上帝所創(chuàng)造的自然法則運(yùn)行,才能在地上建成最好的國家治理樣態(tài),這構(gòu)成傳統(tǒng)西方國家治理的宗教神學(xué)的政治藝術(shù)根脈。近代西方文藝復(fù)興與啟蒙運(yùn)動(dòng)以降,科技理性與資本邏輯把政治智慧中的政治藝術(shù)根脈淹沒在政治技術(shù)與利己主義的冰水之中,同時(shí)也迎來復(fù)興與啟蒙政治藝術(shù)的新契機(jī)。正是在對(duì)古希臘以來的政治藝術(shù)思想根脈深入挖掘的基礎(chǔ)上,福柯才提出政治藝術(shù)概念,并試圖以此克服政治技術(shù)的現(xiàn)代性發(fā)展出現(xiàn)的新危機(jī)、新問題。
再次,政治藝術(shù)是織工的藝術(shù),是以和諧與友誼把所有人結(jié)成一個(gè)整體即國家,并把人們引向至高的幸福。福柯借用柏拉圖《政治家》的觀念,把政治家視為紡織工人,把政治藝術(shù)比作紡織藝術(shù)而非一切都管的牧人藝術(shù),政治、政治家及政治活動(dòng)“把不同的要素相互聯(lián)系起來”,“如紡織工人把經(jīng)線和緯線聯(lián)系起來”。他說:“這種藝術(shù)是要把所有人團(tuán)結(jié)成‘一個(gè)整體,這個(gè)整體的基礎(chǔ)是和諧和友誼’。這就是政治紡織工,通過其特殊的藝術(shù),通過與所有其他人不同的神奇藝術(shù),形成‘國家的全體人民的集體,奴隸和自由人都被裝入這個(gè)神奇的織物之中’。這樣人們才被引向至高的幸福,最終成為一個(gè)國家。”[11](P127)深思可見,福柯政治藝術(shù)、紡織藝術(shù)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政治國家誕生以來一直在解決而從未真正解決的問題,實(shí)質(zhì)是要解決使政治國家成為真正的而非虛幻的共同體這樣一個(gè)不能解決的問題。西方現(xiàn)代性政治理智以自由、平等、博愛所構(gòu)想的和諧共同體與千年王國,在實(shí)踐中破產(chǎn)了,自由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市民社會(huì)的原子戰(zhàn)爭(zhēng)造成了國家與社會(huì)全面的矛盾對(duì)抗與沖突。盡管如此,福柯還是鍥而不舍地堅(jiān)持以博愛原則構(gòu)想出新的紡織藝術(shù),形成政治國家整體上的新團(tuán)結(jié)、友愛的政治學(xué)與個(gè)人自由。但這種主觀理性的超越性構(gòu)想并未超越近代啟蒙政治理性與政治解放,仍然不能解決西方現(xiàn)代性的政治危機(jī)。
最后,政治藝術(shù)是自由主義國家未來治理的普世模式。福柯推崇政治藝術(shù)、紡織技術(shù),把紡織模式看作最好的模式,以自然原則、理性原則和愛的情感原則積極探索自由主義國家未來治理的普世模式。他說:“自己去尋找適合自己模式的東西,這就是治理的藝術(shù)。找到治理的藝術(shù)時(shí),就知道了能夠根據(jù)什么樣的合理性來操作。”[11](P208)那么,這種治理的藝術(shù)、普世模式的規(guī)定性如何呢?他又從阿奎那的統(tǒng)治技術(shù)論中尋找到靈感,認(rèn)為國家治理的政治藝術(shù)達(dá)到優(yōu)秀的標(biāo)準(zhǔn)有三:一要能夠模仿自然,達(dá)到自然境界;二要成為各生命機(jī)體的軸心力量,引導(dǎo)個(gè)體利益趨向共同體利益,達(dá)到利益和諧境界;三要以慈愛與博愛之心盡職履責(zé),謀求民眾的共同利益,達(dá)到民眾至福境界。阿奎那治理藝術(shù)、統(tǒng)治藝術(shù)的制高點(diǎn)在超越地上的、超驗(yàn)的上帝全能藝術(shù)。福柯治理藝術(shù)、政治藝術(shù)的制高點(diǎn)在超越現(xiàn)代性的、虛幻的政治美學(xué),一方面,試圖以自主性的活動(dòng)展開的自由合理性邊界探險(xiǎn),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人的浪漫美學(xué)生存方式;另一方面,所要建造的自由主義烏托邦與模式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治理技藝,而是要把其“作為一般的思想風(fēng)格、分析風(fēng)格和想象風(fēng)格”[8](P194),即普世的模式與政治藝術(shù)。
四、福柯政治技術(shù)論對(duì)當(dāng)代國家治理的啟示
雖然福柯的政治技術(shù)論存在著明顯的西方自由主義國家治理的立場(chǎng)與視野局限,他對(duì)西方現(xiàn)代性社會(huì)政治問題的技術(shù)與藝術(shù)批判也不徹底、不系統(tǒng)。但是,他從政治技術(shù)的獨(dú)特微觀視角與方法出發(fā),對(duì)傳統(tǒng)國家治理尤其現(xiàn)代國家治理的歷史以及未來發(fā)展,進(jìn)行了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探索與分析。他在一定程度上延續(xù)了馬克思?xì)v史主義的、事件與問題式的思考方法以及現(xiàn)代性批判精神,對(duì)我們深刻認(rèn)識(shí)現(xiàn)代西方國家治理的本質(zhì)及問題,深入挖掘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國家治理思想資源,開創(chuàng)性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的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發(fā)展道路等,都具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
首先,有助于深刻認(rèn)識(shí)當(dāng)代西方國家治理的本質(zhì)及問題。誠如福柯揭示的,現(xiàn)代西方國家治理幾百年來磨煉的對(duì)內(nèi)壓制和對(duì)外戰(zhàn)爭(zhēng)的政治技術(shù)已達(dá)到一個(gè)癲瘋狀態(tài)。一方面是政治紙牌屋、政府停擺,另一方面是市民社會(huì)生活依舊、市場(chǎng)自發(fā)運(yùn)轉(zhuǎn);一方面是對(duì)外制造戰(zhàn)爭(zhēng)災(zāi)難與屠殺,另一方面是和平與人道主義救助的旗幟;一方面對(duì)全社會(huì)與全世界監(jiān)視監(jiān)聽,另一方面把自己隱身在那座帶有“百葉窗的監(jiān)視塔”中,等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權(quán)力機(jī)器在信息技術(shù)、資本技術(shù)、市場(chǎng)技術(shù)、社會(huì)技術(shù)、意識(shí)形態(tài)技術(shù)等助推下自動(dòng)瘋狂運(yùn)轉(zhuǎn)著。從玩弄各國的“大棒與胡蘿卜”策略到福柯所說的玩弄人類“死與生的游戲”[6](P815)的政治技術(shù),把西方現(xiàn)代性國家治理的本質(zhì)赤裸裸地展現(xiàn)在越來越開放的世界與覺醒的人們面前。現(xiàn)代性政治技術(shù)最好的一面已經(jīng)被其最壞的一面折損殆盡,對(duì)全球治理與世界和平造成了巨大威脅、巨大風(fēng)險(xiǎn)。現(xiàn)代西方國家的政治技術(shù)正走向萬丈懸崖之邊緣,走向陰謀、邪惡與丑陋,社會(huì)政治歷史發(fā)展仿佛重現(xiàn)“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新任性、新風(fēng)險(xiǎn),以及由此迎來的人類社會(huì)政治發(fā)展新轉(zhuǎn)機(jī)。
福柯的政治技術(shù)論提示我們,要以批判性的態(tài)度和精神來審視西方國家治理,充分發(fā)展和利用政治技術(shù)工具善與美的一面,規(guī)范政治技術(shù)的工具化界限以達(dá)到合理的治理限度,才能做好洋為中用、批判吸收、借鑒外來,避免落入西方強(qiáng)國設(shè)下的埋伏與陷阱。在日益開放與全球化的世界,在日益走進(jìn)世界舞臺(tái)中央的途中,要深刻認(rèn)識(shí)西方強(qiáng)國的圍堵、囚鎖與陰謀,要時(shí)刻準(zhǔn)備以高超的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文化與意識(shí)形態(tài)的技術(shù)、藝術(shù)與之展開偉大斗爭(zhēng)。在當(dāng)前矛盾凸顯的經(jīng)濟(jì)貿(mào)易之戰(zhàn)、信息大數(shù)據(jù)之戰(zhàn)、意識(shí)形態(tài)之戰(zhàn)中,不但要以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占據(jù)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的道義和實(shí)踐制高點(diǎn),更要牢牢掌握駕馭金融資本與市場(chǎng)的技術(shù)、信息通信技術(shù)、意識(shí)形態(tài)傳播技術(shù)等的關(guān)鍵點(diǎn)與制高點(diǎn),才能打破西方強(qiáng)國的霸權(quán)邏輯,化解潛在的系統(tǒng)性風(fēng)險(xiǎn)。
其次,有助于深入挖掘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國家治理思想資源。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理性日出時(shí)刻誕生的馬克思主義面臨的首要理論問題是如何在“批判舊世界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新世界”。就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理論及其治理思想是在批判現(xiàn)代性社會(huì)政治,以及構(gòu)想未來理想的社會(huì)主義國家的過程中闡發(fā)的一些基本原則,并未對(duì)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的政治技術(shù)提出具體構(gòu)想。通過深入挖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觀及其治理思想的基本原則,以及批判性與建構(gòu)性維度、現(xiàn)實(shí)性與理想性維度,我們會(huì)得到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的政治技術(shù)的正確出發(fā)點(diǎn)、現(xiàn)實(shí)方法論與發(fā)展方向。馬克思和恩格斯對(duì)現(xiàn)代性的社會(huì)技術(shù)、國家治理術(shù)的本質(zhì)批判,尤其是《資本論》揭示的資本對(duì)勞動(dòng)、資本家集團(tuán)對(duì)工人階級(jí)從宏觀到微觀的技術(shù)宰治、新型奴隸制的深刻批判,啟發(fā)了福柯的政治技術(shù)論,也啟發(fā)我們思考如何化技術(shù)宰治成為調(diào)動(dòng)勞動(dòng)者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的工具,使人成為技術(shù)工具的主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哥達(dá)綱領(lǐng)批判》等著作中對(duì)未來社會(huì)的現(xiàn)實(shí)性科學(xué)構(gòu)想,告訴我們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的未來是朝向?qū)崿F(xiàn)人類解放的自由人聯(lián)合體,啟發(fā)我們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要思考如何堅(jiān)持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堅(jiān)持無產(chǎn)階級(jí)專政與人民民主、堅(jiān)持世界無產(chǎn)階級(jí)及其政黨的聯(lián)合等一系列策略問題。此外,我們還要深入挖掘列寧和蘇聯(lián)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的理論與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及教訓(xùn),深入總結(ji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治理系列理論與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悠久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給我們留下寶貴而豐富的國家治理思想資源。福柯思考的政治技術(shù)論主要服務(wù)于現(xiàn)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治理,是站在西方治理歷史與文化的傳統(tǒng)上得出的。這也啟示我們,思考政治技術(shù)要立足于新時(shí)代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的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也就必須深入挖掘、繼承發(fā)展中華傳統(tǒng)的國家治理思想根源,才能做到不忘本來。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gè)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gè)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水平?jīng)Q定的,是由這個(gè)國家的人民決定的。”[17](P105)為此,我們要深入思考如何實(shí)現(xiàn)中華傳統(tǒng)國家治理文化中的治吏術(shù)、治民術(shù)等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問題,以滋養(yǎng)新時(shí)代的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
最后,有助于開創(chuàng)性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道路。新中國70余年偉大歷史性變革與輝煌成就背后蘊(yùn)涵著內(nèi)在的制度創(chuàng)新邏輯,從社會(huì)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到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確立,再到新時(shí)代對(duì)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制度全面深化改革與完善的偉大歷史性發(fā)展進(jìn)程,都充分彰顯著社會(huì)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無比優(yōu)越性與巨大優(yōu)勢(shì)。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xí)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偉大正確而堅(jiān)強(qiáng)有力的領(lǐng)導(dǎo)下,在以“堅(jiān)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制度,不斷推進(jì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改革”總目標(biāo)的正確指引下,重點(diǎn)改革創(chuàng)新解決制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體制機(jī)制問題,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構(gòu)建起了系統(tǒng)完備、科學(xué)規(guī)范、運(yùn)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新時(shí)代改革奮進(jìn)的新篇章還在繼續(xù)把深化體制機(jī)制的改革作為突破口,全面縱深推進(jìn)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社會(huì)、生態(tài)、國防和軍隊(duì)、管黨治黨等七大方面的體制機(jī)制改革,逐步達(dá)到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全面成熟與定型,實(shí)現(xiàn)改革的總目標(biāo)與最高價(jià)值目標(biāo)。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最大優(yōu)勢(shì)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18](P20)“我們的制度必將越來越成熟,我國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必將進(jìn)一步顯現(xiàn)。”[19]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ì)提出的“推進(jì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是對(duì)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理論的最新發(fā)展,是新時(shí)代中國共產(chǎn)黨人遠(yuǎn)見卓識(shí)的政治大智慧。學(xué)界把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簡(jiǎn)稱為中國的“第五個(gè)現(xiàn)代化”,俞可平高度評(píng)價(jià)說:“‘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們黨對(duì)社會(huì)政治發(fā)展規(guī)律有了新的認(rèn)識(shí),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從革命黨轉(zhuǎn)向執(zhí)政黨的重要標(biāo)志。”[20](P1)獨(dú)立自主、開創(chuàng)性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道路,是堅(jiān)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政治技術(shù)基石,對(duì)堅(jiān)持、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的偉大事業(yè),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夢(mèng),為全球治理貢獻(xiàn)出全新的中國政治智慧方案,都具有重大而長遠(yuǎn)的戰(zhàn)略意義。
包括政治制度在內(nèi)的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合理性與合法性,已經(jīng)被歷史邏輯、現(xiàn)實(shí)邏輯、理論邏輯、實(shí)踐邏輯、價(jià)值邏輯等所鐵證,是毋庸置疑的,是我們必須自信并長期堅(jiān)持和發(fā)展的,也是會(huì)被越來越多的像福柯這樣的學(xué)者所認(rèn)可的。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的政治制度前提、指導(dǎo)思想、價(jià)值目標(biāo)、發(fā)展走向等都是真善美的,堅(jiān)持黨的領(lǐng)導(dǎo)是中國治理的最大政治特色與優(yōu)勢(shì),堅(jiān)持黨的領(lǐng)導(dǎo)、人民當(dāng)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有機(jī)統(tǒng)一是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民主政治的特色治理原則。現(xiàn)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問題與任務(wù)是如何推進(jìn)黨的建設(shè)新的偉大工程與技術(shù),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歷史而具體的問題和任務(wù)是如何推進(jì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兩大工程的相互協(xié)調(diào)完備、相輔相成。只有把各方面的制度執(zhí)行能力與運(yùn)行技術(shù)提高到新時(shí)代要求的高度,“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更加有效運(yùn)轉(zhuǎn)”[17](P105),“推動(dòng)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更加有效運(yùn)轉(zhuǎn)”[21],社會(huì)主義制度潛在的巨大優(yōu)勢(shì)才能充分展現(xiàn)出來。新時(shí)代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國家治理的偉大征程已經(jīng)在路上,并且在當(dāng)前偉大的“抗疫”斗爭(zhēng)中充分彰顯了中國之治的巨大制度優(yōu)勢(shì),相信偉大政治技術(shù)與政治藝術(shù)的理論與實(shí)踐探索一定會(huì)開出當(dāng)代國家治理的新智慧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