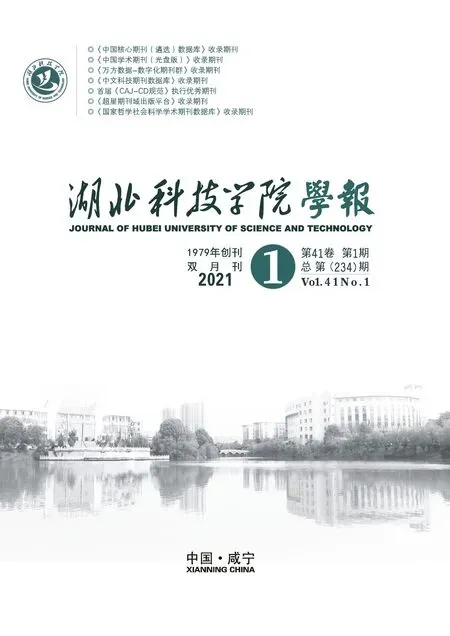在場性、在地化與精確性:農村小規模學校的發展實踐
徐 蕾
(湖北省農村教育與文化發展研究中心;湖北科技學院教育學院;湖北 咸寧 437100)
振興鄉村教育、繁榮鄉村文化是發揮鄉村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的重要舉措,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由之路。作為鄉土文化的重鎮,鄉村學校是鄉村教育改革、人才培養、文化傳承、乃至鄉村社會轉型、鄉村文化變遷的結構性力量,在構建鄉村振興新格局,健全現代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美麗鄉村進程中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的重要意義。
當前,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深入推進,產業結構、區域發展與人口流動的更新優化,城鄉教育格局的調整方向與速度發生了極大變化,隨之出現縣域義務教育學校“鄉弱”“鎮宿”“城擠”等現象,尤其是鄉村小規模學校面臨蕭條化、貧弱化、空心化的發展困境。面對鄉村教育的凋敝,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高度重視農村義務教育”和“推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鄉村振興戰略計劃(2018-2022)》明確提出“統籌規劃布局農村基礎教育學校”“提升鄉村教育質量,實現縣域校際資源均衡配置”等舉措,為破解農村學校發展難題提出了新要求與新視角。同時也需要從辦學定位、文化認同、主體參與等方面整體觀照農村學校與鄉村振興的在場性、在地化與精確性,進一步厘清農村小規模學校的發展走向與變革舉措。
一、在場性: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的價值定位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經歷了從公平到效益再到兩者兼顧的變革歷程。20世紀80年代,國家教委下發《關于實施<義務教育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要求以多種形式舉辦適當減少課程門類與教學要求的村辦小學或簡易小學,促生了“一村一校”的農村教育盛況,普及義務教育的同時也造成了教育資源的分散與教育負擔增加。2000年開始的以撤點并校為主要形式的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旨在提高教育資源使用效能、提高教學質量,體現出效益優先、兼顧公平的價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較高的經濟效益,但又衍生出巨型鄉鎮中心學校與農村中小學撤并萎縮并存、學生寄宿與校車安全問題頻發、家庭經濟負擔加重、學校文化與心理失衡等一系列問題。2018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全面加強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的指導意見》,強調公共資源配置在投入、師資、教學設施等方面重點保障兩類學校建設,補齊短板,進一步振興鄉村教育,基本實現縣域內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追求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
但也有學者認為,當前鄉村建設與鄉村教育建設分別處于“農村視野”與“國家視野”,在政策設計層面處于分離和脫節之中,鄉村教育缺少“鄉村責任”,鄉村建設同樣缺少“教育意識”[1],進而造成了鄉村教育的凋敝與鄉村學校的衰敗。究其原因,鄉村教育、尤其農村小規模學校在鄉村振興這個“場域”內的價值定位尚不清晰,離“場”現象明顯,尚處于“農本教育”與“城本教育”的價值沖突中[2],并俯就于城鎮化學校評價標準體系。
以“場域”理論視角來看,場域既是個體參與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也是社會成員依據特定的邏輯要求共同建構的文化空間,是一種客觀關系的網絡,個體及群體的行動都會受到所在場域的影響,并在經濟、社會、文化等資本層面予以呈現。具體到鄉村發展中,鄉村的振興有賴于政策支持、經費投入、資源配置,但關鍵在于人力資本的生產與優化,在于文化與教育的生產與傳承。從梁漱溟先生的“鄉村自治”、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到陶行知先生的鄉村教育改造,晏陽初先生的平民教育運動,其內里都是鄉村教育與鄉村建設的同向同構。農村學校、尤其是小規模學校發展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保持較高的同步性,與鄉土文化發展、新型人才培育保持較高的同步性,是鄉村振興的題中應有之義。
盡管鄉村學校在師資力量、生源質量、教學水平等方面與鄉鎮中心學校、城市學校還存在較大差距,但它們不應被視為鄉村經濟發展中的累贅或是救助的對象。必須清醒認識到,鄉村學校既是鄉村教育機構,也是鄉土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更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主體之一。鄉村學校是鄉村的中心,甚至是鄉村社區的心臟。[3]鄉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構建應通過相關政策體系,切實保障鄉村學校以“在場”的姿態廣泛、深入地參與到鄉村教育、鄉土文化、鄉風民俗、產業發展等系列鄉村治理之中,努力完善鄉村學校與鄉村家庭、鄉村社區的關系,進而發揮其在鄉村振興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的“溢出效應”。
二、在地化: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的區域優勢
學生人數減少、班級規模縮小、課程質量不高、師資力量薄弱、學校較為孤立等等,一直是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的主要困境。這一方面是國家產業結構、人口結構與生活方式調整的結果,也受教育資源配置中公平與效益的階段性調試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現實選擇。地域差異性、資源配置不平衡性以及教育供需失衡決定了農村小規模學校存在的合理性與長期性。實際上,即使像美、英、法等發達國家,其鄉村教育也經歷了“根植于鄉村”“邁向大城市”再“回歸到鄉村”的演進歷程。學者凱思琳·科頓在分析學生出席率、輟學率、學業成就、課程質量、師生參與度等因子基礎上,探討學校規模與學生學業成績之間的關系,認為小規模學校學生更容易取得較好的學業成就。[4]不僅如此,鄉村學校、學生還是鄉約民規、文化生活、環境保護、衛生治理、疾病預防、防火防盜、交通法規等鄉村生活規范養成與傳播的主渠道。
從各國的教育實踐來看,在地化是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不可忽視的區域優勢。農村小規模學校往往可以立足鄉村實際,充分依托地方資源和政策體系,通過政策扶持、教師服務、多方聯動、技術援助等方式,補足資金、師資等方面的短板,進而發揮地域特殊性、資源獨特性的優勢,以特色性、個性化促進學校發展。例如,美國西部諸州鄉村學校利用自身發達的畜牧業、漁業和多樣化地理與植被,開設地理科學、環境保護、養殖業等特色課程,并與產業發展、學生就業密切結合。英國開展宜人教育探索,發揮小規模學校在學校規模與人際關系方面“化大為小”的優勢,為學生的智力、道德、情感、社會性等方面的健康發展提供人文尺度。[5]美國“農村教育成就項目”“躍進學校計劃”、英國“教學優先計劃”“家庭行動計劃”、日本《偏僻地區教育振興法》、澳大利亞復式教學培訓項目等等,都圍繞鄉村教育發展進行了有益嘗試。
與此同時,我國學者也積極探索分析了鄉村學校發展實踐,探討鄉村教育新的生長點,如整體規劃發展的北京模式、集團化辦學的松滬模式、利用民間資本的浙江模式、“中心校”學區管理的武漢模式,小微聯盟的四川模式,等等。這些探索一是拓展農村小規模學校的辦學理念,通過鄉村教育與農業新業態、農村生活的深度融合,從地理、歷史、人口、倫理道德、風俗習慣、風土人情等方面重塑鄉村學校育人環境,并探索突破對城鎮教育簡單模仿的窠臼;二是創新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機制,通過政府專項財政改善辦學條件,穩定教師隊伍,優化學習生活環境;三是變革農村小規模學校辦學模式,通過小微學校發展聯盟、“1+N”集團化辦學等模式,共享師資、共享管理,實現同類學校的抱團發展與異類學校的共同發展;四是廣泛發動政府、學校、村委會、家庭、社區、社會組織的多元主體的積極參與,聚合政策體制、資金資源、人力智力等多樣化力量,形成小規模學校發展的支持系統。
由此可見,農村小規模學校應是基于鄉村、為了鄉村、服務鄉村、興于鄉村的在地化發展思路,在鄉村發展中尋找到內生力量,并體現在鄉土課程開發、鄉村教師培養、新型人才培養等諸多方面。其在地化的核心是教育要素的回流,通過發現、重估、再造鄉村教育價值,以創造性的方式由外生性制度規制轉向內生性自主發展、由資源輸入型向資源再生輸出型轉化。
三、精確性: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的現實路徑
鄉村學校與城市學校都是現代社會重要的學校形態,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文化傳承和人的全面發展具有不可或缺、同等重要的意義。但兩者間在價值追求、辦學理念、資源配置、治理模式又存在顯著差異,尤其是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在保有共性的基礎上還需進行精確性謀劃。現代鄉村教育具有鮮明的自然性、本土性、開放性、融合性與自治性[6],“小而美”“小而優”的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同樣具有后發優勢,關鍵在于準確把握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的真正脈絡。
——本土化發展。農村小規模學校根植于鄉村之中,與鄉村生活、鄉村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農村小規模學校應倡導自然教育,追求本土化發展。既可以發揮與大自然“零距離”的優勢,通過學校生產勞動、動植物養殖、校園文化建設、鄉村生活服務、社區主題公益等活動,在勞動教育、研學旅行等方面開展城鄉學校之間、校校之間的動態互動,破解現代兒童的“大自然缺失癥”“勞動缺乏癥”;也可以發揮村群生活形態的優勢,通過家訓家規、鄉約民俗、文明生活等教化,涵養新型鄉村文明,培養新型人才,反向助推鄉村振興。這樣,學生在共同生活與勞動實踐中,既能學習掌握一定的勞動技能,鍛煉體魄與毅力,又能培養對自然、家鄉、勞動、土地、家人朋友、鄉村文化、倫理道德的理解、尊重與認同。
——差異化發展。農村小規模學校并不是一種“落后”的學校形態,其教育內容、教學方法、教育環境等相較與城市學校既有明顯區別,同時又有著獨特的差異化優勢,完全可以發揮其在鄉村社會改造和鄉村振興中的核心作用,進而成為陶行知先生所倡導的“改造附近鄉村社會的中心”與“實施各項教學做的中心”。當然,針對當前農村小規模學校的發展局限,需要進一步采取相關傾斜政策,加大資金、資源、資本等方面支持力度,全面補齊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的短板;同時,制定適應鄉村教育需要、符合鄉村教育現實的農村小規模學校辦學標準,給予農村小規模學校在課程設置、教學改革、教師隊伍建設、學校管理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權和選擇性,鼓勵農村小規模學校自主性發展、差異化發展。
——特色化發展。相較于城市學校,農村小規模學校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獨特的鄉村文化資源,但在升學、考選方面又存在明顯弱勢。通過農村小規模學校特色化發展既可以放大鄉村學校的資源優勢,在學習、生活、體驗中重塑師生的鄉土認同、文化認同與鄉村自信,強化歸屬感與責任感;也可以通過鼓勵教師開發“鄉土課程”、建設特色文化項目及品牌,倡導“一校一品”建設等舉措,在避免“千校一面”的低質重復的同時,提升農村小規模學校的辦學品味與質量,提高農村小規模學校與所在村落發展的耦合度,進而達成鄉村教育與鄉村振興的同頻同構;此外,還可以通過“互聯網+”建設,促進“線上學習”“云課堂”“云教研”發展,推進鄉村學校、鄉村文化、鄉村產業發展、新型人才培養的一體化建設,并積極探索未來鄉村新型學校模式,探討以法治化、標準化、信息化手段推進農村小規模學校治理模式變革的合理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