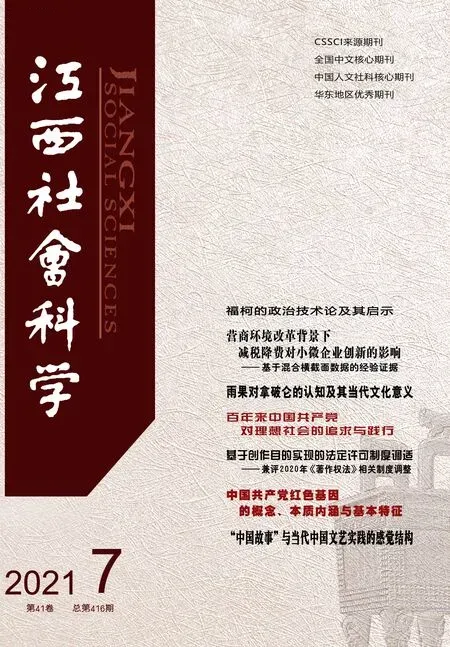基于創作目的實現的法定許可制度調適
——兼評2020年《著作權法》相關制度調整
■劉鐵光 向靜潔
不同作者具有不同的創作目的,但實現創作目的卻是基本相同的路徑,即作品的利用與傳播。法定許可創造了一種無須授權只需付費的作品利用與傳播方式,其降低交易成本與預防壟斷的制度價值,實質上增加了作品利用與傳播的機會。互聯網與數字技術催生了作品傳播的去中心化模式,但中心化傳播模式并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法定許可制度作為實現創作目的的一種制度,依然具有存續的價值,但應允許權利人拒絕。2020年修訂的《著作權法》,非但未在作品廣播法定許可中增加權利人有權拒絕的“聲明保留”,反而在教材匯編的法定許可中刪除了“聲明保留”的規定,這應在未來修訂中予以調整。
一、問題的提出
2012年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草案中有關音樂作品法定許可的規定一經公布①,便遭遇直接抵制:高曉松、劉歡、小柯等知名音樂人簽署聯名書信,呼吁修改“新草案”,認為該條款沒有尊重作者的權利②。中國音樂文學學會甚至認為,有關法定許可的規定將導致著作權人的私權利被公權化,其創作的作品被輕易地、合法地轉化為了公共財產③;中國音像協會唱片工作委員會認為,修訂草案中的法定許可制度,“剝奪了著作權人的許可權和直接獲酬權,摧毀了音樂產業基本的商業模式,也會使一直在困境中掙扎的音樂行業雪上加霜”④。著作權立法主管部門基于該抵制,在公布草案第二稿時直接刪除了該規定。⑤
與現實中《著作權法》修訂草案法定許可制度中只有音樂作品錄制法定許可遭遇抵制相比,我國著作權法理論界則走得更遠,認為至少部分法定許可制度應該退出《著作權法》。持這種觀點的主要論據有二:其一,法定許可這種非自愿許可的方式剝奪了權利人自主協商的機會。“經過二十多年實踐的經驗教訓,我國《著作權法》的法定許可制度已完成其階段性任務,應當逐步退場,由使用人按照商業慣例與權利人協商訂立作品使用合同的自愿授權制度取代。”[1](P29)亦有學者主張:“摒棄試圖一蹴而就構建著作權許可機制的傳統,以恢復和建立著作權市場中產業主體自由協商機制為優先……應在已經具備著作權市場協商機制的領域廢除法定許可的適用。”[2](P80)其二,法定許可制度原本就不具有或者不再具有存在的價值。“我國《著作權法》確立非自愿許可的法定許可制度主要是一種務實之舉,理論上并無充足的依據,也談不上具有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公共利益因素的考量。”[1](P21)亦有學者主張:“我國著作權立法應重新定位法定許可的立法價值,將其視為調和傳播技術發展初期產業利益分配分歧的臨時性工具。”[2](P80)除此之外,還有針對某種特定法定許可應該退出的論據⑥,但這些論據,若無法定許可“剝奪了權利人自由協商機會”或者缺乏穩定的立法價值的論據,則基本也可以忽略。然而,確實如此嗎?有體財產的相關理論套用到著作權領域一定能實現其預想的效果嗎?2020年修訂的《著作權法》對法定許可制度的調整,其合理性需要更深層次的評判。為此,本文將從創作目的的實現路徑出發,分析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存續的正當性基礎,并為其在當前新技術時代提供制度調適的方案,據此對2020年《著作權法》調整之后的法定許可制度進行評析,并提出下一步調整建議。
二、不同創作目的實現的相同路徑
著作權法定許可的理論基礎是經濟學中的科斯定理,即交易費用為零,不管產權初始如何安排,當事人之間的談判都會導致財富最大化的安排,即市場機制會自動達到帕累托最優,在經濟學中通常被表述為“法定權利的最初分配從效率角度上看是無關緊要的,只要這些權利能自由交換”[3](P498)。科斯定理的前提是當事人愿意選擇通過談判的方式進行交易,這對于有體財產權而言確是如此,至少沒有人喜歡其交易財產的自由受到任何的限制。然而,對于以作品為基礎的著作權而言,此觀點并不當然證立。作品源自人的創作,創作與勞動具有本質的區別:勞動是人類生存不得已而為之的必需選擇,故勞動的目的必然是以勞動成果兌換成金錢或者其意欲的替代物;而創作已經超出人類生存的需要,并非人類的必需選擇。哲學領域的研究成果認為創作是一種“精神本能”[4](P160),因為“生命本性可以說就是莫知其所以然的無止境的向上奮進,不斷翻新”[5](P32)。既然創作并非人類生存的需要,創作目的自然就不是,或至少不全是將創作的成果兌換成金錢。盡管每一個時代,確實有部分主體的創作是追求經濟利益,但不能以此否定不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的創作主體存在。根據創作目的的差異進行適當的類型化,至少可將其分為經濟利益需求型創作主體與非經濟利益需求型創作主體。
(一)非經濟利益需求型主體創作目的的實現路徑
非經濟利益需求型創作主體創作作品是基于多種需求,或是為了娛樂,或是為了愛好,或是為了學術,或僅僅是為了表達,等等。但其共性是該類主體創作作品不是基于經濟利益的需求,或者至少不直接是經濟利益的需求。正如美國學者研究新媒體環境下的軟件共創平臺后認為,當前網絡用戶創作動機是多元的,大量網絡用戶參與創作的目的并非基于價格體系,而是基于社會關系與共享的倫理。[6](P276)以學術類的創作主體為例,其并不依賴作品的交易來獲取利益以維持生計,其創作作品是為了提升其學術影響力,進而提升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率,學術界以“作品的被引頻次來評價作者的影響力”[7](P59)就是很好的例證。實際情況亦是如此,如某個學者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論文,不但希望被他人引用,而且希望其論文能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或摘編,這種現象在學術界是無人否認的。因此,學術需求型創作主體創作目的的實現是作品更多的被利用與傳播。實際上,與學術型創作主體一致,娛樂需求型、愛好需求型與表達需求型創作主體,其作品更多的被利用與傳播,能更大程度地實現其娛樂、愛好與表達的目的,至少可以提升娛樂、愛好與表達的價值。正因如此,對于非經濟利益需求型創作主體而言,歡迎任何保留其署名的方式對其作品進行被利用與傳播。也就是說,任何人對其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根本上不需要與該類主體進行任何交易。這正是因為作品被利用與傳播是實現該類主體創作作品目的的相同路徑。
(二)經濟利益型主體創作目的實現路徑
不可否認,傳媒產業的發展確實催生了經濟利益需求型的創作主體,最為典型的是專業小說、電影、廣播電視節目等創作主體。這類創作主體自然希望其作品能以權利交易的方式實現被利用與傳播——尤其是作品創作的投資人——由此獲取可觀的經濟利益。然而,其作品不一定能以交易的方式實現被利用與傳播,因為作品能否被交易,與創作主體的影響力密切相關。對于已經具有一定市場影響力的強勢權利人而言,其作品具有明顯的市場優勢地位,諸如文學領域的暢銷書作家、音樂領域的知名詞曲作者以及電影界的知名導演等,其自然可以實現作品以自主交易的方式進行被利用與傳播的愿望,以獲取其所認可的經濟利益。即便如此,由于創作主體的影響力,又與其先前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程度密切相關,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程度越廣泛,創作主體的影響力就越大。如一個在文學領域具有很強影響力的作家,并不必然反對其作品在九年制義務教育教材匯編中被使用;一個在詩歌領域具有很強影響力的作者,亦不必然反對其作品被電視臺廣播,尤其不會反對在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電視臺進行廣播,比如我國的中央電視臺。至于在某個領域未形成影響力的創作主體,其作品不具備市場交易優勢,故難以得到交易機會。由于作品可以因為更多的被利用與傳播機會而增加知名度,從而提升該創作主體的影響力,以使之將來可以進入具有影響力的創作主體行列并提升未來作品的市場地位。可以想象,一個沒有任何知名度的詞曲作者,是何等的希望知名歌星表演其作品并被具有強影響力的電視臺播放;一個在文學領域沒有任何影響力的作者,是多么渴望其作品被法定許可匯編進入九年制義務教育規劃教材。因此,對于經濟利益需求型創作主體而言,無論其在相關領域是否具有影響力,其創作目的的實現都依賴于其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正因如此,即便是已經具有很強影響力的創作主體,對于可以擴大其影響力的作品被利用與傳播,并不會必然反對。而對于在特定領域沒有任何影響力的創作者,任何保留其署名方式的作品被利用與傳播或許都在受歡迎之列。
前述經驗分析表明,無論是非經濟利益需求型還是經濟利益需求型的創作主體,盡管其創作的目的或者直接為經濟利益,或者為了娛樂、為了學術或者純粹是為了表達,但其目的的實現卻依賴一個相同路徑——即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換言之,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機會越多,作者創作目的實現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法定許可增加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機會
如前所述,無論何種需求類型的創作主體,盡管其創作目的各異,但其實現創作目的的路徑卻并無二致,均為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實際上創造了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方式,即在授權使用之外,增加一種無須獲得授權卻需支付合理報酬的被利用與傳播方式。此外,法定許可還具有防止作品被利用與傳播機會減少的功能,本質上亦是增加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機會。
(一)法定許可創造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機會
對于非經濟利益需求型的創作主體而言,由于其本身目的不在于以交易的方式實現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自然無須“充分協商”的權利,甚至難以承受“充分協商之重”。試想,如果一位學術著述頗豐的學者,對其作品轉載、摘編、編入教材、廣播等都需要與該作者進行單個交易,協商的范圍包括但不限于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報酬及其支付方式、被利用與傳播范圍、被利用與傳播目的、違約責任、訴訟管轄等,估計該學者還必須專門配備一個秘書幫其處理此類工作,否則,其創作時間將消失殆盡。當然,問題的關鍵在于,該類作者并不愿意通過協商以換取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自由協商”自然就成為該類作者的“不可承受之重”。因此,非經濟利益需求型的創作主體對其作品利用意愿的經驗分析至少可以說明,法定許可制度實質上增加了作者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機會。
國家版權局在《著作權法》(修改草案)說明中認為:“從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二十年的實踐來看,基本沒有使用者履行付酬義務,也很少發生使用者因為未履行付酬義務而承擔法律責任,權利人的權利未得到切實保障,法律規定形同虛設。”⑦著作權法定許可廢除論者據此來作為支持其觀點的論據之一。然而,“也很少發生使用者因為未履行付酬義務而承擔法律責任”的結論,極可能是因為鮮有權利人主張權利。如果權利人都不主張權利,使用者如何承擔法律責任?如果權利人主張權利,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又怎么可能“很少發生使用者因為未履行付酬義務而承擔法律責任”呢?由此可知,在權利人有權依據法律規定主張報酬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主體主張報酬。這至少可以表明,權利人非但不反對,甚至是愿意免費提供他人基于法定許可制度的利用。正如鄭成思教授在論證作品轉載的法定許可時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作者的作品能夠被更廣泛地傳播(即被多家報刊轉載),自己也能夠獲得更多的報酬,他們是不會反對的。[8](P356)
法定許可為創作主體創造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機會,權利人并不反對這種限制其充分協商權利的被利用與傳播方式。這一結論與法律經濟學的研究結論一致,法律經濟學有關因為人們的偏好差異而影響私有權賦予效果的結論認為:“如果人們的偏好是有沖突的,私有權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所有權對任何人都不意味著更多的機會。”[9](P3)對于著作權而言,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便是權利人的機會。盡管著作權法選擇將一種私權賦予權利人,由于權利人創作作品的偏好完全不同,私權的賦予并不意味著作品被利用與傳播機會的增多。然而,法定許可卻實在地創造了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機會,即作品增添了一種無須授權但需要支付費用的利用渠道,實際上增加創作主體創作目的實現的機會。若無法定許可,使用人會因為怵于侵權責任承擔的風險而不再被利用與傳播作品,作品被利用的機會必然減少。甚至會出現因作品的利用需求無法得到合理的實現和供給,而形成權利人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錯過的市場(missing market)”⑧,實際上,法定許可制度完全符合著作權法的變革應該“向創作者承諾其作品有機會向其意欲的讀者傳播”⑨的基本原則。
(二)法定許可預防減少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機會
除卻前述防止因為“錯過的市場”而導致的被利用與傳播機會減少之外,法定許可制度因其降低交易成本與預防壟斷的功能,可進一步防止作品被利用與傳播機會的減少。必須明確的是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設計的初始價值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與維護競爭秩序,并非前述學者所認為的“無理論上充足的依據”。著作權制度本身是順應出版產業發展的需求而誕生:英國在1695年之前,書商是依賴《特許法》所授予的出版特權進行出版審查,并賦予其對印刷業的搜查、沒收和罰款的權力,以維護書商在出版產業的壟斷利益。隨著1695年《特許法》的廢除,書商失去了出版特權的庇護,開始遭受盜版之苦,在訴求恢復出版權特權失敗之后,轉而借助作者利益與圖書財產權的名義尋找突破口,并在1710年的《安妮女王法》中得以作者權利保護的方式實現。[10](P21)
相關產業發展亦順應著作權制度的變革邏輯。首先,針對新傳播技術分離出的新產業,以著作權為基礎設立的產業便尋求在著作權法上增加新的權利。當音樂產業從出版產業分離出來之后,著作權法的回應是設立表演權;廣播電視產業出現之后,著作權法的回應是設立廣播權;互聯網產業出現之后,著作權法的回應是設立信息網絡傳播權。其次,新的傳播技術所催生的新產業必須與著作權的權利人進行權利交易方可實現其可持續發展。如果完全采取單個授權的交易方式,新產業的發展必然存在兩種可能的障礙:(1)單個授權交易導致交易成本高昂,尤其是需要海量使用海量作品的新產業,如廣播電視產業。如果不在制度上對單個授權的交易方式進行調整,將導致新產業因為交易成本高昂而難以為繼。因為“一個作品接一個作品”以及“一個權利人接一個權利人”的交易方式必然使交易成本過高[11](P38),從而導致“版權市場或者不能形成,或者功能失常”[12](P149)。難以想象,若廣播電視產業無廣播權法定許可的護佑,現今會處于一個什么狀態。(2)不受任何限制的單個交易,可能導致特定的主體因為獲得大面積權利人的獨占授權而在新產業里產生行業壟斷。美國國會就擔心一個生產鋼琴卷紙名為“Aeolian”公司的音樂獨占許可授權計劃將導致“巨大的音樂壟斷”⑩,其不希望一個持有大量知識產權的公司統治一個國家的藝術方向。[13](P97)為消減或降低交易成本,防止可能出現的行業壟斷,以期不阻礙新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著作權制度便在不同的領域創立了法定許可或強制許可制度,比如音樂領域、廣播領域等都有特定的法定許可或強制許可制度。當然,不同的國家根據本國產業發展的狀況,在法定許可的領域選擇會有所不同,比如我國因為傳媒產業中報刊數量龐大,應對報刊市場的細分需求,為報刊轉摘設立了專門的法定許可。因此,降低交易成本與預防壟斷,是法定許可制度真切的理論依據與初始價值。
除此之外,法定許可還產生一個不可忽視的間接價值,即其降低交易成本與預防壟斷的副作用——預防作品被利用與傳播機會的減少。其一,若無法定許可制度,單個協商獲取授權的高昂交易成本,必然會阻礙作品利用交易的達成,導致作品喪失許多被利用與傳播的機會。而法定許可制度其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價值,防止了因為交易成本過高而減少作品的利用機會。其二,若無法定許可制度,特定領域單個主體獲取大面積權利人的授權,從而產生相關行業的壟斷。隨后,該壟斷主體作為作品利用交易的強勢主體,將形成大面積作品利用的壟斷權利。在利益驅動下,其必然會選擇通過較少作品交易以獲取更高的利益,從而減少了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機會。而法定許可制度因為預防了壟斷,從而預防了因為壟斷導致作品被利用與傳播機會的下降。
綜上,法定許可不但為作者創造了一種無須授權卻需付費的作品被利用與傳播途徑,從正面增加了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機會;而且因其降低交易成本與預防壟斷的功能,防止了作品被利用與傳播機會的減少,反向增加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機會。因此,法定許可本質上增加了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機會,增加了作者實現創作目的的可能。
四、作品傳播中心化與去中心化混合模式時期法定許可的制度調適
互聯網時代,作品的傳播實現了從權利人直接到用戶或在用戶之間傳播,無須依賴傳播中介,呈去中心化的傳播模式。然而,依賴傳播中介進行作品傳播的中心化模式,非但未退出歷史舞臺,反而依然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故法定許可制度應該予以存續。但去中心化的傳播模式已經形成,即作品的權利人可以無須傳播中介而自己將作品傳播到用戶,確實無須法定許可所增加的作品被利用與傳播機會實現其創作目的。從而,一方面,在作品中心化傳播模式中,著作權人依然需要法定許可制度所增加的作品被利用與傳播機會以實現其創作目的;另一方面,在作品去中心化傳播模式中,著作權人則無須法定許可制度便可實現作品被利用與傳播,從而實現其創作目的。在這種狀況下,法定許可制度需要調適以適應當前作品傳播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混合模式。
(一)當今處于作品傳播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混合模式時期
傳統媒體時期,由于作品傳播技術、設備、制作等方面的高成本,包括權利人在內的個人一般難以成為傳播中介,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必須通過諸如出版機構、廣播電臺、電視臺以及電影制作機構等傳播中介的橋梁作用,方可從權利人傳播到用戶,此即作品傳播的中心化模式。傳播中介與權利主體之間關于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交易,如果以單個授權交易的方式必然導致高交易成本以及單個傳播中介因獲得大量作品授權而產生行業壟斷。正是基于降低交易成本與預防行業壟斷,法定許可制度才得以應運而生。但互聯網時代,作品卻可以通過去中心化的方式進行被利用與傳播,即作品可以繞過傳播中介直接向用戶傳播,亦可以在用戶之間傳播,此即外國學者所謂的“去中心化”和“去階層化”的網絡用戶之間共享[6](P278)。理論上,作者與用戶可以通過互聯網實現單個磋商的方式完成權利交易,并且通過拆封合同(shrink-wrap license)與點擊合同(clickwrap licenses)等互聯網線上的格式合同,大幅度降低權利的交易成本。即便是需要大規模使用海量作品的專業媒體,亦可通過互聯網實現低成本交易。單從此方面看,以降低或消除高交易成本為存在基礎的法定許可制度,似乎不再具有繼續存在的價值。正因如此,有學者提出“應在已經具備著作權市場協商機制的領域廢除法定許可的適用”[2](P80)。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以傳統媒體技術為基礎的產業并未退出這個時代,即中心化傳播仍是這個時代作品的主要被利用與傳播模式。無論紙媒、非交互方式的廣播電視、電影院線以及傳統的出版產業都依然在社會占據重要一席,就是很好的例證。加之傳播中介的國家管制與人類生活的慣性,亦必然有部分公眾選擇這種中心化作品傳播模式下的媒介獲取信息,這種傳播模式依然具有廣闊的市場。比如,歐盟對于數字單一市場版權規則現代化的影響評價報告認為,盡管因為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給電視的方式帶來了改變,但傳統電視依然既是經濟上的、亦是觀眾娛樂與信息的主要來源。在2014年,歐盟28個電視臺的市值高達860億歐元,同年,電視內容(包括直播與時間轉換的觀看)在六個國家(法國、西班牙、德國、意大利、英國和美國)中占到96%的視頻消費。?這足以說明,作品中心化的傳播模式及以此為基礎的傳媒產業依然在當今時代占據重要一席。故互聯網所帶來的這種去中心化傳播只是當今時代作品的一種被利用與傳播模式,而非全部,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至少還是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混合模式。
(二)法定許可制度應允許權利人“聲明保留”
去中心化是當今這個時代一種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模式,即無須傳播中介,直接將作品傳播到利用主體,也就無須法定許可制度降低交易成本與預防壟斷。對于經濟利益需求型并具有優勢市場地位、希望作品可以通過充分協商的方式實現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的主體而言,可以更加直接地實現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在這種情形下,應該給予權利主體更多的選擇。在制度的調整上,應該允許權利人以聲明的方式退出該種限制。實際上,我國2010年《著作權法》所規定的法定許可中,除作品(含錄音制品)廣播的法定許可不允許權利人事先聲明保留之外,其他三種法定許可都允許權利人聲明保留。我國有學者將這種“聲明保留”類比美國谷歌數字圖書館案中所提出的“選擇-退出”機制,認為我國《著作權法》法定許可的“選擇-退出”制度具有優越性。[14](P93)雖然在谷歌數字圖書館案中谷歌公司所提出的“選擇-退出”只是一種私人主體的倡議,而我國《著作權法》所規定的“聲明保留”屬于立法上的制度,但兩者之間產生的效果并無不同。但我國《著作權法》法定許可制度中允許權利人“聲明保留”的規定卻在學術界遭受詬病,認為“大量的作者或出版商已頻繁使用其聲明保留權,使得該三種‘法定’許可使用制度完全形同虛設”[15](P280)。此種無實際調研支撐的結論不可能正確。如前所述,不同創作目的的主體具有實現目的的相同路徑即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與有體財產不同,作品著作權的價值取決于作者的影響力,而作者的影響力又取決于作者先前作品的被被利用與傳播狀況,故作品的被利用、傳播的頻次與該作者的影響力成正相關關系。我國2010年《著作權法》頒布后,一直未出現因“聲明保留”而致教材匯編、報刊轉載以及音樂錄制領域無作品可供法定許可之用的狀況。如果當時修訂的《著作權法》規定廣播法定許可亦允許權利人“聲明保留”,更不會出現因為權利人大面積“聲明保留”而致廣播法定許可制度中無作品可供廣播的狀況。因為基于作品被利用與傳播作為不同創作目的實現的相同路徑,權利人愿意接受甚至是歡迎法定許可實際上所增加的作品利用渠道;況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廣播電視依然是具有主導地位的作品傳播平臺,該平臺對權利人作品及其權利人本身影響力的擴大,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大部分權利人對于作品被廣播電視的被利用與傳播求之不得,不可能出現權利人大面積地選擇“聲明保留”。
具體而言,我國2010年《著作權法》法定許可制度可按照如下方案予以調整:(1)繼續保留第23條所規定的教材匯編的法定許可、第33條第2款所規定的報刊轉載的法定許可以及第43條第3款所規定音樂錄制的法定許可,無須進行調整。因為該三種類型的法定許可,可增加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機會,而且其所規定的“聲明保留”,為權利人在去中心化傳播模式中自行利用作品提供了機會,完全契合當前中心化與去中心化混合傳播模式中著作權人實現創作目的對法定許可的不同需求;(2)第43條第2款所規定的已出版作品廣播的法定許可,應該增加“聲明保留”的規定,應調整為:“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他人已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但應當支付報酬。著作權人聲明不許使用的不得使用。”從而使其既契合當今作品傳播中心化模式中實現其創作目的對法定許可制度的需求,又契合作品傳播去中心化混合模式中著作權人無須法定許可便可實現其創作目的的客觀實際;(3)刪除第44條播放錄音制品法定許可的規定,因為我國《著作權法》只賦予詞曲作者廣播權,表演者與錄音制作者并不享有廣播權,對于一個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實質上也只是對音樂作品詞曲作者廣播權的限制,第44條也只能對音樂作品詞曲作者表演權與廣播權的限制。其與第43條第2款對已發表作品廣播的法定許可,區別在于:如果是通過播放錄音制品對音樂作品廣播權的法定許可,必須是已經出版的錄音制品;如果不是通過播放錄音制品對音樂作品廣播權的法定許可,比如找樂隊現場演奏,則只要求該音樂作品已經發表。對于表演者與錄音制品制作者而言,由于均無表演權與廣播權,這種限制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對于音樂作品的詞曲作者而言,都是對其廣播權的法定許可,這種區別亦不具有實際意義。至于該條所規定的“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由于著作權是權利主體的私權,當事人自然可以另行約定,即便是立法未作該種規定,也不影響當事人的另外約定。因此,“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的規定并不具有實際意義。而該條所規定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主要指法定許可制度中報酬確定問題由國務院另行規定。然而,并不僅僅是廣播權法定許可制度,《著作權法》中所有類型法定許可制度中的報酬確定都需要科學合理的配套機制。刪除“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表述,并不影響為所有類型的法定許可確定科學合理的機制。當然,刪除之后,應該在《著作權法》中單獨規定一條,明確由國務院為所有類型法定許可的報酬確定制定辦法,以為報酬的確定提供科學合理的機制。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2020年修訂《著作權法》時,對法定許可制度的調整未能按照上述方案進行,除刪除第44條播放錄音制品法定許可的規定以及繼續保留作品轉載法定許可的規定具有合理性之外,在第25條教材匯編的法定許可中刪除權利人可以拒絕的“除作者事先聲明不許使用的外”的表述,以及未能在規定作品廣播法定許可的第46條第2款增加權利人可以拒絕的“除作者事先聲明不許使用的外”的規定,都是法定許可制度本次調整的遺憾。這些遺憾,剝奪了權利人選擇作品利用方式的權利,應在《著作權法》未來的修訂中予以調適。此外,值得肯定的是,2020年修訂《著作權法》第45條,為錄音制作者在其錄音制品用于有線或者無線公開傳播,或者通過傳送聲音的技術設備向公眾公開播送具有獲得報酬的權利,盡管該條并不采取法定許可制度的固定表達模式——“無須許可,但需支付報酬”,但本質上與法定許可對錄音制作者報酬權的保護并無二致。
五、結語
盡管互聯網與數字技術改變了作品的傳播方式,但由于傳播中介的國家管制與人類生活的慣性,必然有部分公眾依然選擇通過傳統媒體時代中心化作品傳播方式下的媒介獲取信息,且這種狀態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繼續存在。法定許可創造一種無須授權只需要支付報酬的作品被利用與傳播方式,增加了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機會,其降低作品傳播中心化模式下,權利交易成本與預防壟斷所附帶產生了預防作品被利用與傳播機會被減少的作用,實質上增加了作品被利用與傳播的機會。故在當今作品傳播中心化與去中心化混合的時代,法定許可具有繼續存在的價值。但去中心化已經成為當今作品傳播的一種模式,權利主體應該有權選擇繞過傳播中介的模式實現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使經濟利益需求型創作主體中具有市場優勢地位的權利主體,可以拒絕法定許可,從而選擇充分協商的方式實現其作品的被利用與傳播。為此,法定許可在具體制度上的調適,應該允許權利人通過“聲明保留”的方式退出法定許可。2020年最終修訂通過的《著作權法》在法定許可制度的調整方面,既有合理的地方,亦有遺憾之處。這些遺憾,剝奪了權利人選擇作品被利用與傳播方式的機會,需要《著作權法》在未來的修訂中予以調適。被利用與傳播
注釋:
①該草案第46條規定:“錄音制品首次出版三個月后,其他錄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條件,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使用其音樂作品制作錄音制品。”
②參見《版權局回應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兩大爭議》,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7618862.html。
③參見《音著協建議刪除著作權法草案部分爭議條款》,http://www.chinanews.com/fz/2012/04-23/3839351.shtml。
④參見《唱工委:版權局代表無視音樂人呼聲 發表呼吁書表不滿》,http://industry.caijing.com.cn/2012-04-26/111829501.html。
⑤草案第二稿還刪除了錄音制品播放的法定許可(第44條)以及教材匯編法定許可與報刊轉摘法定許可中權利人“聲明保留”的規定。
⑥比如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導致了“超國民待遇”應該予以取消,該種觀點主要基于根據《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第13條的規定,報刊轉載外國作品不適用有關法定許可的規定。
⑦參見國家版權局《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的簡要說明》(2012年3月)。
⑧國外學者用來描述孤兒作品的利用現象,由于孤兒作品無法查詢到權利主體,使孤兒作品的利用需求無法得到合法的供給,從而產生孤兒作品利用的“錯過的市場”。See Dennis W.K.Khong,Orphan Works,Orphan Works,Abandonware and the Missing Market for Copyrighted Good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Volume 15,Issue 1,1 March 2007,p.54.
⑨美國“版權原則規劃:版權變革的方向”的項目研究認為,應將“向創作者承諾其作品有機會向其意欲的讀者傳播”作為現代版權法變革的一項基本原則。
⑩See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v.Copyright Royalty Tribunal,662 F.2d 1,17 (D.C.Cir.1981),at 4.
?See IHS Technology,Current market and Technology Trends in the Broadcasting Sector,May 2015,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