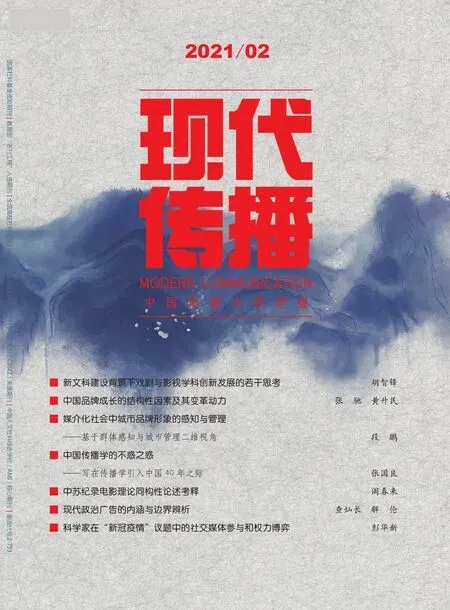在西方發現中國:論達拉斯·斯邁思的東方馬克思主義想象
■ 盛 陽
一、引言
東方馬克思主義(Eastern Marxism)是加拿大傳播學者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1907—1992)在傳播思想史著名的“盲點辯論”中提出的重要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末,正是基于對東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斯邁思才提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媒介與文化分析存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盲點。在以往的傳播思想史研究中,東方馬克思主義這一政治動能并未得到普遍關注。斯邁思與中國傳播的歷史性聯系,盡管在現象學層面得到了較為細致的梳理,但大多論述并未從東方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基底,進入斯邁思的傳播思想內核。①傳播學者比爾·麥樂迪(Bill Melody)曾評價,斯邁思之所以取得超越經濟學、傳播學和社會科學的理論成就,正得益于他對包括毛澤東思想在內的理論資源的充分吸納。②李·阿爾茨(Lee Artz)也指出,斯邁思在新中國前三十年的中國之行,激發他進一步思考“文化與社會發展”這一經典的傳播學問題。③
基于以上思想史背景,本文以斯邁思的東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為考察對象,通過對斯邁思盲點辯論經典論述的文本分析,討論東方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建構、政治內涵和行動取向之間的歷史關系。具體包括以下問題:(1)斯邁思傳播思想的實踐田野是什么?兩者如何發生歷史互動?(2)東方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構成、發生語境與其行動主義的政治內涵之間有何種歷史關聯?(3)新中國傳播實踐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新理念如何再現于斯邁思的東方馬克思主義想象?
二、尋找理論的實踐田野
在西方傳播思想史中,斯邁思的成名作是其1981年出版的關于加拿大媒體政治的著作《依附之路:傳播、資本主義、意識與加拿大》(Dependency Road:Communication,Capitalism,Consciousness and Canada)。但對中國問題的討論,卻為其在學術界贏得了最為矚目和持久的關注。④其中,斯邁思最廣為流傳的未刊手稿《自行車之后,是什么?》(After Bicycles,What?)就是基于他對新中國前三十年傳播與技術政治的田野調查。這份手稿于1994年收錄于他的自傳文集《逆時針:傳播研究透視》(Counterclockwise: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2014年由王洪喆譯介為中文,王洪喆、趙月枝與邱林川共同發表了中文版代編者按⑤。
中國傳播之所以成為斯邁思傳播思想的焦點,與其說是因為中國走上了斯邁思所認同的馬克思主義道路,不如說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為斯邁思提供了不同于西方革命的中國理念。
據斯邁思的學生托馬斯·古拜克(Thomas Guback)回憶,斯邁思很早就認識到中國革命者在理論道路上與西方革命者的差異。與列寧的“技術中立論”截然不同,在毛澤東的理論構想中,傳播與技術政治作為行動的政治主體始終在場。“在閱讀毛主席的作品時,我從未發現他對這一問題有所回避。他也從未像列寧那樣把問題想得過于簡單”“列寧的立場是,‘我們這里需要亨利·福特,需要電力,然后我們就會擁有社會主義’,一旦有人說出這種話,那么他就已經遠離我所認知的政治經濟學者之列了”⑥。
暫且不論斯邁思對列寧的理解實際上承接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蘇維埃道路的歷史性解構⑦,以上論斷不僅表明技術的政治性——即技術的社會化勞動屬性——是斯邁思心中政治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關切,而且也體現出在斯邁思建構其批判傳播理論的過程中,中國革命實踐和理念所扮演的歷史角色。
在此,關鍵問題是如何理解斯邁思對毛澤東思想的閱讀:是其進入中國實踐邏輯對思想的再現,還是沿著自身邏輯對思想的生發和演繹?如果理論的實踐田野并非中國革命,那么他的思想起點和理論歸宿在哪里?
回到其寫作《自行車》的歷史基點,斯邁思不僅在1971—1972年和1979年兩度遠赴中國大陸,考察新中國的文化與傳播建設,還積累了大量調研筆記和理論手稿,并以此為基礎撰寫了多部媒介與社會理論文稿。中國傳播實踐帶來的思想震撼,令斯邁思產生一種“走進未來”的感覺。1972年首次訪華回國后,斯邁思在一封致中國友人的信中寫道:“當我們離開大陸,回到香港后,我們生出一種巨大無比的震撼感:就像從未來穿越回了過去。我在香港賓館待了足足三天,才緩過來”。⑧
斯邁思在此所說的未來和過去,顯然是基于西方語境提出的:盡管社會主義傳播在中國是實存的實踐,但對當下的西方來說,中國是還未發生的未來。換句話說,新中國的傳播實踐并非“此在”或“當下”,而是一種實踐的未來主義。這表達了中國傳播實踐在斯邁思傳播思想中的特定坐標:一方面,有別于北美主流的發展傳播敘事,斯邁思顛倒了西方與中國在傳播發展中的次序,中國被敘述為西方的未來;但另一方面,該論斷依舊建立在對線性發展觀的合法性論證之上。斯邁思在此建立了以西方為基點的另類時間序列。這與斯邁思所欣賞的中國革命者對發展的結構性認知大相徑庭。⑨
盡管新中國傳播實踐是調查走訪的現實對象,《自行車》是直接討論中國問題的理論文本,但斯邁思的思想對象和理論田野并非中國,而是西方傳播業。他的中國研究與其說是從西方外部對傳播問題的理論反思與修正,毋寧說是基于突破西方制度瓶頸這一內部要求而尋找的替代性傳播方案。正是在“尋找理論的實踐田野”方法論基礎上,斯邁思開啟了對新中國傳播實踐的東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建構。
三、建構東方馬克思主義
1978年,《加拿大政治與社會理論學刊》(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繼前一年重磅發表斯邁思的《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Communication: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之后,再次刊發他的理論回應《反駁格雷厄姆·默多克》(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1994年出版的自傳文集將兩篇文章共同收錄,作為理解斯邁思以受眾商品論為代表的大眾傳播批判理論的基礎文獻。
盡管《反駁》從跨國資本主義媒體的意識形態塑造、歐美國家在資本主義合法化建構中的行動主義、觀念政治的社會化生產等多維度回應了盲點辯論的知識論爭,這些議題也在隨后成為理論界的主導議題,但是對當代中國傳播學者而言,文本更重要的意義是,如何理解在西方傳播語境中東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
如何定義東方馬克思主義?斯邁思認為其存在兩種面向,其一,它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與建設中的創造性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地化的歷史建構;其二,理論誕生的知識社會學前提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在闡釋大眾傳播的政治經濟本質方面失去了解釋力。理解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回到理論誕生的文本《盲點》。
斯邁思在文中提出受眾商品論,目的是建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并以政治經濟為根本——的傳播分析路徑,以此挑戰當時傳播研究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大眾媒體的壟斷性解釋。后者認為大眾媒體僅執行“傳播功能一元論”,即意識形態功能。
對他而言,建構新理論的難點在于如何突破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傳播=觀念政治”的知識限定,建構“作為勞動的傳播”這一政治經濟學路徑。在此,斯邁思特別引用了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對文化和政治的理論構想,以改造教條化的物質基礎/上層建筑二分法。
斯邁思認為,《矛盾論》中“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了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⑩這句話,特別適用于對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大眾媒體政治經濟過程的分析。毛澤東思想甚至因而被他盛贊為一套能夠有效解釋當代壟斷資本主義傳播本質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可見斯邁思之所以提出東方馬克思主義,是因為他認定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此失效了。值得一提的是,斯邁思并未訴諸于中國共產黨人對文化、政治和新聞傳播的完整論述(例如宣傳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建構批判理論,而是基于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特定歷史需要,對中國理論進行了抽象化提取。
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理解。
第一,東方馬克思主義將文化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二元論中解放出來,重新強調文化的政治經濟屬性。從政治經濟學重構文化與社會理論,與其說是對文化現象的經濟化約論,不如說是將文化從相對于物質基礎的“被動的能動性”中解放出來。后者反而是對文化的政治經濟屬性存在偏見的經濟化約論。
第二,東方馬克思主義的提出,標志著斯邁思建立了完整的知識坐標。建立文化傳播的政治經濟分析坐標,是解釋傳播與社會的第一步。構建以東方馬克思主義為內核的大眾傳播批判理論,將“有助于發展出一套非經濟決定論的、開放的(non-positive)、非歐洲中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四、東方馬克思主義的發生語境
作為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思想過程的產物,東方馬克思主義的發生語境是什么?歷史與思想的發生語境如何推動斯邁思傳播思想的知識構成?中國革命實踐與理念在其中扮演了何種歷史角色?
第一,東方馬克思主義是基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想象和建構。斯邁思在《反駁》中強調,自己所論述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歐洲和大西洋盆地文化的馬克思主義。它們在理解壟斷資本主義受眾商品現象時存在“文化時差”(cultural lag)。與此對應的是東方馬克思主義,即特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specifically Chinese)。由此可見,理論的提出最先基于西方知識譜系的敘事盲點,而非理論所扎根的中國實踐。
斯邁思曾在反駁理論對手時指出,他之所以沒有提出理論如何在邊緣國家或第三世界應用,并非理論只適用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因為“理論聯系是顯而易見的”。他認為,從資本主義的歷史擴張來看,跨國資本主義對邊緣地帶的媒介化塑造必然伴隨著受眾生產與商品化改造這一歷史過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自有其系統完整性(systemic integrity),即便其中充滿了矛盾;我并不認為它是一系列離散的結構或者領域。”從中亦可瞥見斯邁思建構東方馬克思主義的地理出發點是世界體系中的西方。
第二,東方馬克思主義是對中國革命實踐與理念的重塑。在回應為何回避正面評價新中國傳播實踐這一質疑時,斯邁思指出,即便《盲點》將攻擊的矛頭指向西方馬克思主義,而非東方馬克思主義,這也不能說明他本人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持任何肯定或否定的態度。與這一表達看似相悖的是,斯邁思在《盲點》中并非毫不評價來自中國的傳播思想和實踐經驗,反而多次引用《矛盾論》,并基于其中對文化政治的理論構想,發展出政治經濟學+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傳播思想。
如何解釋斯邁思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在“不置可否”和“深入洞察”之間游移?將這一問題置于立論的歷史語境,就可以發現他的思想起點并非中國往何處去,而是包括大眾傳播在內的西方制度該何去何從等問題。這解釋了斯邁思之所以沒有系統評判中國,而是將全部理論矛頭對準北美壟斷資本主義的原因。
他認為,正因為中國處于以西方為基點的時間序列的后半段,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不會面臨與北美同樣的問題。北美廣告業和傳媒業塑造的“意識工業”(Consciousness Industry)并未對中國展開全面壓制,因此“中國的傳播理論應該有自己的分析方法”。斯邁思對中國傳播實踐的理論想象,建立在西方壟斷資本主義通過大眾傳播構建獨特的政治經濟結構這一歷史現實之上。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視野,決定了斯邁思從西方現實和價值譜系定位中國革命實踐及其理念的歷史必然性。
第三,東方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提出,是因為其中包含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創新,蘊含了挑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潛力。斯邁思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僅從意識形態層面解讀大眾傳播的社會建構功能是不徹底的,更重要的問題是意識形態如何被穩固地社會化生產,而不僅是臨時的“心理操縱”等抽象過程。如果在承認受眾商品論的社會建構性的同時,認為受眾商品論是對傳播與意識形態的經濟化約論,且將意識形態論與受眾商品論并置,那么就是對其理論的誤讀。
只要我們進行簡單的邏輯推導,從理論不同的政策指向,就可以體會兩種認識論之間的差異:以受眾商品論為基準,西方傳播業的問題就是固有的結構性問題,傳播政策最終指向改造壟斷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和勞動分工,取消不平等的雇傭勞動;如果將兩論并置,西方傳播業就存在結構性和觀念能動性兩個問題,傳播政策不只導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改造,也可以從話語政治切入,在此西方傳播業危機只是“流動”的道德危機。
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西方鏡像
汪暉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一方面是一種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是對歐洲和美國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批判”,即“基于革命的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的立場而產生的對于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形式或階段的批判”,是一種在地的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則是中國共產黨人延續這一思路,對世界秩序中的中國如何在思想和政治經濟改造中走向現代化這一問題的經驗探索。
但在斯邁思的傳播思想中,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發展創新的馬克思主義并未得到完整詮釋與接納。進入斯邁思理論建構的歷史邏輯,中國共產黨人基于“世界中的中國革命”提出的文化理論,盡管為提煉基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傳播理論提供了思想動力,但更重要的是為他提供了組建思想的理論材料。
盡管并非出于建構普遍主義的理論動機,斯邁思為有效闡釋西方傳播業的結構性癥候,還是對中國革命思想展開了以東方馬克思主義為名的普遍主義理論抽象。東方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中國革命理論的片段,也是對中國傳播實踐的去歷史化解讀。
但同時,建構以東方馬克思主義為內核的普遍主義坐標系,為西方傳播學的歷史化分析提供了理論基點。斯邁思斷言,“現在需要挑戰和重新檢視歐洲傳統,這亟需仰仗來自中國的經驗”“基層的馬克思主義源自歷史辯證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的階級斗爭”;運用“顯而易見、真實可信的理論工具”分析、預測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首要任務。這體現了斯邁思將中國理論再歷史化的知識政治。斯邁思對中國解放的結構性意義及其潛在危機的有限認知,證明他并非完整的毛澤東思想追隨者,而是限定的毛澤東思想闡釋者。在這個意義上,斯邁思對毛澤東思想的東方馬克思主義想象與建構,與英語世界將“Mao Zedong Thoughts”(毛澤東思想)經由本土化改造譯介為“Maoism”(毛主義),似乎構成一種歷史的思想互動。
即便如此,東方馬克思主義在回應西方馬克思主義時的現實感及其蘊含的行動主義,卻與中國革命思想的政治能動性遙相輝映。斯邁思對中國理論的西方化,遠離了理論本身對“世界中的中國革命怎么辦”的根本關切。但正是通過在西方重新發現中國,斯邁思完成了自己的傳播思想建構,西方傳播理論被重塑為直指資本主義癥候的行動主義實踐哲學。如果說傳播政治經濟學始終存在走向“經學”和“詮釋學”的建制化困境,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批判也易滑向亞當·斯密意義上政治經濟分析之泥淖,斯邁思傳播思想迥異于這一趨勢的創造性、實踐感和革命性,亟需在思想史的書寫中確認。
對東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化解讀,與其說體現了斯邁思傳播思想在中國革命脈絡中的不完整性,不如說其思想的完整性需要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被識別。與其說斯邁思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創新性發展存在想象和再建構,不如說斯邁思傳播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西方鏡像。正是站在西方壟斷資本主義這一歷史節點,斯邁思才對革命理論新的結構與形勢做出新的闡發。
六、余論
在當代思想史的書寫中,斯邁思傳播思想的中國元素非但沒有得到深入討論,反而在理論的實際應用和闡發中被盲點化了。這導致對理論建構最初的實踐面向、歷史主義實質和普遍主義嘗試等議題的探討被嚴重削弱。本文并非在斯邁思與中國革命思想之間建立本質主義的歷史關聯,而是試圖以斯邁思在西方語境中對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化建構——東方馬克思主義——為標本,重新定位新中國傳播實踐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西方批判傳播理論奠基和建構中的歷史意義。
重讀斯邁思傳播思想中的東方馬克思主義,探討斯邁思與中國革命思想在這一特定理論表述中的關系的現實意義在于,當中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后革命時代被思想界普遍歷史化解讀時,有必要重新分析斯邁思如何通過東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對西方歷史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展開了從實踐到理念的普遍主義勾連。基于中國傳播實踐的東方馬克思主義想象,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以西方為中心的方法論民族主義。在西方發現中國,是有別于北美主流論說的另類傳播理論建構,也是斯邁思“以中國為方法”最早的理論嘗試。
(本文系國際關系學院國家安全高精尖學科建設科研專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際傳播與文化安全創新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019GA29〕的研究成果。)
注釋:
①⑧ 史安斌、盛陽:《追尋傳播的“另類現代性”:重讀斯邁思的〈中國筆記〉》,《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第138、143頁。
③ Lee Artz.MediaRelationsandMediaProduct:AudienceCommodity.Democratic Communiqué,vol.22,no.1,2008.p.60.
⑤ [加]達拉斯·斯邁思:《自行車之后是什么?——技術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屬性》,王洪喆譯,《開放時代》,2014年第4期,第97頁。
⑦ 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蘇維埃道路的創造性理解基于特定的政治環境和理論動力,即挖掘不同于斯大林經濟主義的“內部替代性傳統”。盛陽:《漸進的馬克思主義者:雷蒙·威廉斯學術思想評述》,《全球傳媒學刊》,2017年第1期,第55頁。
⑨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通過引述列寧思想論述了兩種發展觀:其一,“發展是減少和增加的,是重復”;其二,“發展是對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為兩個相互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著)”。毛澤東指出,這兩種不同的宇宙觀是辨識世界的基本框架。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頁。
⑩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