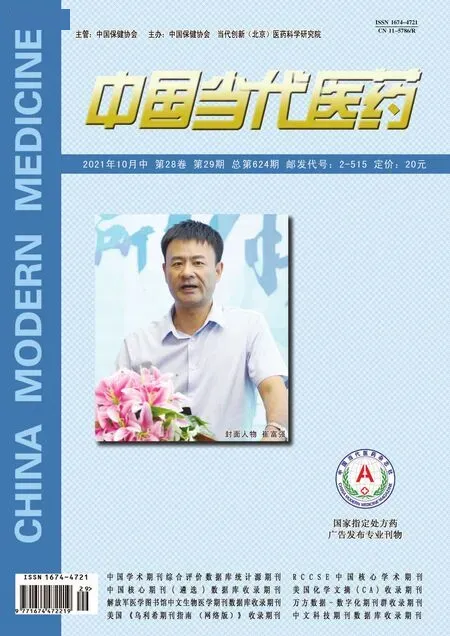紫癜性腎炎患者尿紅細胞形態與中醫證型的關系研究
羅立媛 鐘英超 謝月恒 鐘華文
廣東省陽江市中醫醫院內二科,廣東陽江 529500
紫癜性腎炎作為臨床上常見的腎內科疾病,主要病理表現為壞死性小血管炎,是過敏性紫癜最為常見的并發癥,患者表現為不同程度關節腫痛、腹痛、便血,隨著病情進展會累及到全身多個重要臟器官,降低患者生活質量[1]。傳統西醫治療紫癜性腎炎多以免疫抑制劑、激素為主,盡管能夠對患者臨床癥狀起到緩解作用,但復發率高,且容易引起水鹽代謝紊亂,效果達不到預期。近年來,中醫在紫癜性腎炎治療中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其認為該疾病為本虛標實,多以氣陰兩虛為主,治療強調辨證論治[2]。尿紅細胞形態學檢查在泌尿系統疾病定位中有著較高的應用價值,便于受累部位的檢出、疾病嚴重程度的評估[3]。但關于中醫證型與尿紅細胞形態間的關系研究較少。此次研究選取陽江市中醫醫院收治的100 例紫癜性腎炎患者病例資料,旨在分析尿紅細胞形態與中醫證型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年8月至2021年3月陽江市中醫醫院收治的100 例紫癜性腎炎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54 例,女46 例;年齡26~77 歲;平均(57.63±4.02)歲;病程4 個月~4年,平均(3.38±1.24)年;發病誘因:感染38 例,食物、藥物過敏30 例,勞累18 例,其他14例。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患者及家屬已明確研究目標及流程,加入研究均為自愿并簽署知情同意書。入組標準:①患者經血常規、尿常規及超聲檢查確診為紫癜性腎炎,參照《紫癜性腎炎診治循證指南(2016)》[4]。②患者年齡≥18 歲,可正常溝通交流。排除標準:①心臟受損或肝功能異常者;②合并精神異常、心理障礙或意識喪失患者;③患者存在惡性腫瘤疾病;④聽力喪失、語言溝通不順暢,對研究無法做到順利配合患者;⑤合并凝血功能障礙或血液系統疾病者;⑥存在尿路感染或泌尿系結石者;⑦處于妊娠、哺乳特殊階段女性。
1.2 診斷標準
1.2.1 中醫證候診斷標準 ①風熱搏結證。皮膚可見紫癜,伴隨瘙癢、血尿、發熱、咽痛及腹痛等癥狀,合并面部及肢體浮腫,苔白薄黃,脈滑有力。②熱毒內熾證。臀部、四肢及背部皮膚呈鮮紅紫癜,有瘙癢感,伴隨口干、發熱、黑便癥狀,苔黃脈數。③濕瘀互結證。紫癜反復出現,存在血尿及蛋白尿,次癥有關節腫痛、肢體浮腫,苔膩脈滑。④氣陰兩虛證。紫癜時有時無,合并腰膝酸軟、口干,脈細數舌紅苔薄。⑤脾腎陽虛證。紫癜消退,伴隨蛋白尿、血尿,乏力、畏寒、納差。舌體胖、苔白脈沉細[5]。
1.2.2 西醫診斷標準 參照《紫癜性腎炎診治循證指南(2016)》[4]。①存在皮膚紫癜等腎外表現;②合并蛋白尿、血尿及腎功能不全等腎損害表現;③系膜區存在IgA 沉積,伴隨系膜增生。
1.3 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尿紅細胞形態檢查,指導患者前一晚22∶00 后禁水,取尿樣前4~6 h 開始憋尿,指導患者對外陰進行常規清潔,采集中段晨尿以10 ml 為宜保存于干燥容器中,1 h 內送檢。檢測時將采集尿液混勻保存于刻度離心試管,按照1500 r/min 的離心速率實施離心處理,離心半徑8 cm,離心5 min。完成離心后將離心管取出,避免沉淀物浮起。將離心管傾斜45°~110°,將上清液去除,保留0.2 ml 沉渣。對離心管進行輕搖,混合其中的有機成分。采用移液槍提取0.2 ml尿沉渣,滴在載玻片上,并用蓋玻片對尿沉渣進行覆蓋,防止出現氣泡。采用相差顯微鏡,觀察有機成分時采用10×10 的鏡頭,觀察視野在20 個以上,明確紅細胞形態及計數,對各種變形紅細胞百分率進行計算。
1.4 觀察指標及評價標準
對患者進行辨證分型,比較不同中醫證型患者異常紅細胞與棘形紅細胞百分比情況,比較不同紅細胞形態含量百分比。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組間比較采用t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中醫辨證分型結果分析
中醫辨證分型顯示,100 例患者中風熱搏結證20例(20.0%)、熱毒內熾證12 例(12.0%)、濕瘀互結證23 例(23.0%)、氣陰兩虛證36 例(36.0%)、脾腎陽虛證9 例(9.0%)。
2.2 不同中醫證型與異常紅細胞及棘形紅細胞關系分析
氣陰兩虛證患者異常紅細胞百分比、棘形紅細胞百分比均高于其他中醫證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不同中醫證型與異常紅細胞及棘形紅細胞關系分析(±s)

表1 不同中醫證型與異常紅細胞及棘形紅細胞關系分析(±s)
與氣陰兩虛證比較,aP<0.05
中醫證型 例數 異常紅細胞百分比 棘形紅細胞百分比熱毒內熾證脾腎陽虛證風熱搏結證濕瘀互結證氣陰兩虛證F 值P 值12 9 20 23 36 0.702±0.024a 0.718±0.016a 0.739±0.021a 0.785±0.021a 0.802±0.024 36.723 0.000 0.017±0.004a 0.019±0.003a 0.021±0.003a 0.025±0.012a 0.031±0.013 14.307 0.000
2.3 不同中醫證型紅細胞形態含量百分比的比較
不同中醫證型患者的紅細胞形態含量百分比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氣陰兩虛證異常紅細胞含量百分比靶形紅細胞>正紅細胞>環形紅細胞>其他>小紅細胞>大紅細胞>棘形紅細胞,紅細胞形態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濕瘀互結證環形紅細胞百分比>正紅細胞>小紅細胞>靶形紅細胞>大紅細胞>其他>棘形紅細胞,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風熱搏結證異常紅細胞含量百分比小紅細胞>正紅細胞>靶形紅細胞>其他>環形紅細胞>大紅細胞>棘形紅細胞,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脾腎陽虛證正紅細胞形態含量百分比>其他>小紅細胞>大紅細胞>靶形紅細胞>環形紅細胞>棘形紅細胞,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熱度內熾證環形紅細胞>正紅細胞>其他>靶形紅細胞>大紅細胞>小紅細胞>棘形紅細胞,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2)。
表2 不同中醫證型紅細胞形態含量百分比的比較(±s)

表2 不同中醫證型紅細胞形態含量百分比的比較(±s)
與同一證型其他紅細胞形態含量比較,aP<0.05
組別 例數 正紅細胞 棘形紅細胞 環形紅細胞 靶形紅細胞 大紅細胞 小紅細胞 其他熱毒內熾證脾腎陽虛證風熱搏結證濕瘀互結證氣陰兩虛證12 9 20 23 36 0.261±0.011 0.263±0.014 0.253±0.024 0.239±0.012 0.208±0.013 0.029±0.015 0.025±0.012 0.017±0.004 0.023±0.014 0.028±0.014 0.384±0.041 0.138±0.031 0.122±0.022 0.278±0.035a 0.168±0.041 0.093±0.036 0.149±0.042 0.131±0.021 0.125±0.031 0.289±0.035a 0.081±0.031 0.158±0.031 0.082±0.025 0.104±0.043 0.047±0.021 0.074±0.032 0.167±0.035 0.256±0.037a 0.139±0.024 0.124±0.024 0.108±0.031 0.170±0.035 0.123±0.026 0.098±0.031 0.145±0.038
3 討論
紫癜性腎炎主要指的是免疫復合物在腎臟血管壁大量沉積進而引起的小血管炎癥壞死現象,文獻報道,紫癜性腎炎感染、過敏密切相關[6],隨著病情進展會引起皮膚、胃腸道及關節受累。以往研究認為紫癜性腎炎是自限性疾病,預后良好,但臨床上發現紫癜性腎炎有明顯的遠期并發癥[7]。因為紫癜性腎炎病理類型如同IgA 腎病,即使紫癜消退,尿檢正常,腎臟病變也可能會持續進展,一部分紫癜性腎炎可能會進展為慢性腎功能不全。
中醫學將紫癜性腎炎歸屬為“血證”、“尿血”、“葡萄疫”范疇,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患者先天稟賦不足,復感外邪,外受風熱,兩熱相搏,對膚絡產生灼傷,進而形成紫癜[8]。有學者認為氣陰兩虛是紫癜性腎炎的發病內在基礎,患者外感風、濕、熱、毒之邪,或食用魚、蝦、蟹會導致熱毒乘虛而入,造成血絡灼傷,內壓迫腸胃,外溢肌膚,累及到腎臟從而發病[9]。目前關于紫癜性腎炎各醫學家有著不同的觀點。此次研究通過對100 例患者的中醫辨證分型,可以發現100 例患者氣陰兩虛證占36.0%,其次為濕瘀互結證,占23.0%。紫癜性腎炎患者病程長,易反復發作,西醫多采用激素治療。且患者受熱毒之邪影響,腎陰受到影響,隨著病情進展會導致耗氣嚴重,形成氣陰兩虛。脾肺虧虛、營衛不固進而導致風邪,因此紫癜性腎炎以氣陰兩虛最為常見。過敏性紫癜的辨證主要是八綱辨證,實證多為風熱外感證、濕熱傷絡、血熱妄行證為主,虛證則為肝腎陰虛、氣不攝血為主,還兼有三焦辨證和衛氣營血辨證。早中晚分期辨證在中醫辨證治療過敏性紫癜的臨床應用中,具有指導意義。早期通過中醫辨證協同治療,可以大大減少過敏性紫癜發展為紫癜性腎炎的傾向,能避免病情發展到危重癥。紫癜性腎炎癥狀表現復雜多樣,多伴隨血尿,是患者就診的直接因素[10]。但血尿病因較多,需要與其他類型疾病進行鑒別,傳統腎穿刺活檢具有一定的創傷性、操作復雜,在基層臨床難以開展。近年來,尿紅細胞形態檢查在臨床得以應用,通過對尿中紅細胞異常形態的觀察能夠幫助明確血尿的來源及尿路病變,但基于異形紅細胞形態定義的不同,容易出現較大的誤差[11]。基于此研究提出中醫證候與尿紅細胞形態相結合的方式,其具有價格低廉、無創性、操作簡單等優勢,有利于提升診療工作的規范性。采用尿中異常紅細胞形態含量能夠實現對腎小球血尿的診斷,通常>70%可確診。本研究結果顯示,氣陰兩虛證患者異常紅細胞百分比、棘形紅細胞百分比均高于其他證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分析原因為紫癜性腎炎以氣陰兩虛證居多,患者發病后容易受到熱毒侵襲損傷腎陰,隨著病情進展導致氣虛固攝不足,因此更容易出現異型細胞。尿中棘形紅細胞則是在溶血狀態下產生的一種異常現象,通過棘形紅細胞超過2%可診斷腎性血尿,敏感性高[12-13]。此次研究氣陰兩虛證異常紅細胞含量百分比靶形紅細胞>正紅細胞>環形紅細胞>其他>小紅細胞>大紅細胞>棘形紅細胞,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濕瘀互結證環形紅細胞百分比>正紅細胞>小紅細胞>靶形紅細胞>大紅細胞>其他>棘形紅細胞,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風熱搏結證異常紅細胞含量百分比小紅細胞>正紅細胞>靶形紅細胞>其他>環形紅細胞>大紅細胞>棘形紅細胞,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脾腎陽虛證正紅細胞形態含量百分比>其他>小紅細胞>大紅細胞>靶形紅細胞>環形紅細胞>棘形紅細胞,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5);熱度內熾證環形紅細胞>正紅細胞>其他>靶形紅細胞>大紅細胞>小紅細胞>棘形紅細胞,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有研究報道,脾腎陽虛型患者其尿紅細胞的形態多樣性較其他證型多,且G1 細胞出現頻率高,其病理分級也相對較重,多為Ⅲ級以上[14],與本研究結果一致。掌握患者中醫證候與尿紅細胞形態的關系便于辨證施治,提高治療針對性。但由于樣本少、精力有限,研究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在后續研究中應加大樣本,進一步隨訪紫癜性腎炎證候變化及轉歸情況,為臨床提供更多可靠的依據。
綜上所述,氣陰兩虛證是紫癜性腎炎常見的中醫證候,且不同中醫證型異常紅細胞及棘形紅細胞含量百分比具有一定的差異,氣陰兩虛證與靶形紅細胞關聯性最高,應結合患者證型給予對應治療,增強患者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