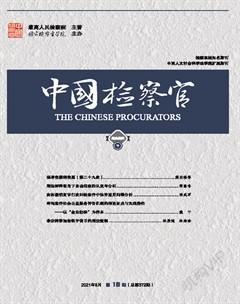刑法解釋視角下自動投案的認定與分析
蔣滌非
摘 要:司法實踐中,對于“一案兩投”案件自動投案的認定有較大爭議,原因在于解釋方法使用不當。具體適用解釋方法時應在得到初步解釋結論后再使用其他解釋方法對結論進行校驗。在自動投案的認定上,應先形式后實質,即先判斷“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的形式要件是否成立,然后再判斷“主動性、直接性”的實質要件是否成立,不應跳過形式要件直接進行實質要件認定。
關鍵詞:自首 自動投案 刑法解釋
實踐中關于自動投案的認定較為復雜。近期,一起“一案兩投”案件對于行為人能否認定自動投案引發爭議。本文對此案件進行復查,通過梳理爭議問題,就自動投案認定中應把握的刑法解釋問題進行分析,供實踐參考。
一、問題的提出
[基本案情]1997年1月2日18時許,謝某在B縣牛鎮東街賣工場打工時與他人發生爭吵,后在與對方的互毆中,謝某用隨身攜帶的匕首刺中被害人翁某平腹部。案發當時,B縣公安局接報警后出警。民警到場后制止了雙方打斗,后謝某乘民警不注意逃離現場。案發后,警方通過取證鎖定犯罪嫌疑人系謝某。1月6日民警書面傳喚謝某。1月7日,謝某到派出所接受訊問并就持刀傷人作如實供述,后回家。3月2日,法醫作出翁某平系重傷的傷情鑒定結論。3月19日,B縣公安局以涉嫌故意傷害罪向檢察院提請批準逮捕謝某。3月23日,B縣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謝某。4月1日,謝某在家屬陪同下到B縣公安局預審科投案,當日預審科對謝某執行逮捕。4月2日,預審科出具謝某“投案證明”。4月7日,謝某親屬向公安局申請取保候審,同日,B縣公安局釋放謝某。4月28日,B縣公安局偵查終結以涉嫌故意傷害罪將謝某移送審查起訴。5月21日,B縣人民檢察院以謝某犯故意傷害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6月29日,B縣人民法院以謝某具有自首情節,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以故意傷害罪判處謝某有期徒刑3年。之后,謝某上訴。二審維持原判,但宣告緩期4年執行。一審、二審裁判文書均認定“被告人謝某于4月1日到公安機關投案,如實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實”,謝某構成自首。
本案中謝某存在“一案兩投”的情況,即謝某分別于1月7日、4月1日向兩個偵辦單位投案,并如實供述。裁判文書以“被告人謝某于4月1日到公安機關投案,如實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實”為依據,認定謝某構成自首,但對謝某1月7日到案未作評判。因此,裁判文書認定謝某構成自首是否錯誤;“兩投”中哪一次可以被認定為自動投案,還是一次也不能認定,成為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二、關于認定自動投案的分歧意見及評析
在案件復查過程中,對謝某是否構成自動投案有兩類觀點。一類觀點認為謝某不構成自動投案,其中又包括七種具體意見;另一類觀點認為謝某構成自動投案。下面分別就兩類觀點進行評析。
(一)關于“謝某不構成自動投案”觀點的評析
意見一:現場逃跑的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因為,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規定,“明知他人報案而在現場等待,抓捕時無拒捕行為,供認犯罪事實的”視為自動投案。對該條反面解釋可得,嫌疑人現場拒捕的不能認定自動投案。本案中,謝某于1月2日捅傷被害人后,在警察到場的情況下現場逃跑,屬抗拒抓捕。其雖在1月7日到派出所接受訊問,但因逃跑拒捕在先,喪失了到案的主動性和自愿性,不能認定謝某自動投案。筆者不同意此種意見。第一,《意見》規定的實際意思是指“能逃而不逃”留在現場待捕的情形,并不能得出只要現場逃跑,或現場拒捕一律不能認定自動投案。因為,嫌疑人雖現場拒捕但最終順利逃脫的,其就具備了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所規定的“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的時空條件,仍能夠自動投案。該規定的反面解釋只能得出一種不能認定自動投案的情形,即嫌疑人現場拒捕并被現場抓獲。即,該意見未區分“現場拒捕后被現場抓獲”和“現場拒捕后脫逃”兩種情形[1],擴大了解釋結論的范圍。第二,《解釋》規定“犯罪后逃跑,在被通輯、追捕過程中,自動投案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舉重以明輕,謝某案發后雖從現場逃跑,但此后未受通輯追捕,1月7日傳喚到案,也應當認定自動投案。
意見二:被傳喚到案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因為,謝某1月7日到派出所系被通知到案,喪失主動性。但是,刑事訴訟法第119條第1款規定,對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傳喚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縣內的指定地點或者到他的住處進行訊問。根據該規定,傳喚只是公安機關的工作方式,并不是強制措施,也不是判斷嫌疑人到案主動與否的標志。而且傳喚到案不能一概認為“有主動性”或“無主動性”,需分情形辨識:一是公安機關發現犯罪嫌疑人后,現場控制并口頭或書面傳喚,直接將嫌疑人帶回公安機關訊問,此情形下被傳喚嫌疑人喪失自動投案條件,沒有主動性;二是公安機關并未在現場發現犯罪嫌疑人或現場發現嫌疑人但未將其當場帶走,而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指定時間地點傳喚嫌疑人,嫌疑人如期自行前往,此情形中嫌疑人具有將自己主動交付公安機關控制、查處的意愿和行動,應肯定其主動性。本案中,謝某是在書面傳喚后第二天根據傳喚要求到案,能夠肯定其到案的主動性。
意見三:被鎖定為犯罪嫌疑人后到案接受訊問的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因為,案發后公安機關已鎖定謝某系犯罪嫌疑人,且公安機關1月7日采用“訊問筆錄”訊問謝某,謝某到案后被“訊問”不符合《解釋》規定的“尚未接受訊問”的要件,不能認定自動投案。但是,《解釋》規定了自動投案的兩個形式要件——“尚未接受訊問”和“尚未被采取強制措施”。兩個要件同時成立能夠認定“標準的自動投案”,只具備一個可認定“準自動投案”,兩個要件都不具備的不構成自動投案。如《解釋》規定“罪行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或者司法機關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自己的罪行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該情形中嫌疑人受到控制但未受到訊問。又如《意見》規定“因特定違法行為被采取勞動教養、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強制隔離戒毒等行政、司法強制措施期間,主動向執行機關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為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該情形中嫌疑人也是受到控制但未受到訊問。本案中,謝某雖被訊問,但具備“未被采取強制措施”的要件,因此應當認定謝某成立準自動投案。
意見四:逮捕決定作出后的投案不成立自動投案。因為,逮捕系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謝某在逮捕決定作出后投案不屬于自動投案。但是,該意見不能對謝某1月7日到案作出合理說明。(1)本案有兩個偵辦環節,一是派出所環節,二是公安局預審科環節(這也是本案產生“一案兩投”的關鍵原因)。兩個辦案部門(環節)是公安機關內部工作分工,但對謝某和社會公眾而言都代表公安機關。因此,1月7日謝某經傳喚到派出所接受訊問,就是其基于本人意志自愿置身于公安機關控制之下的表示,應視為主動到案,不能因為機關內部分工就認為謝某1月7日的到案不是“自動投案”。(2)“投案證明”不是認定投案的唯一依據。本案中,預審科雖出具了投案證明,但該證明僅表明謝某于4月1日又向預審科投案接受訊問,是預審科工作情況的現實記錄。相反,1月7日謝某經傳喚到牛街派出所接受訊問,對于該次訊問派出所沒有出具任何到案證明,但謝某該次到案接受訊問的事實客觀存在,不能因為沒有證明在案,就不予認定。
意見五:逮捕決定作出后犯罪嫌疑人就喪失了自動投案的條件。因為,《意見》規定“在司法機關未確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詢問時主動交代自己罪行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進行反面解釋,司法機關確定犯罪嫌疑人后嫌疑人就喪失了自動投案的機會;而且4月1日謝某到案對案件偵辦沒有實質意義,沒有實現自首制度設置的價值。筆者不認同此種意見。第一,《解釋》規定“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緝、追捕過程中,主動投案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通緝、追捕以確定犯罪嫌疑人為前提,因此司法機關確定犯罪嫌疑人后,除當場抓獲不能被認定為自動投案外,嫌疑人只要沒有被當場抓獲,仍能夠自動投案。第二,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款規定,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機關可以發布通緝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歸案。“通緝”以批準逮捕為前提,因此批準逮捕不是阻卻自動投案的時間點。第三,《解釋》并沒有為自動投案設立“關門”時間,那么實踐也不能人為創立一些時間點(如立案時間、批捕時間、上網追逃時間等)不當限制自動投案成立的范圍。
意見六:不配合逮捕,經家屬規勸后到案的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該意見認為,批準逮捕決定作出后謝某一直逃避逮捕,直至4月1日在家屬規勸下才到案,因此謝某1月7日到案后又拒絕逮捕的行為可以評判為《解釋》規定的“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又逃跑”的情形,不能認定自首。但是,“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又逃跑的”包括兩種情形:一是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又逃跑,但后來又被抓獲的;二是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又逃跑,但沒有被抓獲的。前一種情形,由于逃跑后又被抓獲,自然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但后一種情形,由于嫌疑人已完全脫離司法機關控制,其后又再次自動投案的,仍應認定為自動投案,原因在于:(1)法律和司法要尊重人趨利避害的本性,要允許嫌疑人到案有反復;(2)嫌疑人逃跑后,當然又具備了《解釋》規定的自動投案的時空條件,沒有理由不予認定;(3)《解釋》第1條第(2)項規定,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認定為自首,但在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應當認定為自首。根據體系解釋方法,既然在如實供述問題上允許嫌疑人有反復、遲疑,那么當然也應該在自動投案問題上持同一立場。
意見七:為得到自首認定的到案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因為,公安機關4月1日對謝某執行逮捕,4月7日又對謝某取保候審,7天內完成了到案、收押、釋放全過程,說明謝某4月1日到案目的就是為了換取自首認定并得到取保候審,是假投案,應不予認定。筆者不認同此種意見。第一,《解釋》《意見》以及相關司法文件并未對投案的主觀目的加以限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第17條規定,對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惡意地利用自首規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應當依法從寬處罰。對該規定進行反面解釋得到,“惡意利用自首規避法律制裁的,不應當從寬處罰”。即,該規定沒有因為犯罪嫌疑人惡意利用自首就否定自首成立,而是規定自首成立但不從寬處罰。第二,《解釋》規定“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動,而是經親友規勸、陪同投案的”也應當視為自動投案。“經親友規勸”當然包括“經親友規勸后為得到自首的政策紅利而自首的”情形。因此,即便謝某到案就是為了得到自首認定,根據《解釋》的規定也不影響其4月1日自動投案成立。
(二)關于“謝某構成自動投案”觀點的評析
該觀點認為,謝某1月7日經書面傳喚到案接受訊問并就犯罪事實如實供述,因傳喚不是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謝某成立自動投案及自首。理由主要有兩點:(1)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案例第701號“周元軍故意殺人案”裁判理由指出,《解釋》所指“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中的“強制措施”是指犯罪嫌疑人實施投案行為之前,其人身活動是否處于自由、自主狀態,司法機關是否將其作為犯罪嫌疑對象對其人身予以強制或控制。已被控制的,屬于已被采取強制措施;未被控制的,屬于尚未被采取強制措施。[2]即,《解釋》的強制措施是指司法機關將犯罪嫌疑人作為嫌疑對象對其人身實施的包括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在內的實際控制。謝某于1月7日第一次到公安機關接受訊問時,不論是訊問前還是訊問后,其人身自由并未受到公安機關的限制,不屬于被采取強制措施的情形。(2)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傳喚并非刑事案件的強制措施,不使用械具,沒有人身拘束力。傳喚的形式,可以是電話、口頭,也可以是書面。經公安機關傳喚后,犯罪嫌疑人仍有到案或不到案的自主選擇空間,犯罪嫌疑人經過考慮后主動到案的,應視為是自動將自己置于司法有關控制之下的表現,應當認定為自動投案。刑事審判參考案例第354號“王春明盜竊案”明確認為,公安機關口頭或電話傳喚犯罪嫌疑人后,犯罪嫌疑人主動到案的,應視為自動投案。[3]因此,謝某自動投案成立;謝某自動投案后并如實供述,應認定自首。筆者同意此種觀點。
三 、刑法解釋學的學理評析
確認謝某自動投案,再分析裁判文書,能夠認定:本案中謝某構成自首,但認定謝某自首的事實應該是謝某1月7日的到案并如實供述,而非4月1日。即,一、二審裁判文書結論正確,但事實依據錯誤。本案“一案兩投”事實清楚,但因為公安機關針對4月1日謝某到案出具投案證明,裁判文書又附隨投案證明認定謝某4月1日構成自首,結果引發了謝某是否自動投案的爭議。這其中,既有機關工作問題,也有法律適用問題。就機關工作而言,一是派出所應就謝某1月7日的到案出具投案證明而未出具,預審科沒有必要就4月1日的到案出具證明卻又出具;二是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對投案證明,不加分析判斷,僅作形式審查。就法律適用而言,上述爭議反映出司法人員在解釋方法的使用上還存在較多問題。
(一)刑法解釋方法的使用問題
成文法天然存在規定不夠明確,規定滯后于司法實踐的情況。因此,對條文進行解釋,是法律適用的本來任務。刑法解釋方法主要有文義解釋、體系解釋、反面解釋、補充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等。刑法解釋的目的就是要在個案的司法適用中,圍繞成文法的規定,針對案件事實與法律規定之間的關系得出符合天理、國法、人情的妥當結論。但是,解釋方法不是萬能的,不存在某一解釋方法能應對全部解釋任務的情況。就某一種解釋方法而言,如文義解釋,大多數情況下能夠得出妥當的解釋結論,但在某些例外情形下,確實會因為解釋對象超出解釋“射程”而存在不能解釋、解釋結論荒謬的情形,這時就需要換一種解釋方法,或者配合使用其他解釋方法來檢驗、修正解釋結論。也就是說,解釋方法各有特點,沒有位階高低、解釋能力優劣的區分,在實踐中可以選擇其中幾種方法配合使用,也可以只使用一種方法,但不論如何選用解釋方法,解釋結論一定需要接受校驗和修正,否則容易得到令人吃驚的結論。
就本案而言,前述意見一、意見五就存在適用反面解釋后,僅以反面解釋的結論就簡單認定謝某不構成自動投案,而沒有對反面解釋結論進行修正校驗。如對“民警到場抓捕時無拒捕行為,供認犯罪事實的視為自動投案”進行反面解釋后,認為嫌疑人有現場拒捕行為的,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這一解釋結論就沒有被進一步校驗,未區分“現場拒捕后被抓獲”和“現場拒捕后脫逃”,導致結論失當。妥當的方法是,得出反面解釋結論后應結合“犯罪后逃跑,在被通輯、追捕過程中,自動投案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的規定,適用補充解釋方法進行修正限縮。類似情況還有意見三。意見三在進行文義解釋時,將“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解釋為“和”的關系,認為兩個要件中只要一個不具備就否定自動投案,是“一損俱損”,大幅度限縮了自動投案成立的時間范圍。事實上,“未受到訊問”與“未被采取強制措施”中間是頓號,“未受到訊問”與“未被采取強制措施”兩者是并列關系,兩者既可以同時存在,也可以擇一存在,只要一者在,就“一榮俱榮”,就存在認定自動投案的條件。對于意見三的不當結論,妥當的方法是對《解釋》第1條第(1)項所規定的7種以及《意見》第1條所規定的5種視為自動投案的情形進行分析,如“犯罪后主動報案,雖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沒有逃離現場,在司法機關詢問時交代自己罪行的”情形中,就存在未受訊問的情形,可得出“未受到訊問”與“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是并列選擇關系的結論,然后對之前的結論進行修正。意見六也存在應使用體系解釋的方法,參考同一規范中“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仍應認定為自首的規定,修正之前不當結論的情形。
(二)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的關系問題
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是相互競爭的兩種解釋觀,是罪刑法定原則派生出來的兩種解釋面向。形式解釋認為,對刑法條文的理解和適用應嚴格限制在法律條文的意思范圍內。實質解釋則認為,在刑法的解釋和適用中,還需要加以價值判斷,通過訴諸利益平衡,刑罰的適當性及合理性分析,實現甄別值得處罰的法益侵害行為的機能。[4]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實質解釋也是以承認成文法規定為前提的。但是,實踐中有的解釋者沒有認識到實質解釋只是罪刑法定原則下的一種解釋觀,誤以為實質解釋可以脫離成文法規定,是可以唯“目的”取向的解釋方法,造成解釋結論跨越成文法圍欄的結果。如意見七無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第17條的規定,以謝某惡意利用自首制度為由否定謝某的自動投案。又如意見五以自首設置的價值論為依據,認為謝某4月1日到案對于案件偵辦沒有任何意義,不應當認定自首;意見二則忽視了自動投案的形式要件,以是否主動這一實質要件否定形式要件的規范意義;意見六無視如實供述的可反復性,認為自動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認定自首。事實上,上述觀點只需要解釋者回歸到《解釋》《意見》的相關規定上,妥當運用解釋方法進行修正校驗,就能得到正確認識。
綜上,本案中的“一案兩投”原系司法工作不當造成,本無爭議必要,但源于解釋方法的不當使用,引起激烈討論。最后,需要說明一點:自首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危險性大小的判斷的要素之一,立法上屬可以型量刑情節。自首成立,并不意味著必須從輕、減輕處罰,能否從輕減輕,須結合案件中的其他情節綜合判定。如有學者指出,在死刑案件中,自首能否免死要取決于案件是否存在犯罪情節特別惡劣、手段特別殘忍、后果特別嚴重等情況,如果案件中存在上述情況,且除自首外沒有其他從輕情節,一般不考慮因為自首而判處死緩。[5]因此,對自首認定應持從寬尺度,但需把問題的重心放到“自首成立但能否從輕”的判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