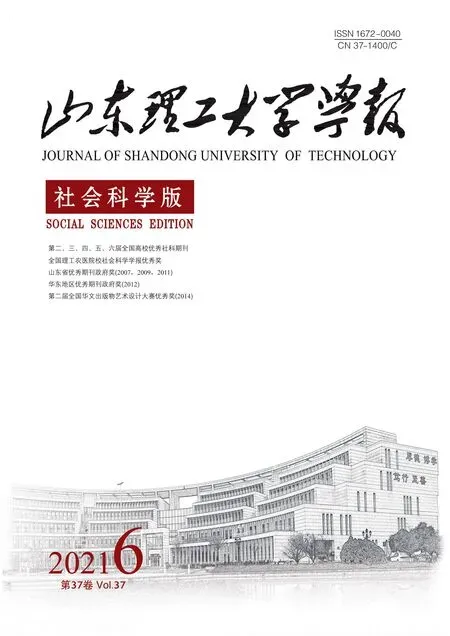《牽風記》藝術突破與美學建構得失談
——兼與部分溢美之評商榷
范愛賢
《牽風記》以高票獲茅盾文學獎,其成功無庸置疑。 但它是否像某些溢美之評所說,“把美與情推向極致”“雄渾與奇妙的結合妙到毫巔”[1],甚至“超越了具體的歷史與意識形態”[2]? 任何過分的溢美之評都令人懷疑。 缺乏審美理性的溢美之詞,不過是空洞的話語狂歡,無助于理解一部作品的真正價值。 對于一部優秀作品來說,其優點有價值,缺陷也同樣有價值。 白璧有瑕,無妨為璧。 基于此種考慮,本文擬從《牽風記》的藝術突破與美學成就入手,就它的得與失提出一己之言,以求教于方家。 就戰爭題材的小說創作來說,《牽風記》藝術上的最大突破可以用“做減法”來概括。 作者在一次訪談中說:“以前小說反映革命戰爭生活,可能更多是做加法。”[3]這里作者雖沒有明言自己在“做減法”,但以“做減法”來概括《牽風記》的藝術突破,應該是恰當的。 在“做減法”的藝術突破之下,隨之而來的是作品的美學建構。 而作品美學建構的得與失,又與藝術突破的“度”密切相關。 從歷史、藝術與審美幾個方面,力求客觀評價《牽風記》的得失,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一、歷史:審美的力與根
《牽風記》“做減法”,在基本的創作觀念上,就是避免對于戰爭的公式化、概念化、口號化的描寫。“把頭腦中那些受到局限束縛的東西徹底釋放,掙脫精神上看不見的鎖鏈和概念的捆綁,拋開過往創作上的窠臼,完全回到文學自身規律上來……盡量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口號化,砍掉頑固的不必要的修飾,返回文學創作的出發地”[3]。
在展開對于《牽風記》的分析之前,對老作家在這里談到的“公式化、概念化、口號化”,及在多次訪談中談到的“重新拿起筆來,不再以宣揚‘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空洞概念為己任”[4],還有必要做進一步的闡述。 首先必須明確,對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來說,“從勝利走向勝利”本身并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真實的歷史”。 當然,這并不否認歷史的過程本身充滿了艱難、曲折,甚至失誤,但“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真實的歷史”是不容否認的。 以藝術的方式向讀者講述“真實的歷史”是每一個文學家、藝術家的責任。 “文學家、藝術家不可能完全還原歷史的真實,但有責任告訴人們真實的歷史,告訴人們歷史中最有價值的東西”[5]。 至于文學家只能寫出空洞的、概念化的“從勝利走向勝利”,當然有作家的問題,作家沒有把握住藝術創作的美學規律,但也不能否認個別時期文藝上極左思想的干擾。 所有這些都與“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真實的歷史”無關,一味刻意地懼怕、否認、回避這個“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歷史,又何嘗不是一種公式化、概念化?
作者對戰爭的反映力求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口號化”,這是符合藝術創作規律的。 但藝術的出發地本身是植根于歷史的,反映戰爭的小說也必須直面戰爭的“真實的歷史”。 作者堅持把小說命名為《牽風記》,體現了尊重歷史的審美辨識力。 先睹為快的批評家曾建議改名為《空弦音》:“總覺得《牽風記》這個書名缺乏貼切感和吸引力,建議改為《空弦音》,含義為主人公的藝術形象與她永不消失的精神追求。 請您考慮。”[6]但作者婉拒了這一提議:“你建議改為《空弦音》,很好! 如果最終決定更換書名,你的建議肯定是第一方案。 不過,從30 歲出頭煎熬至耄耋之年,只剩下了《牽風記》三個字,實在不忍割舍。”[6]關于《牽風記》的命名,作者有一個解釋,“正是我們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拉開了各戰場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的序幕,牽引了全國戰爭的走向是我們這支部隊引為自豪的,所以擬定書名為《牽風記》”[4]。 作者的這個說明,揭示了這一命名的初心,也展現了這一命名的厚重的歷史感,“我們由黃河到長江躍進了一千里。 這個躍進的意義不要小看了,中國從南到北沒有多少個一千里,從長江再躍進一千里就到了廣東、福建的邊界了,下剩不到一千里了……這個躍進的事實表明戰略形勢起了巨大變化”[7],“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 這是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 “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 這個事變所以具有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8]。千里躍進大別山,是中國革命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 完全可以說,“牽風”這一意象,使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這段“真實的歷史”,有了一個最詩意、最形象的審美表達。
至于一些評論家的觀點,所謂《牽風記》“超越了具體的歷史與意識形態”,“甚至不惜顛覆以往戰爭歷史中的實然圖景”[9],筆者實在不敢茍同。 文學能超越“具體的歷史與意識形態”嗎?實則批評家所謂的這種超越本身也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罷了。 夸大地濫用“超越”,不過反映了批評的空洞與漂浮。 “戰爭歷史中的實然圖景”是戰爭史要做的,根本就不屬于文學,又何談顛覆? 這種“顛覆”之談,不過是理論上的唐吉訶德大戰心造的“風車”。 把“真實的歷史”、或者說“歷史中最有價值的東西”表達出來,是文學的責任。 擺脫這個責任,文學就失去了它賴以存在的最深厚的根。 批評家還是慎用“顛覆”,不要跌入虛無主義的泥潭,“虛無主義……只能導致作品和作家的沉落”[10]。
作家原稿焚毀毫不足惜,但唯獨不忍割斥《牽風記》這一名字。 “牽風”這一審美意象,既有對青春歲月的紀念,也有對而立之年文學審美直感的堅守,同時它更是“真實的歷史”對“文學的真實”的最大的饋贈。 進一步說,這一“命名”的堅守,是藝術家的審美直感對批評家鈍化的審美慣性的勝利,是歷史的、文學的真實對批評家理論的抽象與審美的空疏的勝利。 就這一點而言,“牽風”的審美價值是不朽的。 它集質實與空靈、厚重與飄逸于一體。 “牽”體現了歷史的質實與厚重,“風”則體現了文學審美的空靈與飄逸。“風”賦予“牽”的質實與厚重以審美的靈與逸,“牽”則賦予“風”的空靈與飄逸以審美的力與根,“有根基者才有生命力,有根基者才能遠走高飛。不然就會行之不遠,甚至寸步難行”[11]332。 而《空弦音》還不僅僅是“格局太小了”[4],即從審美意象的構成上說,“空弦音”只留下空靈與飄逸的一面,難以承載歷史大轉折的質實與厚重,汪可逾雖是一個很有特色的藝術形象,但承載不了歷史的質實與厚重。 小說失去了質實與厚重,也就失去了審美的力與根。 而且也與老作家心心嘆賞的審美風格相去甚遠。 老作家特別鐘情于孫犁的文學風格,“他唱出一只小曲,我們聽得出背景有氣勢渾厚的交響樂伴奏,他掬起時代巨流中的一束浪花,可以喚起讀者內心驚濤拍岸”[12]。 《牽風記》把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里程碑式的戰略躍進,濃縮為“牽風”這一審美意象,可以說體現了對孫犁審美風格的呼應。
二、執正馭奇:歷史與藝術的辯證法
“牽風”,是對小說整體結構的統攝,“真實的歷史”有機統一于審美的創造,使藝術突破的第二步——出奇制勝,有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牽風記》“做減法”在具體藝術層面是“出奇制勝”。一些評論家所謂《牽風記》的藝術:“類乎于書法運筆中的偏鋒或側鋒”[13],就是具體藝術處理中的尚“奇”、出“奇”。 藝術中的“奇”與“正”是對立統一的。 劉勰談文學批評,“先標六觀”,其中第四觀是“觀奇正”[14]715,強調“奇正若反,必兼解以俱通”[14]530。 藝術上“出奇制勝”的前提是“執正以馭奇”。 如果不能“執正以馭奇”,甚或因“逐奇”而“失正”,必然帶來審美上的損害。
從整體上說,《牽風記》做到了“執正以馭奇”:避開對戰爭全景的正面描寫與刻劃,以大寫意式的畫面組合,點染出“牽風”大轉折中,“真實的歷史”與藝術之審美的別樣風姿。 在這種別樣的審美風姿中,我們看到了,在戰爭歲月的滄桑背景上,在那張泛黃的照片上,那“一束標志性的微笑”。 這束歷史大轉折時期的微笑,穿過了戰爭的歷史的硝煙,綻放在依然年輕的記憶中,成為“含藏于心底的一汪清泉”[15]5。 我們聽到了,在茫茫夜空,在“敵我雙方作戰指揮的電報訊號往返交錯”所織成的一張無形的網上,一首古琴曲,“悠悠然穿過那張熾熱的電訊網,隨疾風流云遠遠傳向四方”[15]17。 飄逸的琴風與承載著民族解放戰爭風云的電訊風相交織,繪成一幅戰地審美奇觀。 我們還看到了,在大轉折的歷史洪流中,那匹名為“灘棗”的戰馬,攜帶500 萬年原始生命積淀而來的記憶,如何跟人類血與火的歷史所譜給它的一曲《關山月》猝然相遇。 遠古的自然生命時空、人類古老歷史的“文”化時空,在一雙纖弱玉手的牽引下,與中華民族大轉折的歷史時空融匯了。 我們也看到了,在哺育過《國風》的“野有蔓草”的大地上,“妻子送郎上戰場”的曹大姐,變成了感覺一直停留于“洞房花燭之夜剛剛才被中斷”[15]36的時刻中的、年輕的老人。 她那執著的守候與綿綿的期待,牽引《國風》的悠悠遠韻,匯入人民解放的歷史風云。 這誕生于歷史大轉折時期的守候,與“那束標志性的微笑”一樣,同其久遠,都因其與歷史大轉折的相遇,成為中國現代女性的審美風姿。 在這種審美風姿面前,那些“虛假”的所謂“人性與生命原始偉力的張揚”[13]的喧囂,應該感到羞愧。 我們還聽到了,“真正”的“一號”那聲“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吶喊。 這句歷經古老歲月“戰火镕煉的……制勝格言”,因與歷史大轉折撞擊,產生了改變歷史的“震撼力與感召力”[15]153。 我們又看到,歷史時空中的一個只能算是停留了瞬間的畫面:一個飼養員牽著一匹馬,渡過了一條河。 如何在“真正”的“一號”手中,變成了對氣勢洶洶的反革命集團的“絕地反擊”。 讓阻擋歷史前進的力量,望著野戰軍遠去的身影,瞠目結舌,徒喚奈何! 同時,我們也震撼于那個“不滿十三歲,挺進大別山年齡最小的”[15]174野戰軍小戰士,他的那聲讓民團鄉保隊“魂飛魄散”的狂笑,成為歷史大轉折血與火的交響樂中最年輕最有力量的音符……
在藝術的整體層面,這些極富節奏感與跳躍感的意象式的場景組合,具有著豐厚的歷史與生命的蘊含,把中原野戰軍所牽引的歷史大轉折,舉重若輕地給予“出奇制勝”的審美觀照。 它與“牽風”——這一對小說整體結構的統攝,一起構成了《牽風記》“中正偉岸”[13]的一面。 它有力地保證了整部小說的審美均衡。 也就是說,它審美上的價值在于,保證小說其他細部所可能出現的“逐奇失正”,不致損害小說文本藝術整體上應有的有機統一,不致造成整體上的審美偏畸。 雖然,在老作家的有意識的藝術努力中,想盡量淡化這屬于“中正偉岸”的一面,但在很多時候,恰恰是人民解放戰爭歷史洪流中,已沉入無意識中的審美積淀,校正了刻意的藝術突破的偏頗,這是歷史的、藝術的辯證法的勝利。
三、出奇制勝:歷史、生命與藝術的辯證法
在歷史與審美相統一的基礎上,《牽風記》“做減法”的第三個層面,就是把“牽風”所牽引的歷史大轉變,向生命樣態回溯。 但小說的生命樣態,并非原始、空洞的生命觀念,而是具體地誕生于人民解放戰爭的歷史洪流中的生命樣態。 整體上,小說展現的生命審美樣態,主要表現為男女兩性生命審美樣態,“人的性別意識無時無刻不在起作用”[15]24。 同時,借此呈現人與萬物生息與共的生命審美景觀。 它的成功同樣有賴于,尊重“真實的歷史”,尊重“執正馭奇”這最簡單、也最豐富的藝術規律,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出奇制勝”的藝術表達效果。
首先,《牽風記》的男女兩性生命審美樣態表現為富有突破性的女性“全裸”形象,可稱之為戰火“夏娃”。 對于《牽風記》中出現的“全裸”形象,作者曾這樣解釋:所“著意的是透過女主人公全裸的形象,進一步展現小說的內在意蘊……一個裸體少女,跟一只灰鴿和一簇蒲公英并無區別,彼此生息與共”[13]。 在“通則不乏”的藝術文脈中,“全裸”形象有跡可尋,最早如老作家八十年代的經典短篇《西線軼事》。 《西線軼事》的結尾:“六姐妹在河灣里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派人站上哨,輪流下河去洗。 她們輕裝很徹底,現在可憐了,沒有替換的衣服。 只好先把衣服……全部洗出來,曬在草地上,然后洗頭洗澡。 完了,扯幾片芭蕉葉鋪著,坐下來梳攏著水淋淋的頭發,等著衣服干。”[16]501這是徐懷中小說創作最早對女性裸體的審美觀照。 與《牽風記》相比,這初次的“女性裸體”最為徹底,真正“夏娃式”的,是戰火“夏娃”的第一次亮相,這是六位剛走出戰火硝煙的“夏娃”。 但在藝術上,把它處理為“觀者”缺席的場景,規避了作為注視者的異性的目光。 原點生命的裸體,因了戰火硝煙的加入,以最自然的姿態,獲得了最恰當的審美距離,獲得了最自然、最美的藝術觀照。 而作為唯一的“注視者”——讀者的目光,也因藝術的距離感獲得審美的凈化。戰火“伊甸園”自然地誕生于戰場上的凱旋,“人”的歷史中的戰火硝煙,賦予最具震撼性的審美場景以一個最為自然的姿態。 其自然性甚至讓敏銳的批評家渾然不覺。 從《西線軼事》發表至今,有大約五篇論文,對《西線軼事》與《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進行對比研究,這其中也只有兩篇僅僅注意到了小說最后,那個放置于注視者目光下的場景:夕陽下,六位女兵一字兒排開走回駐地。 而無一注意到——注視者目光被規避的——“河灣”。
在“變則可久”的藝術創新中,《牽風記》是對《西線軼事》的繼承與發展。 《牽風記》版的“戰火夏娃”,撤除了對注視者的設防,讓“亞當”的目光闖入“夏娃”的世界。 如《牽風記》中呈現的最質樸的“夏娃”場景,發生于狂風暴雨的急行軍后。戰士渾身的衣服都濕透了,作為男性的“戰士們”可以脫個精光,圍成圈烤干衣服。 可擁有“標志性微笑”的汪可逾,“被徹底累垮了,什么也顧不了啦,在一家門洞里支起門板,僅穿一條短褲睡下了……不想一覺睡過了頭,天大亮了。”[15]84于是,十八歲的女八路軍,在歷史大轉折所提供的最自然的時空中,把“純自然狀態下的……一個不拘一格的姿態”[15]88呈現出來,“一名女八路、一只灰鴿、一簇蒲公英,生息與共,感受一同。 大家一起經歷了暴風雨的洗禮,一起迎來冀魯大平原又一個空氣清新的早晨”[15]90。 這是最優雅、最質樸的“夏娃”。 歷史大轉折中的暴風雨,賦予這一場景一個最自然的姿態,這一最自然的生命姿態,又因歷史洪流的暈染獲得富有質感、深度的審美魅力。 顯然這里所呈現的、最重要的,可能并非作者所強調的萬物“生息與共”的生命狀態,而是生命在歷史大轉折洪流中,得以自然地凸顯的別樣的審美風貌。 這一藝術刻劃,與孫犁小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孫犁抗戰小說中,藝術形象的自然生命樣態與人類歷史尺度達到了最自然、最完美的融合。 如孫犁短篇小說《蘆葦》中的經典場景:“姑娘的臉還是那樣慘白,可是很平靜,就像我身邊這片蘆草一樣,四面八方是槍聲,可是草葉子還是能安定自己。”[17]蘆草,草芥生命,在孫犁看似漫不經心的描繪中,與抗日軍民融為一體,讓原始生命樣態與人類歷史達到最自然的結合,從而升華出一種獨具的審美震撼力。 《牽風記》中的“戰火夏娃”生命場景,與孫犁作品中的“草芥”生命形象相比,都具有同樣的、與歷史融為一體的“自然”風貌,但審美震撼性更強。
《牽風記》中其他兩個經典“戰火夏娃”場景:一是十二、十三章,“黃河七月桃花汛”中的“夏娃”群像;二是小說最后描繪的,那個位于大別山主峰至少已有“五百萬年記憶”的巖洞,成為汪可逾的最后歸宿。 汪可逾在這最后的歸宿地,變身成超越所有倫理羞恥感的“最原始的夏娃”。 這些戰火“夏娃”系列,不再規避戰火“亞當”們的目光,但較好地協調了歷史、生命、審美之間的關系,始終守護住了藝術所必須具備的審美的距離,守護了藝術空間的美、雅、潔,而且還“通過文學的審美功能最大程度地誘發了讀者的喜愛之情”[18],出奇制勝的藝術表達比較成功。
其次,《牽風記》中兩性生命審美樣態還體現為集大俗、大雅于一體的“安卵”生命美學。 “安卵”一詞出自《牽風記》“真正”的一號的口中,“今天開的不是握手的會……今天開的是安卵子的會。 我們一些干部……變得不像是一個男人了,遭遇敵人強硬不起來”[15]198。 這一細節,在電影《大轉折》中已出現過。 作為電影《大轉折》的藝術顧問,老作家順手把這一細節挪用到了小說中。 “卵”代表男性原始生命的強力,在小說中,它還喻指軍人所需要的勇敢。 “卵”之需要“安”,意味著這種原始生命強力必須接受人類自覺的“文”化。 而“安”的具體指向,一是當這種生命強力喪失時,需要“安”,以喚起雄性風姿,使原始強力“升華”為扭轉大轉折危機的歷史偉力。 “真正”的一號,脫口而出,不存一絲做作地完成了由大俗到大雅的轉化。 在由大俗到大雅的轉化中,自然地與生理的層面脫離、形成了審美賴以存在的距離感。 二是,當以“卵”為表征的生命強力橫流時,也需要“安”,把“它”納入倫理的、美的秩序,從而與生理的本能的控制脫離,形成藝術所必需的距離。 小說富有喜感地、顯示了“安卵”生命美學這一方面的是關于天才小演員劉春壺的一個經典細節。 舞臺上的天才小演員,生活中卻擁有“小尿壺”這樣一個不雅的外號,以至于日常需要幾位女演員輪流帶他睡覺。 當“永遠帶著一束標志性微笑”、生活中卻又有別人難以理解的“潔癖”的汪可逾,出于同情,破例開放了別人不容染指的禁地,也要帶小春壺睡覺時,小說石破天驚地出現了小演員“憋尿”的經典細節。 小演員沉睡中雖沒有尿床,但“十一歲男子漢那小果果”卻“如同一根旗桿直直地豎立在那里”,嚇得汪可逾不知如何是好。 “‘它憋尿了!’一個女演員近前一看,給出了明確結論”[15]105。 對于一個孩子來說,不雅的“尿床”是一個最自然的行為。 但這種本能的自然的行為,卻在“一束標志性的微笑”面前,似乎自覺接受了人類的“文”化。
《牽風記》生命樣態的別樣審美中,最具崇高美感的“真正”的“原始生命偉力的張揚”,是那繞行堰塞湖底做逆時針奔跑的古代野馬群:“它們重新感受到了草原古馬群來群往狂野無羈的那種熱切振奮,感受到了不受任何羈絆而隨意放飛自我的那種輕快歡愉……它們必須壓縮在這最后一刻,以超高速,跑完自己一生本應該達到的全數奔跑里程。”[15]162-163這群“活在二十世紀的古代野馬群”,把恢弘的原始生命偉力融入到了人類大轉折的歷史洪流中,在短暫的繞行中匯聚起500萬年的生命記憶,來完成一生必須完成的“絕地奔跑”。 這酣暢淋漓的宣泄,讓批評家津津樂道的曹水兒式的“野有蔓草”的表演,只成為一個鬧劇式的空洞道具。
《牽風記》中這些生命審美樣態非常富有審美魅力。 它們的獨創性,可謂石破天驚。 但都較好地把握了歷史、生命、審美之間的關系,自然地內含了“執正馭奇”的藝術文脈。 典華并重,變俗為雅,融生命于歷史,建構出獨特的審美風景。
四、逐奇失正:藝術與歷史的審美失衡
《牽風記》藝術創造的獨特性不容質疑。 說《牽風記》整體上“執正馭奇”做得比較成功,大致是符合實際的。 至于說《牽風記》“雄渾與奇幻的結合妙到毫顛”,“雄渾”為“正”,“奇幻”為“奇”。從至微、至細到至高、至宏(“毫”即“微”“細”,“顛”即“高”“宏”),無處不妙,“妙到毫巔”,顯然過甚其辭,缺乏必要的審美理性。 “至寶必有瑕穢……良工必有不巧”[19]。 認為《牽風記》“白璧”有“微瑕”,無損于它的成就,而說它“妙到毫巔”未必抬高了它。
《牽風記》做“減法”,在最具體的情節結構上,表現為把歷史轉折的大場面,減縮為一匹馬,一個女性,兩個男性,“兩男一女,以及有著500萬年‘記憶’力的一匹老軍馬”[13]。 最成功的形象是軍馬“灘棗”,其次是汪可逾。 這兩個形象的成功之處前面已做了分析,其要義皆在于融生命、歷史、審美于一體,遵循了“執正馭奇”的基本藝術規律,“正”不失“奇”,“奇”不奪“正”。 至于其他兩個形象,因生命、歷史、審美處理的失當,在藝術的“正”“奇”處理上也出現了較大問題,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審美偏畸。
首先,“所謂”的“一號”首長齊競這一形象,在藝術處理上,由“執正馭奇”走向了“逐奇失正”,未能很好守護恰當的審美平衡。 齊競初出場確實讓人眼前一亮,而齊競面對汪可逾的裸體,所不由自主地表現的藝術激情,也讓人非常震撼。而他驚慌失措的尷尬,被汪可逾談笑有聲地消解,更讓人充滿喜劇式的美感。 這些以及類似的場景基本上遵循了“執正馭奇”這一基本的藝術原則,成就了不凡的藝術美感。 但這一形象后來的場景就越來越不協調,越來越減色,終于走向“逐奇失正”。 最大的敗筆發生于第十八章,齊競無法釋懷汪可逾是否被敵人強奸,面對汪可逾竟說出如此低俗之極的話:“所謂‘初夜落紅’,是最潔凈最珍貴最神圣的一種紀念物。 我設想,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應該用一整包藥棉保存下來,裝在一個鐵匣子里……”[15]193。 這使齊競作為一個富有藝術修養,接受了民主自由熏陶,又義無反顧參加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先進知識分子、野戰軍優秀指揮員形象徹底坍塌,成為一個對女性充滿歧視的封建衛道士。 當有的批評家質疑這一藝術處理邏輯上不通、齊競是否是一個應該被批判的角色時,作家也承認了這一細節的不妥當,“應該謝謝你! 你這個意見很中肯,很有說服力。 當初我也有過反復酌量,得失之間不夠那么清晰,半生不熟地勉強作了這樣的鋪排。 齊競這個藝術形象有他復雜性的一面,作者無意將他作為一個批判的對象。 如果有再版的可能,我會重新寫過相關的章節”[13]。 “逐奇失正”,作者坦然地承認了這個不足,也充分顯示了老作家豁達的胸懷。 可能作家尚不十分清晰的是藝術處理失敗的原因。 在筆者看來,《牽風記》中這一藝術處理失敗的原因,源于兩個藝術上的大忌。 第一是“刻意”。 作家在構思時,太刻意于做減法,太刻意于擺脫“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概念化、公式化,太刻意于表達自己的人生感悟,以至于走向了另一種“概念化”。 這已不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概念化,而是藝術形象“性格復雜性”的概念化,作者自身觀念的概念化。 長期以來,中國當代作家就有一個無法擺脫的心結,為了顯示深刻,就要標榜對社會人生復雜性的認識,而要把這種認識表達出來,就要塑造具有“性格復雜性”的藝術形象,以至于不自覺地跌落進“另一種概念化”——復雜人性的概念化,變成“另一種傳聲筒”——復雜人性的傳聲筒。 “在他們把人物寫得單純一些的時候,我覺得是真實可愛的,在他們著意把人物復雜化的時候,他們的作品失敗了……復雜而不統一,不能叫做典型,只能叫做分裂……所謂復雜,應該指生活本身,人物的遭逢,人物的感情等等而言,不能指性格而言。 在這一方面,過多立論,不只違犯生活的現實,對創作也是不利的”[11]405。 老作家孫犁的這個告誡,是深諳藝術規律之談,值得當代作家、批評家重溫。 第二是“偏愛”。 作家對于汪可逾這個人物過于喜愛了。如果作者過分欣賞自己的主人公,那總是不好的。作家也承認汪可逾這個形象過于理想化了:“這個人物形象亦真亦幻,戰爭年代幾乎不可能出現類似這樣的女性。 確實如此,或許過于理想化了”[13]。 作家對于汪可逾的過分喜愛,不知不覺中讓其他人都成了陪襯。 為了陪襯得更有悲劇性,為了讓汪可逾對愛情徹底絕望而拋下一切,而不惜讓齊競有“初夜落紅”這樣拙劣、低俗的自辯。 這一細節造成的“性格分裂”,藝術上,使齊競這一形象失去了內在的有機統一性;審美上,使齊競這一形象隨后的所有懺悔,都失去了應有的悲劇性的感染力。 這一細節的出現意味著齊競這一形象已徹底失敗。 我不理解批評家關于齊競自我救贖的宗教震撼性[13]是如何感受到的,也不理解齊競的形象“一掃陳舊氣息,成為令人為之動容的一幕悲劇”[6]是如何產生的? 齊競形象塑造的失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齊競很大程度被作者符號化了,只是給他貼了一個優秀指揮員的標簽,但并沒有生動有力地呈現出來。 如果這一方面能得到具體的歷史的藝術的呈現,正常的歷史感覺也許會不自覺地校正了藝術突破的“逐奇失正”。但作家太刻意于回避“老舊模式”了,害怕戰爭場面一多,就破壞了自己的藝術追求,“原來構想,是盡可能淡化戰爭背景,不拉到前景來。 擔心戰爭場景寫多了,給人感覺,又回到以前軍事戰爭題材作品那種老舊模式上去了”[4]。 寫戰爭宏大場面,只是一個“寫什么”的問題,并不是一個“怎么寫”的問題,所以它本身不是劃分是否“老舊模式”的標準。 “模式”問題發生于“怎么寫”上,是藝術地寫,還是“公式化”“概念化”地寫? 因為刻意回避戰爭,就使戰爭中的人性表現失去了應有的歷史尺度,而成為“空洞”的人性觀念的演繹,這正是目前許多所謂“創新”作家的創作誤區。
其次,作品形象的審美失當要數曹水兒。 齊競這一形象的審美偏畸表現為由“執正馭奇”走向“逐奇失正”。 而曹水兒這一形象的審美失當源于開端嚴重的“逐奇失正”,以至于后來的“由奇返正”無法制止“逐奇失正”的慣性,使這一形象最后還是失敗了。 曹水兒這一形象的“逐奇失正”,實際上反映了文學創作中的一個普遍問題,如何賦予藝術形象以恰當的歷史尺度,恰當的倫理定位。 藝術形象的價值當然不能以倫理的標準來衡量,但任何一個虛構的藝術形象無疑都具有它所特有的、由人類歷史而來的倫理定位。 就拿《牽風記》第四章,為曹水兒安排的“野有蔓草”的浪漫空間來說。 作家在小說中特意引用了《詩經》中《野有蔓草》的詩句,“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作者對這一詩歌背景的解釋是“周代……未婚男女可以自由相會調笑歡娛,以致同居私奔也并不在禁”[15]46。 雖然,這首詩的美,不在于它宣揚了什么倫理觀念,也不在于經解傳統中的:“朋友相期會也”[20]。 但“未婚男女”的定位,保證了《詩經》中這一場景。 所具有的雖模糊卻恰當的歷史的及倫理的界線。 正是藝術創造與歷史、倫理界線的協調,才保證了藝術場景經久不息的審美魅力與文化魅力。 但《牽風記》“野有蔓草”的“浪漫”所展現的是:一個八路軍戰士拎著幾斤白面,在冀魯豫根據地農村,四處尋歡、四處留情。 每到一處,曹水兒的慣用伎倆是,“一邊大膽靠近獵物,一邊搭訕著上前說‘大嫂! 我這里有白面,跟你討換一點馬料’”[15]44。作者在寫曹水兒的場景時,似乎已經忘記了自身對《野有蔓草》“浪漫”背景的解釋——“未婚男女”。 正是這一細節的失誤,造成藝術突破與人性倫理的不協調,給曹水兒這一形象帶來審美上的惡感。 而作者竟賦予這些場景以“啟蒙”的價值,“烽火遍地兵荒馬亂,雖帶來無盡的禍患,卻也打破了數千年農耕傳統帶給莊稼人的封閉與孤寂。 鄉下婦女,難道就不向往走出煙熏火燎的灶屋間,去探索一下奇妙無窮的外部世界? 編織一串又一串羅曼蒂克的美夢?”[15]44更是匪夷所思。這些不當之處,竟被一些評論者美之曰“愛情”,甚至認為“他的那些風流事情,也顯得非常可愛”[4],實在滑稽。 對曹水兒形象審美“惡感”的論斷,并不是作家所擔心的,人們不能原諒曹水兒,而對他進行道德的評價,“他從不肯忍受任何外力約束,快意跳脫,活出了自己。 相信讀者不至于單純對他做出道德裁判”[13],是源于這一藝術形象,與它所應具有的歷史的及倫理的定位不協調。 不可否認,文學史上許多優秀的藝術形象,往往是倫理上應該被否定的人。 但這類形象,倫理上雖被否定,但與這一形象自身的“倫理定位”卻是協調的,因而也就無損于這些形象的審美魅力。如莎士比亞戲劇中了不起的喜劇形象福斯泰夫。他是個渾身充滿道德瑕疵的形象,但并沒有給讀者帶來審美的惡感。 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這一形象的塑造,維持了審美所要求于藝術形象的恰當的歷史及倫理的定位。 福斯泰夫這一形象,在莎士比亞的劇作中屬于破落貴族。 貴族在文藝復興的歷史發展中,已屬于歷史上及倫理上應該被否定的階層。 但劇中的福斯泰夫,又能自嘲自貶地坦率承認自己的“壞”,這就顯露了“壞”中有“真”的可愛的一面,審美上使人淡忘了他倫理上的瑕疵而具有了藝術上的美感。 但曹水兒這一形象則不同,是一個被作者作為正面的悲劇形象描繪的八路軍戰士。 這一形象道德上可以不完美,但不能是一個無視人性正常倫理的人。 至于有些學者在為這一形象辯護時所取的理由竟是:曹水兒是用白面換取肉體之歡,“不是拿槍逼著要強暴婦女的那一類人”[4],更是無視八路軍作為人民軍隊與舊軍隊、反動軍隊截然不同的政治素質與嚴明紀律,實在是在文學評論中失去了起碼的是非底線。 曹水兒這一形象,盡管作者很喜愛,但在塑造上,因為倫理定位的失當,一開始就違背了基本的藝術規律——執正以馭奇,而走了一條“逐奇失正”的岐路。
與齊競這一形象相比,曹水兒這一形象開端的“逐奇失正”被后來的“由奇返正”有所校正。曹水兒這一形象的“由奇返正”,首先表現為作者對這一形象進行了倫理上的校正。 曹水兒行軍中擔負照顧汪可逾的任務,一反四處留情的惡習,與汪可逾之間的關系始終保持在愛與美的界線上。其次表現為,《牽風記》對曹水兒的勇敢、機智做了生動具體的展現。 這與小說對齊競作為一個優秀指揮員形象的符號化、說教化表現不同。 對曹水兒形象的這些描寫基本遵循了“執正馭奇”的藝術規律。 這一番“由奇返正”的藝術校正,基本上還是成功的。 可惜的是,在小說的第十七章,又讓曹水兒與保長女兒來了一場拙劣的“偽野有蔓草”的表演。 成功的“由奇返正”終又被這最后的“逐奇失正”所破壞。 這樣,由第四章“野有蔓草”開始的“逐奇失正”,最終還是破壞了曹水兒這一藝術形象應有的,藝術、審美與歷史、倫理的內在統一。
作家一旦有了己所不覺的“刻意”與“偏愛”,就會犧牲掉正常的藝術感覺,就會使藝術形象失去藝術所要求的“自然而然”,使藝術形象失掉自身所立足的歷史根基。 這一問題甚至也損害了汪可逾的形象,使這一形象也有了“白璧微瑕”,“不自然”地出現了:拔高有失分寸處,畫蛇添足處,超脫流于矯情處。 提揚有失分寸處,出現在第十一章,把一個年輕的八路軍女戰士,做作地置于“晉冀魯豫解放區三千萬人民”的對立面,不僅失去了起碼的歷史感,而且這種主觀拔高也造成了這一形象的虛假性,失去了立足的歷史根基。 畫蛇添足處出現在第十二、十三章,眾“婦救會們”終于克服種種心理上的、倫理上的障礙,為了安全僅穿內衣,“裸體”展示在眾目睽睽之下,而“眾目”也終于“由興致勃勃而自感無趣,開始在全線撤退”[15]128。 這本是一個非常富有喜劇情趣的人性變化場景,小說只要把它生動地呈現出來,留下一些想象、回味、思考,也就完成了藝術的任務。但作者卻畫蛇添足地,讓汪可逾不失時機對她們進行人類“文”化史的教育,“人類的羞恥意識,正是因為穿衣服才帶來的”[15]129;進行人類進化史的教育,“人類穿起獸皮,大約是十七萬年前的事。 而踏上直立人的進化歷程,至少有四百萬年了。 相比之下,穿起衣服才有幾天的事”[15]130。這里太熱衷于讓汪可逾來表達作者自身的生命與人性觀念了。 這樣的處理從兩個方面看都違背藝術所應有的歷史的尺度。 一是從小說所反映的大轉折的歷史來說,如果我們還沒有忘記,我黨在自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從“識字”運動開始的、對廣大農民進行的艱難的文化啟蒙,那么就應該想到,汪可逾的“文化啟蒙”,顯得多么脫離實際。二是從小說所面對的當代讀者大眾所處的時代來說,汪可逾的“文化啟蒙”只是常識。 在小說里,借人物之口談常識顯然是費力不討好的。 當然從汪可逾——一個剛加入野戰軍不久的新戰士的角度著眼,依此顯示她的真誠、質樸,而又有些脫離實際,也不失為一種可愛的喜劇性。 但問題是作者在安排小說的藝術情調時,處理成“正劇”,而非喜劇式的莊諧兼備,這必然產生一種審美上的不和諧。 超脫流于矯情處出現在第二十二章。 曹水兒九死一生保護汪可逾,冒著極大危險消滅了四個敵人,而汪可逾卻無法忍受曹水兒身上因斃敵而帶來的氣味,宣稱“這種氣味不是河水清洗得掉的!”[15]222小說想把汪可逾塑造為一個“在決定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時代支配的同時”[21]、又堅持著自我超然的人性觀念的形象;但在生死攸關的歷史關頭,這種超然觀念不僅顯得空洞,而且矯情得不可理喻。 面對這么多的敗筆、裂隙,又哪里談得上“把美與情推向極致”? 評論家的“嘩眾取寵”“大花轎人人抬”,實在是不可思議。 究其實,這不是汪可逾的錯,錯在作者把汪可逾這一形象當成了自身戰爭反思的傳聲筒。 作者在一次訪談中,談到自己對戰爭的反思,認為“最好的戰爭,也遠不及最壞的西線無戰事好”[22]。 這里且不說“戰爭”與“無戰事”在邏輯上是不同層面的東西,彼此沒有直接的可比性。 即便從對戰爭的認識來說,戰爭也不能從抽象的、非歷史的“好”與“壞”來區分,只能從具體的、歷史的“正義”與“非正義”來區分。 為了國家民族人民的解放,必須用“正義”的戰爭反對“非正義”的戰爭,用“正義”的革命暴力反對“非正義”的反革命暴力。 戰爭與和平是辯證的,為了和平必須壯大正義的戰爭的力量,為了“無戰事”必須先用“正義”的戰事反擊非正義戰爭的戰事。 在這一問題上,文學界一部分作者中流行的抽象的暴力觀、抽象的戰爭觀,不過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生吞活剝狄更斯《雙城記》、雨果《九三年》對18 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反思,全然脫離20 世紀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具體歷史。 小說不適當地賦予汪可逾超越戰爭的表現,嚴重違背了基本的歷史事實。 作者本人也承認這一形象在那時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過于理想化了。 所以與《西線軼事》中的陶珂相比,汪可逾的“清洗”是“矯情之洗”,遠不及陶珂希望成為的那滴“純凈的水”[16]500更為坦誠。 由于汪可逾形象在這些方面,都脫離了這一形象產生的歷史根基,作者用一個長篇極力渲染的那“一束標志性的微笑”,遠遠不及孫犁的短篇《琴和蕭》所描述的兩個女孩子臉上那“新鮮的俊氣”更富有審美震撼力,“我在孩子的臉上,象那老船夫的話,我只看見了一股新鮮的俊氣,這俊氣就是我的生命的依據。 從此,我才知道自己的心、自己的志氣,對她們是負著一個什么樣誓言的約束,我每天要怎樣在這些俊氣的面孔前面受到檢查”[23]。《琴和蕭》是老作家徐懷中非常喜愛的一個短篇。
五、結語
《牽風記》的藝術突破,概括地說就是“做減法”,美學上的成功得力于尊重小說所要表現的“真實的歷史”,尊重作者自身幾十年由“真實的歷史”積淀而來的審美直感,尊重“執正馭奇”的藝術辯證法,尊重自然生命樣態的歷史尺度,使自然生命樣態在“真實的歷史”洪流中得到自然而然的藝術呈現,從而保證了恰當的審美距離的生成。 但在主要藝術形象的塑造上,其藝術的突破帶來明顯的美學失誤。 失誤的基本原因是,未能恰當處理歷史、生命、藝術、審美之間的辯證關系。由此而帶來的具體失誤有三點。 一是,過分刻意于所謂藝術上的突破,破壞了藝術創造應有的“自然”感。 失去了“自然感”,就犯了藝術的大忌——生硬與做作;所謂的藝術突破就越出了藝術的范疇。 二是,未能恰當地確定藝術形象的倫理定位。 由于藝術形象塑造與人性倫理上的不協調,而帶來審美上的不快感。 三是,《牽風記》把藝術形象作為生命樣本來反映時,卻沒有恰當地把握藝術形象之為藝術形象所必然具備的最基本的歷史尺度。 曹水兒的偽“野有蔓草”,不過是情欲的宣泄,遠遠談不上男女愛情。 而汪可逾,當她在小說中以一個自然而然的生命形象出現時,非常可愛。 生命樣態的質樸性及這種質樸性與人類歷史大轉折的自然嵌合,讓汪可逾這一形象具有了非凡的審美魅力。 但當這一形象的生命樣態脫離了歷史尺度的制約,成為作者生命思考的傳聲筒時,藝術的突破就蛻變為藝術形象的虛假,從而造成審美上的不協調。 這種美學上的不足,可以說是《牽風記》的白璧微瑕。
不否認《牽風記》是一部有藝術獨創性的作品,但它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也是事實。 “白璧”有“瑕”,并無損“璧”的光彩。 《牽風記》的藝術成就有值得借鑒的價值,它的不足是值得吸取的教訓,二者同等重要。 藝術是人的創作,人的創作,力求達到但又永遠不可能達到的境界是“自然而然”,所謂“妙到毫顛”“把美與情推向極致”,對于評價《牽風記》來說,不過是空洞的囈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