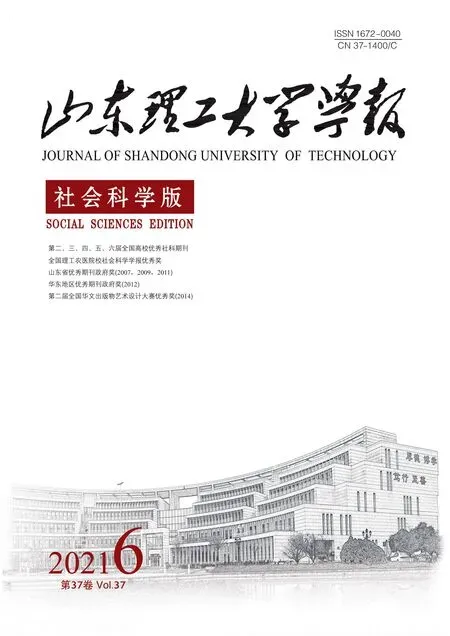精神分析視域下《聊齋志異》的欲望闡釋
張玉霞,馬 健
一、小說中的“白日夢”——無意識的欲望表達
在精神分析學派看來,個體的意識與無意識中隱藏著超我和本我的力量。 意識屬于理性的范疇,受制于理性的桎梏,因此,意識本身并不會自然地釋放欲望。 而無意識則不同,它是存在于人心底的欲望的集合,會產生本能的沖動。 當理性無法壓制無意識時,潛意識中的本能沖動和欲望就會試圖逾越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邊界,并在個體的行為、思想等方面有所體現。 不過,潛意識的活躍在夢中尤為明顯,借助夢,個體潛在的欲望會不斷延伸,在夢中得到釋放。
弗洛伊德曾在《作家與白日夢》中談到,當個體自我感覺幸福時不會有太多幻想,而那些愿望不能得到滿足的人才會去努力幻想。 這種欲望主要分為野心的欲望和性欲,個體在夢中會自然地釋放這兩種欲望,從而獲得一種虛妄的滿足。 關于這點,弗洛伊德認為:“夢本身也常可為一種潛意識欲望的滿足;假使你們把夢看成夢的工作的產物,則舍欲望滿足之外就不再有其他意義了。”[1]也就是說,夢不只是預告或警示,存在于個體潛意識部分的力量會通過欲望層面表現為原始的沖動,而這種力量的結果會使人在欲望中得以滿足。 除了以上的分析,對夢的解釋,可以借助中國的古典小說來完成,從不同的角度闡釋小說中人物的欲望表達。
蒲松齡撰寫的《聊齋志異》中有許多故事都涉及到了夢,無論是關涉人生哲理還是期待愛情又或者是對社會弊病的影射,無不顯示出個體欲望在夢中的活躍與解放。 《蓮花公主》中,書生竇旭在夢中進入了府邸,但他自己因為初進這樣的場合,整個人變得茫然無措,若失魂魄,最后失去了和公主結婚的機會。 為此,竇旭十分懊惱,醒來后,他“冥坐觀想,歷歷在目。 晚齋滅燭,冀舊夢可以復尋,而邯鄲路渺,悔嘆而已”[2]1147。 可見,竇旭在夢中的欲望受到了阻隔,因為自身的局促、魂不守舍導致了自己對男女之情的追尋無法實現,他的欲望并沒有得到滿足。 于他而言,即使知道自己身處夢中,但他仍舊希望自己可以獲得結婚的機會,所以,當他再次被召到桂府,男女之情的欲望獲得了滿足。 他和公主結婚后,為了不讓公主成為一場夢,于是他“戲為公主勻鉛黃,已而以帶喂藥,布指度足。”[2]1147以此來期望自己不要失去當下的幸福感。 對此時的竇旭而言,夢境的現實與否已經無關緊要,即便永遠處在夢中,他也希望能夠保持這樣的狀態。 也就是說,夢境在竇旭看來更像真實的世界,在他的潛意識中他樂于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
但事實不能如他所愿,竇旭剛剛經歷過新婚的喜悅,桂府的大王就告訴他“國祚將覆”,災禍席卷了桂府,而竇旭也在公主的哭聲中被驚醒。竇旭在與友人交談中最后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夢中的公主是蜂房中的蜜蜂,雖然是春秋大夢一場,但這樣的美夢卻無限放大了書生竇旭的潛意識,讓他從中獲得了自我的滿足。 在他的夢中,本我的力量實現了充分的解放,這種欲望的顯現也使得個體有了更多的欲望體驗,指引著個體不斷深入自我,解放自我。
當然,除了男女之情的白日夢,自然也有關涉功名利祿的舊夢。 在《續黃粱》一文中作者通過曾孝廉在夢中的一系列故事,講述了他在夢與現實之間的大起大落。 小說中,曾孝廉在僧舍遇見了一位老僧,他讓曾孝廉做了一個美夢。 夢里,曾孝廉被皇帝賜予了高官,他一時成了大熱的人物,于是不少官顯都來討好巴結,“傴僂足恭者,疊出其門”[2]876。 這讓一個窮苦的書生體會到了權欲的誘惑,于是他利用自己的職權開始謀取私利,提拔親近之人,排擠與自己有仇的敵人。 最后因為欲望的膨脹,曾孝廉變得“荼毒人民,奴隸官府,扈從所臨,野無青草”[2]877。 權欲讓一個窮苦的書生放大了自身的欲求,在夢里,壓抑在他心底的各種欲念不再受理性的節制,欲望的擴張讓曾孝廉不再拘泥于傳統的道德、情義,而是改變了他的價值觀。 他從一個窮書生墜入到官場的爾虞我詐之中,成為了朝野中的狡黠者,淪為了欲望和政治的奴隸。 如果從欲望的更深層次來看,當曾孝廉開始滿足于權力的結果,作為個體的他已經發生了“質”上的變化。 潛意識中的本我突破了桎梏,在欲望層面展現出了強大的力量,推動著個體去破壞,去無節制地放縱,曾孝廉恰恰跌進了這樣的漩渦,無法自拔。
這種“黃粱夢”式的故事實際上在唐朝時期有諸多類似的作品。 比如《南柯太守傳》《枕中記》以及《櫻桃青衣》,這幾個作品都是以“現實—虛幻—現實”的敘述模式來描寫士子文人在官場中的無奈與沉浮。 比如在《南柯太守傳》中,淳于棼經驗到了美夢的虛幻,“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使他明白了人生如蜉蝣一般,轉瞬即逝,于是投入了道教,修身養性。 整體來看,這些作品都是讓故事的主人在夢中得到了滿足,然后由樂轉悲,當他們在現實中明白過來后,只能打消自己的執念,追求一種自由的狀態。 這樣的方式偏重道家的觀念,可以讓人獲得一定的解脫,走向平靜。 而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從現實寫到夢境,再由夢進入鬼神的世界,然后再回到現實,表面是真,深層是假,真真假假的變換中道出了人生的無盡思考。
如果說夢中的男女之情、功名利祿都是對個體的顯現,那么對社會圖景的批判與揭露則是直指社會的陰暗面。 《夢狼》生動地抨擊了封建官府的腐朽、貪虐。 故事前半部分說的是白翁夢游到了兒子白甲的府衙,白翁在門口看到了巨狼擋道,他“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3]1879。 而且,兒子白甲也變成了白虎,以人來“聊充庖廚”,這里影射了封建官場上虎狼當道的黑暗現實,從側面反映出了當時社會的腐朽、沒落。 當白翁回到現實,明白了夢中的事情,讓二兒子前去勸誡白甲,但終究沒能改變他。 他告訴弟弟“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 黜陟之權,在上臺不在百姓。 上臺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能令上臺喜也?”[3]1880在白甲看來,只要做的事情能讓上司喜歡,那就是好官,這番驚人之語直接挑明了當時封建社會中貪官污吏們的共性。 而且故事之后異史氏的點評也一語道破了現實:“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就連魯迅先生也說過“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4]。 可見這些貪官污吏如同虎狼一般蠶食百姓,搜刮民脂民膏,弄得民不聊生。 在這里,作者假借老漢白翁的夢,以個體的無意識為切入點,實現了由個體向社會(群體)的轉換,在夢中展現出了欲望對人的支配和蠶食。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說,《聊齋志異》中這幾個關于夢的故事,都指涉了潛意識中的欲望層面。通過欲望,可以顯現出個體內心的復雜思想,并為古典小說的闡釋提供新的方式,而“夢”中欲望的描寫恰恰彰顯了這種力量對個體的影響。
二、女性身體的欲望顯現
身體是人類感知世界的媒介和方式,它是人類認識世界的途徑,而且,外部世界的問題也會通過身體得以呈現。 簡單來說“世界的問題,可以從身體的問題開始”[5]。 也就是說,對身體欲望的闡釋從女性的角度入手能更好地表達女性主體建構的功能與想象。 《聊齋志異》中對女性身體欲望的發現往往伴隨著性別之間的比擬,女性的身體在小說中本身就是一種文學意象和敘述的符號,對女性身體的描寫也就有了無限的意味和隱喻。
從女性身體入手“不但對于其中的女性建構有更為清晰深刻的理解,更可由此窺見身體與整個歷史傳統、權力結構、社會語境對抗相依的動態過程”[6]。 要知道,視覺的感官是人類感知世界的主導方式,因此,通過視覺對女性身體進行觀望,可以形成視覺圖像,進而將女性的形象呈現在人們面前。 《聊齋志異》中女性身體的顯現并非只是通過視覺來實現,而是以男性的視角對女性身體進行審視,從而讓個體的欲望得到釋放。 男性借助自身對女性的“凝視”,實現了欲望的關聯和對話。 “凝視的概念描述了一種與眼睛和視覺有關的權力形式,當我們凝視某人某事時,我們并不是簡單地在看。 它同時也是檢查和控制”[7]。比如《阿寶》中眾生“審諦之,娟麗無雙。”但實際上這種男性目光的審視本身就帶有了欲望的成分,所謂的審美已經被邊緣化了。 也就是說,男性通過自身的欲望實現了對女性身體的窺探、想象,這其中還凝聚了男性社會的價值體系、心理機制與文化思想。
《聊齋志異》中有一部分故事是關于男女愛情的,但表達男女愛情之深的篇章并不多,小說中更多描寫了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想象。 在不少故事篇目中女性身體的欲望符號成了男性自我滿足的途徑,而愛情則成為了欲望的犧牲品。 例如《畫皮》中,王書生貪圖美色,路遇女子,見人家漂亮就上前搭訕,王書生將女子領回家并與其同居,雖然妻子反對,但他深受欲望的蒙蔽,早已迷失了自我。 “生微告妻,妻陳,疑為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8]200。 此時的王書生早已墜入了欲望的泥潭,女性身體的誘惑使他喪失了基本的理性判斷,通過對女性身體的想象與凝視,他自身的欲望獲得了放大,個體也失去了控制。
通常來說,當男性對女性身體進行“凝視”時,在深層次上會顯現出一種主客體的權力關系。以男性的角度而言,女性的身體成了被觀賞的客體或者對應物本身。 有時候,小說中對女性的描摹會集中于身體上的某個部位,以局部的方式來展現女性身體的誘惑性。 《聊齋志異》里多次描寫女性的玉足,通過這一意象顯現出女性自身的性象征。 在《連瑣》中,楊于畏垂涎女性的身體并喜于把玩,他“戲以手探胸,則雞頭之肉,依然處子。 又欲視其裙下雙鉤……楊把玩之,則見月色錦襪,約彩線一縷。 更視其一,則紫帶系之”[8]535。故事中女性的足部成了引起男性欲望的媒介,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女性的足部已經成為了男性潛意識中的象征物。 正因如此,女性身體的部位變成了一種欲望的象征物,使男性不斷沉溺其中。
實際上,在這樣的男女關系中,女性已經淪為了他者,作為愛情關系層面上的女性已經不復存在,女性成為了滿足男性的工具物。 如果從主客體關系來看,當女性變成他者之后,主體性也不復存在,反倒成了一種物化的客體。 《香玉》這一故事恰好能體現女性的他者化。 在故事中黃生偶遇香玉后,兩人相好,但他對香玉的姐妹絳雪也抱有幻想。 為此香玉還告訴他:“絳姐性殊落落,不似妾情癡也。 當從容勸駕,不必過急。”[9]2788然而香玉又質問他“君隴不能守,尚望蜀耶?”可見,黃生不僅想要和香玉有情感上的關聯,他也想獲得本能欲求的滿足,因此,他也會對絳雪時時念想。 但香玉并沒有怨言,當她委身離去,絳雪就扮演了她的角色,也滿足了黃生的欲望。 這個故事中,香玉作為女性的主體,并未體現出她本有地位,反而在其位置上搖擺不定,變成了游離的他者。 對黃生來說,欲望大于情感,他對香玉和絳雪的需要,更多是要成全自己的私欲,實現一種男權化的控制。
嚴格意義上來說,“觀看”或者“凝視”本身就屬于一種權力的使用,如果從男性的角度放大這部分,會很容易造成女性的缺席,從而產生一種權力或者地位上的不平衡。 所以要使女性的價值和意義不被抹殺,從女性的身體出發,可以獲得某種話語權。 正如波德里亞所說:“除了外表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屬于它——所有權力都從它手中滑落,然而它又能逆轉權利的所有符號。”[10]可以說,女性通過身體的誘惑力實現了對男性話語的反抗。 就《聊齋志異》中的男性來說,當他們遇見女鬼或女妖時,都難以掩飾內心的欲望沖動,但他們又因為受制于道德、文化,只能表現出符合社會規范的樣態。 除了這種道德層面上的自我閹割,也有男性對女色的一種抗拒和畏懼。 在《聊齋志異》中男性對女色的恐懼主要在于這些女性(鬼狐)會對男性的身體造成負擔和傷害。 例如《荷花三娘子》中宗湘若在和女狐妖同居的過程中,日漸憔悴,不出一月就妖氣入體,病榻纏身。 這種對女性身體的迷戀和抗拒造成了男性在道德和欲望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所以,女性身體所帶來的力量對抗也使男性在欲望中不斷淪陷,難以脫離欲望的場域。
在《聊齋志異》中作者還塑造了一部分具有“病態美”的女性,這部分女性實際上承載了社會的權力結構和文化價值觀念。 比如《白秋練》一文中描寫的女性“移燈視女,則病態含嬌,秋波自流” 。 這種病態美的描摹與中國的古典文化傳統有著很大的關系。 在《周易》看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也就是說女從柔男從剛,而柔弱的女性身體恰好可以映射男性的力量,從而使男性的統治秩序得到強化,女性身體欲望的展示迎合了男性的審美標準,完成了另外的文化闡釋。
這種“病態美”的產生離不開文人的深層心理狀態。 在心理學家榮格看來,人的心理存在著兩性的傾向,在男性人格中有著被稱為“阿尼瑪”的女性傾向,因此,小說中女性的“病態美”與文人的落魄、窮困密切相連,而這種柔弱的文人心態也在女性身體的圖景化中得到了放大。 通過女性的身體,男性在欲望中得到了滿足,作為男性話語的一種顯現媒介,女性身體將欲望毫無保留地展示出來,來對抗男性的中心身份,這樣的故事在《聊齋志異》中隨處可見。
三、隱喻性——小說中的政治欲望
《聊齋志異》中除了描寫男女愛情,有一部分故事還重在抨擊社會現實,揭露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壓迫,通過對狐妖鬼怪的摹寫,蒲松齡完成了對政治的隱喻性表達。 政治性話語的直接敘說會讓《聊齋志異》顯得鋒芒畢露,因此,蒲松齡多采用隱喻的方式,完成對政治的闡釋。
比如《促織》中,皇帝喜歡斗蟋蟀,下面的官員每年都搜集好的蟋蟀上交。 成名作為一個文弱的破舊書生,為了完成上司交代的任務,他愁于征收蟋蟀,而他本身心地比較善良,又不想為難百姓,于是,他只能“早出暮歸,提竹筒絲籠,于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 即捕得三兩頭,又劣弱不中于款”[2]811。 但這樣也于事無補,成名依舊完不成上級交代的任務。 不過,好在后來他受神婆的指引,尋到了一只很強壯的蟋蟀,這讓他如釋重負。 但兒子又不小心放走了蟋蟀,大起大落,讓成名悲喜交集,最后,他的兒子化為了蟋蟀,算是幫他完成了任務。 從故事中可以看出,皇帝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造成了一級級的壓迫和剝削,這種欲望建立在了個體的痛苦之上,蒲松齡看到了這樣的現實,于是,通過找蟋蟀來表明對當時社會黑暗的不滿與憤怒。
除了對貪官污吏的揭示和土豪鄉紳的批判,蒲松齡在小說中也借助了狐神鬼怪來暗諷當時的社會現實與政治環境。 通過對政治的批判,實現了個體欲望的放大,在政治場域中完成了欲望和政治的聯結。 從封建傳統的社會體制來看,小說中的文人、官紳無不淪為了政治欲望的附庸,他們雖然有著自我意識,自我的理性判斷,但作為自由的個體而言,他們已經喪失了真正的主體性。《遵化署狐》一文中,官衙之中本來住著很多狐貍,原先的官員都會殺牲畜來祭拜這些狐貍。 到了丘公上任,他下令清除了府衙里的狐貍,“使盡扛諸營巨炮驟入,環樓千座并發;數仞之樓,頃刻摧為平地,革肉毛血,自天雨而下。 但見濃塵毒霧之中,有白氣一縷,冒煙沖空而去”[8]393。 后來,丘公想要讓別人和上級打點一下,實現升官,被他趕盡殺絕的狐貍為了報復他,舉報了丘公的賄賂行為。 在這篇故事中,狐貍本身是具有迷惑性的鬼怪,但和道貌岸然的丘公相比,狐貍儼然可以站在正義的一方。 蒲松齡通過狐妖鬼神的方式,暗諷了當時的貪官污吏,他們為了一己私欲,欺負百姓,禍害一方,變成了麻木的政治奴隸,讓人心寒。
小說中還有一些故事以喜劇的方式諷刺了當時的社會現實。 喜劇性的方式就是要揭穿虛偽的面罩,通過真實與謊言的比照,以此來引起讀者的快感和思考,這樣的喜劇方式實際上也是一種隱喻性的表達。 黑格爾認為:“關于喜劇,其中表現于意志和行動的單純主體性及外界的偶然性成為決定一切關系和目的的主宰。”[11]在他看來,主體性的發笑是因為缺乏某種實質性的東西卻還過度自信造成的,這容易導致主客體的不協調,從而引人發笑。 但在這里,我們不關注主客體的狀態,而是就產生喜劇性的事件來追溯《聊齋志異》中的政治隱喻性。 例如在《濰水狐》中狐翁租了李家的房屋,雙方的關系也十分融洽,后來狐翁還告訴了李家人自己的狐貍身份,城里的一些富豪鄉紳聽說后前來拜謁,想要與狐翁結交。 但是狐翁唯獨不待見縣令,因為狐翁覺得“彼前身為驢,今雖儼然民上,乃飲米追而亦醉者也。 仆固異類,羞與為伍”[8]434。 蒲松齡在這里將縣令和驢放在一起相較,本身就造成了一種不協調感,而且還是用喜劇性的方式將這件事展示出來,以諷刺的形式說明了社會的不合理性。 小說中,作者通過喜劇性的描寫,對政治進行了鞭撻,用幽默而極富喜劇的形式對政治進行了包裝,然后通過揭露這層虛偽的外包裝,從而完成對現實的反抗,并將這種隱喻化的表達傳遞給讀者和聽眾。
不過,如果仔細閱讀小說中的故事,會發現有一些政治的闡釋實際上本身就是一種悲劇,這種悲劇通過欲望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從而塑造出政治化的場域符號。 《成仙》中周生和成生是好朋友,周生家的家奴被送入官府,他怒氣難消,雖然成生勸他不要招惹官府,但他依舊闖入官府,最終被收進了監獄。 好在成生為他平反昭雪,救了周生一命。 當周生面臨悲劇性的現實時,他兩人之間的友情就成了一種“正能量”的悲劇精神。 從另一方面來說,周生與成生的遭遇影射了當時官場的混亂無序,而恰恰是貪官污吏的政治欲望造成了這種悲劇。
《席方平》是蒲松齡描寫官場現實中比較典型的一個故事。 小說中席方平的父親被壞人所害,于是他到城隍廟為父親伸冤,但是在城隍廟“羊懼,內外賄通,始出質理。 城隍以所告無握,頗不直席”[9]2437。 無奈之下,他只能去冥府找冥王說理,孰知,整個冥府都被羊家收買了,沆瀣一氣。 他們對席方平進行威逼利誘,想要迫使他屈服。 但席方平并沒有被嚇倒,在嚴刑拷打之下他都沒有屈打成招,最后,連施刑的鬼差都對他產生了敬意。 席方平的遭遇展現了弱勢群體同社會結構之間的對抗,這是對社會現實赤裸裸的揭露,對于那些貪官污吏而言,他們的政治欲望使個體受到了極大的壓迫,卻又無法實現一種平等的對話。所以說,在政治欲望的層面上,席方平不過是任貪官污吏宰割的魚肉。
《聊齋志異》中無論是對貪官污吏的批判還是以狐神鬼怪的方式來揭露政治的黑暗、現實的殘酷,無不體現出政治話語的隱喻性。 對個體而言,政治權力本身就賦予了個體以欲望的因素,當個體進入政治欲望的層面,只能依照它的方式來生活。 而且,個體一旦被給予一定的政治權力,隱藏于理性背后的欲望就會蠢蠢欲動,支配著個體打破道德的底線,不斷去破壞。 當然,《聊齋志異》中還是多以隱喻的方式批判社會的黑暗,從而完成政治欲望層面的闡釋與批駁。
四、結語
以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聊齋志異》,從夢與欲望、女性身體的欲望表達以及政治層面的欲望闡釋,完成了對中國古典小說的重讀。 悉知,在精神分析學派看來,夢中隱藏著個體本我的潛意識,當它不受理性的約束時,就容易沖破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藩籬,從而將個體壓抑的欲望無限放大。《聊齋志異》中有很多故事都是與夢有關,主人公在夢與現實之間搖擺,不斷體驗著欲望的滋味,無論是男女間的性欲望還是關乎生計的政治欲求,無不展現了個體最為原始的樣態。 而且,小說中有不少故事都描寫了女性的身體。 對男性而言,女性身體成了男權話語的映射,當女性身體成為具有性誘惑力的視覺表征,欲望的顯現就完成了一種新的建構,影響著個體的欲望心理。 當然,政治欲望的描摹也是《聊齋志異》不可缺少的一環,它影響著個體的諸多方面,并在小說中完善了欲望層面的表達。 整體來看,《聊齋志異》中的欲望闡釋,在精神的維度上完成了不同角度的闡揚,豐富了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