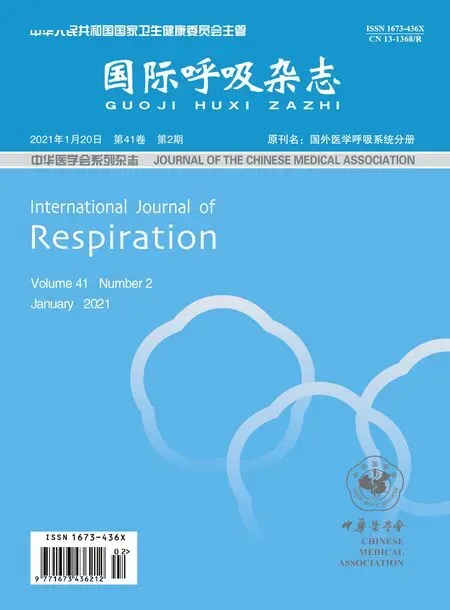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斷研究進展
吳昊 鄭銳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盛京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沈陽110004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出現[1],新型冠狀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 V-2)感染人數迅速增加,WHO宣布將COVID-19作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2]。與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和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相比,SARS-Co V-2具有高傳染性,人群對這種病毒普遍易感,盡管病死率低,但它仍對人們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脅[3]。
截至2020年12月4日12時,中國共86 601例確診患COVID-19,其中累計死亡病例4 634例[4]。截至2020年12月4日18時9分,全世界已有235個國家或地區出現過感染病例,其中疫情最嚴重的美國已有13 759 500例確診病例,其中死亡271 233例[5]。控制疾病傳播,及早診斷和治療可有效控制感染率和病死率。疾病的診斷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本文綜述了COVID-19的臨床癥狀、化驗指標、影像學特征、分子學及血清學檢測方法,和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診療方案多個修訂版本診斷標準的變化,為疾病的診斷提供最新的認識,也可為之后的研究提供參考。
1 COVID-19的臨床表現
COVID-19的臨床癥狀缺乏特異性,在不同人群中的表現也不盡相同。最常見的有發熱、咳嗽、咽痛、流涕、頭痛、乏力、肌痛、結膜炎[6-8]。Luo等[9]發現,16%的患者僅表現為胃腸道癥狀,如食欲差、惡心嘔吐、腹瀉和腹痛等。疾病也可導致厭倦、孤獨和憤怒等情緒變化[10]。重癥患者可表現出多種并發癥,包括ARDS、心臟損傷、肝臟損傷以及繼發感染,嚴重時可出現敗血癥甚至休克[3,11-12]。
年齡與疾病的病死率相關,84%的死亡患者年齡在60歲以上[13]。這可能是因為老年人血清抗體濃度降低,免疫力下降,導致老年COVID-19患者感染后病死率增加[14]。有研究發現兒童感染者潛伏期更長[15],新生兒、嬰兒及兒童的癥狀比成人輕或無癥狀[6,15],有的兒童僅有干咳[16]。也有兒童出現發熱、干咳和乏力,并伴有一些胃腸道癥狀。大多數患兒預后良好,可在發病后1~2周內恢復[17-18]。重癥兒童最常見的癥狀是呼吸困難,其次才是發熱和咳嗽[19]。也可出現多器官損傷,如肝臟及心臟損傷,甚至發生敗血性休克、代謝性酸中毒以及出血和凝血功能障礙,且疾病進展迅速[16,20]。COVID-19感染對孕婦的影響較輕[21]。目前還沒有數據表明懷孕會增加COVID-19的易感性[22]。武漢以外地區大多數孕婦癥狀為輕到中度,主要為發熱和乏力,咽痛和氣短并不常見[23]。部分患者也可出現妊娠并發癥,如死胎和胎膜早破[21]。
總體來說,COVID-19主要表現為發熱、咳嗽、乏力,也可出現消化系統、神經系統和精神癥狀。老年人癥狀相對較重,兒童及孕婦較輕。但COVID-19癥狀和常見的呼吸道感染相似,缺乏特異性,只能對疾病的診斷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需注意和其他疾病的鑒別[24]。
2 COVID-19實驗室指標
COVID-19患者實驗室檢查主要表現在血常規、炎癥指標、凝血指標及肝腎功能的異常,雖然無特異性,但可以對疾病的診斷和預后的判斷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
2.1 血常規 血常規中白細胞計數通常正常或較低[3,6];可能出現淋巴細胞計數減少,這和疾病嚴重程度有關[3,6,25]。有研究發現,死亡組較恢復組患者入院時有更低的淋巴細胞計數和淋巴細胞與白細胞的比值,且比值在住院期間會持續性降低[26]。血小板計數通常正常或稍下降[6,27]。難治型較一般型患者有更低的血小板計數[8]。血小板計數降低可使重癥患者風險增加5倍[28]。
2.2 炎癥指標 關于常見的炎癥指標,大多數患者表現出C-反應蛋白、ESR升高,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水平通常正常[3,6]。重癥患者PCT水平高于輕癥患者[25]。和成人患者相比,PCT升高更常見于兒童,其更易出現混合感染,因此兒童的抗微生物治療很重要[29]。但也有研究發現,兒童患者PCT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正常的。PCT>0.5μg/L時表明與細菌共感染[20]。
多數研究發現,COVID-19患者炎癥細胞因子中的IL-6、IL-8和IL-10高于其他疾病,且重癥患者更為明顯[3,19,30-31]。同嚴重程度相同的其他疾病相比,COVID-19患者更易觀察到高水平的IL-6和IL-10[3]。COVID-19重癥患者的IL-8和IL-10高于非重癥患者[30]。一項對19歲以下患者的研究表明,IL-6可作為重癥COVID-19感染的潛在預后指標[31],對重癥兒童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論[19]。但也有研究發現,COVID-19和其他類型肺炎患者的IL-6水平均升高,且兩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32]。這需要進一步研究加以證實。
2.3 凝血指標 凝血指標和COVID-19的發生及預后密切相關。研究發現,COVID-19患者的D-二聚體、纖維蛋白/纖維蛋白原降解產物(fibrinogen degradation products,FDP)和纖維蛋白原均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嚴重SARSCo V-2感染者的D-二聚體和FDP水平更高[25],這有助于早期發現危重病例[33]。同樣,重癥兒童也出現D-二聚體水平升高[20]。一項對預后的研究發現,入院時死亡組D-二聚體和FDP水平明顯高于存活組,71.4%的非幸存者和0.6%的幸存者在住院期間符合彌散性血管內凝血的標準。重癥COVID-19患者易發展為膿毒癥及多臟器衰竭,膿毒癥是彌散性血管內凝血一個重要原因[34]。
2.4 肝功能及腎功能 少數患者可出現肝功能、腎功能的異常。與非COVID-19相比,COVID-19表現出更為異常的肝功能指標,如天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谷丙轉氨酶、γ-谷氨酰轉移酶等[32]。相比于恢復組,死亡組谷丙轉氨酶、天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和肌酐的水平更高[26]。
雖然COVID-19患者化驗指標沒有明顯的特異性,但可以作為診斷及判斷預后的輔助手段。成人和兒童的實驗室指標未見明顯差異,但有研究表明兒童更易出現降鈣素原水平升高,這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證實[29]。
3 COVID-19影像學特征
COVID-19的影像學檢查對疾病的診斷有很大價值,且胸部CT較X線更為敏感[6]。COVID-19患者的影像表現具有多變性。在特殊人群以及不同年齡、不同地域人群具有不同的特點。
3.1 COVID-19影像的典型和非典型表現 COVID-19典型CT表現包括:雙肺多發、斑片狀、節段性磨玻璃影或實變,可伴有“鋪路石”征[1-2],甚至出現“白肺”[35]。非典型CT表現可見胸膜下小葉間隔的網格狀或蜂窩狀增厚,支氣管壁增厚,實變結節伴周圍磨玻璃影[1]。
一些少見的表現還有胸腔積液、心包積液、氣胸、淋巴結腫大等[36]。隨訪CT中可出現類似“供血管征”表現,這可以預測最初的肺部惡化。少量胸腔積液提示臨床預后不佳[37]。
因此,教師應積極引導學生對自己經營失敗的思想認識,盡量將經營失敗歸因于自身努力不足等相對不穩定的內因,以及將偶爾的失敗歸因于不好的運氣等,使其保持學習的持續性或付出更大的努力。
3.2 影像學病灶分布 病灶在胸部CT上分布也有一定規律。常見分布于雙肺支氣管束或胸膜下[38-39]。半數以上患者病灶表現為雙側多灶性周圍分布[3,40],個別患者可出現局灶性非外周分布[41]。COVID-19患者全部肺葉受累占44.4%,單個肺葉受累占30.2%[42]。病變多位于下葉[40],右下肺葉病變最常見[43]。但有研究表明,病灶在兒童以左肺下葉為著[44]。個別患者病變會出現在右肺中葉及左上肺磨玻璃影[36,41],進展期病灶主要分布于肺中部和外部[42]。重癥及危重癥患者病變常累及4~5個肺葉,多分布在雙側更偏上或偏下的肺葉[7]。總之,COVID-19肺部病灶主要分布在支氣管束或胸膜下,多位于雙肺下葉,重癥患者會出現更多肺葉受累。兒童的病變分布是否與成人一致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
3.3 特殊人群影像表現 針對孕婦的研究發現,磨玻璃影及磨玻璃影合并網格影更常見于非妊娠組,但實變更常見于妊娠組,這意味著疾病嚴重程度的增加[45]。
有研究表明,所有感染的嬰兒都有家庭聚集現象[46],但家族聚集性發病的影像學表現也不同[47]。COVID-19兒童的胸部CT表現與成人相似,但多為輕癥。實變影周圍出現暈征是兒童的典型表現[29,45]。對重癥兒童的研究發現,胸部影像學最常見的是多發斑片狀陰影,其次是磨玻璃影[19-20]。
疾病的CT表現也與年齡分布有關。年輕患者(<50歲)往往有更多磨玻璃影,而年長患者(>50歲)有更多的實變合并機化肺炎影[48-49]。
3.4 不同地域人群影像表現 不同地域人群影像表現各有不同。在中國湖北省以外省份患者的影像表現更為溫和[50-51],而其他國家患者影像表現輕于中國[52]。在中國湖北以外地區,如浙江和北京,患者的臨床癥狀及影像表現都輕于湖北武漢[50]。這部分患者的胸部CT更多表現為磨玻璃影,部分可有“鋪路石”征[51]。無實變的磨玻璃影在韓國病例中占45%,在中國占45%~67%。中國COVID-19患者中實變為主病變的比例約為30%~60%,但韓國患者沒有實變為主病變[52],影像表現更輕[52]。
研究發現,最嚴重的CT表現常出現在癥狀發生后9~10d[53-54],與臨床癥狀改善相對應的影像表現通常發生在發病第2周以后[36],但CT的表現和臨床癥狀并不完全相符。部分患者胸部CT無陽性表現[2,55],尤其是兒童、青少年及年輕患者[7]。CT表現可先于癥狀發生[54],也可出現臨床癥狀緩解時CT表現加重[47],因此定期復查CT有助于判斷疾病進展及預后。
總的來說,胸部CT主要表現為雙肺胸膜下磨玻璃影,可合并斑片影、實變影、小葉間隔增厚等。胸腔積液、淋巴結腫大、氣胸等表現不常見。中國湖北以外的地區以及其他國家患者的影像表現更溫和。另外,CT表現和臨床癥狀不一定相符,定期復查CT有助于判斷疾病進展。
4 COVID-19分子學及血清學檢測
WHO推薦將分子學檢測作為確診COVID-19的首選方法,血清學檢測主要在疾病監測和流行病學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56]。
雖然核酸檢測可以作為診斷的直接證據,但該方法存在一定的假陰性率[59,62]。這可能和標本的收集方法、干擾物質存在、接受檢測患者治療等因素有關[63]。流行病學史、化驗和影像學檢查的聯合應用,可以幫助篩選出陽性患者。
4.2 COVID-19血清學檢測 目前人們對SARS-Co V-2特異性Ig M和IgG抗體的產生時間有較多爭議。研究表明,SARS-Co V-2感染人體后,其Ig M抗體在5~7d產生,IgG抗體可在10~15d產生[64]。也有研究發現,發病5d后可檢測到Ig M和IgG抗體[65]。羅效梅等[66]證實最早在發病4d時可檢測出Ig M抗體陽性,8d時其陽性率達到100%;28d后Ig M抗體開始消失,IgG抗體陽性率開始提高;Ig M和IgG抗體陽性率與發病天數有關,與疾病的分型無關。但也有研究得出不同結論,血清IgG抗體產生同時或早于Ig M抗體[67]。研究結果的不同可能與血清學抗體檢測方法不同有關[58],另外個體免疫應答產生抗體的差異性、抗體檢測時間、不同研究中人群的年齡分布也會影響檢測結果[14,68]。
Ig M抗體陽性往往表明最近接觸了SARS-Co V-2,而IgG抗體陽性則表明一段時間前接觸了病毒[69]。Ig M濃度下降或消失,IgG濃度升高,預示著患者逐漸痊愈,并產生了對SARS-Co V-2的免疫力[65]。也有研究證實,SARSCo V-2棘突抗原刺激產生的抗體對機體可能有保護作用[69-70]。與單一Ig M或IgG抗體檢測相比,Ig M-IgG抗體聯合檢測具有更好的特異度和敏感度[68]。血清學方法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檢測的陽性率[64],但抗體產生時間和假陽性率仍是需要關注的問題。
5 中國COVID-19診斷標準的變化
疾病爆發后,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并且隨著疾病的進展和對疾病認識的逐漸深入,從2020年1月15日至2020年8月18日先后進行了8個版本的修訂。其中診斷標準分為疑似病例和確診病例的診斷[71-77]。疑似病例主要通過流行病學及臨床表現診斷。確診病例通過核酸檢測、病毒基因測序和SARS-Co V-2特異性Ig M和IgG抗體判定。不同版本之間的比較體現了對疾病認識的逐步完善。和第一版相比,第二版給出了病毒人傳人的傳播途徑。確診方法增加了實時熒光RT-PCR檢測手段。第三版中重癥病例的診斷標準更加嚴格[71]。第四版強調部分患者影像學檢查可能為陰性,確診標準中增加了血液標本。同時增加了臨床分型,其中重型患者的納入條件更少,降低了重癥患者的比例[72]。臨床分型可以及早發現重癥及危重癥患者,使其盡早接受更多的醫療支持,提高生存率,同時有利于資源合理分配。第五版增加了臨床診斷病例,這部分患者雖然核酸檢測可能為陰性,但同樣需要引起重視[73]。第六版重型病例增加了影像學的診斷標準,強調影像學復查的重要性[75]。第七版增加了血清學方法作為確診標準,提高了診斷的準確性和敏感性[76]。第八版強調了重型/危重型高危人群的范圍,同時增加了重型/危重型的早期預警指標,更有助于判別重癥患者,使資源得到更合理的應用[77]。
綜上所述,COVID-19作為高傳染性疾病,其主要表現包括發熱、咳嗽、乏力等,也可出現胃腸道、神經系統及精神癥狀。實驗室檢查主要表現為血常規、炎癥指標、凝血指標及肝腎功能的異常。影像學表現在特殊人群以及不同年齡、不同地域的人群也會有所不同。核酸及血清學抗體的檢測作為確診的主要手段,具有一定的假陽性和假陰性率,規范操作、減少污染等可以提高其準確性和敏感性。臨床醫師應結合流行病學史、化驗及影像學檢查、核酸及血清學檢查等方法加以診斷。我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診斷相關研究幫助人們提高對COVID-19診斷的認識,及早的診斷并有效地控制疾病傳播,使感染者得到更加有效的治療,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利益沖突 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