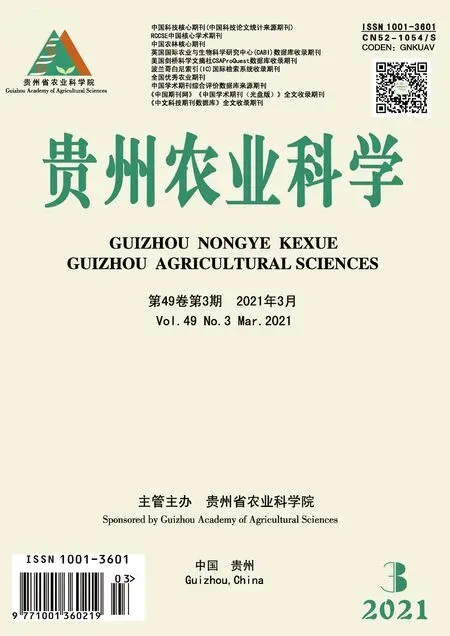“三無村”的精準脫貧實踐與鄉村振興展望:以宣城市山河村為例
李 雪
(河海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江蘇 南京 211100)
0 引言
隨著脫貧攻堅戰役的全面勝利,為讓全體農民盡快過上美好生活,需要進一步加快農業現代化工作,在銜接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之間,項目制或項目治理是目前基層實踐中不可忽略的總體性因素,從農村產業項目或涉農項目的視角看,對近年來精準扶貧領域中的政策實踐效果進行總結,有利于為新時期新政策的實施過程提供更多的現實經驗。精準扶貧領域中的產業扶貧是一種在縣級地方政府與貧困村之間建立起的精準項目傳輸渠道[1],以改善貧困村貧困現狀,提高其特色產業發展能力與村民個人“造血”能力[2]的治理模式。近年來,安徽省堅持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將產業扶貧作為提高貧困村發展能力的重要推手,發展一村一品特色產業,31個貧困縣的特色產業不斷壯大,帶動了村集體經濟的快速發展。截至2020年4月,3 000個貧困村全部出列;集體經濟收入由2013年年底的0.53億元增至2019年年底的6.72億元,村均由1.76萬元增至22.4萬元,增長12.72倍[3]。
山河村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區養賢鄉東北部,水陽江畔,屬專業漁民村。目前,全村121戶、321人,曾是典型的“三無”村(無山林、無水面、無土地)、空殼村,極度缺乏自然資源稟賦;2014年被列為全區13個貧困村之一;村民收入主要以天然捕撈和水產養殖為主,兼帶少量外出務工。近年來,圍繞聚焦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山河村積極創新發展思路,走出了一條精準脫貧、產業發展、鄉村振興同步推進的“三變”改革之路,取得了優異的成效,但發展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在鄉村振興背景下,精準扶貧時期的實踐經驗必然為其現階段的改革工作提供參考。鑒于此,以宣城市山河村為例,分析其精準扶貧領域中的產業扶貧發展經驗與存在問題,并提出在鄉村振興階段的相關對策建議,以期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參考。
1 多項精準措施與幫扶體制帶動扶貧產業發展
1.1 產業扶貧項目的聯系性輸入,使村集體騰飛
近年來,山河村積極申請產業扶貧項目,立足于當地漁業養殖的傳統生計方式,積極進行土地流轉并進行養殖池塘改造工程,通過將養殖池承包給當地養殖大戶,獲得出租類集體經濟收入。2015年依靠區農委農業產業化項目,承包鄉屬“五一場”水面12.53 hm2,通過改造升級后公開掛網拍賣經營權,年獲分配利潤10萬元。隨后,每年堅持走養殖池改造項目道路,可獲利6萬~10萬元/年。2017年山河村利用鄉鎮政府的空余土地與辦公樓,分別建成裝機容量60 kW、100 kW光伏發電站,年收益與補助共計16.5萬元。2019年山河村聯合大山庵村注冊成立宣城市大山河旅游發展有限公司,規劃打造總面積143.33 hm2的“漁民山莊”旅游項目,兩期項目建成后預計年收入20萬元。
縣級政府與貧困村之間的項目聯系是產業扶貧項目可以精準進入基層場域中,發揮了扶貧項目帶動村社經濟發展的最大效益。山河村集體經營性收入2016年達10萬元,告別了“零收入”;2017年達24.2萬元,同比增長1.42倍;2018年達32.5萬元;2019年達75萬元。
1.2 多方幫扶主體助力資源精準傳遞
為發揮體制單位內部的動員作用,宣州區建立了單位包村、干部包戶的雙包制度,建立起貧困村與幫扶單位、貧困村與基層干部之間的聯系。幫扶單位在扶貧項目資金援助、技術指導等方面為貧困村提供了一系列的幫助,通過各年度走訪與調查及選派的第一書記掌握貧困村發展情況,進而為其提供切實有效的幫助。干部包戶制度在單位干部、基層干部與貧困戶之間建立起聯絡的橋梁,通過每年至少12次的走訪要求,幫扶干部對其幫扶貧困戶的脫貧狀況、享受扶貧政策待遇等情況有所了解,并盡量幫助村干部解決貧困村扶貧政策之外的生活困難。此模式在貧困村與幫扶單位、貧困戶與幫扶干部間建立起了直接的聯系,使體制內部的動員資源以一種更有效的方式輸入到貧困地區的內部。
另外,通過創新“企業+驛站+愛心超市+貧困戶”模式,以愛心超市為紐帶,以扶貧驛站為渠道,為就業扶貧開辟新陣地,為貧困戶解決就業服務最后一公里。扶貧車間解決30余人就近就業,其中貧困戶4人。電商扶貧拓寬農產品銷售渠道,增加農戶收入。解決輔助性工作崗位增加貧困戶收入,5戶6人從事巡路、巡河、綠化和保潔崗位,貧困戶靠自己雙手實現脫貧,靠技術勞動實現創收。并對11戶貧困戶26人、5戶邊緣戶17人憑積分兌領生活用品。
1.3 基層黨建引領扶貧產業發展方向
村黨支部書記陳五順說,不改革,村里沒有任何希望;不發展,山河村依然村貧民窮。只有擼起袖子加油干,拔窮根、摘窮帽,凝聚合力、攻堅克難,才能將舊貌換新顏。
山河村之所以能夠找到快速、跨越發展的新路徑,關鍵在于有一個團結拼搏、有戰斗力的“兩委”班子和駐村工作隊。在2014年的貧困村申請過程、2016年農村集體經濟股份改革的“三變”改革過程等關鍵性發展事件中,村黨支部始終把黨建領航、支部引領擺在首位,謀事、干事、成事,最終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立足村情實際和廣大村民期盼,結合村干部自身個人發展的實地經驗,把改革措施謀深謀實。實踐證明,村兩委中一系列村干部謀略出的山河村發展路徑是經過實踐檢驗且務實管用的路徑,為貧困村擺脫貧困作出了有益嘗試。
1.4 集體經濟產權改革保證“返富于民”
“三變”改革是我國目前農村集體經濟產權改革的主要形式,“三變”改革是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堅持和深化[3],是對我國農村歷次改革的拓展和升華,體現我國農村改革的延續性和系統性[4]。
2016年,山河村率先在宣州區完成產權制度改革工作,成立了山河村股份經濟合作社,發放股權證124份,由此拉開“三變”改革的帷幕。2017年被列為宣城市“三變”改革試點村,注冊了宣城市漁豐現代農業有限公司,依托扶貧項目和政策集成“杠桿”,撬動股改“破冰”前行;鄉屬“五一場”水面的承包與改造升級,每年獲分配利潤10萬元。村集體經濟收入2018年達46.8萬元,2019年達75.39萬元,由昔日的“三無村”邁入全省經濟強村。扶貧項目為山河村提供了穩定的收入,為脫貧攻堅及鄉村振興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2 產業項目扶貧與社會治理中呈現的問題
2.1 項目依賴性導致產業選擇過于保守
山河村為貧困村期間,連續的項目輸入使山河村每年發展資金充裕,但是這一種資源輸入模式與治理方式,往往會限制村莊的項目類型選擇。以項目制為核心追求短、平、快的目標嚴重降低了產業扶貧成效[5]。相較于以往的整村推進時期,精準扶貧時期以來,項目的獲得方式從層層競爭獲得項目的實施經營權轉變為保障貧困村的聯系性項目輸入,隨著項目輸入方式的改變,也匹配了更加細致與嚴格的專項資金審計制度與項目成功驗收制度。在此制度變遷背景下,過于嚴格的監管制度與過于輕易入村的項目使得項目在建設類型選擇方面與后期運營模式方面的選擇更為保守。為完成地方政府的審核壓力,基層村莊往往會選擇建設時間短、獲益時間短的項目,多為廠房建設出租或種養殖基地出租項目。
2.2 產業結構單一致使對接市場能力不足
多年來,山河村村集體經濟收入的提高主要源于扶貧項目的承包出租,此類盈利方式難以促進產業與市場的進一步對接,從而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2020年以來,隨著長江流域禁捕期時代的到來,依靠天然捕撈為生的漁民慢慢難以以往的方式維系生計,而年齡較大、學歷不高的漁民又難以在目前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就業市場中尋找到比較安穩的就業機會。
精準扶貧以來,雖然山河村通過產業扶貧項目的申請與運營實現了村集體經濟收入的大幅增長,但是依舊面臨產業結構過于單一,過于依靠出租收入的問題。近年來,山河村將產業扶貧項目的著力點落在流轉土地進行養殖池挖掘與開發,并將其出租給當地水產養殖戶。該產業經營方式過于依靠每年的財政扶貧資金的輸入,一旦缺失財政扶貧資金支撐,便很難進行后續的項目生成。另外,此經營方式僅僅依靠出租收入,難以在村莊內部打造產業扶貧的真正“血液”,難以提高村莊真正的產業再生產能力。
2.3 村民主體缺位背景下民主公共參與不足
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在現實中難以形成有效的村民集體參與經濟組織決策與監督的行為與機構。村級“四議兩公開”、“村民說事”等制度雖得以落實,但是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一是因為人口流出嚴重,多數青壯年勞動力常年在外務工,留守人員多為老弱婦孺。二是因為目前的基層鄉村中傳統鄉規民約的集體主義式公共參與行動基本已不存在。建立一個村民公共參與決策、管理、監督的集體行動體系的難度主要在于參與村民的積極性不高、村民并不具有一定的專業性知識,從而導致村民的民主參與及民主監督會面臨過高的參與成本。
3 鄉村振興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3.1 利用社會資本優勢,促進產業結構轉型
積極爭取盤活資源實現多贏,利用財政扶貧資金、幫扶資金、社會扶貧資金等多渠道資源,積極爭取幫扶單位在政策、資金、項目、技術等方面的支持。健全管理運營、收益分配制度等,全面提升黨組織管理水平和自治能力,達到增加村級集體經濟積累、增強基層組織等“多贏”效果。
新型經營主體是帶動貧困戶就業增收的重要力量[6]。可以通過整合村內后天然漁業時期的勞動力,將以往散落在村內的家庭小漁場與漁民整合起來,將老漁民的豐富養殖捕撈經驗與年輕漁民的勞動力資本相結合,深入探索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多種途徑,形成村內人力資源的累計與再生產。
3.2 深化村干部隊伍的深度,提高發展眼界與視野
深化村兩委隊伍建設,開闊發展視野。鼓勵高校畢業生返鄉參與村級建設,通過提高村干部待遇,留住有能力、有水平的外出務工青年,并在家鄉挑起村干部的重任。提高“兩委”干部文化、業務素質,集眾人之智慧創新方法發展產業。在活動場所開設各類便民服務平臺,把場所打造成電子商務、便民超市、村民議事、代辦服務等陣地,擴大村黨支部的活動覆蓋面,做好黨員活動推廣和幫助村民做好相關農產品推介等工作。此外,著力推進“強村富民”計劃。建立“支部+企業+貧困戶”的發展機制,加強村企人才合作、招商引資,在環境保護的前提下興辦實體企業,為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注入生機。
3.3 激發村民公共事務參與感,建立鄉村文化共同體
村集體經濟或合作社一方面要加強宣傳,增進農民對村集體運營項目與產業的了解,強化其作為一個集體經濟組織中“一份子”的存在,讓該存在呈現出利益相關者及對集體組織的認同感與自豪感。另外,針對集體股的設立與大額占比極易產生“內部人控制”的現象,可建立管理層收益分享制度[7]。村集體經濟運營良好的集體可選擇外聘職業代理人或律師事務所等專業性的經營或監督機構,將原屬于村集體與村民間樸素的委托代理關系轉變為現代化的契約性關系。通過定期的經濟收益分紅與監督報告實現對村集體經濟活動的有效參與。
4 結語
政策變遷或政策創新的過程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無論是精準扶貧這類強調改善弱勢群體并改善慧農資源分布不平衡的政策改革過程,還是農業現代化改革、農村集體產權股份改革等側重提高農業生產資源利用效率的政策改革過程,都是在經歷不斷的政策創新或政策循環試驗而逐漸成型的。為進一步開拓具有一定農業發展潛力的中部省份脫貧地區的生產力,利用現今的財政資源分配模式及其衍生出的基層治理形態尤為重要。山河村的脫貧之路精妙之處在于對制度性優勢的充分利用及基層領導班子敢作敢為的“振興”之心之間的相互激勵。通過對山河村項目制運行過程的分析發現,利用項目制背后的技術導向、專家治國的生命力,進一步規避其高政治壓力與高監察機制帶來的項目“漂移”、項目制治理在調動基層資源與鼓勵村民積極參與公共生活等將成為鄉村振興實踐過程中需要進一步關注與解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