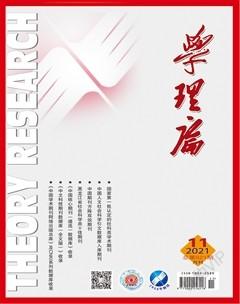恩格斯國家觀的理論內容研究
武玲玲
摘 要:以19世紀資本主義國家統治和社會階級對立以及思想蓬勃發展為社會背景,以恩格斯不同時期的著作為文本基礎,總結歸納恩格斯國家觀中市民社會與國家既一體又獨立的關系,國家組織在階級的產生和相互斗爭中出現,國家組成人員在財產私有后的異化與解放,國家作為上層建筑對物質資料和人本身的兩種生產的服從,與經濟力量息息相關的政治權力的強化與消失。在此基礎上探討國家的本質,以期更加明晰“國家”的發展規律及其現實意義。
關鍵詞:恩格斯;國家觀;國家;階級;政治權力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21)11-0055-03
19世紀,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基本確定了資產階級在國家中的統治地位,資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后陸續確立了對其有利的法律法規。工廠的工作方式導致工人階級生活方式發生巨大變化,貧民窟的生活環境和工廠集體作業的工作環境極大損害了工人的身體,并且由此造成對下一代不可逆轉的惡劣影響,階級之間的鴻溝逐漸拉大。同時,歐洲各國知識大爆發,這一爆發得益于讀寫能力的整體性提高,大學的改革及廣泛建立,以及統計學、歷史學和新聞業等的大規模發展。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階級背景下,恩格斯的國家觀思想逐漸發展成熟并廣泛傳播。
一、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獨立與統一
在國家與社會的問題上,恩格斯早期就已經意識到社會成員之間的分裂和國家與社會的分裂,在《英國狀況》中恩格斯講到廢除封建制度的政治改革使國家制度更加不合乎人性,這種政治改革宣布“人類今后不應該再通過強制即政治的手段,而應該通過利益即社會的手段聯合起來”[1]94,恩格斯在這里表明社會成員之間聯結點的變化,即一開始是政治的聯結,后來是利益的聯結,而這種利益的聯結是需要在封建社會的下一個階段——資本主義社會中實現的,體現了社會成員之間由于私有制發展程度越來越高產生的完全意義上的分裂。在唯物史觀確立之后,恩格斯不再片面地指出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分裂,而是更加全面、辯證地認識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恩格斯將不同生產階段的市民社會作為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1]544,并指出市民社會是“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1]582-583,這里的市民社會包括一切物質生產及其結果,是宏觀上的市民社會,包含著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等一切產物,而不僅僅是微觀上指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市民社會。這里明確表明“國家”只是市民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呈現的形式,有國家的歷史只是市民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初步表達出國家與市民社會本為一體的觀點。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首次講到國家權力的由來,即“一切政治權力起先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為基礎的”[2]190,并根據發展條件快速發展,否則會陷于崩潰。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詳細講述了國家(權力)的由來及其與社會成員對立的過程。在氏族社會公共權力的前提下,財產私有的出現導致社會分裂為世襲貴族和廣大人民,階級利益的斗爭產生出國家,國家產生后成為與社會相對立的機關。國家的由來衍生出國家的本質——“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3]135。國家產生后出現之前社會沒有的暴力性機關、官吏和意識形態。前兩者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說明的,國家與社會分離之后逐漸產生之前沒有的強制性暴力機關,表現為武裝軍隊、監獄和法庭等機構,這種暴力機關主要針對國內階級對立和國外的爭相霸占,用以維護統治階級利益。掌握著強制性暴力機關的官員隨著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凌駕于社會之上,他們通過手中的暴力機關建立權威,而這種權威在之前的氏族社會中是自愿的尊敬,這表明國家與社會分離后統治者的權力增大而威信卻下降。后者是在《關于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說明的,國家與社會獨立之后,變成脫離經濟基礎的職業機關,產生獨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關事務中與經濟事實的聯系越來越少,國家及其公職人員的獨立性愈加明顯。在這一著作中,恩格斯還指出,國家與社會獨立后國家越代表某一個階級的利益,它就越獨立。
二、國家中階級的產生與發展
在恩格斯國家觀中關于國家與階級的問題闡述了三個方面的內容:國家與階級的產生、國家成為統治階級的工具、國家與階級的滅亡。
首先,社會分工導致階級的產生,繼而產生國家。由于生產水平較低,社會生產的總產品只能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在此之外極少有剩余,生產勞動幾乎占去社會成員全部的時間,為了提高社會的生產效率和滿足社會各方面職能的要求,社會內部開始分裂為不同的集體,進行生產工作和非生產工作的分工,繼而出現窮人和富人的區別,財產利益的統一和沖突導致階級出現。階級利益的沖突導致階級對立日益尖銳,社會產生階級之外的第三種力量進行矛盾的調和,壓制階級沖突以保證各個階級都能容于生產發展的領域內,這一產生于社會之中卻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第三種力量,就是國家。因此,階級和國家產生的根源就是生產發展程度的低下和勞動組織方式的落后。若生產力發展程度持續低下,分工就無法停止,階級就必然存在,階級統治就無法消除。
其次,國家產生后成為統治階級的工具。因為國家是從控制階級沖突的需要中產生的,因此必然成為社會中占優勢的階級的工具。公民權利在氏族社會按血緣劃分,國家產生后按照財產狀況來劃分,因此國家在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方面必將成為統治階級的有力保障。社會中本就占優勢的階級由于掌握了國家也直接獲得了更強大的鎮壓階級矛盾的手段,即國家出現后產生的強制性暴力機關——軍隊、官僚、法律、法庭和監獄等。另一方面,統治階級必須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才能將其統治持續下去,這些暴力機關就被用來維護表面上的“普遍利益”以暫時緩和尖銳的階級矛盾,但是“國家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3]195。
最后,階級和國家的消失具有必然性,社會中也會逐步出現促使其消失的原因、主體、條件和方式等具體因素。“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一切政治斗爭都是階級斗爭,而一切爭取解放的階級斗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3]306。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生產力的繼續發展要求生產的完全社會化,而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與生產社會化必然產生矛盾,生產力的向前發展遇到阻礙,必然要求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促進生產社會化的實現。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生產成果更多而生活條件沒有改善,如果不進行階級斗爭就不能擺脫階級壓迫從而無法繼續生存,生存的壓力必然激發無產階級的巨大潛力去消滅資產階級,從而消滅人類社會最后一種階級分裂,實現階級的消失。由于階級產生的根源是社會生產能力低下,階級消失的原因就必然是生產的高級化發展和科學的勞動組織方式。階級社會的發展動力是階級斗爭,人類社會最后一種階級社會的任務就必然落在最后一個被統治階級——無產階級的肩上,無產階級只有消滅了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消滅自身,從而消滅階級和國家。無產階級在進行階級斗爭中只有首先通過革命奪取政權,把生產資料轉變為國家財產,消除國家政權對以往由于階級特權而產生的社會關系的干預和影響,消滅社會中存在的對人的統治,只剩下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只有這樣,人的生存斗爭才能結束,無產階級才能被徹底消滅,作為國家的國家才能真正消失。階級和國家消失后,那時的教育和勞動就能達到使得年輕人熟悉整個生產系統的水平,他們可以根據愛好和需要選擇不同的勞動,勞動中的片面性被消除,真正實現了一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三、國家組成人員的異化與解放
在《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這一信件中恩格斯指出:“從分工的觀點來看問題最容易理解。社會產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職能,被指定執行這些職能的人,形成社會內部分工的一個新部門。這樣,他們也獲得了同授權給他們的人相對立的特殊利益,他們同這些人相對立而獨立起來……”[4]596也就是說,氏族社會的生產方式中發展出通過分工進行生產的方式,分工的出現導致階級的產生,導致社會中的普遍利益分裂為各種特殊利益,利益的分裂使得國家的出現成為必要,階級關系成為社會關系的主要方面。分工導致人的活動是被迫的,人的活動本身及其產物都對人進行異化,它們使人被迫處于一定的社會活動范圍內,并且聯合成為統治人的獨立強制力量。異化人的生產力經過幾個社會歷史階段的發展,單個人的歷史擴大為世界歷史,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具有世界性,生產成為世界性的生產活動,相應地,異己的力量也擴大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異化的主體和力量達到頂峰。這一歷史階段就是資本主義社會階段,國家在這一歷史階段上的生產力基礎是資本,私有制在這一階段對人的異化是讓人變成市場上有價格的商品,人的特點和本質被買賣關系淹沒,人的道德也被異化和扭曲,犯罪現象只增不減。私有制和交換的存在使得單個利益純粹表現為物質化的財產,利益的統治關系表現為財產的統治關系,人對人的統治實質上是財產對人的統治,被統治的人不再是人的附屬物,而是財產這種物的附屬物。財產的作用是通過控制工業實現的,商業成為社會關系的紐帶,一切人的關系和物的關系都通過商業實現,人的本質被財產異化,在形式上被商業異化。財產作用下人的異化程度達到最高階段,這個階段也是人的異化的最后一個階段,內含著消除異化的因素:財產這種單個利益使得人與人之間不再聯合,變成單個的人,在社會關系上成為單個人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正是自由人聯合的前兆和鋪墊因素。
《德意志意識形態》已經指出人的解放的兩個條件:一是被統治階級在統治下無法繼續生存,革命的意愿形成,異化成為革命要消滅的對象;二是大多數人同少數的人相對立,革命的階級成為社會中占據人口多數的階級。無產階級的解放正是在這兩個條件成熟之后奪取國家政權,將自己的利益轉變為社會的普遍利益,實現生產資料國有化,生產資料成為全體社會成員共有的財產,生產工具和產品分配不再有特權和剝削,無產階級才能真正解放自己。但是無產階級在解放自身之后要實現人的解放還需要滿足以下條件:消滅分工和雇傭勞動,消滅國家并形成新的共同體。只有在消滅分工的共同體中,個人力量才不會繼續轉化為物的力量對人進行異化,只有在這樣的共同體中,才能實現所有人的解放。私有制和分工被消滅之后,勞動的異化就消滅了,勞動產品的供求關系不再被干擾,生產和交換之間的矛盾消失了,人重新成為社會關系的主導者。以前在階級內部的聯合是階級成員的所屬關系下的聯合,這種聯合看起來使得人與人之間聯系密切,實則是相互分離的。人類解放后形成的共同體中,每個人都是單個的自由人,人與人之間看起來是相互分離的,但在社會關系中卻是彼此緊密聯合的。
四、決定國家進程的“兩種生產”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指出,“當某一個國家內部的國家權力同它的經濟發展處于對立地位的時候……斗爭每次總是以政治權力被推翻而告終,經濟發展總是毫無例外地和無情地為自己開啟道路”[2]191。可見政治權力,即國家,作為上層建筑,是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基礎的。在恩格斯的國家觀中,物質資料的生產和人本身的生產的“兩種生產”理論是重要內容,也是經濟力量的主要來源。在物質資料的生產中,分工是體現生產中人與人關系的主要方式。分工的不同方式表現為所有制的不同階段,在政治方面表現為國家的不同階段,在不同階段中每個人的勞動關系和產品占有的關系表現為國家權力作用的具體方面和個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權利和義務。國家是分工產生后出現特殊階級的結果,國家作為生產力之外的力量雖然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但本身作為獨立的力量具有自身的獨立性。國家只有當其與經濟發展相適應時才能繼續存在和發展,否則就會造成國家內部局面動蕩甚至被經濟發展所需的力量推翻。在物質資料的生產中,人本身的生產是其重要方面。人的生產不僅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提供生產者,同時更是物質資料生產發展中最為革命和活躍的因素。物質資料生產的全過程都離不開人本身的生產,人不僅是物質生產的主體(即勞動者),同時也是物質生產的目的,是推動物質生產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而且只有通過人本身的不斷生產,才能保證物質資料的持續發展。人本身的生產和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一個內容的兩個方面,二者相互交織進行,共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國家內部社會關系和制度體制的變革。恩格斯將“物質資料的生產”和“人本身的生產”這兩種生產看作“廣義的”生產,即“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5]119-120。在物質生產和人的生產中出現了國家這一組織,這一組織的形成和發展與兩種生產密切相關,物質生產和人的生產的結果既是國家產生的原因,也是推進國家滅亡的主要矛盾。
五、國家中政治權力的強化與消失
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件中指出,“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么我們何必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斗爭呢?暴力(即國家權力)也是一種經濟力量!”[4]600-601可見,國家權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量,是社會中根本力量的反映,無論哪一階級想要真正獲得階級社會的統治權力,都必須首先占有社會中一切的經濟力量及其反映形式,即生產資料和政治權力。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領域做出的突出貢獻,即將政治權力的內核歸結于經濟力量,社會中掌握生產的階級就是政治上的統治階級,他們掌握國家的政治權力。
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家權力最大限度地服務于資本擴張的要求,生產資料私有化和生產活動社會化程度逐漸提高,國家統治階級對生產的調節和控制達到頂峰,統治階級手中的國家權力空前強化。這一現象是國家權力高度發展的表現,同時蘊含著變革的因素。國家權力達到強化的頂點,資本對于社會資源的利用和控制程度無法繼續提高,標志著革命和無產階級力量沖破阻礙的時機將要到來。無產階級通過聯合起來的革命將國家權力從資產階級手中爭奪過來,作為反抗和保護自身的武器,在搗毀資本主義國家的同時也搗毀了國家本身,國家權力的作用對象消失,其本身作為強制力量也隨之消失。國家政治權力的消失標志著階級和國家機器的消失,即統治力量和特權、壓迫的消失,國家的暴力職能不復存在,國家權力經過螺旋式發展最終又恢復為社會權力。
六、結論
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其《英國狀況》《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包含了關于國家與社會、階級、生產、人本身、政治權力等之間關系的豐富研究成果,且“國家”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哲學領域都是重要的主體,因此對恩格斯國家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同馬克思一樣,恩格斯的理論研究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進行的,他在吸收前人和同時代人的理論思想的基礎上,結合自身所經歷的社會現實,以解開內心疑慮和現實矛盾為動力,對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質疑和研究。如今我國處于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重要歷史時期,國家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日益凸顯,國家治理也面臨調整進入新階段的挑戰,在這一重要的歷史和現實節點上,研究恩格斯的國家觀對厘清國家與其內部因素關系的本質,科學分析國家發展的歷史規律并指導我國更加科學地實現社會主義并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林鋒.“兩種生產一體論”究竟是不是恩格斯的思想?[J].東岳論叢,2018,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