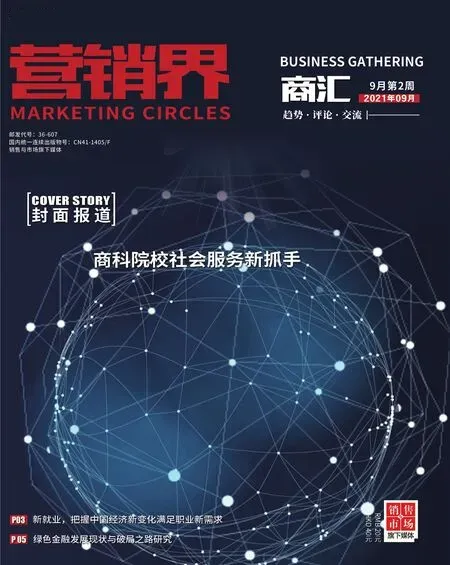股權結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左佳輝(山東科技大學)
所有權綜合改革的實質是引入不同的投資機構,改善所有權結構,以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公司競爭力。自通過分離兩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來,股權結構對公司績效的影響已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所有權結構不僅是不同股東所持股份的比例,而且是擁有股份的股東的水平。前者用于對總股本權益的各種特征進行分類,包括國有股,法人實體,可動用股份等;它通常包括最大股東,前三名股東和前五名股東。此外,股東結構還涉及諸如股票檢查和結余以及股票控制權之類的問題[1]。
■ 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從2013年至2017年在我國注冊的創業板公司中選擇了277家制造公司,因為該研究代表了所有權結構,技術創新能力與公司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
(二)變量指標選取
如前所述,本研究采用三個指標,即大股東比例和股權余額水平來衡量公司的所有權結構。同時,基于眾多學者的研究,力量和凈資產回收方面的研發投入分別用于衡量公司的技術創新和績效。產品性能和創新技術公司以及生產過程受許多因素控制,只有在研究開始時才在主板上列出制造公司。除股權結構外,每家公司資產的負債水平和程度也會影響研究結果。為了有效地控制這些因素,本研究提出了三個控制變量:資產負債率,企業成長和企業規模[2]。
(三)股權結構、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三者間關系模型構建
本研究建立了一個多學科的內聚模型,以測試創業板制造業中上市公司的技術創新,股權結構和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并建立了一致直接的框架來通過方程式定義變量之間的關系。
1.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關系檢驗模型
根據前文提出的H1~H3研究假說,建立了以下三個模型:
模型 1:ROE= -0 +β1CR1+β2DAR+β3GROWTH+β4LINSIZE+ε
模型2:ROE = -0 +β1CR1-5+β2DAR+β3GROWTH+β4LINSIZE+ε
模型 3:ROE= -0 +β2DARβ1Z5β3GROWTH+β4LINSIZE
在上述模型中,模型1通常用于測試ChiNext列出的制造公司的CR1和ROE(H1)之間的關系;模型2用于測試制造公司中CR1-5和ROE(H2)之間的關系。ChiNext;模型3用于測試ChiNext生產公司Z5對ROE(H3)的影響。在這三種類型中,β0是一個常數項,β1、β2、β3和β4是回歸系數,而ε是不加選擇的誤差。
2.股權結構與技術創新關系檢驗模型
基于述中的H4~H6假設,本研究建立在以下模型的基礎上:
模型 4:RD = -0 +β1CR1+β2DAR+β3POWER +β4INSIZE +ε
模型 5:RD = -0 +β1CR1-5+β2DAR+β3POWER +β4INSIZE +ε
模型6:RD =-0 +β1Z5β2DARβ3GROWTH+εβ4LINSIZE
在上述三種類型中,模型4最常用于檢驗在中國業務增長市場(H4)中上市的制造公司的CR1和RD之間的關系;模型5用于測試CR1-5和RD在所列產品中的作用。公司(H5):模型6用于測試Z5對RD(H6)的影響。在這三種類型中β0是一個常數項,β1,β2,β3和β4是回歸系數,而ε是不加選擇的誤差。
3.技術創新中介效應檢驗模型
基于上述假設和研究模型,并基于研究假設H7至H9,開發了以下三個模型以測試技術創新作為中立替代方案對公司的結構和績效以及交付過程的影響。
模型 7:ROE = -0 +β1CR1+β2DAR+β3GROWTH+β4LINSIZE+ε
模型8:ROE = -0 +β1CR1-5+β2DAR+β3GROWTH+β4LINSIZE+ε
模型 9:ROE = -0 +β1Z5+β2DAR+β3GROWTH+β4LINSIZE+ε
在上述三種類型中,waa0是常數項,β1,β2,β3,β4和β5是回歸系數,并且是不加選擇的誤差。 模型7,模型8和模型9分別用于測試我國注冊公司GEM的CR1,CR1-5和Z5 ROE中RD的中間和傳輸方法。
■ 研究結果
(一)相關性與多重共線性檢驗
在這項研究中,統計分析程序SPSS 20.0用于處理數據。通過相關分析,變量ROE和CR1,CR(1-5),RD,LINSIZE和GROWTH在1%的水平上都很重要。同時,DAR與ROE和CR(1-5)呈負相關(5%),與RD 1%呈負相關,與CR(1-5)呈負相關。使用通貨膨脹值指數(VIF)值分析上一節中構建的9個模型,以找出變量之間是否存在較大的可變性問題。測試結果表明,在這9種類型中,不同類型的VIF值都接近1,表明該研究中選擇的許多變量都沒有問題,并且上述9種類型可以更好地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
(二)股權結構、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回歸檢驗
股權集中度[CR(1-5)]和公司績效(ROE)的協同分析結果(F=26.952,AJSR2=0.126,P<0.05)。 同 時,CR(1-5) 和ROE的相關系數為正,且p<0.01,表明在1%顯著性水平上存在正相關。在控制變量中,LNSIZE(平均分布=0.015)和GROWTH(平均增長=0.255)對ROE具有積極的激勵作用,而DAR對ROE則具有負激勵作用(平均值=0.126)。優先級為1%。這表明該模型有效地控制了其他變量對回歸結果的干擾和影響。
在建立一個整合所有權結構和技術創新的發展過程中,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創業板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特點是所占份額較高,而其他股東所占份額較小。因此,基于股權結構的特點和對市場競爭的廣泛考慮,我國的創業板制造企業應在配置股權機制以有效保護企業的同時,改善股權結構,逐步完善其治理體系,并充分考慮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興趣、利益相關度。同時,我們還必須優先考慮技術創新,增加研發投入,在中國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下,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新關乎此戰略能否成功,股權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企業創新行為,大量的實證和研究發現[3],股權集中度與創業板企業的績效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股權制衡度卻與之負相關。
結合當下中國的企業股權結構的聚集度較為明顯和突出,并且我國的監督管理措施和法律法規制度不健全,信息充足度不夠全面,無法從根本上避免集中度較高的企業通過隧道效應侵占中小股東的利益,從而缺乏激勵去研發創新。此處提到的隧道效應,在經濟學中即企業中的控股股東會通過中間行為從公司轉移資產、資源、利潤,從而損害公司中中小股東的利益,造成創新資源、資產和創新激勵的匱乏。所以會使企業的創新成果的減少和績效低下。股權集中度越大,大股東通過隧道關聯交易的方式從上市公司轉移相關資源的概率就高。因此,當下中國企業的股權治理面對的首要問題是股權結構,“隧道效應”的付出和企業創業創新成本的管理相關度較為突出,若隧道效應理論的本錢大于企業投入研發科技創新的本錢,聚集度較高的股東就很少愿意去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企業就會有足夠的空間、資源、動力去進行科技創新投入,從而提高企業績效[4]。
■ 總結
在企業競爭強度與股權結構對企業績效影響方面,本文論證表明,企業競爭強度會對股權集中度與創新投入有正向調節關系,而對股權制衡與創新投入有反向的調節關系。行業競爭作為一個明顯的外部因素,會影響企業內部治理以及企業創業創新行為與動機,面對外部市場競爭環境,股權集中特性的企業創新投入更高,與此同時,盡管分享控制權的股東之間對于高風險的創新投入具有較大的不一致,但為了提高企業競爭力,不得不在公司創新投資方面達成一致。因此,競爭強度削弱了股權制衡對創新投入的負面影響,更有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