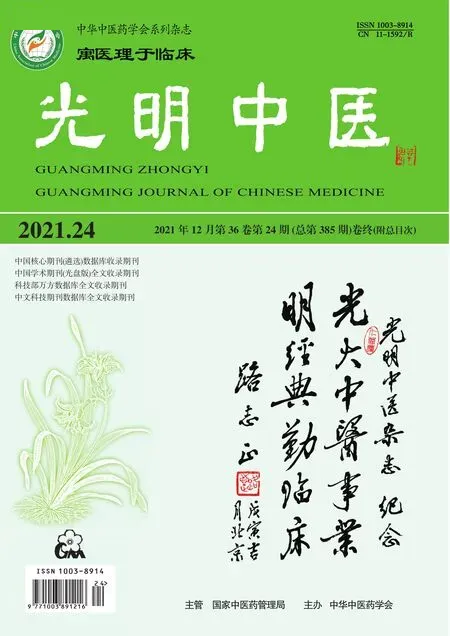張聲生教授和解祛毒治療慢性萎縮性胃炎伴異型增生*
馬永劍 馬學忠
胃癌是我國常見的消化道腫瘤,在慢性胃炎-萎縮性胃炎-腸上皮化生-異型增生-癌的經典Correa 癌變模式過程中,胃上皮異型增生是重要的胃癌前病變。
張聲生教授是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首席專家, 連任兩屆中華中醫藥學會脾胃病分會主任委員,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專科全國脾胃病協作組組長,從事中醫臨床工作三十余年,擅長慢性萎縮性胃炎的治療,對于異型增生性胃癌前病變有獨到見解和豐富治療經驗,筆者有幸跟隨張教授學習,頗受啟迪,特整理總結,以饗同道。
1 癌毒是導致胃癌前病變發展為胃癌的重要因素
張聲生教授認為慢性萎縮性胃炎病機的關鍵在于因虛、因毒致瘀,瘀毒交結,其病機基本特點是虛實夾雜,本虛以脾胃氣陰兩虛為主,標實有濕毒、血瘀、氣滯,臨床多從“虛”“毒”“瘀”論治本病[1]。若出現異型增生病變,對于“毒”的認識與解決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在正氣內虛,血氣瘀滯不利的情況下,此“毒”持續的攻擊機體,進而會演變為胃癌,此“毒”實際上已屬于致癌因子——“癌毒”的隊列,在部分患者檢出異型增生與胃癌并存,恰恰亦印證了這一點。
“癌毒”是獨立于痰、瘀、熱毒之外的一種毒邪、具有致癌的特異性,其既不同于一般的六淫邪氣,亦不同于一般的內生五邪及氣滯、血瘀、痰凝諸邪,而是由于各種致病因素長期刺激,綜合作用而產生的一類特殊毒邪[2]。癌毒致癌的中醫理論目前被中醫學界普遍所認可,凌昌全教授提出了“‘癌毒’為惡性腫瘤之本”的學術觀點和“癌毒”學說,建立了完善、系統的“癌毒理論”[3,4]。王捷虹[5]提出毒瘀交阻是胃癌前病變的關鍵病機,李佃貴提出癌毒作為一種致病因素,不僅存在于惡性腫瘤中,也是導致胃癌前病變向胃癌發生發展的重要因素,即癌毒作為一種致病因素也存在于胃癌前病變中[6]。所以“癌毒”是導致胃癌前病變發展為胃癌的重要因素。
2 陰陽失衡 正氣內虛是癌變內在根本因素
現代醫學研究認為腫瘤的發生、發展與人體免疫系統的紊亂、破壞相伴而行,互為因果,最終免疫系統破潰而腫瘤細胞逃逸且無法控制。某種意義上,出現臨床上可見的腫瘤代表著免疫系統和腫瘤的博弈中落敗了[7],同時研究表明在機體免疫系統中有類似于“加速器”和“制動器”的蛋白質分子等物質,“加速器”類物質激活機體免疫細胞如T細胞,觸發完全免疫反應,進行防御,“制動器”類物質具有抑制免疫激活的作用,這種在“加速器”和“制動器”之間復雜精細的平衡對于嚴謹的免疫調節是極其必要的,他可確保免疫系統充分攻擊防御外來入侵微生物,同時避免因過度激活而導致健康細胞和組織的自身免疫破壞[8],防止正常細胞癌變。免疫紊亂、破潰不能防御、清除致癌因子正是正氣虧虛、無力祛毒的表現,而“加速器”和“制動器”平衡失控正是陰陽失衡的表現,《黃帝內經》云:“生之本,本于陰陽”,陰陽失衡是慢性萎縮性胃炎伴異型增生的基本病機,而正氣內虛與毒、痰、濕、瘀諸邪之實,寒熱錯雜,燥濕相混,氣血失調,毒邪與諸邪膠結都是陰陽失衡的具體表現。
3 癌毒與諸邪膠結 虛實夾雜 陰陽失衡是胃癌前病變基本病機
“癌毒”與痰濁、瘀血、濕濁、熱毒等病理因素同時膠結存在、互為因果,亦可兼挾轉化、共同為病[9]。“癌毒”因腫瘤病理類型的不同,其病機的寒熱、峻緩、兼挾等方面也必然具有鮮明的自身特點,甚至相互間差異很大[10]。但“癌毒”致癌,必須與其內虛之因相合而為病,正氣不足是癌癥發生的前提條件,邪氣拒之是癌癥發生的重要原因,陰陽失衡是癌癥發生的根本原因,情志內傷是癌癥發生不可忽視的因素[11]。因此癌癥基本病機為陰陽失調、毒拒正虛,臨床表現常寒熱、燥濕、虛實等矛盾錯雜,慢性萎縮性胃炎伴異型增生患者的病機亦常常是虛實夾雜,氣血同病,寒熱錯雜,痰濕瘀毒膠結,二者病機不謀而合。
4 和解祛毒 協調陰陽治療慢性萎縮性胃炎伴異型增生
張聲生教授主張以和解祛毒,協調陰陽為治療慢性萎縮性胃炎伴異型增生大法,采用破結攻毒結合調肝理脾,扶正祛邪,調和氣血,調節寒熱,燥濕相濟,調和脾胃,升降氣機等法,以祛除致癌因子,修復、平衡免疫系統,提高免疫防御功能,以期截斷癌變的發生、甚或逆轉癌前病變。
4.1 破結攻毒以祛毒張聲生教授認為對于此“毒”不可與一般之邪對待。《金匱要略心典》曰: “毒者,邪氣蘊蓄不解之謂”。其與痰濁、瘀血、滯氣、濕濁、熱邪膠結,常被裹挾于內,欲除之,須先破解其膠著凝結之勢,使蘊蓄之毒邪外露而攻除之,猶如僵持的談判,膠著的戰爭,必須先要打破僵局,打出開口,破結攻毒,故常常結合病證所現之滯氣、瘀血、痰濁、濕濁、熱邪等具體情形,使用破滯、破血、破肝、散肝、軟堅、消積、芳透、化濁、豁痰、通絡等法,疏郁散結通滯,開通道路,“拔”毒而出,剔“毒”而去,使水道通暢,血氣條達,寒熱平復,陰陽平衡。破滯氣用草豆蔻、枳實、厚樸、檳榔等藥物;破血、破肝常以三棱、莪術、郁金、全蝎等藥物,注意三棱、莪術用量不宜過大,以免引起出血;散肝常用三七、丹參、赤芍、延胡索、桃仁、紅花、川芎、香附、檀香、五靈脂、蒲黃、預知子、娑羅子等;軟肝化瘀常用鱉甲、牡蠣、珍珠母、海螵蛸等;軟堅化痰用夏枯草、浙貝母、山慈菇、旋覆花、瓦楞子等藥物;消積常用雞內金、瓦楞子、山楂等藥物;芳透以白豆蔻、藿香、蒼術、砂仁等藥物;泄濁化濕用草果、蠶沙、生薏苡仁等藥物;豁痰用石菖蒲等藥物;通絡常用蜂房、全蝎、蜈蚣、地龍、穿山甲、僵蠶、絲瓜絡等藥物,痰滯經絡多用植物類,而瘀血阻絡重者多用蟲類;溫散通陽用肉桂、吳茱萸、烏藥、干姜、橘核、荔枝核等藥物。同時依證配伍白花蛇舌草、山慈菇、黃連、生薏苡仁、半枝蓮、三棱、莪術、蜂房、穿山甲等具有抗腫瘤作用的藥物清熱解毒、利濕祛毒、化瘀祛毒、通絡攻毒,對于攻毒之藥,遵《黃帝內經》“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力求有功而無過,適可而止。
4.2 從矛盾對立統一入手和解以協調陰陽張聲生教授謹遵《黃帝內經》:“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之旨,以協調陰陽為治病之本。陰陽相互制約,互根互用,諸如虛實、氣血、寒熱、升降、燥濕等均是陰陽矛盾兩方面的具體表現,張聲生教授重視從矛盾的對立統一入手,補消結合、調節寒熱、調理氣血、升降氣機、燥濕既濟等以協調陰陽。
張聲生教授補消結合常以自研萎胃治療方加減治療萎縮性胃炎,方以四君子湯補虛,加預知子、陳皮、神曲、雞內金行氣運脾消食,合三七粉化瘀,氣血同調,張聲生教授臨床恒用三七,指出三七活血定痛而不動血妄行,化瘀止血且能補虛益氣,能散肝、破瘀、軟堅,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具有增強免疫功能和抗癌作用,雞內金善磨谷消積,健脾強胃,而不傷正氣,對于伴異型增生,或加蜂房、全蝎、白花蛇舌草等破結攻毒,攻補兼施;調節寒熱常用半夏瀉心湯或佐金丸,寒熱并用,辛開苦降,半夏瀉心湯辛開苦降甘調,寒熱并用,調理脾胃肝膽之寒熱及氣機之升降,佐金丸中,吳茱萸辛苦大熱,辛熱溫散能疏肝,味苦而能降泄,黃連苦寒清熱而降泄,二藥相合,辛通苦降,依病證寒熱之多少,定吳茱萸、黃連孰君孰佐,黃連為君則清胃泄肝,兼以燥濕,吳茱萸為君則暖肝溫胃散寒通陽;重視脾胃氣機之升降,《臨證指南醫案》云:“脾胃之病,虛實寒熱,宜燥宜潤,固當詳辨,其于升降兩字,尤為緊要”“脾宜升則健,胃宜降則和”,故常以黃芪(黨參)、白術、柴胡、葛根等升補脾氣,并配伍娑羅子、預知子、木香、厚樸、枳實、炒萊菔子等下氣消脹,升清降濁,調和脾胃,臨證尤善用旋覆花配伍赭石和中降逆,旋覆花,《神農本草經》云:“主結氣,脅下滿,除水,去五臟間寒熱,補中,下氣”,其苦降辛散咸軟,辛以宣散而先升,繼以苦咸而后降,可以軟堅散結,化痰去飲,降氣除滿,赭石苦寒質重,《長沙藥解》云:“其降胃而下濁氣也”,《醫學衷中參西錄》云:“降胃之藥,實以赭石為最效”,兩藥配伍,宣降結合,和胃降逆,為治療胃氣上逆的常用藥對。脾為己土,易為濕困,喜燥惡濕,胃為戊土,易為燥化,喜濕惡燥,張聲生教授治療脾胃病重視兼顧脾胃潤燥之性,臨證不一味純用辛香溫燥或甘涼滋潤之藥,過則反傷,務求潤燥相合,陰陽既濟,對于濕邪困脾證,常選用薏苡仁、砂仁、蠶沙、玉米須、白扁豆等藥輕力緩的淡滲利濕藥物,溫而不熱,香而不燥,可防止過于溫燥而有傷胃陰,對于胃燥津傷者,常于麥冬、北沙參、石斛等滋養胃陰,佐以砂仁、陳皮、紫蘇梗等辛香走散、辛苦流動之品,為防其滋膩礙脾、陰柔壅胃,對于濕熱蘊結,津液損傷,常用黃連配伍生地黃,或以黃芩配伍黃精,使清熱利濕而無燥傷之弊,養陰生津而無助濕之慮。
4.3 調肝理脾為常法張聲生教授認為肝脾失調與疑難脾胃病關系甚為密切,《黃帝內經》云:“土得木而達”,《脾胃論》云:“膽者,少陽春升之氣,春氣升則萬化安。故膽氣春升,則于臟從之;膽氣不升,則飧泄腸澼,不一而起矣”,《臨證指南醫案》云:“肝病必犯土”。土虛則木易乘,情志不舒,則肝郁易犯脾,因此提出調肝理脾法是治療疑難脾胃病的常用和基本治療大法,臨床常以此法治療慢性萎縮性胃炎伴異型增生,具體方法有疏肝健脾法,代表方為小柴胡湯或逍遙散;“抑木扶土”法,代表方為痛瀉要方;“培土泄木”法,代表方為柴芍六君子湯;補脾養肝法,代表方為六君子湯合四物湯;泄肝和中法,代表方為柴胡疏肝散合左金丸;柔肝滋脾法,方用一貫煎;暖肝溫脾法,代表方為理中丸合吳茱萸湯;理氣化癖法,方用血府逐瘀湯;清利濕熱法,方用茵陳蒿湯合連理湯[12],臨床隨證施用,靈活加裁。
5 臨證驗案
尚某某,女,40歲。2015年7月22日初診,主訴:胃脘脹滿1年余。刻下癥見:胃脘脹滿,痞悶不舒,噯氣頻作,畏食生冷,偶反酸燒心,食少納差,口苦,大便稀溏,日1次,小便可,寐差易醒,素性情急躁,舌暗苔白膩,脈細弦。胃鏡:非萎縮性胃炎?病理:胃竇慢性活動性萎縮性胃炎伴腸化及輕度異型增生,Hp(+)(北京中醫醫院)。中醫診斷:胃痞(脾虛肝郁,濕瘀膠結)。西醫診斷:慢性萎縮性胃炎伴輕度異型增生。治法:健脾疏肝,除濕化瘀。方藥:黨參15 g,炒白術10 g,生薏苡仁15 g,三七粉(沖)3 g,厚樸10 g,木香10 g,白芍15 g,延胡索15 g,焦神曲25 g,藿香10 g,預知子20 g,蜂房5 g,白花蛇舌草25 g,旋覆花(包)10 g。14劑,水煎,分2次早、晚餐后溫服。并囑患者調節情緒,保持樂觀心態,合理飲食,規律起居,按時休息。
2015年8月19日二診:患者服上方28劑,噯氣明顯減輕,胃脹滿悶較前略減輕,偶有反酸,仍寐差,大便成形,日1次,偶有排便不凈感,小便可,舌紅苔薄白干,脈細弦。患者氣逆之勢消除,予去旋覆花、厚樸,加珍珠母,其味咸入血走心而入腎,性寒能滋肝陰,清肝火,平潛肝陽而收魂,合遠志交通心腎,寧心安神,易生薏苡仁為炒薏苡仁,并加白扁豆10 g,增強益氣健脾除濕之力,14劑,煎服法同前。
患者服上方后癥狀緩解,并復診繼續治療,于2016年1月10日在北京中醫醫院復查胃鏡示:慢性萎縮性胃炎伴腸化、伴膽汁反流。2016年1月27日復診:胃脘脹滿減輕,食欲改善,但飲食不慎仍易發作,大便欠暢,小便可,寐差易醒,舌淡紅苔薄白膩,脈弦細。方藥:黨參25 g,炒白術10 g,茯苓10 g,益母草20 g,佛手10 g,木香10 g,白芍25 g,延胡索15 g,合歡花20 g,炮姜10 g,珍珠母(先煎)10 g,紫蘇梗15 g,香附15 g,白扁豆15 g,郁金10 g,草豆蔻10 g,柏子仁25 g。14劑,煎服法同前。
患者繼續堅持于門診就診治療,胃脹等癥狀逐漸緩解,至今已復查3次胃鏡,鏡下及病檢均未發現異型增生病變。
按:患者脾虛肝郁,痰濕瘀膠結,以黨參、白術、薏苡仁益氣健脾以扶正,白芍、延胡索、預知子養血疏肝,和胃理氣,木香、厚樸行氣醒脾,化濕和胃,旋覆花化痰降逆,軟堅散結,合延胡索、三七粉、蜂房,化瘀和血通絡,白花蛇舌草解毒祛濕,焦神曲消食助運化,方中厚樸、預知子、延胡索、旋覆花、三七、蜂房以破滯氣、散肝、軟堅、通絡以開通膠結,白花蛇舌草、蜂房以通絡泄濁解毒,全方共奏益氣健脾,疏肝和胃,理氣降逆,化瘀通絡,除濕解毒之功效,隨證加減,攻補兼施,養正除積,扶正解毒。此病痼結,非短期所能克除,必悉心調治,緩圖而取效,急功近利只能適得其反,故開導患者,既要重視疾病,積極堅持治療,又要心態放松,調節情志,合理飲食起居對于疾病恢復都有積極意義。
6 展望
中醫藥治療胃癌前病變有一定的優勢,研究報道個體化辨證論治取得一定療效,如楊國紅[13]對該病分型辨證論治總有效率達86.7%,單兆偉[14]應用參夏蓮草湯加減治療不典型增生療效顯著,魏玥等[15]研究證實益氣化瘀解毒法可顯著抑制p-PI3K p85蛋白的高表達、治療CAG伴Dys、逆轉PLGC、防治胃癌,因此總結、研究、推廣名老中醫相關經驗對于防癌治癌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