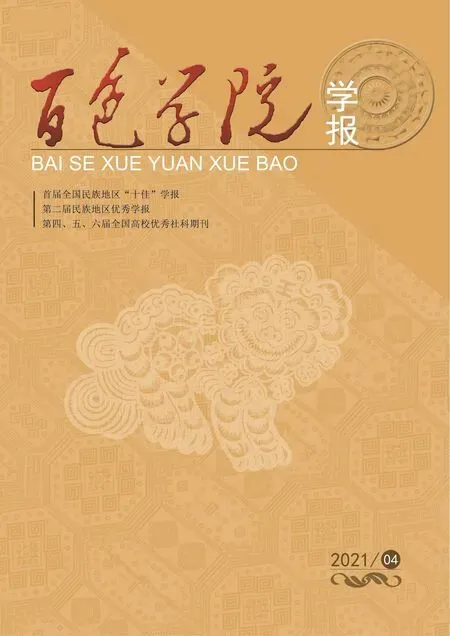儀式敘事研究:民族文學研究的新維度
楊杰宏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以其體裁多樣性、歷史悠久性、傳承活態性、社會功能多元性而名,而且多與當地的民俗活動、祭祀儀式有著天然的聯系,也就是說,它不像傳統的作家文學那樣是供讀者閱讀的,更多是讓受眾參與到民俗及儀式活動中,通過傾聽、觀看、歌舞、祭拜等行為來達成理解與體驗。簡言之,民族文學的敘事與民間儀式互為表里,互文同構,儀式中有敘事,敘事融于儀式。所以研究民族文學,不能僅限于口頭與書面文本,必須顧及與敘事文本相關的儀式的各個層面及要素。
儀式一直被人類學家視為觀察人類情緒、情感以及經驗意義的工具,成為民族地研究者閱讀和詮釋社會的一種不可多得的“文本”;比起日常生活中“秘而不宣”的意義而言,儀式是較為公開的集體性敘事,具有經驗的直觀性。儀式的這些特征都使得人類學家熱衷于將它作為一種文化生成及意義的研究對象。而人類學家關注的儀式中,神話、史詩、故事、傳說成為儀式敘事的主要表征,尤其是神話與儀式的關系成為最早關注的研究視域,甚至形成了專門以此為研究對象的“神話—儀式”學派。相形于“神話—儀式”學派所關注的象征、意義、結構、宗教等“外在性”研究,晚近崛起的口頭詩學學派則更側重于口頭傳統的“內在性”研究,即這些神話、史詩等口頭敘事文本的內在構成及表演規律研究,二者共同構成了口頭詩學觀照儀式敘事研究的理論背景,這也是建構口頭敘事與儀式敘事研究的主要理論來源及理論支撐點。從20 世紀90 年代國內學者把口頭詩學理論引介到國內來以后,30 余年來口頭詩學視野下的民族文學研究已經發展成蔚為壯觀的中國文學研究現象,這方面的成果可謂層出不窮,碩果累累,初步形成了口頭傳統研究的“中國學派”。[1]但縱觀這些成果,其研究重點以民族口頭傳統的文本、口頭程式、創編與演述為主,而對與口頭傳統相關的儀式構成、儀式敘事、儀式要素等相關研究成果及影響明顯不抵前者。這可能與口頭詩學理論濫觴之時并不涉及儀式有內在關聯。口頭詩學視野下的民族文學與儀式敘事關系研究不僅可以拓展口頭詩學的研究領域,同時可以促進形成民族文學研究的新維度,推動民族文學研究的可持續發展。
一、“神話—儀式”學派諸說概述
“儀式”是一個具有理解、界定、詮釋和分析意義的廣大空間和范圍;被認為是一個巨大的話語(large discourse)。[2](P1)儀式的概念所指涵蓋了歷史及社會各個方面,由此也帶來了概念理解的巨大差異性。儀式與神話關系研究的鼻祖應算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他提出的戲劇起源于酒神祭祀儀式的學說迄今沒有更權威的學說取而代之。酒神狄奧尼索斯本身亦莊亦諧的特點和精神是促使戲劇產生于酒神祭祀儀式的深層原因,同時祭祀儀式中的酒神頌及儀式中面具的使用對戲劇的形成也至關重要。[3]
英國著名女學者赫麗遜(Jane EllenHar-rison)在其《古代藝術與儀式》中,考察了盛行于原始希臘的各種春季儀式(springrites),并根據古希臘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以及哲學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提供的線索,得出一個意義深遠的發現:希臘悲劇是從一種春季儀式——酒神儀式移位而來。亞里士多德的戲劇起源說是從詩學發生論的視野來論述的,而“神話—儀式”學派則把研究視野投射到廣闊的宗教、思維、語言、歷史等學科領域中,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知識譜系。根據神話—儀式理論,所有存在的神話都和儀式密不可分,所有神話都是早期人類對儀式的解釋。根據史密斯的理論,人們最初進行的儀式和神話沒有關系。后來我們忘記了最初舉行儀式的原因,就嘗試編一些故事來解釋儀式,并聲稱舉行儀式是為了紀念神話中描述的事件。由此斷言,“神話來源于儀式,而非儀式來源于神話”[4](P15)。弗雷澤也認為原始人最早信仰魔法,后來人們對魔法失去信心,就發明了神話,并且說他們之前舉行的魔法儀式為了安撫眾神而進行的宗教儀式。弗雷澤卻又斷然拒斥儀式總是或者通常先于神話的觀念。就其關于巫術和宗教的觀點所體現出來的一般傾向而言,神話先于儀式的理論或者教條正是其所需要的:只要在他看來儀式行為有著理性的目的,就預設了一個自然因果關系的理論或者某種神學。[5](P711)現代人類學家哈里森則也持“儀式一定是先于神話”的觀點,他認為在古希臘語中,神話的定義就是“在儀式行為中所說的東西”。后期人類學家逐漸摒棄了神話與儀式孰先孰晚的“雞與蛋”問題,普遍轉向把二者相互交融的同一范疇體系研究。利奇認為神話和儀式都是對同一種信息的不同交流方式,二者都是關于社會結構的象征性、隱喻性表達。[6](P713-14)美國歷史學派代表人物博厄斯也認同神話與儀式的協約關系,認為“儀式本身是作為神話原始性刺激產物”[7](P617)。功能主義學派奠基人馬列諾夫斯基則從“功能”角度闡述了二者關系:神話并不僅僅是歷史的敘說;神話作為一種口頭傳承的“圣書”,作為一種對世界和世人的命運施以影響的現實,為古老意識所領受。所謂神話與儀式均為某種舉措的再現與重演。[8]
但儀式與神話并不總是如此協約般對應出現,在不同時空條件下二者也存在互疏關系,如南非卡拉哈里沙漠的游牧民族的神話異常豐富,而儀式卻寥寥無幾;北美洲的因紐特人卻與此恰好相反。[9](P42)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考察尺度是歷時性的文化變遷,諸多神話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從儀式中脫落,或者儀式中的神話數量與內容呈現遞減情況。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洪從儀式與神話的辯證關系中洞察到了二者的矛盾性:二者在同一背景和環境變數中發生的變化并不一致,相對于作為“行為模式”的儀式與作為“觀念模式”的神話,儀式更容易產生變化。[10](P320)
筆者在此引述“神話—儀式”學派的不同理論觀點,重在說明“神話—儀式”所涵蓋的內涵及范圍構成了一個“一個巨大的話語”(large discourse),其構成因素、功能、意義、范圍極為復雜多元,特別是那些重大的、神圣的、祭祀的、傳統的、代表性的儀式往往具有文化的整體表述功能。比布·布郎恩認為,《圣經》中的“文學”與儀式相結合形成的“儀式表述與敘事”(Ritual Words and Narrative),本質上是一種不可替代、不容置疑的權力“話語”和“勢力”,其功能是讓人們相信“上帝是真實存在的”。[11](P8)克利福德—格爾茲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正是通過圣化了的行動——儀式,才產生了同“宗教觀念是真實的”這樣信念;通過某種儀式形式、動機與情緒及關于秩序的一般觀念才是相互滿足和補充的。通過儀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組象征形式而融合起來,變為同一個世界,而它們構成了一個民族的精神意義。[12]儀式敘事傳統中,儀式中的神話敘事是其主要特征,“儀式”與“神話”的深層關系既是構成其敘事傳統的內核所在,也是儀式敘事的程式化特征研究的關鍵著力點。“神話—儀式”學派的諸多觀點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程式的生成與儀式敘事的傳統指涉性密切相關,對此的深入研究必須建立在儀式與神話的互文研究中。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學派的理論旨趣并不在口頭詩學與文學研究,更多是傾向于人類學、社會學學科范疇內的功能、意義、結構、象征等學科,這些概念可為研究民族文學學者所借鑒,但不能淪為這些學科的附庸或資料提供者的角色,這是不能不察的。
二、口頭詩學理論視野下的儀式敘事研究
20 世紀30 年代,美國學者帕里、洛德二人通過對南斯拉夫地區活形態史詩的田野調查研究與《荷馬史詩》的文本分析相結合,發現與南斯拉夫的史詩演述風格相似,荷馬史詩的演唱風格也是高度程式化的,從而論證了《荷馬史詩》是口頭傳統的產物。帕里—洛德的研究范式建構了一整套嚴密的口頭詩學分析方法——口頭程式理論。程式是構成口頭詩學的核心概念。洛德發現,程式不僅存在于循環性重復使用的傳統性片語上,而且也存在于故事的主題或典型場景,以及不同的故事范型中。弗里從歌手立場出發,把程式片語、主題或典型場景、故事范型稱為“大詞”(large word)。他認為:“運用著程式、話題和故事型式這三個‘詞’,口頭理論解答了行吟詩人何以具有流暢的現場創作能力的問題。這一理論將歌手們的詩歌語言理解為一種特殊的語言變體,它在功能上與日常語不同,與歌手們在平常交際和非正式的語言環境中所使用的語言不同。由于在每一個層次上都借助傳統的結構,從簡單的片語到大規模的情節設計,所以說口頭詩人在講述故事時,遵循的是簡單然而威力無比的原則,即在限度之內變化的原則。”[12]
相對說來,帕里—洛德理論關注的是歌手如何傳承、創編口頭史詩的內部運作規律,而對儀式與史詩的復雜關系并不作為研究對象,另外,南斯拉夫地區口頭史詩生存的文化形態也與“神話—儀式”學派的人類學家所關注的“儀式”也大相徑庭。帕里、洛德之后,把史詩研究領域拓展到儀式、宗教領域,且成就較大的以格雷本·納吉、勞里·航柯為代表。
納吉為《荷馬史詩》的語境恢復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但他也認識到《荷馬史詩》與其他國家、不同民族的史詩不具有等同性,如印度史詩與《荷馬史詩》不可等同論之。他認為宗教在印度活形態口頭史詩傳統中起了關鍵性作用,而他對“宗教”的理解是基于神話與儀式兩個層面的交互作用,是用崇拜(cult)來限定“宗教”的概念范疇,“崇拜”界定為“將儀式和神話的諸要素結合起來的一整套實踐”。[13](P61-68)印度史詩傳統功能的表現既是儀式又是神話,“史詩演述通過儀式成為保護和治療;同時史詩的敘事表達了地方意識形態,進而在地域性神話與泛印度的神話之間形成種種通衢”。[13](P61)由此他認為古希臘史詩敘事傳統的形成與制度化的宗教祭奠節日——泛雅典娜節密切相關。“在祭儀中,這些英雄受到崇拜的特定語境中,它擴展到了英雄的概念……在古希臘有關英雄的史詩傳統及其發展中,對英雄的崇拜可以說是一種亞文本(subtext)。此外,在地方層面上是英雄崇拜,在泛希臘層面上則是英雄史詩。”[13](P68)
勞里·航柯通過對印度西里人(Siri)的口傳史詩的研究,對取例于西方的史詩傳統概念進行了反思,他把史詩文類的內涵界定置于全球的、區域的、地方的三個傳統背景中;認為史詩的宏大性突出表現在它的神話和歷史結構上的意義,對族群的重要意義上;超級故事(superstories)以其長篇的形式、詩學的力度、神話和歷史內容,為集團或個人的文化認同鋪平了道路。史詩是關于范例的宏大敘事,這個表述保留了以往關于史詩的一些基本認識,即史詩是關于歷史上的英雄及其業績的長篇敘事詩歌,但是去掉了“詩歌”的限定。因為,史詩未必都是以詩體來演述的。就印度西里人的史詩來說,除了詩歌本身之外,它還以其豐富的內涵展示出豐富多彩的人物和事象。這種豐富性,其中的一部分來自于反復出現的形象和行為:誕生、訂立婚約、婚禮、成年禮、享宴、葬禮等,這些事象把史詩的敘事統合起來,與史詩的受眾的個人經驗相互作用,其結果便是,史詩的文化意義大大超越了某一個史詩文本的局限。[14]
筆者意在說明,西方學術體系下“史詩”概念內涵的形成與擴大基于已經與儀式高度脫離了的《荷馬史詩》,而以此作為“史詩”概念的法則,事實上以先驗論的形式區隔了史詩的兩種形態:典型性史詩與非典型性史詩[15](P2),由此也遮蔽了不同區域、民族的史詩傳統的多樣性特征。格雷戈里·納吉與勞里·航柯的為史詩研究的轉向做出了突出貢獻,也促進了國內口頭詩學研究的深層拓展,這也為本文的立論提供了諸多理論支撐。儀式敘事傳統的形成、傳承與流布與民族宗教或族群文化認同的形成、發展密切相關,敘事傳統與族群傳統存在互構的同一性,而這一互構過程與早期文化底層的繼承、發展,對周邊民族宗教文化的吸納等文化事實存在內在邏輯關系。具體來說,儀式敘事傳統背后存在一個吸納、消化共源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本土化過程。納吉認為古希臘神話與史詩的形成過程與“祖語”(pro?to—language)希臘化的三個過程是同步進行的:印歐語系詩歌的希臘化、印歐語系神話與儀式的希臘化、印歐語系社會意識形態的希臘化。[16]儀式敘事傳統中的洪水神話、上天求婚、送魂、父子聯名制、火葬、山神、樹神、水神、祖先神等包含在內的自然崇拜與祖先崇拜等傳統文化與彝語支、藏緬語族的文化存在著共源關系,而這些共源文化又因所處的地理環境、歷史進程、經濟發展、民族關系等狀況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由此也折射到本土化過程中,形成大同小異或小同大異的文化現象。譬如納西族的東巴教在吸納了大量的苯教、藏傳佛教、道教內容后,與同一語支內的原生宗教形態發生了較大的差異,而這些差異也是儀式敘事傳統本土化的結果。具體來說,儀式敘事傳統的本土化進程是通過三個層面達成的:語言文字及口頭傳統的本土化、宗教儀式的本土化、宗教意識形態的本土化。儀式敘事傳統的核心特征是宗教敘事,口頭傳統依存于宗教儀式中,史詩演述成為族群傳統文化的宏大敘事,具有“社會憲章”的文化功能。在此意義上,儀式敘事傳統中的神話、史詩、故事不只是用來審美的文學消費品,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意義的實踐。
三、口頭詩學觀照下的儀式敘事研究的國內實踐
具體來說,口頭詩學理論視野下的儀式敘事傳統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尹虎彬的《河北民間表演寶卷與儀式語境研究》雖并不是專門研究儀式與敘事傳統關系,但其強調的敘事傳統的文化整體性、注重敘事語境的理論視角及方法論也涉及本論題的研究范疇。作者把寶卷文本和它的表演、表演者、表演場合、社會生活和民間組織置于廣泛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予以考察,“后土寶卷與其他民俗學文本,如劉秀走國、后土靈驗的民間敘事、地方傳說和古代神話,民間神社的儀式、儀式音樂、民間藝人、地方的神靈祭祀傳統,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彼此依存的系統,只有在這個系統內各個文化要素才具有生命力”[17]。作者借鑒了納吉的印度神話史詩與古代希臘史詩傳統的比較研究成果,提出了“神靈與祭祀是民間敘事傳統的原動力”的理論假設,并結合田野民族志與文獻考證,論述了寶卷和民間敘事文本存在著借用、傳遞、標準化、地方化的動態影響過程,地方性知識構成了寶卷與民間敘事文本互為文本化的語境。由此拓展了寶卷文本的認識范疇,“即寶卷不僅是字傳的、語言層面的篇章,也是心理的、行為的、儀式的傳承文本”[17]。作者把帕里—洛德的程式、主題、語篇結構的理論應用置于寶卷和民間口頭敘事文本的互文性關系上,闡釋了寶卷與神話、信仰、儀式之間的互文關系在特定傳統內部歷史演變的過程,由此也論證了寶卷與相關的民俗學文本互為文本,以地方性的民間敘事為文本特征,以后土崇拜為核心內容,以傳統的神話為范例,以神靈與祭祀為民間敘事傳統的原動力的文化事實。[17]
巴莫曲布嫫是對儀式與史詩關系研究著力甚多,成果突出的學者。①參見巴莫曲布嫫的以下論述成果,包括:《敘事語境與演述場域:以諾蘇彝族的口頭論辯和史詩傳統為例》,《文學評論》2004 年第1 期;《在口頭傳統與書寫文化之間的史詩演述人:基于個案研究的民族志寫作》,《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1 期;《“民間敘事傳統格式化”之批評:以彝族史詩〈勒俄特依〉的“文本迻錄”為例》,《民族藝術》2003 年第 4 期、2004 年第 1 期、2004 年第 2 期。她以口頭詩學、表演理論、民族志詩學觀照彝族史詩,通過深入有效的田野研究,提煉出諸多開創性學術理論觀點及概念。“敘事語境”主要指史詩演述中的儀式化語境,具有客觀性,敘事文本的語境化有利于對文本與田野之間互動性的把握,但“語境”的概念內涵的泛化不利于對具體民俗事象的深細觀察與分析,由此提出了“演述場域”的概念。“演述場域”是研究者在田野現場中對表演事件、行為的一種考察視界,具有主觀性,對有泛化之嫌的“語境”有細化功能,主要用于界定具體的表演事件及其情境(situation),相當于英文的“situ?ated fields of performance”。巴莫曲布嫫認為演述場域的確定“能夠幫助觀察者在實際的敘事語境中正確地調整視角,以切近研究對象豐富、復雜的流變過程。”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上,有利于通過跟蹤觀察、多重“透視”,從而洞察到不同儀式場景及其時間節點上史詩“演述”在形式與內容方面或隱或顯的變化。“最后得到的表演結果——文本也就會投射出表演行動的過程感、層次感、音聲感,其文本記錄的肌理也會變得豐富而細致起來,同時也能映射出演述傳統的內在品格。”[18]
高荷紅對滿族神歌與儀式關系研究對儀式敘事研究也有參考價值,她的《滿族薩滿神歌的程式化》一文對滿族神歌本中的程式歸納為請神、祭祀緣由、供品、祭祀時間、神靈、送神、虔誠態度、其他程式等八類,這些程式在薩滿創作、表演時起到了重要作用。[20]另外,她從家祭儀式的程式與神歌的關系、放大神神歌與儀式的關系、野祭儀式中薩滿舞蹈形式與神歌的關系三個方面分析了儀式與神本子的關系,認為儀式和神歌并非一一對應,但關鍵的一些行為都記錄在神本子中,從某種角度說,神本子成了薩滿祭祀儀式的保存工具。[19]
近年來,筆者以東巴敘事傳統為研究個案,對儀式敘事中的程式化特征進行了重點研究,提出了“儀式程式”的概念。在長期的跟蹤調研中發現,東巴在儀式中敘事不僅與口頭和書面文本的吟誦活動密切相關,且與儀式的東巴音樂、東巴繪畫、東巴舞蹈、東巴工藝等多模態敘事的文本交織融匯于一體,從而體現出多元模態敘事文本的形態,其中,程式是這些多模態敘事文本得以有機聯結的共同基因。這些程式在儀式多模態敘事文本中是相對穩定的,重復律是共性,在不改變儀式敘事的核心結構及情節基干前提下,儀式的程序、主題、規模、時間、空間可以進行相應的調整、增減、組合,并共同成了一個流動的、活態的、互構共融的多模態的儀式敘事文本。儀式程式在儀式敘事的功能如同口頭歌手在口頭表演中運用的“大詞”,為儀式主持者靈活機動地組織、創編儀式敘事及儀式表演提供了充足的“武器庫”。“儀式程式”概念的提出,基于“口頭程式理論”的延伸性研究,也是這一理論對儀式敘事中的一次理論實踐,這對與儀式敘事緊密關聯的史詩、神話等口頭傳統的研究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同時對于儀式表演以及傳統戲曲的深入研究也有相應的參考價值。[20](P259-261)
四、余 論
儀式敘事傳統并非是孤立的文化現象,它與社會、歷史、族群傳統的整體性密切相關,其本身包含了口頭的、文字的、圖像的、儀式的、表演的(如音樂、舞蹈、游戲等)諸多要素,這些要素構成了互為文本,彼此聯系的系統。由此,對它的研究必須置于宏觀層面的整體性中,這樣才能準確、完整地理解儀式敘事傳統的深層內涵。儀式敘事傳統以活形態的方式延續至今,儀式是其最重要的傳承載體和表述“文本”,是各民族社會生產、生活實踐以及歷史、傳統的反映,其本身也是一種敘事行為,或者說“儀式敘事”是儀式敘事傳統的主要表現特征。而對儀式敘事的深層理解與闡釋,必須有效把握其敘事語境與演述場域,深入到不斷流動、變化的儀式時空及儀式表演事件的各個環節中,對構成演述場域的“在場”諸要素予以跟蹤觀察、多點“透視”,由此達成儀式的、口頭的、文字的、表演的不同敘事文本的內在邏輯的統一。
對儀式敘事研究而言,上述研究成果雖論及口頭傳統與儀式敘事的關系層面,但研究重點仍以口頭詩學或民間敘事在儀式中的表現形式為主,對儀式敘事的內在構成、運作機制,儀式敘事的構成要素分析,口頭傳統與儀式敘事的內在邏輯關系,儀式敘事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等方面的研究仍存在諸多不足。而這些問題構成了儀式敘事研究研究的目的所在,這也是建構口頭傳統研究中國學派的重要攻關課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