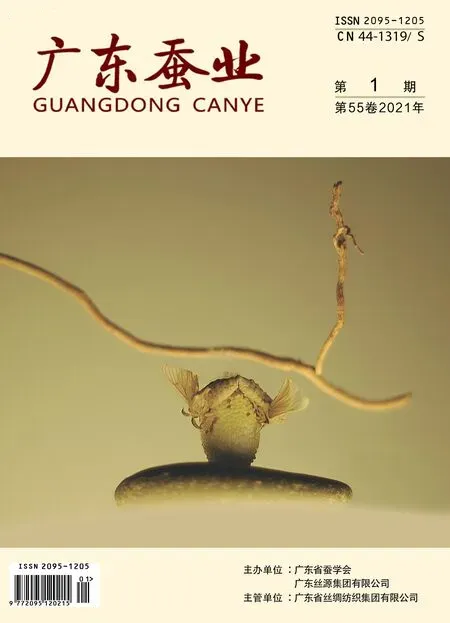家蠶Toll受體的研究進展
楊偉鋒 陳雪晴 林泳儀 梁業彬 劉吉升
(廣州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廣東廣州 510006)
1 家蠶及其價值
家蠶(Bombyx mori),又名桑蠶,屬于鱗翅目蠶蛾科,具有28 對染色體,起源于中國,由古代的原始野蠶馴化所獲得,距今已超過五千年。在2004年,全國絲綢工業年產總值就達到了1 385.35 億元,繭絲的產量占全球總額的70%,出口量占全球總額的80%,年創匯達40 億美元[1-2]。家蠶作為我國歷史悠久的經濟昆蟲,不僅具有能夠為紡織原料提供蠶絲這一經濟價值,同時也是鱗翅目昆蟲中的模式生物,有著良好的基礎研究積累,并保存有大量的突變體。在2004年,我國西南大學家蠶基因組研究團隊率先繪制出了家蠶基因組框架圖,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家蠶表達序列標簽數據庫,發現了與家蠶發育和變態、性別的決定、激素調節及免疫等密切相關的關鍵功能基因群[3]。在2009年,該團隊完成了對家蠶基因組精細圖譜的繪制,超過13 000 個基因被定位于家蠶染色體上[4]。同時還對29 個家蠶突變品系和11 個中國不同地理來源的野桑蠶進行了全基因組測序與序列比較分析,從基因組水平方面揭示了家蠶的起源進化[5]。家蠶是鱗翅目中第一個完成全基因組測序的昆蟲,是鱗翅目的模式生物,具有重要的科研價值。
2 昆蟲免疫
昆蟲雖然有著非常出色的機體物理屏障,如角質表皮或甲殼能夠保護機體免受外源體入侵,但昆蟲與哺乳動物不同,并不具有高度專一的特異性免疫,其免疫系統僅擁有的非特異性免疫成為保護機體免受病原微生物入侵的重要保障。昆蟲具有強力高效的非特異性免疫系統,能夠鑒別并消除入侵的病原體和寄生蟲[6-7]。該系統針對微生物入侵感染做出的免疫反應包括細胞免疫(cellular immunity)和體液免疫(humoral immunity),這兩個免疫反應間具有緊密的聯系。在面對外來病原體入侵時,無論細胞免疫或者體液免疫都會首先通過模式識別受體(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進行識別,這些模式識別受體可以特異性地識別外來病原體上的病原相關分子模式(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細胞免疫反應中包括吞噬作用和包被反應,隨著體內血細胞的循環進行調節,而由昆蟲脂肪體合成和分泌抗菌肽而形成的體液免疫比細胞免疫更快更早地產生防御應答[8]。昆蟲具有復雜的抗菌肽基因表達調控機制,不同種類的抗菌肽能夠特異性地激活特定基因的表達,當抗菌肽結合到細菌或真菌表面時,能夠引起菌體的裂解和死亡[9]。抗菌肽的合成由兩條不同的信號通道調節,分別是Toll 信號通路和IMD (immune deficiency)信號通路,它們介導合成不同的抗菌肽。其中,Toll 信號通路不僅能夠介導機體對入侵的病原真菌和革蘭氏陽性細菌的感染,快速地產生相應的抗菌肽[10],同時它在細胞免疫應答中也起著關鍵的作用[11]。Toll 信號通路的激活包括細菌的識別、配體Sp?etzle 的活化、Toll 受體的結合與激活,以及對下游作用基因的轉錄,能夠快速調節抗菌肽的合成及分泌[12]。
3 Toll 受體的結構與發現
Toll 受體是一類存在已久的受體蛋白,屬于I 型跨膜糖蛋白,其胞外段富含亮氨酸重復序列(leucine-rich repeats,LRR),能夠參與配體識別;胞內段含有保守的TIR 結構域(toll/interleukin-1 receptor domain),能夠與下游分子如髓樣分化因子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88,MyD88)、TIR受體蛋白(toll/interleukin-l receptor domain adapter protein,TIRAP)、β 干擾素TIR 結構域銜接蛋白(TIR-domaincontaining adaptor inducing interferon-β,TRIF)、TRIF 相關接頭分子(trif-related adaptor molecule,TRAM)進行信號轉導,并激活Sp?etzle 蛋白[13]。Toll 受體是在1980年研究黑腹果蠅(Drosophila melanogaster)胚胎發育的過程中被首次發現的一種蛋白[14],最初發現Toll 受體時,人們認為這是一類與發育相關功能的蛋白,而后續研究發現Toll 受體可以識別并激發出免疫和炎癥反應以破壞入侵機體的病原微生物,普遍存在于無脊椎動物和脊椎動物等真核生物中,在無脊椎動物的非特異性免疫和脊椎動物的特異性免疫中起重要作用。1988年,Toll受體被發現是一類跨膜蛋白質,同時也研究了其蛋白的結構[15]。1991年,發現該蛋白細胞外亮氨酸富集重復序列(leucine-rich repeats,LRR)與哺乳動物細胞內Toll-白介素1 受體(interleukin-1 receptor,IL-1R)具有同源性,二者的細胞質部分相似[16],該研究提示了Toll 受體可能與免疫有關。1994年,Nomura 等人首先報道了人類中的Toll 受體[17],然而當時Toll 受體的免疫學功能并沒有被發現,所以人們仍然認為Toll 受體參與了哺乳動物發育的相關調節。1996年,Toll 受體的研究結果發現其在果蠅的非特異性免疫起著重要作用,對不同的微生物如真菌、細菌等能夠誘發相應的免疫效應,從而確立了Toll 受體的免疫學意義[18]。
Toll 受體于昆蟲的非特異性免疫中就如同一個監視器,能夠監視和識別各種不同的病原相關分子模式(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在昆蟲抵御外源入侵機體中起著重要作用[19]。昆蟲Toll 受體的分布會因物種、受體的亞型、發育時期及所處環境條件的不同而有所差異[10]。自1980年在研究果蠅胚胎發育時,首次發現了Toll 受體在果蠅胚胎背腹軸分化形成中起著重要的作用[14],目前,在果蠅中已經發現存在有9 種Toll 受體,依次命名為Toll、Toll2~Toll9。其中果蠅Toll 受體除了在胚胎發育中起著關鍵作用外,同時在非特異性免疫中也具有明確的功能,能夠對革蘭氏陽性細菌和真菌病原體響應[20]。Toll 和Toll7 受體能夠結合多個Sp?etzle 蛋白并激活抗菌肽基因的轉錄[21]。另外在蜜蜂(Apis mellifera)中已經發現存在有5 種Toll 受體,在甲蟲中發現9 種Toll 受體[22],在岡比亞按蚊(Anopheles gambiae)發現 11 種 Toll 受體[23],同時在煙草天蛾(Manduca sexta)、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豌豆蚜(Acyrthosiphon pisum)等昆蟲中都發現了不同的Toll 受體;而在家蠶(Bombyx mori)中已鑒定出14 個Toll 相關的基因[22,24]。
4 家蠶Toll 受體的功能研究
2002年家蠶首個Toll 基因被克隆出來[25],近年來在家蠶中鑒定出14 個Toll 相關的受體,分別命名為BmToll3、BmToll6、BmToll7、BmToll8、BmToll9、BmToll10 和BmToll12,其中BmToll3 受體中包含BmToll3-1、BmToll3-2 及BmToll3-3 受體,BmToll7 中同樣包含BmToll7-1、BmToll7-2 和BmToll7-3 受體,而BmToll9 受體又存在著BmToll9-1 受體與BmToll9-2 受體,BmToll10 受體中存在著BmToll10 -1、BmToll10 -2 及BmToll10 -3[24]。家蠶的Toll受體分布在不同的染色體中,BmToll9 定位在3 號染色體上,BmToll7-3 定位在6 號染色體上,BmToll3-1定位在12號染色體上,BmToll3-2 和BmToll3-3 定位在14 號染色體上,其余8 個家蠶Toll 受體基因在23 號染色體上形成串聯重復群。而針對家蠶的Toll 相關受體的系統進化樹分析得出,BmToll7 的3 個受體具有更近的進化關系,而BmToll3-2 和BmToll3-3 具有同一祖先,BmToll10 -1 和BmToll12 具有較近的進化關系。大部分Toll 受體都在進化樹上處于接近的位置,而唯有BmToll9 是個例外,與其他Toll 受體的進化距離都較遠[22]。家蠶Toll 基因的時空表達譜表明BmToll7-2、BmToll7-3 和BmToll3-3 在卵巢和中腸都富集表達,BmToll10 -1、BmToll10 -2 和BmToll10 -3 在精巢特異表達,表明這些Toll 基因可能與性別特異性的生物學功能相關。BmToll9-1 主要在中腸中表達[26],BmToll9-2 基因在家蠶幼蟲不同齡期中不同組織的表達各異,其中4 齡期在脂肪體、馬氏管、神經和絲腺中表達較明顯,而5 齡期則在脂肪體、中腸、馬氏管和神經中表達較為明顯[27]。
目前研究表明,家蠶Toll 信號通路能夠被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和白僵菌(Beauveria)誘導激活[28-29]。而家蠶Toll基因在不同的外源入侵物的感染實驗發現,BmToll7-2 在被脂多糖誘導后,大部分組織的表達量均下調[25],BmToll7-3在被真菌和大腸桿菌誘導下表達量也下調,而BmToll3-2、BmToll3-3、BmToll10 -2 和BmToll10 -3 則在真菌和大腸桿菌誘導下表達量顯著上調,表明這類基因可能參與了家蠶的免疫調節過程,而BmToll7-2 和BmToll3-3 則在大腸桿菌誘導下表達量明顯下調[22]。對家蠶幼蟲進行白僵菌感染實驗發現,不同的Toll 受體在家蠶受到白僵菌感染后的表達模式也存在顯著的差異,BmToll3-2、BmToll6、BmToll7-1 和BmToll9 基因在不同的注射時間顯著上調,而BmToll10 -2與BmToll10 -3 基因則出現下調現象[28]。目前針對家蠶Toll9受體的研究報道較為詳細,已發現對家蠶幼蟲注射雙鏈RNA 和脂多糖后,能明顯抑制BmToll9-1 基因在中腸中表達,且BmToll9-1 受體也被鑒定為具有先天性免疫以及調節RNA 干擾機制基因表達的功能[30]。而當家蠶被大腸桿菌和白僵菌感染后,其腸道中BmToll9-1基因的表達水平顯著提高[26]。關于家蠶BmToll9-2 基因的研究表明,對家蠶4 齡和5 齡幼蟲注射脂多糖和大腸桿菌可誘導BmToll9-2 基因的表達[27]。對家蠶5 齡幼蟲注射肽聚糖和金黃色葡萄球菌能使BmToll9-2 基因表達上調[31],推測家蠶Toll9 受體在受到外源入侵。由此可以看出,并非所有家蠶Toll受體在受到外源入侵時都做出相同的響應,不同的Toll受體在受到不同的外源物入侵時存在著明顯的表達差異,這可能是由于家蠶不同的Toll 受體在免疫通路上發揮著不同的作用或識別的受體不同所導致的,然而每種Toll受體的具體功能仍需進一步探究。
5 小結
家蠶是我國歷史悠久的經濟昆蟲,同時也是鱗翅目昆蟲中的模式生物。近年來我國桑蠶業的發展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本土桑蠶病害對蠶繭質量的影響較大,2014年中國絲綢商品出口總額僅為 30.79 億美元,同比下降了12.19%[32],隨后幾年出口總額整體呈下降趨勢,到2019年中國絲綢商品出口額為21.69 億美元,比2018年出口額29.58 億美元同比下滑了26.66%[33]。因此,提高家蠶對病害的抵抗力不僅對桑蠶相關產業經濟具有重要意義,更有利于我國實現蠶絲業的可持續發展。
Toll 受體作為免疫通路上的重要成員,具有配體識別并產生免疫和炎癥反應以破壞入侵機體的病原微生物的功能。Toll 受體在Toll 信號傳導的過程中起著連接細胞內外的作用,其中涉及各種不同的信號轉導因子[34],而不同的信號轉導因子在家蠶免疫過程中可能存在不同的調節模式[28]。Toll 信號通路中存在著復雜的調控機制,而Toll 受體在其中發揮的具體作用仍需進一步探究。近年來關于家蠶Toll 受體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分析其時空表達譜,以及對各種外源病原體的入侵進行探究,然而并沒有得到確切的功能相關報道。而從果蠅的相關報道中發現,其Toll 受體除了在胚胎發育中起著關鍵作用外,同時在非特異性免疫中也具有明確的功能,能夠對革蘭氏陽性細菌和真菌病原體響應[20]。果蠅Toll9 受體也在2001年被鑒定出能夠對真菌產生免疫反應[35],而在2011年有研究表明對果蠅的Toll9 受體進行缺失突變改造后,果蠅胚胎的致死率增高,果蠅發育成蟲出現延遲以及壽命縮短的現象。因此,關于家蠶Toll 受體的相關功能,仍需進一步深入研究,明確家蠶Toll 信號通路具體的分子機制,對家蠶的免疫乃至防治桑蠶病害具有一定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