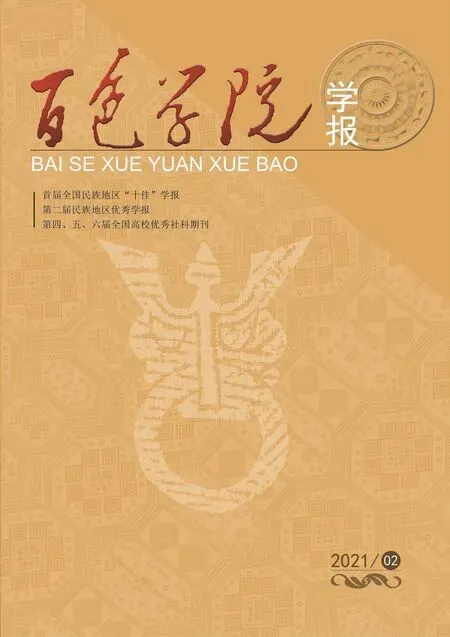文化自覺視域中的《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的新求證》
張艷蕊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河南鄭州 450046)
葉舒憲新著《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的新求證》①葉舒憲:《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的新求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下文簡稱《玄玉時代》),是“中華創世神話考古專題·玉成中國叢書”中的一部,在叢書第一輯七部整體講述玉文化催生華夏文明具體歷程的研究大格局中,這部講述中原玉文化發生史的《玄玉時代》排序在首位,凸顯出中原文明在整體的華夏文明發生中的關鍵性地位。導論以“創世——宇宙秩序與顯圣物”點題,將《山海經》《越絕書》《竹書紀年》等古文獻中關于黃帝食玉、種玉等長久以來被視為神話的內容,落實到21 世紀新發現的中原考古文物玉禮器,將玉禮器視為華夏先民崇奉的顯圣物,揭示物的背后潛蘊著的先民們宇宙秩序觀念和生命觀念。第一章“華夏文明起源之謎”,聚焦近代以來有關“華夏文明五千年說”的虛實爭論,確認迄今的知識條件下能夠證明什么,不能證明什么。從而找出足以確證五千年社會歷史發展脈絡的符號物——玉禮器系統,有效地走出文字牢房,超越囿于文獻的文化小傳統探究文明起源的局限,強調應從考古挖掘的史前時代所特有的“神圣遺留物”入手,解讀這些象征符號的神話觀念與宗教信仰,找到對華夏文明產生至關重要的文化基因。第二章“玄玉時代說”,是大膽提出新理論命題的部分。闡明了“玄玉時代”的命名依據、年代范圍(距今5500 年至4000 年)和空間覆蓋范圍。強調這一時代是說明中國文明國家起源的可實證的新線索。第三章“玄玉時代開啟”,以河南靈寶西坡仰韶文化墓葬玉器的用玉材質、玉器品種,從“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視角,打通宗教學、神話學等學科知識,解析靈寶西坡大墓結構的模式化編碼(玄黃二元編碼),超越學界關于華夏文明分別發源于神權崇拜與世俗王權兩種不同文化模式的現有觀點。第四章聚焦黃河上游地區史前玄玉分布,兼及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齊家文化的承繼關系,說明中原用玉取材的來源地、中原玉文化與黃河及其支流的漕運關系。第五章具體考察中原以北和中原以西三個龍山文化遺址的用玉情況,以距今4000 年前后玄玉所占比例日漸衰減的情況,說明玄玉時代的結束。第六章對玄玉的源流做全面的考證,勾勒出西玉東輸運動的六個階段,完成一部長達5000多年的玄玉資源更新換代史。
《玄玉時代》是作者在學術研究領域創建中國話語的一次成功嘗試。無論是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結論,都體現了一位立足時代前沿、有強烈使命感的學人敏銳的文化自覺意識,對于中原文化的尋根溯源,對啟迪本土文化自覺,有著重要的推進意義和引領作用。
一、研究對象:華夏文明溯源的中原定位
自1921 年瑞典學者安特生在河南澠池縣發現中原仰韶文化以來,迄今已百年。百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在以河南為主的黃河中游地帶累計發現多達5000 多處仰韶文化遺址。2005 年和2006 年發掘、清理出的西坡墓地入選2006 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一個世紀以來仰韶文化最重要的發現之一。《玄玉時代》主要以21 世紀考古新發現的河南靈寶西坡大墓(屬于仰韶文化廟底溝期)及其玄玉禮器為研究對象,將出現這類玉禮器的時代命名為史前的“玄玉時代”。
《玄玉時代》通過解讀玄玉這種前文字時代的重要文化符號,重建史前期仰韶人生活于其間的文化文本,追尋史前玉石神話信仰在中原地區乃至整個華夏文明創生期的核心作用。葉舒憲強調,提出玄玉時代的意義在于,這是對中原地區玉文化發展情況的考察,而中原文化與中國文明國家的起源緊密相關。沿著玄玉時代的脈絡,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華夏先民如何由史前期對玄玉的崇拜出發,發展到夏商周三代王權國家對玉禮器資源的渴望與尋找,進而依次發現西部地區特產的優質玉料,自西周中期開始形成中原人對“昆山之玉”的無限神往,最終“昆山之玉”中的羊脂白玉成為華夏文明國家統治者們夢寐以求的神圣信物,羊脂白玉制成的玉璽升格為帝國王權“受命于天”的神圣物證。從此,在漫長的中國大一統王權時代,手持玉璽的歷代君主成為天命所歸的統治者,一個又一個朝代以奉天承運的名義更迭相續。“只有中原地區的玉文化發展本身,才能有效擔當一個至關重要的任務,那就是說明中國文明國家起源的可實證線索。”①葉舒憲:《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的新求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62 頁。
《玄玉時代》主要圍繞河南靈寶西坡的墓葬群用玉材料、禮器品種等展開深入分析和追蹤探索,其范圍從河南靈寶擴展到中原與西部地區相連的周邊地域,進而從點到線、從線到面,經過廣泛排查和對比,獲得規律性認識。從靈寶西坡到石峁遺址發現的玄玉禮器,其年代間隔為距今5300 年至4000 年,對應于傳說中的黃帝時代,這時代正是中原地區文明國家孕育和奠基的時期,因此,玄玉時代說的提出,給華夏文明起源的百年研究史,提出一種全新的理論命題和解決方案,其研究方式和空間地域系統采樣的求證范式,都具有空前的意義。
鄭州商城、安陽殷墟以及華夏第一王都——偃師二里頭考古遺址,三者的歷史時限為距今3600 年至3200 之間,以此說明中原文明國家的玉禮器源流,顯然是有所欠缺的。《玄玉時代》立足于仰韶文化而提出的新的史前時代劃分方法,將中原史前文化向文明演進的標志性禮器的完整傳承脈絡,向前推進了1000 多年,即上推到距今5300 至5500 年。從靈寶西坡仰韶文化廟底溝期批量出現的玉鉞禮器,到二里頭出土的象征王權之玉鉞,其年代相隔長達1700 年。這1700 年間中原玉禮器數量不斷增加、材質逐漸多樣化,玉禮器體系規模不斷擴大,推動玉禮器變化史的根本力量是史前先民虔信的神話信仰觀念,即“拜物教的信仰和以玉為神為圣為永生不死的神話觀念體系”。②葉舒憲:《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的新求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67 頁。這也正是突破文化小傳統之后,從大傳統中發掘到的華夏文明延續五千載不曾中斷的文化基因。
《玄玉時代》指出,先秦禮書中有關“夏人尚黑”的說法、《山海經》中有關黃帝播種“玄玉”的神幻敘事,乃至先秦諸子中的墨家得名,道家尚玄,皆可以歸因為中原地區以甲骨文、金文為主的早期漢字系統對無文字時代的玄玉時代的遙遠記憶,而先于中原地區的南方與北方地區的史前玉文化,由于沒有當地文字系統的及時承接,就幾乎完全淹沒在歷史地表之下了。這樣對照之下,更加凸顯“玄玉時代”對于開啟中原玉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
二、研究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玉成中國”叢書旨在借助考古發現的玉禮器,解讀華夏先民們在無文字時代通過作為象征符號的玉禮器所表達的神話觀念與信仰特點,找尋并重建文化大傳統時期華夏文明的創生過程。為此,葉先生組織了多達15 次名為玉帛之路/玉石之路的田野考察,走遍了中國西部各省區所有主要玉石資源產地,還包括中原與西部各省史前玉器出土之地,將玉礦資源地的玉料標本與考古出土的史前玉禮器標本相互對照,勾勒出玉石產地與玉器加工和消費地之間的傳播輸送路線圖,并考察不同時期玉石開采、運輸與玉器使用的發展變化情況。《玄玉時代》作為“玉成中國”叢書的開山之作,是“玉成中國”研究宗旨、研究方法的標準樣本。其研究方法的突出特色是跨學科性,這種方法突破傳統的從書本到書本的紙上談兵式研究,充分利用系列實物多地點舉證的方式,綜合采用文化人類學田野考察和考古學文物測年數據,大量借用藝術學、宗教學、神話學等領域的新知識,著力創建集傳世文獻、出土文獻、活態文化、出土文物“四重證據法”為一體的中國話語。
《玄玉時代》在研究方法上突出文學人類學派獨家倡導的四重證據法,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為第一重、第二重證據,民族學和民俗學研究領域內的活態文化傳承作為第三重證據,出土的遺址和文物則為第四重證據。文中借用的文獻涉及中外多個時代、多種學科,既有傳世文獻也有出土文獻,顯示了作者廣闊的學術視野與深厚的學術功底,除了《山海經》《淮南子》《越絕書》《周易》《爾雅》《史記》《漢書》等中國古典文獻,還有弗雷澤的《金枝》、金巴塔絲的《活著的女神》、伊利亞德的《宗教思想史》、利普斯的《事物的起源》、肯·達柯的《理論考古學》、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以及古埃及的《金字塔》《亡靈書》等。臺灣世居排灣族對琉璃珠的崇奉和云南白族的神話等,各種民間活態文化是文中對先民崇奉玉石的語境化還原與激活的嘗試。在四重證據法的運用中,《玄玉時代》更突顯第四重證據的表征作用。書中用大量圖片展示出土玉器實物,用葉先生在“中華創世神話考古專題·玉成中國”總序中的話說,是“讓史前中國所特有和獨有的一系列玉器文物發出聲音,讓玉禮器自己講述出的華夏文明的創世記”①葉舒憲:《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的新求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3 頁。。書中展示的各類玉器圖片主要根據第十一次玉帛之路考察(2017 年5 月隴東陜北道)中對中原仰韶文化廟底溝期玉禮器的認識線索,是作者走訪各地大中小型博物院館乃至私人博物館和研究院、博物院館、文管所的文物庫房,查閱大量玉器考古資料以及實地考察考古工地現場所得,在大量實物觀察、圖片對比基礎上,重新梳理出土文物,為以往的博物館陳列知識尚語焉不詳的史前期中原地區蛇紋石玉禮器正名,賦予其“中原文明第一玉”的應有地位。
對考古發現的借用是《玄玉時代》的重要特色。該書充分挖掘出土文物這類第四重證據的強大解碼功能和文化闡釋力,使得原本停留在文獻文字學方面即文化小傳統方面的資料,超越了文獻記載,上溯至史前大傳統的文化基因。正如葉舒憲所說:“一個古老文明中的最高價值物認定,絕非一朝一夕或哪些個人所能夠完成。史前文化大傳統時期,才是孕育此類圣物崇拜的漫長積淀過程。”②葉舒憲:《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的新求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97 頁。“文化文本的歷史性生成,貫穿于大傳統到小傳統的全過程。”③葉舒憲,等:《文化符號學:大小傳統新視野》,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25 頁。自仰韶文化發現百年以來,隨著考古工作者在黃河中游地帶累計發現多達5000 多處的仰韶文化遺址,今人對中原文化的認知可前推至5000 年前,遠遠超過將堯視為最早圣王的孔子、將黃帝演繹為捕風捉影傳說的司馬遷以及近代以來的康有為、梁啟超等學人。《玄玉時代》應時代需求,將以往僅僅停留于專業考古領域的知識引入文學文化研究,徹底改變了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認知缺乏有力佐證的窘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是對文學人類學以中國話語闡釋玉文化對建構華夏文明、民族精神的生動寫照。學術領域的跨學科組合與互動,使得“務虛”的文學研究有了“實在”的立足點,深入到文學文化文本的根源,挖掘出驅動各類文學文化現象產生的文化基因。這種跨學科方法汲取文學研究強調理論建構、整體框架、宏大視野的學術優長,將考古發現視為某種象征符號,致力于尋找“物”背后的觀念,讓文物“活”起來。這種方法的推廣、運用,對于考古學、歷史學等學科來說又何嘗不是一件幸事!
三、研究結論:物證優先,實證五千年
葉先生所追求的學術目標十分明確:那就是要彌補我國文科學術的最大短缺,不遺余力地創建中國版的文化理論,以文化文本論為核心內容。文學人類學派的中國話語的建構實踐,已經堅持30 多年,四重證據法的研究實踐充分整合考古學、人類學、比較文學、神話學、民俗學和宗教學的知識與方法,并在近年形成“物證優先”指導原則,以多學科視野的文明起源攻堅研究為基石,從中提煉和總結能夠為新文科建設提供系統解決方案的、可操作的研究經驗和理論體系。這正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文科學界所期盼已久的。
“玄玉時代”特別看重從實證出發的研究,從靈寶西坡仰韶文化大墓出土的、中原最早的一批玉禮器——玄玉制成的玉鉞、玉環等,鏈接周邊各地的同類器物,從而得出結論:歷史上存在一個距今5000年以上的玄玉時代。為落實這一論點,多年來相繼考察黃河上游及其各大支流地區,中原以北和以西的史前用玉情況,并勾勒出玄玉材料來源的六個階段,為玄玉時代的發生、發展及結束提供準確翔實的周邊實證。
華夏文明為何崇奉玉石,《玄玉時代》認為玉石崇拜最根本的原因是出自一種堅定的信念:相信玉石承載著神圣的能量,代表天、天神或天意,因而足以通靈通神、驅邪逐疫、護身保家、禳災祈福、拒敵避害。玉因此成為本國祭祀即“禮”的核心物質要素。①葉舒憲:《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的新求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35 頁。《山海經》這部上古之書,之所以有近200 處關于玉石產地的記載,并非好事文人的虛構創作,而是在玉石神話觀念驅動下的特色行為方式使然。史前初民對不同玉石種類的關注和搜尋,其背后正是對玉石神話的堅定信念。至于史前仰韶人為何獨尊玄玉這一問題,《玄玉時代》也作了解答,一方面是由于中原地帶缺乏其他更好的玉石資源,另一方面也是“天玄地黃”上古觀念的作用使然。
5000 年前采用蛇紋石玉料的玉鉞,作為隨葬品的靈寶西坡大墓靠近黃河,有同樣用玉情況的陜西楊官寨遺址位于黃河支流渭河與涇河邊上,4000 年前有大量玉器隨葬品的清涼寺遺址位于黃河北側附近,同一時期的石峁古城與陶寺古城也位于黃河支流邊上。通過對史前文化遺址的實地探查所勾勒出的這些事實,自然導向一個結論:黃河作為中華文明搖籃的說法,是否僅僅指向其作為農業灌溉的功能?是否還應指向黃河及其支流作為玉料漕運的史前文化大通道作用?《玄玉時代》關于黃河作為文明搖籃的新說,是非同凡響的,也值得關注和思考。
《玄玉時代》結論的提出,不僅有由點到線再到面的實物譜系驗證,而且有對中國古代文獻的追根溯源、對中外文獻的對比與篩選。文中涉及的各類中外文獻和考古報告達上百部(篇),涉及學科眾多。得益于這種宏大的學術視野、深厚的理論背景,其實證性的結論還獲得理論建構的有利契機,具有從整體上宏觀把握文明源流的大格局與大氣派。
此外,《玄玉時代》立論時體現出“實證優先,追根溯源”的原則,對學界已有的權威觀點也保持著清醒,不盲從也不隨意附和。嚴格遵循實事求是原則,從實證材料中謀求見解上的推陳出新。學界因仰韶文化遺址的面貌相對于5000 年前的北方紅山文化和南方良渚文化,顯得十分簡陋樸素,既沒有大量精雕細刻的玉器群,也沒有規模宏大的廟宇和建筑,故此一面倒地認為中國文明起源有兩種不同模式,簡樸節約的中原仰韶文化屬于催生出夏商周王權國家的世俗王權模式,而南方文明則屬于神權信仰模式。葉舒憲認為,不能僅因為中原仰韶文化遺址中玉器少而得出其屬于勤儉節約的世俗王權文明、沒有神話信仰觀念的結論。通過對墓葬物敘事功能的深入解讀,葉舒憲發現,仰韶文化時期的墓葬、死者頭部和隨葬玉器等大都朝向西方,隨葬玉器多被放置于死者頭部旁,以灶釜組合為主的隨葬陶器多在死者腳下,諸如此類模式化的設計,顯然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傳達出中原先民用于祝福死者、撫慰生者的某種宗教神話和來生信仰。對玉石礦產資源地的田野考察進一步證明,仰韶文化廟底溝期大墓玉器隨葬品數量稀少、品種單一,極有可能是限于當地缺乏優質玉料資源的現實條件,并不能證明是當時出于世俗王權勤儉節約的考慮。再聯系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克里特文明、特洛伊文明等世界各文明古國都植根于神權信仰的比較神話學知識,更不能得出中國文明起源于兩種不同模式的認知。這種有理有據的質詢,為學術領域的推陳出新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四、文化自覺的學術體現
“文化自覺”是由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提出的,這一說法超越了費先生《鄉土中國》《江村經濟》強調文化要素制約個人的局限,看到個人對文化的能動作用。費孝通提出:“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①費孝通:《從實求知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398-399 頁。文化自覺理念體現了對自我文化歷史傳統的重視,其任務首先是要對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只有充分了解、認識自我文化,才能看到他者文化的長處和劣勢,“美人之美”,達到文化自覺的理想狀態,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②費孝通:《從實求知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399 頁。自費孝通先生1997 年首次提出“文化自覺”說來,迄今已20 余載。作為專業研究者,如何將文化自覺的精神體現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呢?
葉舒憲《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的新求證》通過對文物的考證和西玉東輸地理路徑的勾勒,讓我們認識到,中原與黃河沿岸地區對華夏文明的搖籃意義,原來并不僅是農耕文化的經濟基礎奠基作用方面,還在于其對華夏文明發生期的“玉成中國”信念的建構方面。沒有史前漕運渠道和西玉東輸運動,中原地區的玉文化就沒有發生的物質條件。這部書既是對華夏文明創生的新思考結晶,也是作者自己通過學術研究達成文化自覺的生動案例。
我國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問鼎中原之類的流行說法。當代的河南省領導也曾有一句名言,叫作“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國史”。《玄玉時代》聚焦中原玉文化發生發展這一特殊視角,重建出一個大大先于甲骨文漢字而存在的,總共延續1000 多年的“玄玉時代”。這一學說所蘊含的文化創新意義,不論對河南的地域文化還是對華夏文明整體而言,都是不言而喻的。本土文化自覺的啟迪之門已經打開,以玉為神圣并信奉君子如玉的民族精神,千百年來傳承不息。從玉成中原到玉成中國的大思路,《玄玉時代》給出令人耳目一心的理論建構。就華夏文明起源這個老話題而言,我們可以不再停留于人云亦云、自說自話的舊局面,重新把握本土文化再認識和再自覺的學術機緣。文化不僅是龍門石窟、白馬寺、甲骨文等物的存在,更在于對文物的深入研究與解讀。傳承文化,也不僅是對文物象征符號外在物象浮光掠影的介紹,更在于深入領會其對史前先民精神世界的符號塑造作用。《玄玉時代》對中原文化根源和華夏文明創生過程的細致挖掘,無論是對學界還是普通大眾,都有很切實的啟發意義。
飲水思源,培根固本。華夏文明尋根的思考像一場接力賽,剛剛問世的《玄玉時代》一書無疑屬于這場接力賽中的新時代領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