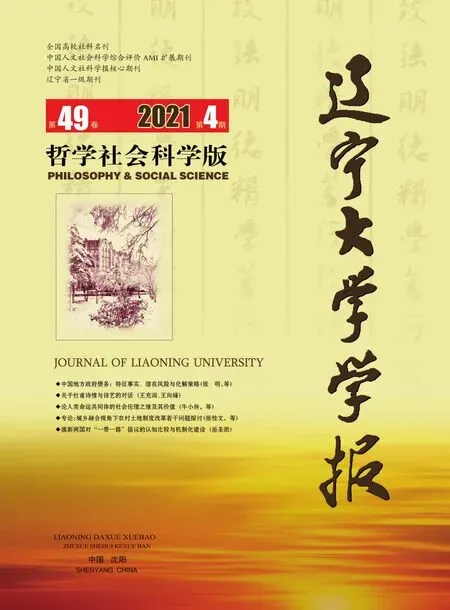馬克思“協作”概念之形成
——兼論其批判性維度
潘沈陽 夏 瑩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北京 100084)
一、前 言
今天工人的勞動組織形式已完全有別于馬克思所處的大工業時代,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與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他們“帝國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同世界》(Commonwealth)中指出:“馬克思認為,資本家確保協作,就像戰場上的將軍或者樂隊的指揮一樣。但是,在生命政治生產中,資本并不決定協作的組織,起碼不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①〔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112頁。也就是說,在哈特與奈格里看來,作為今天勞動組織形式之主流的生命政治生產(或非物質勞動)②在哈特與奈格里兩人這里,“生命政治生產”與“非物質勞動”這兩個概念是同義語。參見〔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第6頁。過程中的協作已經脫離了資本,于是在今天“與其說是資本提供協作,不如說是剝奪協作”③〔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12頁。(黑體為原文所加,下不贅述),而正是在這種資本與協作的裂隙之間爆發出革命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即在資本“剝奪”協作之前自行選擇“出走”(exodus),出走的主體被他們稱為“諸眾”(Multitude),而“這個出走的籌劃就是當下階級斗爭所采取的的首要形式”。①〔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30頁。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認為哈特與奈格里在《大同世界》中的表達近乎陷入在非物質抽象領域中,從而缺乏具體的形式以及對物質方面的討論,在這個“作品中要少一點斯賓諾莎,多一點馬克思”。②〔英〕大衛·哈維、王行坤:《解釋世界還是改造世界——評哈特、奈格里的〈大同世界〉》,《上海文化》2016年第2期。哈維的判斷是合理的,事實上,正是因為哈特與奈格里在“協作”概念上遠離了馬克思,才使得他們對于協作本身作出一種“中性”的判定,從而對革命報以樂觀的預期。但與他們判定截然相反的是,馬克思的“協作”概念是“非中立”從而具有深厚的批判性內涵的。
馬克思本人在事實上也確實對“協作”(Kooperation; Coopérative; Co-operation)概念予以了充分的重視,甚至“分工”(Teilung der Arbeit; Division du Travail; Division of Labour)這一經典概念在馬克思晚期視域里都不過是“協作”的一種獨特形式:“分工以協作為前提或者只是協作的一種特殊形式。”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9頁。“分工是一種特殊的、有專業劃分的、進一步發展的協作形式……”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第301頁。并且在馬克思對“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美好設想中也有協作的一席之地:“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4頁。遺憾的是,目前學界對于馬克思的“協作”概念及其思想鮮有專門性的研究,由此帶來兩方面的困境:一是,在勞動組織形式已急劇凸顯協作——而非凸顯固定性的分工——特征的今天,缺乏一個協作維度的馬克思主義考察視角,從而也缺乏同當代其他思想家在該問題下的討論契機;二是,馬克思的協作-分工理論本就包含協作與分工這兩個方面,“協作”概念及其理論的失語也是馬克思協作-分工理論研究本身的一大空白,若對馬克思“協作”概念不予以澄明,“分工”這一經典概念——作為協作的一種特殊形式——也是無法得到圓滿闡釋的。
而在回應當代問題以及填補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空白之前,首先需要對馬克思“協作”概念的形成予以考察與說明,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充分把握馬克思本人在引入“協作”概念時的現實背景與問題意識,從而揭示“協作”概念的批判性內涵,為之后同馬克思協作理論相關的研究工作打下一個堅實的地基。
二、“協作”概念的前身:共同活動方式
部分學者將《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共同活動方式”(Weise des Zusammenwirken)或“共同活動”(Zusammenwirken)概念視作馬克思晚期“協作”概念的同義語:例如孫淑橋、杜昌建就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共同活動方式’即是分工協作的方式……”⑥孫淑橋、杜昌建:《馬克思論“共同活動方式”的生產力意義——馬克思社會公共性思想初探》,《湖北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楊喬喻在對馬克思生產力概念進行分析時也強調:“馬克思的共同活動實際上是分工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協作。”⑦楊喬喻:《探尋馬克思生產力概念生成的原初語境》,《哲學研究》2013年第5期。姜海波也認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共同活動方式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對于分工、協作和管理等生產過程中的要素的抽象。⑧參見姜海波:《青年馬克思的生產力概念》,博士學位論文,黑龍江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2011 年,第104頁。由于鮮有針對馬克思協作思想的專門研究,這種將“共同活動方式”與“協作”近乎相等同的判斷也只是散見于討論其他問題的文獻,并沒有被單獨討論過。但該判斷其實面臨一個顯而易見的困境:如果“協作”和“共同活動方式”的內涵是一致的,那么為何馬克思在晚期沒有繼續沿用“共同活動方式”這一說法,而采用“協作”呢?不過,我們也不能因此將這兩個概念判斷為是彼此之間毫無關聯的,因為它們確實存在內涵上的一致性。對此,筆者認為如下解釋具備一定的合理性:“共同活動方式”可以被視作“協作”的前身,它們在內涵上具備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共同活動方式”這一概念外殼并不能充分表達“協作”的內涵,由此馬克思在晚期轉用了“協作”而非“共同活動方式”。
(一)“共同活動方式”與“協作”的一致性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共同活動”指的是同“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緊密相連的、許多個人之間的活動,它作為“生命的生產”——“無論是通過勞動而生產自己的生命,還是通過生育而生產他人的生命”——的“社會關系”這一面相而存在。①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頁。由此,“共同活動”一方面是指向人與人之間聯系的關系態存在,這是其普遍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是具備歷史性與物質性的,這是其特殊性的一面。而所謂“共同活動方式”則是這種關系態在具體的、一定的歷史語境下的表達形式。馬克思的“共同活動方式”與“協作”的一致性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首先,“共同活動方式”與“協作”都能創造出,或者本身就是一種生產力。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談道:“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2-533頁。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378頁。生產力在這里充當了理解“共同活動方式”與“協作”的關鍵媒介,它在被這兩個概念賦予關系性、整體性的同時,反向也強調了“共同活動方式”與“協作”本身的物質性與客觀性。馬克思對生產力的這種判定顛覆了以往我們對于生產力構成的一種僵化理解,即將生產力理解為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者這三種實體性要素的機械結合,但從一開始馬克思就賦予了生產力一個關系性、整體性的考察視角。
其次,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共同活動方式”與“協作”對于工人而言都表現為異質性甚至是支配性的存在,但它們在本質上都是出于人自身的力量。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指認由于共同活動受到了分工的制約,“共同活動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這種社會力量在這些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身聯合的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頁。《資本論》第一卷中也有類似的表述:“雇傭工人的協作只是資本同時使用他們的結果。……因此,他們的勞動的聯系,……作為他人意志——他們的活動必須服從這個意志的目的——的權力,而和他們相對立。”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385頁。由此,“共同活動方式”與“協作”發揮出的社會性力量在雇傭工人看來都是資本的力量而非自己的力量。
最后,在馬克思對于未來理想社會的構想中,“共同活動方式”與“協作”在工人那里從自發轉為自覺,并且從中生成的社會性力量為無產階級所掌握。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當中,“共同活動方式”在自然發展出其世界歷史性時,由于共產主義革命的爆發,其內含的社會性力量將被創造出他們的人們重新占有。同時“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即在個人的獨創的和自由的發展不再是一句空話的唯一的社會中,這種發展正是取決于個人間的關系,而這種個人間的聯系則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面,即經濟前提,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必要的團結一致以及在現有生產力基礎上的個人的共同活動方式。”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6頁。《資本論》第一卷“所謂原始積累”一章的最后,馬克思談到資本主義生產由于其自身邏輯的矛盾性將會對自身造成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874頁。另外,在《資本論》第一卷的1872年德文版中馬克思對協作還有“自由工人的”這一限定,也就是說這種協作是“自由工人的協作”(der Kooperation freier Arbeiter),②Marx-Engels-Gesamtausgabe-2 II/6,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S. 683.是自覺而非自然的。在這個意義上,自覺的“共同活動方式”與“協作”同樣都是馬克思對未來理想社會構想不可或缺的一環。
(二)“共同活動方式”何以無法承載“協作”的內涵
然而盡管“共同活動方式”或“共同活動”③在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語境下,一定歷史條件、一定生產條件下的共同活動總是有一定的方式的,所以“共同活動方式”和“共同活動”沒有太大的差別。與“協作”擁有上述三個方面的一致性,馬克思最終選擇的概念外殼是“協作”而不是“共同活動方式”或“共同活動”,這意味著后者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從而并不能充分表達馬克思在晚期所想要表達的內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說馬克思最終選擇了Kooperation(協作)這一概念外殼,并不意味著他在之后從未使用過Zusammenwirken(共同活動)這個詞,而是意味著馬克思讓Kooperation 承載了更加豐富的、他本人所想表達的內涵。事實上馬克思在晚期依舊使用Zusammenwirken 這個詞,只是其不再具備理論語境下的概念豐富性,回歸其最原始的意義:一起工作,一塊兒干活。④這一點從Kooperation與Zusammenwirken共同出場的語段中就可見一斑:“這種生產力是由協作(Kooperation)本身產生的。勞動者在有計劃地同別人共同工作(Zusammenwirken)中,擺脫了他的個人局限,并發揮出他的種屬能力。既然勞動者不在一起就不能直接地共同工作(zusammenwirken),既然勞動者集結在一定的空間是他們進行協作(Kooperation)的條件……”。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382頁。在這里Zusammenwirken 被譯作“共同工作”,只是單純指代一堆人在一起共同勞動這種情況,并沒有任何特殊性。反倒是“協作”,作為一種具體的、有計劃的共同工作/活動的形式而出場。所以在《資本論》里,Zusammenwirken 有時也被譯作“共同勞動”:“……在同一些手工工場內共同勞動(Zusammenwirken)……”。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 卷),第394 頁。其動詞形式有時又被譯作“擠在一起干活”:“‘一走進有30 到40 個機器工人擠在一起干活(zusammenwirken)的低矮工廠……’”。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 卷),第544 頁。這足見其已經失去了更加豐富的理論色彩。
而Zusammenwirken 最終退出理論舞臺主要在于:Zusammenwirken 這個詞帶有濃厚的莫澤斯·赫斯(Moses Hess)的底色,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當中使用Zusammenwirken 時所表達的理論內涵早已超出了赫斯的理論高度,由此就產生了這個概念本身蘊含的理論色彩與馬克思的理論指向存在錯位這一矛盾。
“共同活動”(Zusammenwirken)⑤廣松涉將其翻譯為“協動”。是赫斯《論貨幣的本質》(über das Geldwesen)一書中重要的概念,而《論貨幣的本質》則對馬克思產生過積極的影響,在1844 年之前,赫斯在理論上可謂是馬克思的先行者。共同活動在赫斯那里是指個體之間的交往關系,被視作人的本質:“個體的生命活動的相互交換、交往,個體力量的互相激發,這種共同活動,是個人的現實的本質(wirkliches Wesen),是他們的現實的能力(wirkliches Verm?gen)”。⑥〔德〕莫澤斯·赫斯:《赫斯精粹》,鄧習譯編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38頁。共同活動保證了個體作為肢體同整個社會身體的關系,也保證了人的現實生活。在赫斯理論框架中的共同活動甚至也能實現生產力:“只有這種共同活動才能實現生產力(Productionskraft),因而是每一個個體的現實的本質。”①〔德〕莫澤斯·赫斯:《赫斯精粹》,第139頁。同時赫斯似乎也意識到這種屬人的共同活動在其所處時代反倒是遠離了人,并且希望在他所設想的理想社會里為人所掌握:“我們需要它們,因為我們還沒有聯合起來,但是我們的力量的聯合或者共同活動就是我們的生活。因此,我們必須在我們之外去尋找我們自己。”②〔德〕莫澤斯·赫斯:《赫斯精粹》,第166頁。即便赫斯在敘述中挪用了經濟學中“交換”(Austausch)、“生產力”等概念,但是其理論基底依舊是濃厚的費爾巴哈人本主義色彩:一方面,赫斯的“共同活動”雖然被其指認為人的本質、人的生活本身,但是對其具體的說明卻流于單純哲學思辨的水平,同具體的、物質的勞動過程無涉;另一方面,“共同活動”作為人的本質已然具有了先驗性,從而缺乏歷史性與生成性,這從赫斯用的“生產力”還是Productionskraft 這一凸顯靜態性的詞中就能看出。在赫斯那里,共同活動不過就是將本就內含于人的生產力給實現了出來,物質性勞動并不起什么重要的作用。
但馬克思則不然,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共同活動方式”或“共同活動”總是同“一定的”(bestimmt)生產方式、“一定的”工業階段條件相聯系,從而與歷史性、物質性生產勞動密切關聯。同時其蘊含的社會力量雖然屬于人,但并不先天地屬于人、內含于人,而是需要個人通過合作經過一系列對象性勞動、物質性實踐之后才能生成以及被占有。所以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二卷《對各式各樣先知所代表的德國社會主義的批判》中就直接指出:“他們始終一貫地把這些一定的個人間的關系變為‘人’的關系,他們把這些一定的個人關于他們自身關系的思想解釋成好像是這些思想是關于‘人’的思想。”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9頁。馬克思在這里戳破了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赫斯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制造的幻象,即把具體的個人之間的關系說成某種非歷史的、本質性的東西,從而完成某種向費爾巴哈式的人本主義的復歸。由此,在這里就存在馬克思本人雖然使用著帶有濃厚赫斯色彩的概念但是同時又對以赫斯為代表的理論觀點不滿的矛盾。于是,馬克思必然需要尋找一個更合適的概念外殼以澄清他的思想,而帶有經濟學底色的“協作”成了其最后的選擇。正是在19 世紀50 年代初,馬克思以一種獨特的方式遭遇了“協作”這一概念。
三、“協作”何以獨特:《倫敦筆記》中殖民地問題研究
1849 年8月,馬克思與恩格斯流亡至倫敦。1850 年6月,馬克思獲得了英國博物館閱覽室的出入證,從此便長時間地在這里研究各類材料,他在1851年6月給約瑟夫·魏德邁(Jose-pheydemeyer)的一封信里談到自己待在英國博物館里的時間大概是從早上9 點到晚上7 點。④參見〔英〕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第4版),王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38、272頁。由此,馬克思在1850 年9月-1853 年8 月度過了一段充分占有各式各樣材料的時間。⑤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1848年和1849年《新萊茵報》以及隨后發生的一些事變,打斷了我的經濟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才能在倫敦重新進行這一工作。英國博物館中堆積著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于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點,最后,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產階級社會看來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我再從頭開始,批判地仔細鉆研新的材料。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似乎完全屬于本題之外的學科,在這方面不得不多少費些時間。”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3-594頁。與此同時,馬克思也留下了大量的筆記與少量手稿,即《倫敦筆記》(Londoner Hefte),其內容覆蓋面非常之廣,近乎涵蓋當時西方社會的全部文化科學。⑥參見張一兵:《回到馬克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頁。
《倫敦筆記》的第14 冊與第21-23 冊是馬克思對殖民地問題相關討論的摘錄性筆記,正是在這里凸顯了“協作”的獨特重要性、形成了馬克思“協作”概念誕生的契機。但這部分筆記卻并沒有得到較多的理論重視。然而,馬克思對殖民地問題的關注緣由以及他所選擇的摘錄材料,都是我們理解馬克思的協作概念及其理論不可或缺的思想背景。
(一)殖民地問題進入馬克思的理論視域
馬克思比較集中地研究殖民地問題是從1851 年開始的,①參見張鐘樸:《馬克思在〈倫敦筆記〉中對殖民地問題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第4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第297頁。而殖民地問題在此時進入馬克思的理論視域并非偶然,其中包含兩個方面的主要原因:
第一,當時資產階級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對殖民地問題的研究是理解該新階段的一個重要視角,殖民地問題已然成為資本主義經濟自我發展需要直面的對象。一方面,在19世紀50年代初期,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行為日益加強,殖民政策問題已是英國議會辯論的焦點。另一方面,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系有了新的發展。1837 年的經濟危機之后,資本過剩、利潤率下降與市場狹小已然成為英國經濟的一個大問題。②參見陳其人:《殖民地的經濟分析史和當代殖民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2頁。在這種情況下,將過剩的資本投入到殖民地(主要是澳大利亞)中去成了英國的選擇。此時資產階級對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關系的理解已不再局限在貿易的維度,同時還有投資這一全新的維度。
只有真正到了工業化程度最高、資本主義關系發展得最透徹的英國,馬克思才直觀地感受到殖民地問題的重要性。1852年8月19日,馬克思給萊比錫出版商亨利希·布羅克豪斯(Heinrich Brockhaus)致信,問他是否需要一篇題為《1830 年至1852 年的英國現代國民經濟學》的評論文獻,殖民地問題就屬于其中的一部分重要內容。③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1頁。可見,正是英國本身所經歷的經濟現實以及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指向使得關注現實的馬克思必然轉向殖民地問題進行專門性研究。
第二,對殖民地問題的研究包含從外部思考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誕生與形成的視角。在西歐內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誕生是一個被田園詩式的神話掩蓋的秘密,但是資產階級自己的殖民理論恰是該秘密的赤裸揭示。1849 年,英國殖民理論家愛德華·吉本·韋克菲爾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在倫敦出版了其《略論殖民藝術》(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在其中他細致地說明了其著名的“系統殖民”(Systematic Colonization)理論。“系統殖民”有別于“自然殖民”,它要求在殖民地人為地制造出工人對資本的從屬關系。馬克思在《倫敦筆記》的第14 冊中就對《略論殖民藝術》一書進行了摘錄,同時還摘錄了韋克菲爾德的“門徒”④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882頁。赫爾曼·梅里韋爾(Herman Merivale)的著作《關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說》(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他們兩人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非自然性:“在人口稠密的殖民地,勞動者雖然是自由的,但自然地依賴資本家;在人口稀少的殖民地,這種自然依賴的缺乏必須通過人為的限制來滿足。”⑤Marx-Engels-Gesamtausgabe-2 IV/9, Berlin: Dietz Verlag, 1991, S. 481.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殖民化不是發生在某個地方,而是在發生在任何可能發現資本的地方:它是系統的,其系統性質對于理解資本的野蠻性至關重要。⑥參見Mark Neocleous,“International law as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r, the secret of systematic colon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4, no.4(December 2012), pp.941-962.
事實上,馬克思本人在19世紀50年代前就對于資本關系的人為構造有所自覺:“資產階級……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36頁。但那時的馬克思對此的理解還沒有涉及具體的形成機制,有的僅是一種寬泛的判斷、口號式的宣言。但在19 世紀50 年代初,對于已經擁有相似問題域的馬克思來說,英國博物館閱覽室充足的文獻材料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深深地吸引了他,對殖民地問題及其理論的研究就成為其本身理論體系的一種必要的完善。
綜上,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現實與馬克思本人的理論興趣共同促成了他在《倫敦筆記》時期對于殖民地問題的關注與研究。
(二)協作之獨特重要性的初步顯現
雖然馬克思在《倫敦筆記》里對韋克菲爾德《略論殖民藝術》一書摘錄不多,但考慮到馬克思本人在之后又閱讀了韋克菲爾德于1833 年出版的《英國和美國。兩國社會狀況和政治狀況的比較》(England and America. A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both nations)以及在《資本論》第一卷專門以其“系統殖民”理論為核心單獨開辟一章作為結尾,這里同韋克菲爾德的首次邂逅一定令馬克思印象深刻。
同時,馬克思初步形成了自己對于協作的理論興趣。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為其協作思想舉例說明時,經常引用自己在《倫敦筆記》中的摘錄:②Marx-Engels-Gesamtausgabe-2 IV/9, S. 489.“‘有許多工作非常簡單,不能分割開來,沒有許多人手的協作就不能完成。例如,把一根大樹干抬到車上……總之,凡是許多人手不同時再同一個不可分割的工作上互相幫助就不能完成的事情,都是這樣。’(愛·吉·韋克菲爾德《略論殖民藝術》1849年倫敦版第168頁)”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378頁。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資本論》第一卷里馬克思將這段摘錄作為注釋而未做更多的說明,但是在《1861-1863 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同樣摘錄了這段話,并直接稱其為“有關協作的這一簡單形式的一段話”。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第291頁。“巧合”的是,韋克菲爾德亦將這種協作稱為“勞動結合”(the Combination of Labour),⑤Edward Gibbon Wakefield, 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 London:Batoche Books, 2001, p.52.同馬克思晚期的“ 結合勞動”(Kombinirten Arbeit; Travail Commun; the Combined Labour)⑥馬克思將在協作過程中的勞動稱為結合勞動。概念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對應。
為什么韋克菲爾德對于在殖民地制造出工人對資本從屬關系的理論努力中會意外地凸顯協作獨特的重要性呢?因為韋克菲爾德在外部視角點明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以維系的在勞動過程方面的兩個要素:勞動的結合(Combination)與恒常(Constancy)。但是“在過去的國家里,(勞動的結合和恒常性)是不需要資本家的努力和思慮的,這僅僅是通過雇傭大量的勞動者來實現。在殖民地,雇工很少。雇工短缺是殖民地普遍抱怨的問題。”⑦Marx-Engels-Gesamtausgabe-2 IV/9, S. 489.
關于勞動的結合,⑧馬克思在《倫敦筆記》中對于“結合勞動”的關注其實不止于對韋克菲爾德理論的研究,例如前文摘錄的“幾乎所有的藝術和技能產品都是結合勞動的結果”(Marx-Engels-Gesamtausgabe-2 IV/9, S. 11);“……充足的資本和良好結合的勞動力比孤立和獨立的勞動力具有更高的生產力”(Marx-Engels-Gesamtausgabe-2 IV/9, S. 138)。只是在韋克菲爾德這里,“勞動結合”與“勞動分工”被明確進行了區分,并且前者的理論意義被明確指認為高于后者。韋克菲爾德指出以往政治經濟學家一直認為在應用方面的最重要的改進是“勞動分工”(代表人物即亞當·斯密),但這不過是陷入了一種語言上的錯誤,所謂的“勞動分工”完全取決于“勞動結合”。①韋克菲爾德以斯密的大頭針工廠為例,認為除非所有這些人在同一屋檐下被聚集在一起并被誘導進行合作,制作大頭針的整個工作的各個部分根本不能分配給不同的人。而把工人聚集在一起,并誘導他們合作,是一種勞動的結合:不能用任何其他名稱正確地稱呼它。在韋克菲爾德看來,同一件事怎么可能同時是分工和結合呢?其中一個表達式肯定是錯的。勞動結合就是勞動結合,并非所謂的“勞動分工”:把一項工作的幾個部分分配給不同的勞動者,不是勞動的分工,而是工作或職能的分工。制作大頭針的全部工作被分配給許多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部分:他們的勞動不是被分配的,而是相反地被合并在一起,以便使他們能夠分配工作。②Edward Gibbon Wakefield, 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 p.52.這一簡單的原理是直到對殖民地展開考察才被清晰揭示出來的,因為在經濟學家們所在的地方,勞動總是以一種結合的姿態出現,它似乎是一種自然的財產。但是在殖民地則不然,在那里,資本家的每一步努力和每一個行業都遇到了誘導許多人為了不管什么目的而結合勞動的困難。③Edward Gibbon Wakefield, 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 p.53.
勞動的恒常性是另一重要的原則,“……工業的大部分運作,尤其是生產量與所用資本和勞動力的比例很大的工業活動,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完成。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如果不能確定他們能堅持好幾年的話,就不值得一試。他們使用的資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固定的、不可兌換的、持久的。如果有什么事情阻止了運作,所有的資金都會流失。如果收成不能收獲,使它生長的全部花費就都浪費了”。④Marx-Engels-Gesamtausgabe-2 IV/9,S. 489.但是在殖民地里,勞動的恒常與持續反倒成了一個鮮見的事情,因為工人隨時可以違背資本家的意見而停止其工作,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小生產者。這種工作的間斷性已然成了在殖民地發展工業生產力的嚴重阻礙,在殖民地保證勞動的恒常性同在短時間內完成勞動的結合一樣困難。⑤Edward Gibbon Wakefield, 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 p.53.
正是因為充分地意識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非自然的,韋克菲爾德才由此提出了自己的“系統殖民”理論,⑥由于本文主要討論馬克思的協作理論,故不在正文中對“系統殖民”理論做更多的解釋。簡單來說,韋克菲爾德的系統殖民理論即:提高殖民地的土地價格,由此移民需要在一段時間內作為雇傭工人在工廠賺取工資以購買土地,再脫離雇傭勞動成為獨立的生產者。并且土地的價格應當是“充分的”,唯有如此才能保證在殖民地找得到雇傭工人,宗主國也不會存在大量過剩的人口。希望以一種人為的方式將這種關系構建出來。但在這里韋克菲爾德只是談到用某種“充分價格”(Sufficient Price)來給土地定價,從而使得移民不得不成為一段時間的雇傭工人,這就在最低意義上保證了勞動的結合與恒常。但這僅是一種外在的制衡,并非從勞動組織/結合形式本身對這兩個原則進行保障。馬克思或許對此也有所意識,因為他同時也摘錄了體現梅里韋爾對于協作制度本身關注的語段:“如果實行一種明智的協作(cooperation)制度,不浪費勞動力或資本,那么產生預期結果所需的勞動力或資本就要少得多……”⑦Marx-Engels-Gesamtausgabe-2 IV/9, S. 463.
值得注意的是,在《倫敦筆記》中馬克思不僅在理論意義上關注到協作的獨特重要性,同時在實踐意義上馬克思也非常關注殖民地人民通過協作來取得效果的案例,例如其摘錄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特(William Hickling Prescott)《秘魯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中的語段:“不使用工具或歐洲人所熟悉的機器,任何人(在秘魯)都只能做很少的工作;但是大批的人在統一的指揮之下進行工作,靠堅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成果,等等。”⑧Marx-Engels-Gesamtausgabe-2 IV/9, S. 428.(這段文字在《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也有被馬克思引用)①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第246頁。
由此,《倫敦筆記》時期對韋克菲爾德殖民理論的研究以及對相關問題的關注使得馬克思開始意識到協作區別于分工的獨特重要性:其一,進行工作或者職能的分配的前提條件是勞動的結合,這種結合并非天然,而是需要人為構造的;其二,勞動完成結合以后,還需要保證其恒常性,也就是說協作并非天然是可持續的;其三,一種合理的協作制度可以使得耗費的勞動力或資本減少。
但《倫敦筆記》時期僅僅是馬克思對大量資料的一個占有階段,尚未有理論成形,只有到了寫作《資本論》及其手稿的時候,馬克思的“協作”概念才擁有其完備的理論內涵。
四、“協作”概念的完成:《資本論》及其手稿
“協作”作為一個被自覺使用的概念出現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已是比較后期。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當中,馬克思已經開始有意識地以區別于“分工”概念的形式使用“協作”概念,例如“工人的聯合——作為勞動生產率的基本條件的協作和分工——和一切勞動生產力一樣,即和決定勞動強度因而決定勞動在外延方面實現程度的力量一樣,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7頁。但這種區別還沒有以明確的形式呈現出來,對此,直到《1859-1861 年經濟學著作和手稿》的《資本章草稿計劃》中《資本的生產過程》篇里,馬克思“第一次談到了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三個歷史階段,即協作、分工和機器”。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第588頁、前言第12-13頁。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韋克菲爾德”及其關于結合勞動的強調的筆記被置于“分工”這一小標題之下,可見此時馬克思比起“分”更加注重“合”。在《資本論》及其手稿文獻群中,“協作”概念的支援背景較《倫敦筆記》時期的殖民地問題研究也更加豐富、深厚,由此鑄就了獨屬于馬克思的“協作”概念及其最終的理論形態。
(一)“協作”概念的基本內涵
馬克思對于“協作”概念的基本界定為:“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作協作。”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378頁。在這種協同勞動形式中的勞動被稱作“結合勞動”。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378頁。更為關鍵的是,“結合勞動的效果要么是單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么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378頁。總的來說,馬克思的“協作”概念包含如下四個方面的內涵:
第一,協作是“相互聯系的生產過程”,也就是說協作這種協同勞動形式并不必然要求單個勞動者職能的固定性,只要求展開協作的勞動過程之間⑦當然也可以是在同一個勞動過程之中。保有某種聯系、指向同一個工作。在協作過程中勞動者的勞動本身是并未被完全規定下來的,例如在捕魚這項工作當中,劃船、掌舵以及撒網這三個職能如果可以被三個人輪流承擔,那么這還不是“真正的分工”,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第301頁。“而真正的分工卻是:‘當一些人互相為彼此勞動時,每個人可以只從事他最拿手的工作等等’”。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第301頁。由此,在一般性的協作語境中,勞動者的職能還具有相對的流動性,一個人可以自主地選擇是去劃船還是掌舵,或者是上午劃船、下午掌舵,但是在特殊性的協作語境——分工——中,一個人只能行使固定的職能,并將其發展為自己“最拿手的工作”。①值得注意的是,“最拿手”并不意味著“最符合勞動者的理想”或者“最符合勞動者的需求”,只是說明勞動者行使這項職能時勞動效率最高,因此筆者認為馬克思這里所說的“真正的分工”并沒有展現出一種對于分工的價值上的肯定意味。
第二,協作需要“有計劃”,這就意味著它不是一種自發地、自然地形成的形式,而是有意識地、人為地組織的結果。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可以被視為是針對阿倫佐·波特爾(Alonzo Potter)的,因為在波特爾看來,勞動的協作、結合是工人勞動分工②在波特爾看來,“劃分(division)這個術語只適用于過程;過程進一步劃分為不同的操作,而這些操作又在一定數量的工人之間分配或分割。因此,這是通過過程的進一步劃分來實現的工人的結合”(A. Potter D.D., Political Economy: Its Objects, Uses, and Principles: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American People : with A Summary,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New York: Harper&Brothers, 1841, p.76.)。之后自發達到的結果,也就是說,工人們“沒有任何先前的一致,只服從于強大而穩定的利己沖動”,③A. Potter D.D., Political Economy: Its Objects, Uses, and Principles :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American People: with A Summary,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p.83.僅僅是出于對自然利益追求便能“順其自然”地達到結合、協作的結果。波特爾稱這種無形的力量為“無誤的本能”(Unerring Instinct),但本質上只是對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蜜蜂的寓言”的粗陋表達。所以馬克思指出,分工和結合之間是“互為條件”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第317頁。的,無論是在工廠內部還是社會內部發生的都并非從分工到結合這一單線的必然之路。馬克思在這里雖然沒有完全認同韋克菲爾德那“結合大于分工”或“只有結合沒有分工”的論斷,但依舊給予結合勞動以十分重要的地位。更為重要的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結合不是一種屬于工人本身并從屬于作為聯合的工人的關系”,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第318頁。而是一種來自異質權力的構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從本質上控制并改變了勞動”。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第318頁。所以波特爾那種將勞動的結合視作內在于、發生于勞動者本身的,并將其與分工簡單對立起來的觀點,被馬克思視作是一種“空話”。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第318頁。總之,協作是一種“有計劃”的勞動形式,它絕非自發、自然就能形成的結果,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個“計劃”的制定者不是勞動者,而是資本。
第三,協作作為一種“協同勞動形式”,其本身就包含一種結合性力量,這一方面表現在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的結合,另一方面又表現在各個勞動力量的結合。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結合又體現在兩個方面:(1)從生產過程角度來看,“結合”是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的一種社會活動形式,但它“是一種同工人對立的外在的、統治工人并控制工人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實際上是資本本身的力量和存在形式,每一個單個工人都從屬于資本,它們的社會生產關系也屬于資本”;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第317-318頁。(2)從產品角度來看,這種“結合”又凝結在了最后的商品當中,而這種勞動產品又是和工人本身對立的。
第四,協作本身就能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生產力。“……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378頁。而這種集體力形成的原因就在于“人即使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379頁。恰是人的這種社會本性決定他們在一起進行協同勞動時會激發出一種社會性力量。
馬克思也在《資本論》第一卷里介紹“協作”概念基本界定的末尾添加了一條腳注:“‘Concours de forces’[‘協力’]。(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論意志及其作用》第80 頁)”。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378頁。可見,德斯杜特·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的“協力”思想也給予了馬克思一定的啟發。③這本《論意志及其作用》(Traité de la volonté et de ses effets)是特拉西《意識形態的要素》(Elémens d’idéologie)第四、五冊的1826年法文版(1823年以《政治經濟學概論》(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為名出版),也是馬克思自寫作《巴黎手稿》起就有所引用的文本。這里足見形成問題意識的重要性,若沒有《倫敦筆記》時期對殖民地問題研究這一契機以及由此形成的對于協作的關注,即便在馬克思閱讀已久的文本里已經零星地提到協作的重要性,馬克思也無法將單一的理論碎片構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在特拉西思想研究專家埃米特·肯尼迪(Emmet Kennedy)看來,《論意志及其作用》可能是馬克思讀過的唯一一本特拉西寫作的專著。參見Emmet Kennedy,“‘Ideology’from Destutt De Tracy to Marx”,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40,no.3(July- September 1979), pp. 353-368.其原初語境是:“協力,知識的增長和保存,以及分工——這些是社會的三大優勢。”④Destutt De Tracy,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Bouguet et Lévi, 1823, p.80.并且與韋克菲爾德一致的是,在特拉西那里,協作的力量在這里是高于分工的,在介紹分工時,他說:“社會的第三個優勢遠沒有前兩個優勢重要。”⑤Destutt De Tracy,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p.80.這自然也影響到了馬克思本人對協作與分工之間關系的看法,這主要體現他認為流行于他所處的時代的那種工場手工業式的分工“的許多優越性都是由協作的一般性質產生的,而不是由協作的這種特殊形式產生的”。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393頁。協作能夠創造出,或者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勞動的自然力”。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第291頁。
(二)“協作”概念的批判性維度
至此,馬克思的“協作”概念獲得了說明,無論是其在馬克思理論視域內的發展還是其最終的內涵所指,都包含有明顯的批判性維度。并且,這種批判性在馬克思自身理論成熟的過程中不斷科學化以及清晰化。
在馬克思還沒有對“協作”帶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并且開展具體研究之前,“共同活動方式”充當其前身已然具備了晚期“協作”概念的一定內涵,其批判性維度主要體現在馬克思對“共同活動”之異化的批判,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們的共同活動產生的力量反而“作為完全異己的力量威懾和駕馭著他們”,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2頁。唯有通過共產主義革命才能轉而控制以及自覺駕馭這股力量。這里的異化已然不是馬克思早期那種“主-客”結構式的異化,而是以一定歷史條件下社會關系為基礎的關系式的異化。⑨廣松涉稱前者為“異化”,后者為“物象化”。但總的來說,一方面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尚未充分學習經濟學,另一方面也沒有基于殖民地問題研究的契機而以外部視角審視資本關系下的勞動組織形式,所以此時的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理解尚未到達其晚期的科學高度,他“仍然在哲學邏輯的方向上建構新的歷史性話語。”⑩張一兵:《回到馬克思》,第453頁。
到了《倫敦筆記》時期,雖然馬克思在該階段做得更多的是摘錄性工作,但此時其對“協作”的關注恰是基于這一批判性維度的凸顯:資本是一種關系,并且它需要被人為地構造出來,而非是某種自然的存在。①孔特拉·坎尼(Contra Chimni)認為殖民主義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沒有影響”(Chimni, B. S,“Prolegomena to a Clas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1, no.1(February 2010), pp.57-82.),但很顯然他忽略了殖民問題作為一個“外部”視角在審視資本主義內部運行機制時的重要性。加布里埃爾·皮特伯格(Gabriel Piterberg)與洛倫佐·韋拉西尼(Lorenzo Veracini)認為,正是因為在馬克思的分析框架里,韋克菲爾德理解資本積累是建立在事先拒絕獲得一定的生存手段和隨后普遍的雇傭勞動的基礎上,所以韋克菲爾德對馬克思來說是不可抗拒的。②參見Gabriel Piterberg, Lorenzo Veracini,“Wakefield, Marx, and the world turned inside out,”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10, no.3(October 2015), pp.457-478.在同協作相關的摘錄性筆記中,不僅僅體現出資本主義條件下結合勞動在表面上同人的異質性,更是將這種異化了的勞動組織形式同資本自身之間的密切聯系從客觀的外部視角予以凸顯:這是資本為了延續、發展自身的必需的選擇與操控。在這個意義上,奈格里與哈特所認為的“在今天資本不提供協作,只是剝奪協作”這一命題就難以成立,因為這無異于將協作視為同資本本質上無涉的存在——從而可以隨時剝離——但是協作是資本關系得以可能的前提性條件,資本主義條件下具體的協作本就是按照資本自身的邏輯被塑造的。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充分學習經濟學以及受到殖民地問題研究啟發的馬克思更是深刻挖掘資本對于協作的控制機制。在“協作”概念內涵的四個方面中,處于資本主義剝削邏輯核心的是其第四個方面,即協作能夠創造出全新的生產力(下稱其為協作生產力),③程啟智指出要素與協作是人類生產活動的兩個維度,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也相應地可以分為要素生產力與協作生產力兩個部分。參見程啟智:《論馬克思生產力理論的兩個維度:要素生產力和協作生產力》,《當代經濟研究》2013年第12期。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生產力無疑是被無償占有的。同時基于資本自我增殖的邏輯,它定不會滿足于單純的無償占有協作生產力,而是要占有最大化了的協作生產力。對此,馬克思分析出七種資本主義條件下提升協作生產力的方式,④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382頁。并且進一步揭露了勞動過程中資本主義管理的雙重性:(1)協作這種內含結合性的協同勞動本身就決定了該過程中需要有人發揮監督、管理的職能,在這個意義上管理是與資本無涉的;(2)資本關系中,監督、管理同時又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1頁。的必然結果,而這才是決定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管理方式的核心。但是第二個方面總是利用第一個方面的一般性與普遍性將自己化作“無辜”的面貌從而逃離關于“剝削”的指認,例如企業主的收入直接被稱作管理勞動的工資。⑥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6卷),第432-433頁。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剝削成了組織協作的要旨:對協作的塑造不僅以協作生產力最大化為導向,甚至還利用管理的二重性掩蓋這種塑造-剝削機制。由此,資本主義協作總是與剝削緊密相連,處于這種協作中的勞動主體也總是同其勞動過程相異化。
五、結 語
綜上,“協作”在馬克思那里絕非是超歷史、純然中立的,恰恰相反,它是在資本主義語境下一個極具批判性的概念。誠然,當代的協作形式或許使得所謂“自主性”獲得了某種意義上的發展,但正如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所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是一個技術過程,相反,它被客體化的社會關系形式(價值、資本)所模鑄。”⑦〔加〕莫伊舍·普殊同:《時間、勞動與社會統治》,康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44頁。協作作為生產方式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自然也是被其原初的集結性力量——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這種力量就是資本——所模鑄,在樂觀地期待“出走”之前,我們仍需冷靜下來反思:(1)如果具體的協作同其集結性力量本就存在高度共謀,這種出走何以可能?(2)即便出走成功,將這種協作化為己用,被資本主義關系已然模鑄的協作何以真正而本質地成為理想社會的協作呢?
我們依舊需要將研究的焦點落到資本邏輯自身的機制及其矛盾中去,因為“一種歷史生產形式的矛盾的發展,是這種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歷史道路”。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562頁。唯有如此,我們對當今資本主義全新發展的理解才是深刻而本質的,從而才能夠在現實意義上追求與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語境下的積極協作樣態,使勞動過程與勞動產品真正地歸于人本身,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提供有力的理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