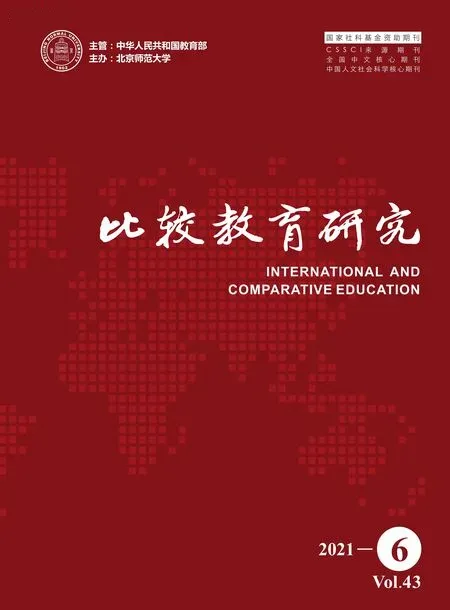全球貧困治理視域下世界銀行推動職業(yè)教育發(fā)展路徑與邏輯
唐智彬,王池名
(湖南師范大學職業(yè)教育研究所,湖南長沙 410081)
長期以來,世界銀行以促進人類共同繁榮為使命,在全球范圍內(nèi)推進貧困治理,旨在于2030年消除極端貧困。在發(fā)展教育方面,世界銀行是向發(fā)展中國家教育事業(yè)投資最多的機構(gòu),在8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開展項目,2019財年世界銀行共提供30億美元用于教育發(fā)展、技術援助和改善學習等方面的項目,目前世界銀行的教育投資組合總額達160億美元。[1]作為貧困治理的重要手段,職業(yè)教育和技能培訓長期得到世界銀行的高度重視,是世界銀行全球教育發(fā)展和援助的重點。本文對世界銀行全球貧困治理的職業(yè)教育理念、政策演進與實施重點進行研究,以深入理解其貧困治理的運作邏輯。
一、以教育促進全球貧困治理:世界銀行的重要理念
多年來,世界銀行不斷拓展工作領域,從單一金融機構(gòu)向多元化全球治理主體轉(zhuǎn)變,強調(diào)在發(fā)展經(jīng)濟的基礎上推動全球貧困治理的途徑創(chuàng)新。其中,發(fā)展教育作為貧困治理的重要議題,其重要性在世界銀行的業(yè)務中逐步增強。世界銀行也逐步形成了清晰的貧困治理教育思路,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增加教育機會,促進貧困人群個體人力資本積累。提供優(yōu)質(zhì)教育,并通過教育創(chuàng)造人力資本,能有效促進貧困群體增加就業(yè)機會,提高收入水平,從而減少貧困,并使整個社會獲益,讓全體民眾共享繁榮。這其中的關鍵在于實現(xiàn)真正的教育機會平等。[2]世界銀行報告《對世界貧困的反擊:農(nóng)村發(fā)展、教育和衛(wèi)生問題》(The Assault on World Poverty: Problems of Rur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Health)強調(diào),鑒于目標群體和教育任務的多樣性,除了正規(guī)學校制度外,有效利用非正規(guī)教育和培訓是可取的。[3]顯然,面對貧困群體的發(fā)展需求,首要的是增加教育機會,實施相應的教育方案,特別是針對那些已經(jīng)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應采取舉措為他們提供“第二次機會”,使其獲得生存與發(fā)展的技能。
第二,改進技能水平與生產(chǎn)力,以擴大就業(yè),促進社會公平。工作技能缺乏是生產(chǎn)力和收入持續(xù)低下的原因之一。“技能缺口”“技能錯配”、低技能和無技能的狀況造成人們就業(yè)困難,身陷貧困。由此,世界銀行提出通過“STEP技能評估計劃”[The Towards Employability and productivity(STEP)Skill Measurement Program]來改進中低收入國家技能狀況,這也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在中低收入國家評估技能的倡議。該計劃通過提供與技能政策相關的數(shù)據(jù),可以更好地了解勞動力市場的技能需求,促進技能獲得與教育成就,討論個性和社會背景之間的后向關聯(lián)(backward linkage)、技能獲得與生活水平之間的前向關聯(lián)(forword linkage)、不平等與貧困現(xiàn)象的減少、社會包容以及經(jīng)濟增長等議題。[4]2019年《世界銀行發(fā)展報告:工作性質(zhì)的變革》(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9: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提出,通過成人掃盲計劃、帶薪就業(yè)技能培訓和創(chuàng)業(yè)計劃等來幫助貧困人群獲得新技能和提升技能[5],以高質(zhì)量的培訓促進技能發(fā)展和提升勞動生產(chǎn)力,顯示出世界銀行在科技發(fā)展背景下對弱勢群體公平就業(yè)與個體發(fā)展的特別關注。
第三,提高地區(qū)總體受教育水平與群體素質(zhì),實現(xiàn)包容性發(fā)展。弱勢青少年需要良好的教育以支持其學習成績提升和能力發(fā)展,但很多國家和地區(qū)存在著“學習危機”。由于教育資源與教育技術的匱乏,全球教育質(zhì)量參差不齊,貧困地區(qū)教育水平低下。2011年世界銀行報告《全民學習:投資于人們的知識和技能,以促進發(fā)展》(Learning for All: Investing in People's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Promote Development)對教育反貧困問題進行了更全面的深刻闡釋。一方面,報告強調(diào)知識和技能是實現(xiàn)經(jīng)濟增長和擺脫貧困的有效手段,提出了“盡早投資、明智投資、全民投資”,側(cè)重教育投資的早期性、適應性和公平性;另一方面,報告提出不僅要關注職業(yè)技能問題,而且更要關注社交、溝通、團隊合作、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為這些技能與能力對于貧困人群在勞動力市場及其在家庭、社區(qū)的生活以及工作中的成功都具有重要意義。[6]這種理念也體現(xiàn)在《學習以實現(xiàn)教育的愿景》(Learning to Realize Education’s Promise)中,該文件強調(diào)真正的教育應該是促進人們共享繁榮并減少貧困的工具,只有改變家庭貧困和貧困代際傳遞現(xiàn)象,促進全體社會成員通過知識和技能走向個體全面發(fā)展,才能實現(xiàn)全社會共同繁榮與可持續(xù)發(fā)展。
第四,關注特殊群體的發(fā)展問題。以女性為例,世界銀行認為,在一個家庭中,女性受教育水平對下一代的成長至關重要。但是,到2019年,全世界估計有7.8億成人文盲,其中近2/3是婦女。在一些國家,婦女被排斥在社會發(fā)展和技術進步之外。[7]因此,教育應服務于特定目標群體,以產(chǎn)生更大的社會效益。2019年世界銀行報告《從性別平等中獲利:釋放非洲婦女企業(yè)的潛力》(Profiting from Parity: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Women’s Businesses in Africa)提出了包括職業(yè)技術教育與培訓在內(nèi)的多元化女性就業(yè)解決方案。世界銀行也在各國推出針對性項目,如利比里亞“女童和青年女性賦權(quán)項目”(The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and Young Women)、肯尼亞“Ninaweza計劃”、尼泊爾“少女就業(yè)倡議”(Adolescent Girls Employment Initiative)等項目,成效明顯。此外,世界銀行還積極推動青年貧困群體、殘障人士、少數(shù)族裔及社會邊緣群體的教育和技能反貧困行動,以幫助他們重返社會。
二、世界銀行推動全球貧困治理的職業(yè)教育政策歷程
1963年,世界銀行出臺了第一份教育文件《世界銀行及國際開發(fā)協(xié)會在教育領域的政策提案》(World Bank and IDA Policy Proposals in Education),提出面向發(fā)展中國家資助教育項目。時任行長喬治·戴維·伍茲(George David Woods)在其備忘錄中強調(diào),要優(yōu)先考慮資助那些為了經(jīng)濟發(fā)展的人才培養(yǎng)教育貸款項目,集中關注各級職業(yè)技術教育與培訓以及中等教育領域。[8]為此,世界銀行穩(wěn)步增加對公共職前技能開發(fā)機構(gòu)和培訓方案的支持。根據(jù)1975年發(fā)布的《對世界貧困的反擊:農(nóng)村發(fā)展、教育和衛(wèi)生問題》,世界銀行1963-1971財政年度投入大力支持技術和職業(yè)教育(29%)與農(nóng)業(yè)教育和培訓(15%),職業(yè)教育教師培訓機構(gòu)也獲得了大約12%的貸款。[9]1980年《世界發(fā)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的“職業(yè)教育與培訓”部分指出,嚴重依賴學校職業(yè)技能開發(fā)通常效率低下,而那些提供具有廣泛適用性、能作為后續(xù)在職培訓或短期課程的培訓機構(gòu)更可能成功。[10]世界銀行還提出職業(yè)培訓與技術教育系統(tǒng)是年輕人以及成年人,尤其是弱勢群體接受培訓和再培訓的重要資源。[11]
1991年,世界銀行職業(yè)教育政策小組推出《職業(yè)技術教育與培訓:世界銀行的政策文件》(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 World Bank Policy Paper),并列專章討論了“將培訓作為公平戰(zhàn)略的補充”問題。由于發(fā)展中國家貧困群體大多生活在農(nóng)村地區(qū),其主要資產(chǎn)是勞動力,因此報告確立了世界銀行面向貧困群體的職業(yè)教育與培訓總體思路:提高總體教育層次與水平,開展農(nóng)村和城市貧困人群自雇傭培訓,以技能培訓改善婦女群體獲得有薪工作的機會,降低培訓費用,消除就業(yè)歧視。[12]
21世紀以來,世界銀行貧困治理體系持續(xù)改進,職業(yè)教育政策呈現(xiàn)新的特征。2000年,世界銀行報告《轉(zhuǎn)型經(jīng)濟體對教育系統(tǒng)的隱藏挑戰(zhàn)》(Hidden Challenges to Education System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重點討論如何提高世界銀行的反貧困工作,報告分析了低教育水平與低收入的雙向因果關系、貧困群體的特殊教育需求以及相關建議對貧困人群的影響。報告認為,在其他所有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教育促成人力資本形成,提高了生產(chǎn)率,從而促進了產(chǎn)業(yè)進步、經(jīng)濟發(fā)展與收入增長,因此公平的教育機會對消除貧困至關重要。世界銀行進一步強調(diào)要通過展職業(yè)教育、促進教育公平來實現(xiàn)反貧困目標。[13]2010年世界銀行在工作文件《未竟事業(yè):動員新的力量,實現(xiàn)2015年千年發(fā)展目標》(Unfinished Business : Mobilizing
New Efforts to Achieve the 2015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中提出幫助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國家創(chuàng)造經(jīng)濟發(fā)展機會,以改善貧困人群的生活,并突出職業(yè)教育與培訓作為全方位知識服務的重點,集中提高世界銀行職業(yè)教育項目支出效益。[14]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以來,世界銀行快速反應,推出了《技術和職業(yè)教育與培訓系統(tǒng)對COVID-19的回應:挑戰(zhàn)與機遇》(TVET Systems’Response to COVID-19: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研究報告,指出疫情讓更多貧困學生的學習面臨困難,同時可能會導致許多國家的勞動力市場發(fā)生結(jié)構(gòu)性變化,因此職業(yè)教育系統(tǒng)必須盡早評估,并響應新出現(xiàn)的技能需求。否則,需求缺口可能成為發(fā)展瓶頸,從而減少獲得(更高)收入的機會,這對收入水平最低的人群影響更大。[15]因此,政府、職業(yè)教育機構(gòu)和社會伙伴應確保職業(yè)教育與培訓供應能夠適應新出現(xiàn)的需求,提升技能系統(tǒng)助力經(jīng)濟復蘇的能力。
在推動全球貧困治理過程中,世界銀行一直認為,教育是強大的發(fā)展推動力,也是減少貧困以及改善健康、性別平等、維持和平以及穩(wěn)定社會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從收入方面來說,教育具有巨大、持續(xù)的回報,也可應對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xiàn)象。[16]因此,面向所有人提供優(yōu)質(zhì)的幼兒教育和基礎教育,發(fā)展高水平職業(yè)教育和培訓,培養(yǎng)工作技能,促進職業(yè)教育適應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是實現(xiàn)2030年消除貧困目標的關鍵。
三、世界銀行推動全球貧困治理的職業(yè)教育發(fā)展重點領域
(一)強調(diào)職業(yè)教育與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之間的直接聯(lián)系
世界銀行認為,外部經(jīng)濟環(huán)境和條件是影響職業(yè)教育和技能培訓體系的根本因素,因此非常強調(diào)職業(yè)教育與經(jīng)濟發(fā)展之間的聯(lián)系。《教育:部門工作文件1974》(Education: Sector Working Paper1974)提出,“教育內(nèi)容必須被重新導向為教授工作所需的技能,以確保畢業(yè)生順利就業(yè)”[17]。因此,世界銀行提出對勞動力市場政策和效率分析也應成為宏觀經(jīng)濟政策制定的一個重要部分。[18]只有當技能真正在職業(yè)活動中被使用時,技能培訓才能夠提高勞動者的生產(chǎn)力和收入。2005年世界銀行發(fā)布《教育部門戰(zhàn)略升級》(Education Sector Strategy Update),提出“全民教育”和“知識經(jīng)濟”兩大發(fā)展目標,并強調(diào)通過發(fā)展教育增進經(jīng)濟增長所需的高水平技能與知識,突出教育在知識經(jīng)濟中的基礎性地位。[19]2018年,世界銀行報告《學習實現(xiàn)教育的愿景》強調(diào),“將技能培訓與就業(yè)聯(lián)系起來,奠定堅實的發(fā)展基礎”,明確了優(yōu)質(zhì)職業(yè)教育的關鍵特征,如“在設計培訓方案之前在學習者與雇主之間建立合作關系”“將課堂學習與工作場所學習緊密結(jié)合”等。[20]這充分體現(xiàn)了世界銀行全球貧困治理過程中的經(jīng)濟理性和效益導向。
(二)重點發(fā)展非正式職業(yè)培訓,關注私人培訓部門和企業(yè)培訓
世界銀行在介入貧困地區(qū)職業(yè)教育發(fā)展初期,將支持重點主要放在公共部門,貸款和信貸都關注教育部門和農(nóng)業(yè)部門主辦的各類職業(yè)學校。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銀行許多國家項目報告顯示,參加職前培訓的畢業(yè)生較大比例無法對口就業(yè)。各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與勞動力市場變革,尤其是技術的突飛猛進對發(fā)展中國家職業(yè)教育與培訓系統(tǒng)提出了極大挑戰(zhàn)。基于相關研究結(jié)論,世界銀行開始逐步探索支持由雇主主導的職業(yè)培訓,包括非正式職業(yè)培訓,認為這是培養(yǎng)人們技能的一種成本更低、效益更高的方式。世界銀行一項關于非正規(guī)教育研究顯示,非正式培訓計劃的目的、目標人群、覆蓋范圍、機構(gòu)特征和教育技術更具多樣性。數(shù)據(jù)顯示,1987-1991年間世界銀行教育貸款總數(shù)的60 %用于支持職業(yè)培訓,而中等職業(yè)學校僅占相關經(jīng)費的19%。[21]
1991年《職業(yè)技術教育與培訓:世界銀行的政策文件》強調(diào)發(fā)展初等和中等教育,鼓勵私營部門培訓,提高公共培訓有效性和效率,并將培訓作為必要的補充。[22]2007年,世界銀行分析報告提到要在發(fā)展中國家的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建立伙伴關系,試圖通過平衡對技能和人力資本投資來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和競爭力,改善貧困狀況。[23]例如,世界銀行與莫桑比克的技術和職業(yè)教育及培訓項目以促進現(xiàn)有的職業(yè)教育與培訓系統(tǒng)向“需求導向”發(fā)展為過渡目標,旨在讓私營部門參與進來,建立一個由政府、行業(yè)和社會民眾代表組成的治理結(jié)構(gòu)。[24]在推動貧困治理的過程中,世界銀行不斷擴大治理范圍,創(chuàng)新治理模式,拓寬教育服務領域,強調(diào)私人教育對公共教育的補充和完善,突出職業(yè)教育與培訓的反貧困效果。
(三)推動與業(yè)務國家形成多類型的職業(yè)教育合作項目
隨著各類項目推進,世界銀行全球治理結(jié)構(gòu)逐步清晰,越來越強調(diào)與各個業(yè)務國家實施援助與合作計劃,項目呈現(xiàn)出多元化特征。中國從1984年開始籌備“世界銀行貸款職業(yè)技術教育項目”,2002年第二個職業(yè)技術教育發(fā)展項目執(zhí)行完畢,兩輪共引進8000萬美元世行貸款,151所中高職學校直接受益,其中包括一批貧困地區(qū)職業(yè)學校。此后,世界銀行在中國甘肅、新疆、云南等貧困地區(qū)都推動了系列職業(yè)教育發(fā)展項目貸款,重點“放在從制度層面和學校層面加強校企合作,使技能培養(yǎng)更好地符合企業(yè)的需求”[25]。2008年,世界銀行在中國發(fā)起了農(nóng)民工培訓與就業(yè)項目。在肯尼亞,世界銀行通過技術和職業(yè)憑單計劃(The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Vouchers Program),聯(lián)合當?shù)卣蚯嗄臧l(fā)放職業(yè)培訓券,同時打破性別壁壘,推動女性接受培訓。同年,世界銀行建立土耳其職業(yè)介紹所,幫助弱勢群體獲得就業(yè)機會。在馬拉維共和國,世界銀行通過合作實施職業(yè)培訓計劃,重點幫助15~24歲的年輕人學習技能。在多米尼加共和國,世界銀行集團和美洲開發(fā)銀行成功實施了一項青年培訓和就業(yè)計劃,為貧窮青年提供職業(yè)和生活技能培訓以及在職實習。2010年以來,世界銀行在巴布亞新幾內(nèi)亞實施“城市青年就業(yè)項目”(The Urban Youth Employment Project)通過職業(yè)培訓、就業(yè)匹配和補貼,幫助該國應對日益緊迫的經(jīng)濟形勢。2012年,世界銀行針對孟加拉國的失學兒童(The Reaching Out-of-School Children)II項目擴大到11個城市,為未入讀正規(guī)學校的青少年試行職業(yè)技能培訓計劃。此外,世界銀行通過“過渡復員和重返社會計劃”(Transitional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Program)開展職業(yè)培訓,為盧旺達退伍人員提供社會援助,幫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
四、以職業(yè)教育推動全球貧困治理的運作邏輯
(一)構(gòu)建“金融支持-教育發(fā)展”互動的貧困治理體系
作為一家以金融為主導業(yè)務的國際組織,在推動全球貧困治理的過程中,世界銀行治理思路與治理邏輯都體現(xiàn)了以經(jīng)濟為核心的內(nèi)在特征,經(jīng)濟理性貫穿世界銀行各項全球治理方案。與多數(shù)減貧理論一致的是,世界銀行發(fā)展經(jīng)濟學家們也提出將改善貧困地區(qū)的教育水平作為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對策,但在具體行動方案上又有所差異。世界銀行采取“金融支持-教育發(fā)展”互動的貧困治理方案。在具體運作上,金融支持主要體現(xiàn)為世界銀行與發(fā)展中國家在形成合作關系的基礎上,由發(fā)展中國家根據(jù)自身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總體目標及職業(yè)教育發(fā)展需求,向世界銀行提出融資需求;世界銀行根據(jù)專家評估,通過雙方的反復溝通、談判確定資金支持的內(nèi)容、規(guī)模以及方式。具體說來,國際復興開發(fā)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主要負責為中低等收入國家提供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貸款,國際開發(fā)協(xié)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DA)則更主要偏向提供更優(yōu)惠的無息貸款,雖分工不同,但都旨在實現(xiàn)世界銀行的貧困治理目標。
與此同時,隨著全球治理模式與治理手段推進,世界銀行在貧困治理上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特點,比如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干預越來越精細化。在職業(yè)教育與培訓上,世界銀行傾向于向業(yè)務國家“兜售”其主導推動的發(fā)展模式,通過“制度復制”的方式,“將理想化、統(tǒng)一的制度藍圖強加給發(fā)展中國家”[26]。以中國為例, 1998年,世界銀行在《中國21世紀教育發(fā)展戰(zhàn)略目標》(Strategic Objectives of China's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中為中國職業(yè)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與發(fā)展的政策建議,但其中部分建議明顯不符合中國職業(yè)教育改革的現(xiàn)實情況,如管理體制、普職比例等。世界銀行的“制度復制”全球治理方式往往與金融手段和資金支持配套使用,提供貸款支持的同時,也隱含了“制度復制”的相關要求。不可否認,“金融支持-教育發(fā)展”的“組合拳”改善了世界銀行長期以來所認為的教育與經(jīng)濟需求脫節(jié)、教育供給效率和效益低下等問題,通過加大教育投入,在改善貧困地區(qū)基本教育條件的基礎上,提高了職業(yè)教育發(fā)展效益和貧困地區(qū)的人力資本水平,減少了貧困。
(二)以高水平的知識服務奠定世界銀行作為國際組織的權(quán)威性
世界銀行在不同治理事務上選擇不同的治理工具與治理方式,貸款資金支持與知識共享兩條不同的治理路徑。這兩種治理按照相應的邏輯各自展開與實踐,兩種治理路徑也給世界銀行形成了不同性質(zhì)的權(quán)威。在發(fā)展中國家面向貧困群體發(fā)展職業(yè)教育,是兩種治理路徑的融合。一方面,世界銀行一直為發(fā)展中國家推動職業(yè)教育發(fā)展提供了大量無息貸款、信貸和贈款,改善基礎辦學條件,培養(yǎng)和培訓職業(yè)教育教師;另一方面,通過長期發(fā)展與積累,世界銀行已經(jīng)逐步成為發(fā)展中國家的“知識銀行”(knowledge bank),在知識革命、全球創(chuàng)造以及積累發(fā)展經(jīng)驗和知識等方面,是有力的促進者和創(chuàng)造者。[27]“知識銀行”為世界銀行奠定了典型的專業(yè)權(quán)威基礎,尤其是近年來世界銀行通過出臺一系列直接以教育為主題的報告進一步強化了世界銀行在教育發(fā)展方面的專業(yè)權(quán)威。同時,世界銀行集聚了全世界最優(yōu)秀的專家隊伍在長期的貧困治理研究與國際實踐中積累了大量行業(yè)經(jīng)驗和國別發(fā)展知識,進一步強化了專業(yè)權(quán)威。
世界銀行作為國際組織的組織理性、組織道義性和專業(yè)知識是其穩(wěn)定的權(quán)威基礎和充分自主性的來源和保障。[28]對于各國而言,在通過發(fā)展職業(yè)教育推動貧困治理的過程中,世界銀行的權(quán)威既來自其提供的職業(yè)教育政策咨詢和發(fā)展經(jīng)驗模式以及貸款服務的客觀績效,同時也受到發(fā)展話語、國際規(guī)范等因素的國際社會性影響。國際組織權(quán)威是國際社會建構(gòu)的產(chǎn)物,體現(xiàn)了國際組織以及各個國家的主體間性。[29]世界銀行持續(xù)數(shù)十年,積累了多個領域、多個地區(qū)的綜合性數(shù)據(jù)庫,從而奠定了其專業(yè)咨詢、政策服務和治理機構(gòu)的地位。職業(yè)教育作為世界銀行的重要貧困治理工具,經(jīng)過多年推動,已經(jīng)形成了完備的職業(yè)教育理論、政策以及貸款的發(fā)展支持體系,世界銀行的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理念、政策與貧困治理機制也得到了各個國家的認同與執(zhí)行。
(三)在反思與創(chuàng)新中改進世界銀行全球貧困治理的職業(yè)教育路徑
在推動全球發(fā)展的過程中,世界銀行也面臨與其他國際組織和機構(gòu)的競爭,如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等。為了保持自身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角色和地位,世界銀行一直通過推動貧困治理理念與治理方式的變革,適應全球治理發(fā)展的需求。對于國際組織自身的變革有三個方面的理論解釋,包括國家推動、規(guī)范傳播和針對治理失敗的主動反思。[30]其中,從推動適應貧困地區(qū)世界銀行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的歷程中,可以看出世界銀行的組織反思與治理創(chuàng)新的過程。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在發(fā)展經(jīng)濟學和人力資本理論的基礎上,世界銀行貧困治理方案重在將經(jīng)濟發(fā)展作為目標,將人作為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一種重要資本進行教育與培訓開發(fā)。隨后,新古典主義經(jīng)濟學思想成為世界銀行治理理論基礎,強調(diào)重新評價政府、市場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地位,強調(diào)市場力量,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為此,世界銀行職業(yè)教育政策與制度理論基礎出現(xiàn)轉(zhuǎn)變,發(fā)展思路與模式上發(fā)生明顯變化。這一變化體現(xiàn)了貧困治理思路的幾個對立:一是職業(yè)教育出發(fā)點的人力規(guī)劃與市場需求的對立;二是職業(yè)教育組織上的政府與市場的對立;三是職業(yè)教育重心的正規(guī)學校教育與企業(yè)非正規(guī)在職培訓的對立等。[31]20世紀80年代后,世界銀行轉(zhuǎn)換投資重點,對部分欠發(fā)達國家貧困地區(qū)所實施的“中等教育多樣化課程計劃”(Diversified Secondary Curriculum Projects)失敗進行了反思,開始推動基于市場導向的職業(yè)教育與培訓改革。[32]隨著進入知識經(jīng)濟時代,世界銀行在反貧困的過程中更加重視知識的生產(chǎn)、選擇、適應和使用,重視個體能力的養(yǎng)成。[33]在職業(yè)教育政策和思路轉(zhuǎn)換過程中,不難看出世界銀行治理轉(zhuǎn)變的基本邏輯是“失敗—反思”機制,體現(xiàn)出世界銀行全球貧困治理的職業(yè)教育路徑在發(fā)展反思中不斷改進。
世界銀行在推廣自己的全球貧困治理方案過程中,既有基于過往實踐的反思改進,也有針對實施項目的評估,尤其重視投資的效益反饋,受援國家需要達到世界銀行的要求或者條件才能夠獲得其持續(xù)的援助。如在《減貧戰(zhàn)略文件》(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和《國家援助戰(zhàn)略》(Country Assistance Strategy)的制定過程中,世界銀行強調(diào)受援國應發(fā)揮主導作用,充分調(diào)動各方力量,制定以發(fā)展效果為導向的長遠綜合性發(fā)展規(guī)劃。[34]由于受援國家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可能出于“私利”而不按照世界銀行的治理方式實施相應治理行為,可能導致治理策略失效和治理目標漂移。因此,在長期的全球貧困治理實踐中,世界銀行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成果導向的項目管理方式,能夠明確地測量發(fā)展融資和政策支持的成果,強調(diào)在融資項目和政策研究中設定可測量的發(fā)展目標,以便反思其項目績效與后續(xù)跟進。例如,世界銀行要求坦桑尼亞“結(jié)果導向教育項目”(Education Program for Results)要實現(xiàn)小學二年級學生平均閱讀速度從每分鐘18個單詞提高到24個單詞才算達到項目目標。這種項目管理方式和援助實效評估有效提升了項目質(zhì)量,提高了世界銀行全球治理的績效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