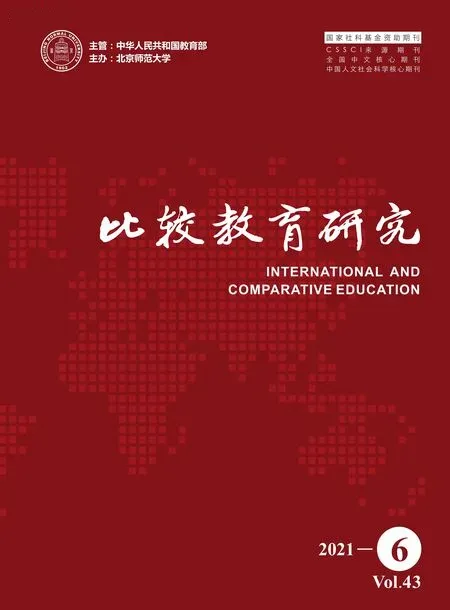國(guó)際教育測(cè)評(píng)項(xiàng)目抗逆學(xué)生研究探析
張平平,袁玉芝
(1.鄭州大學(xué)教育學(xué)院,河南鄭州 450001;2.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教育學(xué)院,北京 100872)
雖然個(gè)體的知識(shí)、技能等人力資本的積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背景的制約,但仍有相當(dāng)一部分成長(zhǎng)于弱勢(shì)背景家庭中的個(gè)體獲得了出乎意料的卓越教育成就,為人生發(fā)展奠定了良好基礎(chǔ),這些學(xué)生被稱為“抗逆學(xué)生”(resilient students)。個(gè)體面臨可能導(dǎo)致學(xué)業(yè)失敗的風(fēng)險(xiǎn)和不利條件,仍然獲得學(xué)業(yè)成功的現(xiàn)象被稱為“學(xué)業(yè)抗逆”(academic resilience)。[1]數(shù)十年來,研究者圍繞抗逆力的界定與測(cè)量、抗逆?zhèn)€體的特點(diǎn)、抗逆力的保護(hù)因素和干預(yù)策略開展了研究。現(xiàn)有的學(xué)業(yè)抗逆研究多基于局部地區(qū)的大學(xué)生樣本開展個(gè)體訪談和教育自傳分析,缺少基于代表性的中小學(xué)生樣本開展的實(shí)證研究,不利于從總體上揭示處境不利學(xué)生如何在個(gè)人、家庭和學(xué)校的努力下獲得卓越的教育成就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階層躍遷的一般規(guī)律。本文將系統(tǒng)梳理以國(guó)際學(xué)生評(píng)價(jià)項(xiàng)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為代表的國(guó)際項(xiàng)目在抗逆學(xué)生界定、抗逆學(xué)生的特點(diǎn)和抗逆學(xué)生形成的促進(jìn)要素方面的發(fā)現(xiàn),并結(jié)合基于PISA和國(guó)際數(shù)學(xué)與科學(xué)趨勢(shì)研究項(xiàng)目(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開展的抗逆學(xué)生研究,說明這些發(fā)現(xiàn)對(duì)于豐富相關(guān)理論以及促進(jìn)教育公平的政策和實(shí)踐的意義。
一、抗逆學(xué)生比例是國(guó)際項(xiàng)目用來衡量教育公平的重要指標(biāo)
同教育質(zhì)量一樣,教育公平是國(guó)際教育測(cè)評(píng)項(xiàng)目評(píng)估各國(guó)教育政策質(zhì)量的重要維度。比如,PISA構(gòu)建了包含“學(xué)習(xí)結(jié)果的均等”“教育資源分配的公平”和“克服學(xué)生背景的學(xué)習(xí)公平”在內(nèi)的分析教育公平與教育不平等狀況的框架。PISA以高低成就表現(xiàn)學(xué)生之間的成績(jī)差距和未達(dá)到基準(zhǔn)素養(yǎng)水平的學(xué)生比例來反映“學(xué)習(xí)結(jié)果的均等”;以學(xué)校中學(xué)生的平均家庭經(jīng)濟(jì)社會(huì)文化地位(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 ESCS)與學(xué)校中擁有大學(xué)學(xué)歷的全職教師比例/學(xué)校教育資源質(zhì)量指數(shù)/生機(jī)比/生師比等指標(biāo)的相關(guān)系數(shù)來反映“教育資源分配的公平”;以家庭ESCS及其各成分解釋的學(xué)生成績(jī)變異、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梯度、不同家庭ESCS學(xué)生的成績(jī)差距和抗逆學(xué)生比例來反映“克服學(xué)生背景的學(xué)習(xí)公平”。[2]自2011年發(fā)布《超越逆境:在學(xué)校取得成功的處境不利學(xué)生》報(bào)告以來,在每輪的PISA測(cè)試中,經(jīng)濟(jì)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均以抗逆學(xué)生比例及其年度變化作為反映一國(guó)或經(jīng)濟(jì)體的教育公平及其進(jìn)展?fàn)顩r的核心指標(biāo)進(jìn)行報(bào)告。此外,OECD發(fā)布的多項(xiàng)焦點(diǎn)報(bào)告和工作論文也基于國(guó)際比較數(shù)據(jù),分析國(guó)家、學(xué)校和家庭如何幫助處境不利學(xué)生提升抗逆力、縮小與處境有利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結(jié)果差距。比如,2018年的《教育公平:打破社會(huì)流動(dòng)的障礙》報(bào)告就專門討論了各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處境不利學(xué)生的認(rèn)知成就、社會(huì)情感抗逆結(jié)果和教育代際流動(dòng)問題。
二、國(guó)際項(xiàng)目對(duì)認(rèn)知成就抗逆學(xué)生的界定
在學(xué)業(yè)抗逆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基于一個(gè)或多個(gè)學(xué)業(yè)風(fēng)險(xiǎn)指標(biāo)以及標(biāo)準(zhǔn)化成就測(cè)驗(yàn)分?jǐn)?shù)在樣本學(xué)生中的位置來定義抗逆學(xué)生與非抗逆學(xué)生。[3]參考這一做法,PISA將那些取得了超出家庭ESCS預(yù)期學(xué)業(yè)表現(xiàn)的處境不利學(xué)生定義為抗逆學(xué)生,即盡管與本國(guó)(地區(qū))其他學(xué)生相比,這些學(xué)生的家庭ESCS處于排名靠后的位置,但他們的素養(yǎng)成績(jī)卻居于國(guó)際或國(guó)內(nèi)樣本前列。PISA結(jié)合學(xué)生的家庭ESCS和素養(yǎng)成績(jī),從國(guó)際、國(guó)內(nèi)和“核心技能”三個(gè)視角來界定何謂在認(rèn)知成就方面實(shí)現(xiàn)抗逆的學(xué)生。
(一)國(guó)際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
國(guó)際視角是被國(guó)際項(xiàng)目應(yīng)用最廣泛的抗逆學(xué)生定義方式,主要服務(wù)于比較國(guó)家(地區(qū))間教育公平程度和探尋國(guó)家(地區(qū))層面抗逆促進(jìn)要素的目的。在這個(gè)視角下,家庭ESCS處于何種水平稱之為處境不利是采用國(guó)家特定標(biāo)準(zhǔn),素養(yǎng)成績(jī)達(dá)到何種水平稱之為學(xué)業(yè)表現(xiàn)超出預(yù)期是采用國(guó)際基準(zhǔn)。比如,在基于PISA 2006數(shù)據(jù)撰寫的抗逆學(xué)生專題報(bào)告中,OECD將“家庭ESCS處于本國(guó)(地區(qū))樣本最低1/3而且校正了ESCS之后的科學(xué)成績(jī)處于國(guó)際樣本最高1/3的學(xué)生”稱作“國(guó)際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4]這個(gè)校正了的成績(jī)指的是學(xué)生的科學(xué)測(cè)試成績(jī)與根據(jù)其家庭ESCS預(yù)測(cè)得到的科學(xué)成績(jī)之差。作為反映教育公平的重要指標(biāo),國(guó)際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占比用來揭示不同教育系統(tǒng)克服學(xué)生家庭背景對(duì)學(xué)習(xí)結(jié)果帶來影響的能力差異。PISA 2009~2015的結(jié)果報(bào)告和相關(guān)工作論文在界定“國(guó)際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時(shí),將家庭ESCS標(biāo)準(zhǔn)調(diào)整為居于本國(guó)(地區(qū))樣本最低1/4,將學(xué)業(yè)表現(xiàn)標(biāo)準(zhǔn)調(diào)整為校正了ESCS之后的主測(cè)試領(lǐng)域成績(jī)居于國(guó)際樣本最高1/4。[5][6][7]
國(guó)際視角下的定義也被許多學(xué)者參考用于基于其他國(guó)際項(xiàng)目數(shù)據(jù)開展的抗逆學(xué)生研究。比如,埃布魯·埃爾貝爾貝(Ebru Erberber)等人的研究將家庭ESCS低下(家庭藏書量少于25本、孩子沒有獨(dú)立的房間和互聯(lián)網(wǎng),而且父母都未接受中學(xué)后教育)但學(xué)業(yè)表現(xiàn)優(yōu)秀(數(shù)學(xué)成績(jī)高于TIMSS國(guó)際基準(zhǔn))的學(xué)生界定為抗逆學(xué)生。[8]
(二)國(guó)內(nèi)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
考慮到在一些國(guó)家(地區(qū))中,根據(jù)國(guó)際視角下的定義識(shí)別出的抗逆學(xué)生數(shù)量非常少(可能不足30人),無法實(shí)現(xiàn)對(duì)學(xué)生和學(xué)校特征與抗逆結(jié)果之間關(guān)系的精確估計(jì),且很難為相應(yīng)的教育系統(tǒng)提出改進(jìn)教育結(jié)果公平的適切性建議,因此有必要考慮識(shí)別國(guó)內(nèi)的抗逆學(xué)生。在國(guó)內(nèi)視角下,家庭ESCS處于何種水平稱之為處境不利與素養(yǎng)成績(jī)達(dá)到何種水平稱之為學(xué)業(yè)表現(xiàn)超出預(yù)期都是采用國(guó)家(地區(qū))特定的標(biāo)準(zhǔn)。比如,《超越逆境:在學(xué)校取得成功的處境不利學(xué)生》報(bào)告將家庭ESCS處于本國(guó)(地區(qū))樣本最低1/3且PISA 2006科學(xué)成績(jī)處于本國(guó)(地區(qū))樣本最高1/3的學(xué)生定義為“國(guó)內(nèi)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9]在《教育公平:打破社會(huì)流動(dòng)障礙》和《PISA 2018結(jié)果報(bào)告II:哪些地方的所有學(xué)生都能成功》報(bào)告中,OECD又將識(shí)別“國(guó)內(nèi)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時(shí)使用的家庭ESCS標(biāo)準(zhǔn)調(diào)整為居于本國(guó)(地區(qū))樣本最低1/4,將學(xué)業(yè)表現(xiàn)標(biāo)準(zhǔn)調(diào)整為居于本國(guó)(地區(qū))樣本最高1/4。[10][11]
國(guó)內(nèi)視角下的定義也被許多學(xué)者參考用于本國(guó)的抗逆學(xué)生研究。比如,一項(xiàng)對(duì)土耳其中學(xué)生的研究將家庭ESCS居于樣本后1/3且數(shù)學(xué)成績(jī)居于樣本中前1/3的學(xué)生定義為抗逆學(xué)生。[12]一項(xiàng)對(duì)我國(guó)流動(dòng)留守小學(xué)生的研究將來自農(nóng)村且父母至少一方在外打工但數(shù)學(xué)成績(jī)居于全國(guó)樣本前1/3的學(xué)生定義為抗逆學(xué)生。[13]一項(xiàng)對(duì)我國(guó)初中生的研究將來自農(nóng)村且認(rèn)知能力高于全國(guó)樣本均值1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的學(xué)生定義為抗逆學(xué)生。[14]
(三)“核心技能”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
“核心技能”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定義旨在識(shí)別出哪些家庭處境不利學(xué)生擁有充分參與社會(huì)生活和有機(jī)會(huì)在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上取得成功所必備的技能。在《教育公平:打破社會(huì)流動(dòng)障礙》報(bào)告中,OECD將家庭ESCS居于本國(guó)(地區(qū))最低1/4且PISA 2015閱讀、數(shù)學(xué)、科學(xué)素養(yǎng)表現(xiàn)均達(dá)到水平3①根據(jù)各測(cè)試領(lǐng)域素養(yǎng)成績(jī)的高低,PISA將學(xué)生的閱讀、數(shù)學(xué)和科學(xué)表現(xiàn)分別劃分為7個(gè)水平,從低到高依次為水平1a、水平1b、水平2、水平3、水平4、水平5和水平6。及以上的學(xué)生界定為“核心技能抗逆學(xué)生”。在PISA中,達(dá)到水平3的學(xué)生在閱讀中開始表現(xiàn)出構(gòu)建文本意義、利用多個(gè)獨(dú)立信息片段形成精細(xì)化理解的能力,在解決數(shù)學(xué)問題時(shí)能夠處理成比例關(guān)系、進(jìn)行基本的解釋和推理,能夠處理不熟悉的科學(xué)問題。[15]
“核心技能”視角下的定義具有多種優(yōu)勢(shì):一是綜合考慮閱讀、數(shù)學(xué)和科學(xué)素養(yǎng),符合PISA關(guān)于三個(gè)領(lǐng)域的表現(xiàn)構(gòu)成個(gè)體參與社會(huì)生活和終身學(xué)習(xí)所必需的能力這一觀點(diǎn),使得不同輪次測(cè)試間的結(jié)果更具可比性。二是將抗逆視為一種區(qū)別于某領(lǐng)域卓越表現(xiàn)的積極適應(yīng)性,強(qiáng)調(diào)了確保所有學(xué)生達(dá)到使其過上充實(shí)而富有成效生活的最低標(biāo)準(zhǔn),也不顯著改變識(shí)別抗逆學(xué)生時(shí)用到的表現(xiàn)水平。三是由于不需要根據(jù)觀測(cè)的家庭ESCS與成績(jī)的關(guān)系來調(diào)整識(shí)別抗逆與否的閾值,因此,這種定義有助于進(jìn)行更容易和更穩(wěn)健的趨勢(shì)比較。[16]我國(guó)學(xué)者陸璟基于PISA 2018數(shù)據(jù)測(cè)算了各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核心技能抗逆學(xué)生”占處境不利學(xué)生和全體參測(cè)學(xué)生的百分比,并進(jìn)行了抗逆學(xué)生特征的描述和核心技能抗逆結(jié)果影響因素的分析。[17]
三、處境不利學(xué)生在認(rèn)知成就方面的抗逆結(jié)果及其影響因素
基于不同視角下的定義,國(guó)際教育測(cè)評(píng)項(xiàng)目為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計(jì)算出認(rèn)知成就抗逆學(xué)生(也稱為學(xué)業(yè)抗逆學(xué)生)比例,并且從個(gè)體、家庭、學(xué)校和國(guó)家層面識(shí)別出影響處境不利學(xué)生轉(zhuǎn)化為抗逆學(xué)生的關(guān)鍵要素,為評(píng)估教育公平狀況和尋找促進(jìn)教育結(jié)果公平的政策措施提供參考。
(一)認(rèn)知成就抗逆學(xué)生比例的國(guó)際比較
PISA基于三種視角下的定義,以抗逆學(xué)生占參測(cè)學(xué)生總數(shù)/處境不利學(xué)生數(shù)的百分比來比較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間的教育結(jié)果公平程度。相關(guān)學(xué)者也基于類似定義,采用TIMSS數(shù)據(jù)進(jìn)行了抗逆學(xué)生比例的國(guó)際比較。
根據(jù)PISA 2009數(shù)據(jù),OECD國(guó)家平均有30.6%的處境不利學(xué)生取得了超出家庭ESCS預(yù)期的閱讀成績(jī),成為國(guó)際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中國(guó)上海的該比例為75.6%,居于65個(gè)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的第1位。[18]根據(jù)PISA 2012數(shù)據(jù),OECD國(guó)家平均有6.5%的15歲學(xué)生取得了超出家庭ESCS預(yù)期的數(shù)學(xué)成績(jī),成為國(guó)際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中國(guó)上海的該比例為19.2%,居于65個(gè)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的第1位。[19]根據(jù)PISA 2015數(shù)據(jù),OECD國(guó)家平均有29.2%的處境不利學(xué)生超越了家庭ESCS低下造成的逆境,在科學(xué)成績(jī)方面實(shí)現(xiàn)了抗逆;中國(guó)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四省市的該比例為45.3%,居于72個(gè)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的第8位。[20]根據(jù)PISA 2018數(shù)據(jù),OECD國(guó)家平均有11.3%的處境不利學(xué)生取得了優(yōu)異的閱讀成績(jī),成為國(guó)內(nèi)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中國(guó)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四省市的該比例為11.7%,居于77個(gè)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的第39位,落后于多數(shù)東亞國(guó)家。[21]基于國(guó)際視角下的界定對(duì)TIMSS 2011八年級(jí)數(shù)學(xué)測(cè)試樣本的研究顯示,中國(guó)香港、中國(guó)臺(tái)灣的抗逆學(xué)生占處境不利學(xué)生的比例分別為54%和51%,在有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的28個(gè)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中分別居于第2和第4位。[22]
除了在同一輪測(cè)試中進(jìn)行國(guó)家間的橫向比較之外,PISA還縱向比較了各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在主測(cè)試學(xué)科相同的不同輪次測(cè)試中的抗逆學(xué)生比例,用于說明其教育結(jié)果公平的變化情況。結(jié)果顯示,在2003~2012年間,土耳其、墨西哥、波蘭、意大利、突尼斯和德國(guó)等國(guó)在PISA數(shù)學(xué)成績(jī)上實(shí)現(xiàn)抗逆的學(xué)生比例顯著提高,而芬蘭、新西蘭、瑞典、中國(guó)澳門、法國(guó)、西班牙、澳大利亞、丹麥、冰島、加拿大、烏拉圭等國(guó)(地區(qū))的抗逆學(xué)生比例則出現(xiàn)了顯著下降趨勢(shì)。[23]在2006~2015年間,美國(guó)、西班牙、挪威、德國(guó)、日本、丹麥、拉脫維亞、中國(guó)澳門、英國(guó)、卡塔爾、羅馬尼亞、斯洛文尼亞、保加利亞等國(guó)(地區(qū))在PISA科學(xué)成績(jī)上實(shí)現(xiàn)抗逆的學(xué)生比例顯著提高,而突尼斯、芬蘭、匈牙利、約旦和泰國(guó)的抗逆學(xué)生比例則出現(xiàn)了顯著下降趨勢(shì)。[24]
(二)認(rèn)知成就抗逆學(xué)生與非抗逆學(xué)生的區(qū)分特征
第一,抗逆學(xué)生的家庭ESCS優(yōu)于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①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指的是與抗逆學(xué)生具有相似的不利家庭ESCS,但學(xué)業(yè)表現(xiàn)較差(比如,校正了家庭ESCS影響之后的成績(jī)居于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后1/4)的學(xué)生。。根據(jù)PISA 2006數(shù)據(jù),抗逆學(xué)生和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的家庭ESCS分別低于本國(guó)平均值3/4~1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和約1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在多數(shù)參與國(guó)(地區(qū))中,抗逆學(xué)生的家庭ESCS略高于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且這種差異主要源自家庭文化資源擁有量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而不是源自家庭財(cái)富的多少和父母職業(yè)地位的高低。[25]
第二,抗逆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時(shí)間、學(xué)習(xí)情感投入多于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根據(jù)PISA 2006數(shù)據(jù),OECD國(guó)家平均而言,相比于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抗逆學(xué)生的科學(xué)學(xué)習(xí)興趣顯著更高,平均每周多花1~2小時(shí)用于學(xué)校的科學(xué)課程學(xué)習(xí)。[26]根據(jù)PISA 2012數(shù)據(jù),OECD國(guó)家平均而言,抗逆學(xué)生在測(cè)試前兩周遲到、逃課的比例分別低于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11.2和9.5個(gè)百分點(diǎn);抗逆學(xué)生的學(xué)校歸屬感、對(duì)學(xué)校的態(tài)度指數(shù)分別高于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0.04和0.12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抗逆學(xué)生的問題解決堅(jiān)持性、內(nèi)部學(xué)習(xí)動(dòng)機(jī)和工具性學(xué)習(xí)動(dòng)機(jī)分別高于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0.32、0.28和0.25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27]根據(jù)PISA 2018數(shù)據(jù),OECD國(guó)家平均而言,抗逆學(xué)生的閱讀興趣、掌握目標(biāo)動(dòng)機(jī)指數(shù)和學(xué)習(xí)目標(biāo)指數(shù)分別高于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0.64、0.22和0.16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28]
第三,抗逆學(xué)生的自我認(rèn)知比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更加積極。PISA測(cè)試顯示,OECD國(guó)家平均而言,抗逆學(xué)生的數(shù)學(xué)焦慮感指數(shù)低于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0.56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數(shù)學(xué)自我效能感、數(shù)學(xué)自我概念指數(shù)均高于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0.77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29]科學(xué)自我效能感、科學(xué)自我概念指數(shù)分別高于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0.8和0.56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30]抗逆學(xué)生擁有成長(zhǎng)心態(tài)和期望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別高于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5.8和29.2個(gè)百分點(diǎn)。[31]
(三)影響處境不利學(xué)生認(rèn)知成就抗逆結(jié)果的因素
第一,國(guó)家層面的教育投入對(duì)抗逆學(xué)生比例有顯著影響。對(duì)PISA 2009歐盟15國(guó)的分析顯示,國(guó)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年均教學(xué)時(shí)間、15年教齡教師的平均(法定)工資和學(xué)生第一次教育分流的年齡顯著正向預(yù)測(cè)處境不利學(xué)生成為國(guó)際視角下閱讀領(lǐng)域抗逆學(xué)生的發(fā)生比。[32]對(duì)PISA 2000~2012合并數(shù)據(jù)的分析顯示,對(duì)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較低的國(guó)家(地區(qū))而言,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顯著正向預(yù)測(cè)抗逆學(xué)生比例;對(duì)于所有國(guó)家(地區(qū))而言,學(xué)校教育資源的平均質(zhì)量也能正向預(yù)測(cè)抗逆學(xué)生比例。[33]
第二,學(xué)校質(zhì)量對(duì)處境不利學(xué)生的抗逆結(jié)果有顯著正向影響。PISA數(shù)據(jù)顯示,相比于生源階層弱勢(shì)學(xué)校的處境不利學(xué)生,就讀于生源階層優(yōu)勢(shì)學(xué)校的處境不利學(xué)生成為核心技能抗逆學(xué)生和國(guó)內(nèi)視角下抗逆學(xué)生的比例分別高出32.6和22.2個(gè)百分點(diǎn);[34]在控制學(xué)生和學(xué)校背景特征后,學(xué)校教育資源質(zhì)量顯著正向預(yù)測(cè)處境不利學(xué)生成為閱讀領(lǐng)域抗逆學(xué)生的發(fā)生比,[35]學(xué)校課外活動(dòng)豐富性顯著正向預(yù)測(cè)處境不利學(xué)生成為閱讀、數(shù)學(xué)和科學(xué)領(lǐng)域抗逆學(xué)生的發(fā)生比;[36]教師更多使用以學(xué)生為中心的教學(xué)策略和探究性教學(xué)策略,將有助于縮小與家庭背景相關(guān)的學(xué)生數(shù)學(xué)和科學(xué)成績(jī)差距;[37]積極師生關(guān)系、良好的學(xué)校紀(jì)律氛圍、學(xué)生間的合作能顯著提升處境不利學(xué)生的抗逆概率。[38][39]基于TIMSS 2011數(shù)據(jù)的研究顯示,教師對(duì)學(xué)生的信心顯著正向預(yù)測(cè)低家庭ESCS學(xué)生取得學(xué)業(yè)成功的發(fā)生比,[40]注重學(xué)業(yè)成功的學(xué)校氛圍、高質(zhì)量的課堂教學(xué)將對(duì)低家庭ESCS學(xué)生起到有效的補(bǔ)償作用,整體提升教育質(zhì)量。[41]
第三,學(xué)習(xí)情感態(tài)度積極的學(xué)生實(shí)現(xiàn)抗逆的概率更高。根據(jù)PISA 2006數(shù)據(jù),OECD國(guó)家平均而言,在控制學(xué)生和學(xué)校背景特征后,科學(xué)學(xué)習(xí)興趣每提高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處境不利學(xué)生成為抗逆學(xué)生的概率提高74%。[42]根據(jù)PISA 2015數(shù)據(jù),成就動(dòng)機(jī)居于前后1/4的處境不利學(xué)生成為核心技能抗逆學(xué)生和國(guó)內(nèi)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比例分別相差11.6和7.4個(gè)百分點(diǎn);在測(cè)試前兩周沒有逃學(xué)與逃學(xué)一天的處境不利學(xué)生在核心技能方面實(shí)現(xiàn)抗逆的比例相差12.7個(gè)百分點(diǎn),成為國(guó)內(nèi)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比例相差6.9個(gè)百分點(diǎn)。[43]
第四,家長(zhǎng)支持程度與認(rèn)知成就抗逆結(jié)果之間呈正相關(guān)。根據(jù)PISA 2018數(shù)據(jù),學(xué)業(yè)抗逆力與家長(zhǎng)支持之間呈現(xiàn)正相關(guān),在絕大多數(shù)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中,家長(zhǎng)情感支持指數(shù)居于前1/4的學(xué)生中,在閱讀領(lǐng)域?qū)崿F(xiàn)學(xué)業(yè)抗逆的比例顯著高于家長(zhǎng)情感支持較弱的學(xué)生。[44]
第五,學(xué)生和學(xué)校背景特征的影響。學(xué)生的性別、移民背景、留級(jí)經(jīng)歷、學(xué)前教育經(jīng)歷,以及學(xué)校所在地、學(xué)校性質(zhì)對(duì)抗逆結(jié)果有顯著影響。根據(jù)PISA 2015數(shù)據(jù),有無移民背景、有無留級(jí)經(jīng)歷、接受學(xué)前教育經(jīng)歷與否、城市與農(nóng)村、普通學(xué)校與職業(yè)學(xué)校的處境不利學(xué)生中,在核心技能方面實(shí)現(xiàn)抗逆的比例分別相差7.4、21.3、6.6、3.8和12.2個(gè)百分點(diǎn),成為國(guó)內(nèi)視角下科學(xué)領(lǐng)域抗逆學(xué)生的比例分別相差4.1、10.8、2.6、2.7和7.2個(gè)百分點(diǎn);處境不利男生成為國(guó)內(nèi)視角下抗逆學(xué)生的比例高于女生2.7個(gè)百分點(diǎn)。[45]
四、處境不利學(xué)生在社會(huì)與情感幸福感方面的抗逆結(jié)果
在關(guān)注認(rèn)知成就表現(xiàn)的同時(shí),PISA還將處境不利學(xué)生的社會(huì)和情感幸福感作為其教育結(jié)果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探究。比如,PISA 2015結(jié)合學(xué)生的總體幸福感、社會(huì)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將對(duì)生活感到滿意、在學(xué)校感到有融入感且沒有遭受考試焦慮的處境不利學(xué)生定義為“社會(huì)情感抗逆學(xué)生”。[46]參考這一定義,陸璟將“對(duì)生活感到滿意、在學(xué)校感到有融入感且在失敗時(shí)不懷疑自己”的處境不利學(xué)生定義為“社會(huì)情感抗逆學(xué)生”,[47]并利用PISA 2018的數(shù)據(jù)分析了中國(guó)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四省市抗逆學(xué)生的分布、學(xué)習(xí)特點(diǎn)和相關(guān)因素。
(一)社會(huì)情感抗逆結(jié)果的國(guó)際比較
根據(jù)PISA 2015數(shù)據(jù),OECD國(guó)家平均而言,在處境不利學(xué)生中,有41.3%的學(xué)生不存在考試焦慮、80.5%的學(xué)生在學(xué)校有歸屬感、66.4%的學(xué)生對(duì)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26.2%的學(xué)生在社會(huì)和情感幸福感方面實(shí)現(xiàn)了抗逆。中國(guó)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四省市的上述比例分別為36.9%、73.4%、52.2%和16.3%,在有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的49個(gè)經(jīng)濟(jì)體中,分別排在第27、第35、第45和第39位。[48]根據(jù)PISA 2018數(shù)據(jù),中國(guó)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四省市的處境不利學(xué)生中,有54.6%的學(xué)生對(duì)生活總體上感到滿意,有78.9%的學(xué)生在學(xué)校感覺不是局外人,有48.5%的學(xué)生在失敗時(shí)不懷疑自己的未來計(jì)劃,有27.8%的學(xué)生在社會(huì)和情感幸福感方面實(shí)現(xiàn)了抗逆,在有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的經(jīng)濟(jì)體中,分別排在第60、第24、第32和第31位[49];與閱讀、數(shù)學(xué)、科學(xué)三項(xiàng)成績(jī)?cè)?9個(gè)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中均排名第一的結(jié)果相比,中國(guó)四省市在社會(huì)情感幸福感這一教育結(jié)果上的公平程度較差。
(二)認(rèn)知成就抗逆結(jié)果和社會(huì)情感抗逆結(jié)果的關(guān)系
認(rèn)知成就抗逆學(xué)生是否會(huì)因?yàn)槠鋵W(xué)業(yè)成功而遭受社會(huì)孤立或情緒壓力,還是情感幸福感方面的良好表現(xiàn)會(huì)促進(jìn)處境不利學(xué)生取得更好的成績(jī)?研究表明,兩種類型的抗逆力是相輔相成的:認(rèn)知成就抗逆學(xué)生也更有可能在社會(huì)情感方面實(shí)現(xiàn)抗逆。根據(jù)PISA 2015數(shù)據(jù),OECD國(guó)家平均而言,相比于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國(guó)際視角、國(guó)內(nèi)視角和核心技能抗逆學(xué)生成為社會(huì)情感抗逆學(xué)生的可能性分別高出59%、78%和66%;中國(guó)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四省市三類認(rèn)知成就抗逆學(xué)生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情感抗逆的比例分別是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的1.90、2.18、2.02倍。在部分國(guó)家,認(rèn)知成就和社會(huì)情感抗逆結(jié)果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度更大,比如在冰島,國(guó)際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成為社會(huì)情感抗逆學(xué)生的發(fā)生比是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的2.64倍;在比利時(shí)和冰島,國(guó)內(nèi)視角下的抗逆學(xué)生成為社會(huì)情感抗逆學(xué)生的發(fā)生比是低成就學(xué)生的將近三倍;在巴西和墨西哥,核心技能抗逆學(xué)生成為社會(huì)情感抗逆學(xué)生的發(fā)生比是低成就學(xué)生的將近三倍。[50]然而,相關(guān)研究也發(fā)現(xiàn),對(duì)大多數(shù)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而言,認(rèn)知成就抗逆學(xué)生比例高和社會(huì)情感抗逆學(xué)生比例高是較難同時(shí)實(shí)現(xiàn)的。[51]因此,對(duì)于處境不利學(xué)生而言,促進(jìn)學(xué)業(yè)、社會(huì)和情感發(fā)展結(jié)果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五、抗逆學(xué)生研究的特點(diǎn)及意義
自2011年首次發(fā)布相關(guān)專題報(bào)告以來,以PISA為代表的國(guó)際教育測(cè)評(píng)項(xiàng)目圍繞抗逆學(xué)生與處境不利低成就學(xué)生的區(qū)分特征、以抗逆學(xué)生比例衡量的教育結(jié)果公平及其進(jìn)展?fàn)顩r,以及不同層面促進(jìn)處境不利學(xué)生轉(zhuǎn)化為抗逆學(xué)生的因素開展了系統(tǒng)研究,這些研究具有以下幾個(gè)方面的特點(diǎn)和意義。
首先,抗逆學(xué)生的研究在多個(gè)維度上持續(xù)深化。一是在抗逆學(xué)生的界定方面,經(jīng)過幾輪探索,PISA發(fā)展出國(guó)際視角、國(guó)內(nèi)視角和核心技能視角下對(duì)認(rèn)知成就抗逆學(xué)生的界定,以及基于生活、社會(huì)和心理幸福感的社會(huì)情感抗逆學(xué)生的界定,滿足了不同國(guó)家(地區(qū))間橫向比較、同一國(guó)家(地區(qū))縱向比較,以及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內(nèi)部基于抗逆結(jié)果改進(jìn)教育公平的實(shí)踐需要。二是在抗逆學(xué)生的識(shí)別方面,PISA將國(guó)際和國(guó)內(nèi)視角下篩選處境不利學(xué)生的標(biāo)準(zhǔn)從居于參測(cè)國(guó)(地區(qū))前1/3調(diào)整為前1/4,將(校正了家庭背景影響之后的)素養(yǎng)表現(xiàn)在國(guó)際或國(guó)內(nèi)樣本中的位置居于前1/3調(diào)整為前1/4,使得識(shí)別出的抗逆學(xué)生數(shù)量更合理,且保證了抗逆學(xué)生與非抗逆學(xué)生在個(gè)人和學(xué)校特征上的區(qū)分性。三是在抗逆結(jié)果的分析方面,從最初只基于平均數(shù)差異檢驗(yàn)比較認(rèn)知成就抗逆學(xué)生與非抗逆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情感態(tài)度和所在學(xué)校的基本特征,到基于單輪次的數(shù)據(jù)、使用單水平或多水平邏輯回歸探討不同層面影響認(rèn)知成就抗逆學(xué)生形成的因素,再到綜合不同輪次測(cè)試數(shù)據(jù)、使用面板數(shù)據(jù)固定效應(yīng)模型來探討宏觀層面的因素對(duì)抗逆和教育結(jié)果不平等的影響,以及基于邏輯回歸等探討認(rèn)知成就抗逆與社會(huì)情感抗逆結(jié)果的相互關(guān)系,分析不斷深化。
其次,抗逆學(xué)生的研究具有多個(gè)方面的理論價(jià)值。一是,其為教育結(jié)果公平的測(cè)度與改進(jìn)研究提供了新視角。以往研究主要基于標(biāo)準(zhǔn)差、差異系數(shù)和泰爾指數(shù)等來測(cè)量不同學(xué)生群體的學(xué)習(xí)結(jié)果差異,或基于回歸分析探討家庭背景對(duì)學(xué)生學(xué)業(yè)成就的影響,以此來評(píng)估教育結(jié)果公平,并探析對(duì)解釋成績(jī)差距或縮小家庭背景與學(xué)業(yè)成就間關(guān)系有貢獻(xiàn)的因素。國(guó)際教育測(cè)評(píng)項(xiàng)目以抗逆學(xué)生比例作為教育結(jié)果公平的重要指標(biāo),以新的視角來勾勒處境不利學(xué)生發(fā)展與國(guó)家教育質(zhì)量、教育公平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實(shí)現(xiàn)了研究視角的創(chuàng)新。二是,其拓展了基礎(chǔ)教育階段學(xué)校情境中人力資本投資的研究?jī)?nèi)容。傳統(tǒng)的教育生產(chǎn)函數(shù)研究以學(xué)生的認(rèn)知能力或?qū)W業(yè)成就為產(chǎn)出指標(biāo),以學(xué)生的個(gè)人特征和學(xué)習(xí)努力程度、家庭背景和各類資本、學(xué)校的辦學(xué)條件和師資等為投入指標(biāo)進(jìn)行各要素的邊際效率分析。國(guó)際教育測(cè)評(píng)項(xiàng)目將排除家庭背景影響之后的、學(xué)生的學(xué)業(yè)或社會(huì)情感抗逆力視為一種特殊的人力資本,探索其投入產(chǎn)出機(jī)制,開辟了人力資本投資研究的新領(lǐng)域,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轉(zhuǎn)了教育與社會(huì)流動(dòng)領(lǐng)域研究關(guān)于家庭和學(xué)校雙重再生產(chǎn)作用的悲觀論調(diào)。三是,其為檢驗(yàn)教育效能理論和教育公平理論增加了新的有利證據(jù)。教育效能研究設(shè)定了教育生產(chǎn)過程的基本形態(tài),識(shí)別出學(xué)校因素對(duì)學(xué)生學(xué)業(yè)成就的一般性影響,但是關(guān)于學(xué)校因素在補(bǔ)償特殊學(xué)生群體方面可能發(fā)揮的均等化作用的研究仍然較少。國(guó)際教育測(cè)評(píng)項(xiàng)目通過分析影響抗逆力的因素,檢驗(yàn)了教育效能理論模型對(duì)解釋弱勢(shì)群體人力資本生產(chǎn)的適用性;通過對(duì)個(gè)體、家庭、學(xué)校和國(guó)家層面的教育投入、教育過程對(duì)抗逆結(jié)果的影響效應(yīng)分析,揭示了不同層面的教育機(jī)會(huì)公平、過程公平對(duì)教育結(jié)果公平的影響,驗(yàn)證了教育公平的相關(guān)理論。[52]
最后,抗逆學(xué)生的研究發(fā)現(xiàn)對(duì)于降低教育不平等的政策和實(shí)踐有一定的參考價(jià)值。國(guó)際項(xiàng)目抗逆學(xué)生的相關(guān)研究說明,貧窮和低教育成就不是命運(yùn),處境不利學(xué)生有很大可能在國(guó)家、學(xué)校、家庭和個(gè)人的積極努力下縮小與處境有利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結(jié)果差距。具體而言,政府可以通過保障教育支出、提升教師工資等政策促進(jìn)更多的家庭處境不利學(xué)生轉(zhuǎn)化為抗逆學(xué)生;教育行政部門可以通過給處境不利學(xué)生提供在高質(zhì)量學(xué)校就讀的機(jī)會(huì)、給處境不利學(xué)生集中的學(xué)校配以高質(zhì)量的教育資源來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學(xué)校可以通過改進(jìn)課堂教學(xué)方式、提供豐富的課程活動(dòng)以及構(gòu)建支持性的學(xué)校氛圍來彌補(bǔ)處境不利學(xué)生在家庭學(xué)習(xí)資源、校外補(bǔ)償性學(xué)習(xí)機(jī)會(huì)和家庭內(nèi)社會(huì)資本等方面的不足,從而發(fā)揮對(duì)家庭教育投資的部分替代作用,提升處境不利學(xué)生獲得超出預(yù)期表現(xiàn)的可能性;處境不利學(xué)生家長(zhǎng)可以通過營(yíng)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圍、為孩子提供心理和行為層面的支持來幫助其縮小與家庭背景優(yōu)勢(shì)同伴的發(fā)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