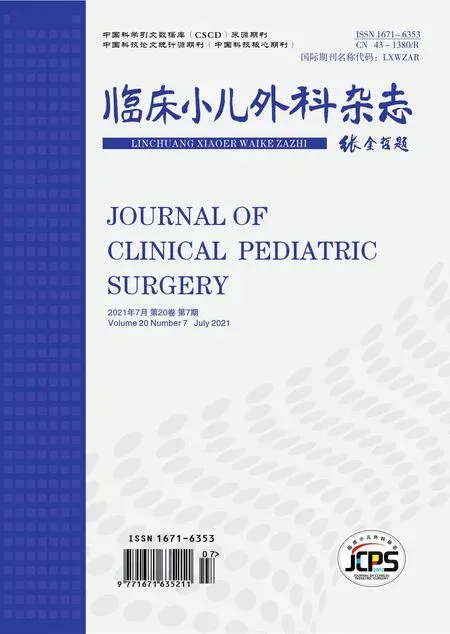髓母細胞瘤分子分型及危險分層的研究進展
李偉清 綜述 董子龍 陳 乾 審校
髓母細胞瘤(medulloblastoma,MB)是兒童時期最常見的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惡性腫瘤,約占所有兒童CNS腫瘤的15%~20%[1]。WHO中樞神經系統腫瘤分級將其歸類為Ⅳ級,組織學上惡性程度高,極易通過腦脊液傳播,主要分為經典型(classic)、促結締組織增生/結節型(desmoplastic/nodular,DN)、廣泛結節型medulloblastoma with extensive nodularity,MBEN)和大細胞/間變型(large cell/anaplastic,LC/A)四種病理亞型[2]。MB兒童患病年齡呈現3~4歲和8~10歲雙峰特點[2,3]。目前基于病理分型的手術聯合放化療的綜合治療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遠期生存率,5年生存率標危組已提高到85%,高危組也提高到70%[4]。然而,MB預后與治療并發癥密切相關,如神經認知障礙、內分泌缺陷和繼發性腫瘤等[5]。另外,嬰幼兒和有轉移、復發的患者長期生存率仍然很低[6,7]。近年來,整合基因組學研究表明,MB不是一個單一形態的實體腫瘤,在分子水平上,至少可以分出四種在生物學表現、臨床特征及預后方面均具有明顯差異的分子亞型[8]。國內外學者對MB進行了分子分型及危險分層,進一步改善了患者的預后。2016年WHO更新了中樞神經系統腫瘤的分類,新增MB四種分子分型,分別為WNT活化型、SHH活化型、Group 3型、Group 4型,SHH活化型再分為TP53突變型和野生型[2]。目前推薦采用DNA甲基化圖譜取代基因表達圖譜作為MB分子分型診斷的金標準[9-11]。伴隨研究方法的不斷更新,腫瘤內的異質性進一步被識別,可將MB根據原來的研究基礎進一步細分為7~12個亞型[12,13]。
一、髓母細胞瘤分子分型特點
(一)WNT型MB
WNT型MB起源于胚胎下菱唇祖細胞,根據在該亞群的發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的WNT信號通路命名[14,15]。此類發病人數占比最少,約占所有MB的11%,青少年多見,極少見于嬰幼兒,男女性別比例約1∶1。在組織學水平上,幾乎均為經典型,極少部分為LC/A型[16]。該型是所有亞型中預后最好的,很少發生轉移,16歲以下的MB患者5年生存率超過95%,可能與該型缺乏完整的血腦屏障,允許高濃度的化療藥物在腫瘤內積累有關[17]。CTNNB1基因的第3號外顯子活化突變是WNT亞型最顯著的標志,而CTNNB1基因編碼的β-catenin蛋白是WNT信號通路重要的效應因子,β-catenin在細胞核內不斷聚集,通過與TCF-LEF家族轉錄因子的共同作用,進一步激活下游靶基因,從而引起該型腫瘤的發生[7,18]。缺乏體細胞CTNNB1突變的WNT型MB常含有腫瘤抑制基因APC的突變[19]。腫瘤抑制基因APC可通過調控腺瘤性結腸息肉病 (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APC)蛋白介導β-catenin的降解[18]。這正好可以解釋由于APC基因突變導致的Turcot綜合征通常具有明顯的遺傳易感性,且常合并MB的發生[20,21]。另外,比較常見的突變還包括DDX3X(36%)、SMARCA4(也稱為BRG1,19%)、CSNK2B(14%)、PIK3CA(11%)、EPHA7(8%)和TP53(14%)[9]。盡管TP53突變是SHH型MB和其他癌癥的高風險標記,但對于WNT型MB患者,TP53突變在生存率上沒有明顯差異[7]。細胞遺傳學上的顯著特征是6號染色體出現單倍體,常同時伴有CTNNB1基因突變[22]。然而這兩者并非存在于所有的WNT型MB中,臨床上常規將兩者中的任意一個陽性作為WNT型MB的判定標準,但這樣會漏診10%~15%的真正WNT型MB患者[23]。Schwalbe等[8]通過對DNA甲基化的分析研究發現,該型顯著的五個基因高甲基化位點分別為P360(ASCL2)、E76(ASCL2)、P609(ASCL2)、P49(MT1A)、E13(MT1A)和低甲基化位點分別為P344(HDAC7A)、P493(RAB32)、E331(DDR2)、E273(HFE)、P414(HDAC1)。有研究者用SNF(similarity network fusion)的方法進一步鑒別出WNTa 和WNTb兩個子亞型:WNTa主要分布在兒童群體,有普遍存在的6號染色體單倍體;WNTb主要分布在成年人群體,常伴有6號染色體的二倍體[22]。
(二)SHH型MB
SHH型MB起源于小腦的顆粒神經元前體細胞(granule neuron precursors,GNPs),常位于一側小腦半球,同樣根據在亞群的發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的SHH信號通路命名[14,15,24]。SHH信號通路在誘導GNPs增殖和遷移小腦發育的過程中起重要作用[7]。該型約占所有MB的28%,好發生于嬰幼兒和成人,男女性別比近1∶1。組織學上可表現為四種病理的任何一種,但幾乎所有MBEN都屬于SHH 型,預后中等,5年生存率在60%~80%[16]。大部分SHH型MB的SHH信號通路相關基因均存在生殖系或體細胞突變和拷貝數改變,包括PTCH1(43%)和SUFU(10%)的失活突變或缺失、SMO的活化突變(9%)、GLI1或GLI2(9%)和MYCN(7%)的擴增[9]。PTCH1的失活突變或缺失直接導致受跨膜蛋白PTCH1抑制的G蛋白偶聯受體SMO發生轉位至纖毛膜,活化下游GLI蛋白家族從其自然抑制因子SUFU釋放出來,然后進入細胞核,轉錄激活參與小腦GNP增殖的基因,最終導致腫瘤形成[1,25,26]。TP53突變發生在21%的SHH型MB中,預后很差,是導致該型MB最重要的危險因素[27]。另外TERT(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啟動子突變約在83%的SHH型MB中發現,年齡分布差異明顯,98%的成人SHH型MB攜帶體細胞TERT啟動子突變,而嬰兒和兒童SHH型MB分別占13%、21%[28,29]。常見于神經膠質瘤的IDH1基因突變也在該亞型中被發現,這些突變導致DNA高甲基化表型與在其他IDH1/2突變型癌癥中發現的表型類似[23]。細胞遺傳學標志性特征包括染色體9q和10q的缺失,這直接導致關鍵的腫瘤抑制基因丟失,如PTCH1(位于9q22)和SUFU(位于10q24),它們分別編碼SHH信號的負調節因子,以及其他潛在的調控因子[30]。顯著的五個基因高甲基化位點分別為P1008(MSH2)、P270(CCKAR)、E79(CCKAR)、E90(DSC2)、P93(IL16),低甲基化位點分別為E9(VAV1)、P317(VAV1)、E273(HFE)、P833(TGFB1)、E333(MET)[10]。Schwalbe等[13]研究發現可依據年齡將SHH型再分為MBSHH-Infant(<4.3 歲)和MBSHH-Child(≥4.3 歲):MBSHH-Infant病理分型多為DN型,富含SUFU突變,預后較好,5年總生存率約為62%;MBSHH-Child病理多為LC/A型,主要表現為TP53、TERT突變和MYCN、GLI2的擴增,DNA甲基化水平高,染色體9q缺失和9p獲得,5年總生存率約為58%。Robinson等[31]在研究≤5歲兒童SHH亞群MB中,發現了兩種不同的甲基化亞型,并命名為iSHH-Ⅰ和iSHH-Ⅱ。iSHH-Ⅰ中位年齡為2.0歲,男女比1.3∶1,富含SUFU突變、染色體2獲得,預后較差,5年無進展生存率為27.8%;iSHH-Ⅱ中位年齡亦為2.0歲,男女比例1∶1.3,富含SMO活化突變、染色體9q缺失,預后較好,5年無進展生存率為75.4%。Cavalli[12]等綜合聚類分析鑒別出SHHα、SHHβ、SHHγ和SHHδ四個子亞型:SHHα預后最差,TP53突變,富含MYCN、GLI2、YAP1擴增并染色體9q、10q和17p缺失;SHHβ多見于嬰幼兒,多伴有轉移,預后較差;SHHγ病理多為MBEN,預后較好;SHHδ主要由成年人組成,富含TERT啟動子突變[12]。
(三)Group3型MB
Group3型MB真正起源尚不清楚,常位于腦干附近的第四腦室[32]。有研究顯示Trp53缺失的小腦祖細胞可以轉化為與之類似的腫瘤[33]。該亞型MB約占所有MB的27%,好發于10歲以下的兒童,成人罕見,男女性別比近2∶1。病理類型以經典型為主,但大部分LC/A型也屬于此型,易發生轉移,臨床預后最差[16]。MYC基因高水平擴增是該型最顯著的特征,常同時伴有非編碼RNAPVT1共擴增,后者可以協助MYC蛋白高水平穩定表達[9,34]。也有研究發現,存在PVT1的1號和3號外顯子與MYC的2號和3號外顯子會發生融合轉錄[35]。其它突變率較高的基因還包括SMARCA(9%)、KBTBD4(6%)、CTDNEP1(5%)和KMT2D(5%);此外還有MYCN(5%)和OTX2(3%)的擴增,OTX2作為一種轉錄因子,在控制不同祖細胞分化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7,9,23]。已有研究識別出原癌基因GFI1和GFI1B在大約1/3的Group3型MB會出現互斥的活化,導致體細胞基因重排[36]。循環性基因事件通路分析揭示Notch和TGF-β信號通路相關基因在此型中出現顯著的過度表達[23]。細胞遺傳學方面主要表現為染色體1q、7和17q的擴增,以及10q、11q、16q和17p的缺失。此外還存在等臂染色體17q(isochromsome17q,i17q),可作為Group 3亞型MB不良預后的重要標志[37,38]。另外,一些微小RNA(如MiR-182、MiR-135b等)在Group 3型MB中可呈過表達[39]。NPR3蛋白免疫組化染色陽性能否作為Group 3的特征性標志物有待進一步研究確認[1,8]。顯著的五個基因高甲基化位點分別為P969(WRN)、E34(FES)、E273(HFE)、P223(FES)、P93(IL1RN),低甲基化位點分別為P668(BLK)、E102(ZNFN1A1)、P605(THBS2)、E268(PLA2G2A)、P226(CHI3L2)[10]。Schwalbe等[13]將Group3型分為MBGrp3-HR和MBGrp3-LR:MBGrp3-HR病理多為LCA型,富含MYC擴增、GFI1突變、i17q,還有大量甲基化CpG位點,5年總生存率為37%;MBGrp3-LR病理多為經典型,嬰幼兒居多,細胞遺傳學表現為多個染色體的缺失,預后相對較好,5年總生存率為69%[13]。Cavalli等[12]綜合聚類分析結果鑒別出Group3α、Group3β and Group3γ三個子亞型:Group3α分布為大部分嬰幼兒,多伴轉移,伴8q缺失,預后相對較好;Group3β轉移發生較少,GFI1和GFI1B癌基因的活化頻率更高,OTX2擴增;Group3γ預后較差,伴8q獲得,富含i17q,MYC(8q24)拷貝數增加。
(四)Group4型MB
Group4型MB疑似起源于胚胎上菱唇前體細胞,與Group3型相似,也好發于腦干附近的第四腦室[31,40]。該型發病人數約占所有MB的34%,發病年齡高峰在5~13歲,男女性別比近2∶1,組織學以經典型最常見[16]。預后中等和SHH型類似,介于WNT型和Group3型之間。Group4亞型最顯著的驅動事件為增強子劫持介導的PRDM6活化過表達[23]。也常見SNCAIP基因(位于5q23.2)的串聯復制[35]。PRDM6位于SNCAIP下游近600 kb的位置,且PRDM6在有SNCAIP相關的結構變異的Group 4型中MB表達顯著提高[23]。其他的基因突變還包括KDM6A(9%)、ZMYM3(6%)、KMT2C(6%)、KBTBD4(6%)的突變,以及MYCN(6%)和OTX2的擴增(6%)、CDK6(6%)和GFI1和(或)GFI1B過表達(5%~10%)[23]。有研究顯示,卵泡素相關蛋白5(follistatin-related protein 5,FSTL5)是Group 4亞型MB預后不良生物學標記物[41]。大量染色體畸變在該型中被發現,最常見的結構改變為i17q,占比約80%[7]。然而Group4型MB,i17q在判斷預后方面不如在Group 3型中明顯[38]。另外還有染色體7(40%~50%)、染色體17q(>80%)的擴增,染色體8(40%~50%)、染色體11(>30%)、染色體17p (>75%)的缺失[34]。顯著的五個基因高甲基化位點分別為P993(WNT10B)、E189(TRIM29)、P414(HDAC1)、E136(MMP10)、E333(MET),低甲基化位點分別為P307(PIK3R1)、E79(CCKAR)、Seq48S1(HIC1)、P270(CCKAR)、P581(RAN)[10]。Schwalbe等[13]將Group4型也分為MBGrp4-HR和MBGrp4-LR:MBGrp4-HR,病理多為經典型,多有PRDM6的擴增;MBGrp4-LR病理多為經典型,MYCN擴增明顯,伴染色體7、 17q的擴增和染色體8、11的缺失,5年總生存率約為80%。Cavalli等[12]綜合聚類分析鑒別出Group4α、Group4β和Group4γ三個子亞型:Group4α富含MYCN的擴增,染色體8p的缺失和7q的擴增;Group4βSNCAIP擴增明顯,同時伴有i17q的廣泛存在;Group3γ富含CDK6的擴增增加[12]。
二、髓母細胞瘤危險分層
目前國內根據年齡、手術切除程度、有無轉移、病理類型將MB進行分組。對于年齡>3歲的兒童MB,標危的判定標準為:腫瘤完全切除或近完全切除(殘留病灶≤1.5 cm2),無擴散轉移;高危的判定標準為:手術次全切除(殘留病灶>1.5 cm2);伴有轉移疾病(包括神經影像學播散性疾病,手術14 d后腰穿或腦室腦脊液陽性細胞學證據或顱外轉移;病理組織學彌漫間變型)。對于年齡≤3歲兒童MB,標危的判定標準為:同時符合腫瘤完全切除或近完全切除(殘留病灶≤1.5 cm2)、無擴散轉移、病理亞型為促結締組織增生型和廣泛結節型兩項標準;除標危外全部判定為高危[42]。2015年海德堡會議就結合分子分型重新定義兒童(3~17歲)MB危險分層達成共識。根據預后5年生存率劃分為四個組: ①低危組(>90%):無擴散轉移的WNT型、無擴散轉移和伴染色體11的缺失或染色體17的獲得的Group 4型; ②標危組(75%~90%):無擴散轉移、不伴TP53突變和無MYCN擴增的SHH型,無擴散轉移和MYC擴增的Group 3型,無擴散轉移和不伴染色體11的缺失的Group 4型; ③高危組(50%~75%):伴有轉移的SHH型或Group 4型,MYCN擴增的SHH型; ④超高危組(<50%):伴有轉移的Group 3型,伴有TP53突變的SHH型[43]。2017年Schwalbe等[13]通過結合新的分子分型和對215例3~16歲MB患者建立生存模型分析,根據5年無進展生存率提出新的危險分層: ①低危組(>90%):MBWNT,沒有高危標志的MBSHH-Child(高危標志:伴有轉移,術后殘留病灶>1.5 cm2,大細胞型/間變型,MYCN擴增),沒有MYC擴增和伴染色體13缺失的MBGrp3/Grp4; ②標危組(75%~90%):沒有MYC擴增的MBGrp3-LR/Grp4-LR; ③高危組(40%~75%):沒有MYC擴增的MBGrp3-HR/Grp4-HR; ④超高危組(<40%):有高危標志的MBSHH-Child,MYC擴增的MBGrp3。
三、小結和展望
臨床上不同的MB患者在疾病進展及預后上存在明顯的差異,依據目前的危險分層及據此進行的分層治療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部分患者過度治療或治療不足的問題。隨著分子生物學研究的進展,MB分子分型不斷完善,精準醫學不斷進步,結合分子分型、臨床特點、病理分型等因素對MB進行更加精確的危險分層,指導MB患者個體化治療,可幫助患者從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