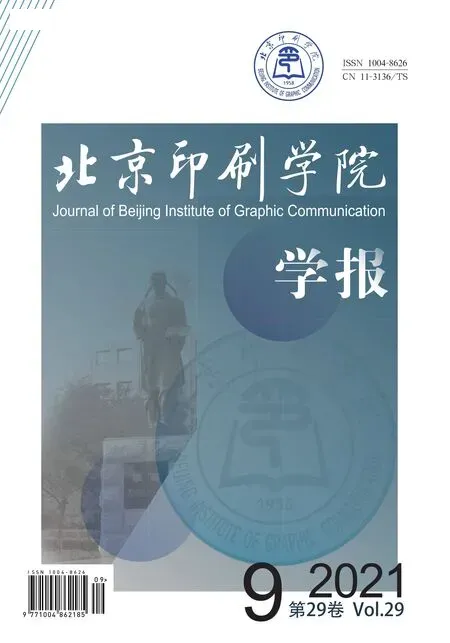本土化演變
——試析我國鄉土現實主義油畫變遷
曾永明
(福建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福州 350007)
結合歷屆全國美展的油畫獲獎作品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鄉土現實主義題材作品占比最大,如《陽關三疊》《工棚》《早點》等,由此可見,鄉土現實主義在藝術家和國人內心中的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現階段鄉土現實主義油畫在我國存在被邊緣和冷落之勢,由此催生的一系列挑戰必須引起重視。
一、本土化演變的源頭
為深入了解我國鄉土現實主義油畫的本土化演變,首先需要從現實主義和傳統文化鄉土情結入手進行分析。圍繞現實主義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其存在藝術的寫實手法和藝術的創作方法兩層含義。我國理論界將現實主義定義為,“凡在繪畫中關注現實、表現的思想”,因此,現實主義繪畫在傳統意義上需要對現實生活的本質進行反映,同時需要采用寫實手法。現實主義能夠立足于現實生活,關注生活環境,實現現實與藝術審美關系的客觀反映,實現人的靈魂與情感挖掘。寫實表現手法屬于一般情況下現實主義繪畫的載體。分析我國現實主義藝術可以發現,其主張準確而詳盡地關注現實問題和社會生活,底層普通民眾生存狀態屬于其中重點,這是我國現實主義藝術的生存和發展的現實出發點及理論依據。圍繞傳統文化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鄉土情結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極高。
作為文明古國,我國長期以農業為本,在歷史和社會的發展中農民、農村、農業的地位極高,這使得農耕文化與傳統文化結合在一起,濃厚的鄉土文化情節得以形成。鄉土文化屬于同時具備空間和時間因素的時空概念。作為一種特定生活模式,鄉土文化形成于特定地域文化背景,這里的“地域”不單單屬于地理概念,也可以視作國家、民族、族系的歷史文化沉淀。作為“文化”的地域化,鄉土文化在我國的影響力極大。在中國人形象譜系中,農民形象屬于最普遍、最主要的一種,在文學藝術各個階段均有所體現。精神層面的文學藝術必須關注農民的生存環境、生存狀態、社會心理和精神狀態。民族性格心理的形成受到的傳統文化觀念影響較為深遠,這種影響在故土、鄉情、鄉音等文化符號中均有所體現,大量寄托對故土的眷戀、對鄉音鄉情情誼的藝術作品受此影響在不同時期大量涌現[1]。
結合上述分析及相關研究可以發現,我國鄉土現實主義油畫的本土化演變源于鄉土與現實主義的結合,寫實油畫的形成和發展便屬于這種結合的代表。相較于傳統的中國畫、雕塑、版畫,寫實手法表現的油畫注重表現物體的空間感和體積感,同時存在擅長細微刻畫、表現力強、色彩豐富的特點,客觀事物對象的真實描述可由此實現,這也屬于寫實油畫的優勢所在。我國的現實主義油畫引進后,寫實占據的位置極高,同時與傳統文化中鄉土文化存在密切聯系。
五四運動后,我國油畫藝術中的寫實油畫開始反映鄉土題材。受大批留學歸來的美術學子影響,具有鄉土氣息的農民形象在20世紀30年代前后出現于我國油畫作品中,這與當時油畫藝術和整個社會戰爭環境對“現實主義”的選擇存在直接關聯。深入分析可以發現,在“藝術當隨時代”的鐵則下,面對抗戰爆發、國難當頭、民生凋敝帶來的殘酷社會現實,前輩藝術家在從海外歸來后,紛紛從西方經典油畫藝術的形式結構、繪畫語言轉向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基于對普通勞苦大眾的同情和關注,大量現實主義精神、寫實類型的作品不斷涌現,中國油畫因此“不斷在沉重的現實中喘息和掙扎”。在現實主義發展與現實環境完美結合下,鄉土現實主義從特殊時期開展不斷發展壯大,普通農民形象也因此成為鄉土現實主義油畫創作核心[2]。
二、單一語言發展演變
(一)鄉土啟蒙時期
鄉土啟蒙時期指的是五四運動后,留學歸來的美術學子開展的改造中國畫探索,先進的理念和教學方法由此傳入我國,這屬于表現農民形象的我國鄉土現實主義油畫源頭。《敦煌農民》《四川農民》《棄民圖》等作品均屬于這一時期刻畫的底層勞動人民形象代表,明顯的鄉土的表象已經存在,時代精神下敏感的藝術家們紛紛通過畫筆揭露舊中國的丑惡。以王悅之的《棄民圖》為例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在對“破產”農民形象的描繪中,王悅之采用了類似中國畫線描方法,對油畫的線條和色彩進行了針對性改造,使作品因此更好地被國人所接受和理解,同時得以兼顧中國畫作品的美學特點。鄉土啟蒙時期的鄉土現實主義油畫作品中農民形象多以“受害者”“斗爭者”和“壓迫者”等“類”的總體形象出現,嚴格意義上這類作品僅具備現實主義因素,在藝術家認識深度方面尚存在一定不足,但藝術家們在將農民和“國民”融合、將民族苦難與個人苦難視為一體的探索上具備較高借鑒價值,對我國鄉土現實主義油畫的本土化演變帶來的影響也較為深遠[3]。
(二)鄉土融合時期
鄉土融合時期,與早期“海歸”藝術家們創建的專業美術機構、學校存在密切關聯,如上海圖畫學術院、北京美術學校、國立藝術院校,真正意義上的本土油畫家由此得以大量涌現。鄉土融合時期的鄉土現實主義油畫的本土化演變需關注新中國成立前后存在的差異。
在新中國成立前,藝術家更多關注抗戰爆發所帶來的苦難,此時畫家筆下衣衫襤褸的農民外表蘊含著激揚的斗志,遭受苦難最深重、處于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形象因此大量出現于油畫作品中。以徐悲鴻的相關創作為例,通過結合古典主義嚴格而完美的造型和印象主義的光與色表現,其創作的《徯我后》《田橫五百士》等優秀作品對中國規范化的油畫形成和發展也帶來了深遠影響。此外,解放區畫家圍繞連環畫、版畫等輕便繪畫形式開展的探索也需要得到重視,這種情感、思想上的鍛煉對鄉土現實主義油畫的本土化演變帶來的影響同樣較為深遠。
在新中國成立后,客觀環境變化顯著,國家對藝術表現力豐富和現實生活反映力度深刻的油畫給予了高度重視,鄉土現實主義油畫的本土化演變速度因此進一步加快。這一時期的鄉土現實主義油畫創作主要圍繞歷史題材、民族化展開,比如:《地道戰》《開鐐》《開國大典》等革命歷史畫屬于歷史題材探索代表,作品中的農民更多擁有無畏的英勇氣概和革命熱情,同時成為了“革命者”或“反抗者”角色;《山歌》《延安人》《天安門前》等作品屬于民族化探索代表,這源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指導,通過借鑒傳統書法、傳統國畫、傳統年畫并尋找東西方文化結合點。以董希文的《山歌》為例,這一藏民肖像畫的創作結合了傳統繪畫的“寫意”特點,使人物形象做到了精神飽滿、造型準確、富有生氣,最終創作出具有獨特氣質特征的西藏青年牧民形象。到1963年左右,現實生活題材逐步取代油畫創作中的歷史題材。《夯歌》《金色的季節》《間苗》屬于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這類作品中有著直觀體現。這一時期的鄉土現實主義油畫多采用比較質樸、真實的創作手法,多以生活中客觀存在的農民形象為原型和底本[4]。
(三)鄉土“文革”時期
這一時期正常的油畫創作活動幾乎完全停止,臨摹照片的領袖油畫肖像大量涌現,《東方紅——無產階級司令部》《毛主席去安源》等便屬于其中代表,單一的油畫題材和對所謂“高、大、全”式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盲目追捧,使得鄉土現實主義油畫發展受到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鄉土“文革”時期同樣出現了一些富于生活氣息、來自現實生活的鄉土題材油畫作品,如《血衣》《黃河頌》《我為偉大祖國站崗》《淚灑豐收田》等,但這類優秀鄉土題材油畫作品的占比極小。這一時期油畫作品的農民形象塑造具備特別明顯的舞臺特征,戲劇化傾向顯著,過于“理想化”和“美化”的形象處理使得農民自身的固有形態與作品中的農民形象存在嚴重偏離,農民的“鄉土氣質”因此丟失。到了文革后期,出于對虛假、概念化粉飾主義的反感,優秀鄉土題材油畫作品大量涌現,如《崢嶸歲月》《不可磨滅的記憶》《紅燭頌》等。
三、多元化發展時期
(一)“傷痕”鄉土時期
文革結束后,文革的一些藝術流弊被糾正,這一階段的鄉土現實主義油畫創作具備“傷痕美術”特征,油畫《為什么》《西藏組畫》《春風已經蘇醒》《父親》等均屬于其中代表。以羅中立的油畫作品《父親》為例,基于局部特寫式的構圖、美國克洛斯式照相寫實主義表現手法、超大尺寸,一位貧窮、憨厚、善良、樸實、勤勞的四川老農形象躍然于紙上,真實、不虛假屬于該作品的最大特點,稱得上是當時中國社會最廣大階層、中國國民與中國社會的象征。“傷痕美術”代表著“神”的時代結束,鄉土現實主義油畫的本土化演變也因此進入多元化、自律性發展道路,尋求真實的觀察、體驗和表達成為藝術家的追求,偽飾和造作、種種“左”的清規戒律均得以突破和摒棄[5]。
(二)“多味”鄉土時期
“傷痕美術”的興起使得繪畫形式、語言、風格不斷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畫家基于現實主義進行鄉土描繪。鄉野生活、童年青春、淡淡的傷感、對社會和勞動的禮贊均屬于這一時期的常見油畫題材。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加深,在“雙百”方針和“二為”方向的指導下,西方的各種藝術流派、風格、技法大量涌入我國,受此影響很多藝術家開始探索運用象征、寓意、夸張、變形等多樣化手法進行鄉土題材處理,鄉土現實主義語言因此日漸豐富。在豐富多彩的藝術語言、不斷擴展的藝術內容、多樣化藝術風格、不斷轉變的藝術觀念下,油畫創作中的農民形象在“多味”鄉土時期存在“多樣化”的面貌和多向發展的態勢。受“85美術新潮”影響,面貌迥然、風格各異的鄉土油畫流派和佳作不斷出現,呈現了多層互補、多樣并存、百花齊放、綜合發展的藝術格局。較為典型的鄉土油畫流派主要包括以孫為民為代表的印象抒情式、以羅中立為代表的表現象征式、以王沂東為代表的古典唯美式、以宮立龍為代表的風情浪漫式、以方力鈞為代表的玩世現實主義。以風情浪漫式為例,宮立龍的鄉土現實主義油畫創作采用象征主義表現手法,但這并不影響其對現實農民生活狀態的陳述,基于現實主義的農民角度融入表現主義成分,做到了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折衷。總的來說,“多味”鄉土時期使得鄉土現實主義油畫不斷發展和延伸,鄉土化演變也使得其發展前景愈加廣闊。
(三)“變味”鄉土時期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畫家在鄉土現實主義油畫創作中對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對人性的思考、對自身表現語言的挖掘進一步深化,這與改革開放、城市化進程加速存在直接關聯,農民工也成為鄉土現實主義油畫創作的重要題材。作為當代社會的特殊階層,長期以來農民工一直是我國的弱勢群體,這使得很多畫家出于一種歷史責任感開始描繪農民工等農民群體的新變化,鄭藝、王宏劍、忻東旺等人均屬于其中的代表,《眺望新世紀》《熾心已飛》《陽關三疊》《打工圖》《明天,多云轉晴》等作品均屬于其中的代表作。以忻東旺為例,其鄉土現實主義油畫創作主要以“民工潮”作為主題,在描繪為生存而背井離鄉的個體生命過程中,其筆下的人物往往給人以沉重和茫然之感,同時中國文化的血脈也在其創作中有所體現,其民族人格重建的藝術良知也由此得到更好展現。總的來說,“變味”鄉土時期直接受到“農民工”階層出現影響,畫家更多以一種“我”的觀察方式進行創作,而鄉土現實主義油畫創作對農民工、弱勢群體等問題的關注一直持續至今。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鄉土現實主義油畫變遷受到的本土化影響較為深遠。在此基礎上,本文涉及的鄉土啟蒙時期、鄉土“文革”時期、“傷痕”鄉土時期、“變味”鄉土時期等內容,則直觀展示了鄉土現實主義油畫的本土化轉變。為更好推進鄉土現實主義油畫發展,全球藝術環境帶來的影響、后現代繪畫觀念的適當吸收、自身藝術個性語言不斷創新均需要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