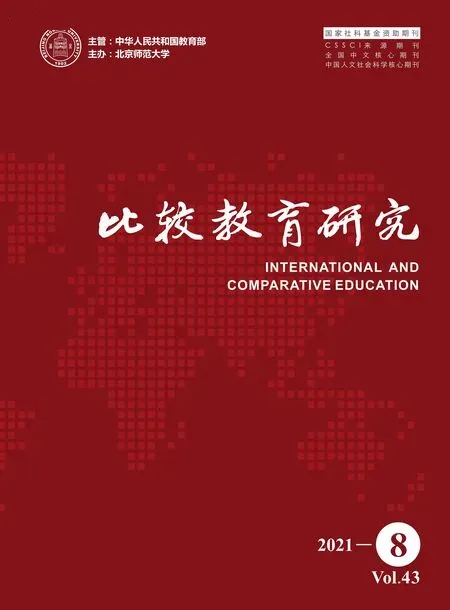以色列“補充教育”的實質、途徑與特色
唐彬君
(西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西安 710129)
重視教育是猶太民族的傳統,注重歷史與傳統教育使其歷經幾千年流散而不亡,重視創新教育又助其在全球化與信息化的進程中實現強國目標。以色列是猶太人的精神家園與現實世界中最為集中的族群聚居地,以色列的教育經驗無疑沉淀著猶太教育的智慧。國內現有的以色列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學校教育、創新教育、儀式教育等領域。本文關注的“補充教育”是以色列青少年的課外活動教育,它對于以色列民族意識、民族文化的培養與傳承和青少年技能的發展同樣功不可沒。
一、以色列“補充教育”的歷史發展與實質
“補充教育”(complementary education)是以色列建國后建立的一種教育制度,在當時被界定為“供青少年在放學或結束工作后的休閑時間內參加的活動。任何人都可以享受,不受族群、社會經濟地位或是政治態度的影響”[1]。當時,以色列剛剛建國,大量移民涌入使得教育需求猛增,學校不能完全勝任教育工作。以色列政府意識到需要發揮課外活動的教育作用,實現青少年教育的延伸與拓展,“補充教育”應運而生。
(一)“補充教育”的思想淵源
由于地緣關系和歷史上的人口流動,以色列與歐美流散地猶太人的關系源遠流長,因此其教育理念呈現出既傳承民族歷史傳統,又吸取歐美教育經驗的特點。“補充教育”制度實質上是本土化的以色列非正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它吸取了歐洲非正式教育思想以及猶太非正式教育(informal jewish education)的理念。
歐洲非正式教育思想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它主張:學校教育是按照國家統一制定的課程標準,在固定的教學場所內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對學生施加影響,促使其朝著所期望方向發展變化的活動;非正式教育則與學校教育相區分,其主要特點是相對松散的組織結構、沒有固定的課程標準以及靈活的組織時間。區分二者的主要標準一是看是否遵循教育部等部門制定的課程標準,二是看是否由固定成員在固定的場所按照固定的頻率參與教學活動。也有西方學者引入“non-formal education”概念,將具有一定課程計劃和教學安排,但是以實地體驗等方式在博物館、教育基地等場所進行的教育活動稱之為“nonformal education”。①也有學者稱之為“non-institutional formal elucation”,參見ESHACH H. Bridging in-school and out-of-school learning:formal,non-formal, and informal education[J].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2007, 16(02): 173.埃里克·科恒(Erik H.Cohen)認為,兩個術語經常在文獻中交換使用,而且informal education的適用度更廣,包容性更強。[2]
另外,以色列教育承襲了猶太教育的傳統,以色列非正式教育也發揚自猶太非正式教育。早期北美猶太人將學校教育和非正式教育視為猶太教育的兩大支柱,并各有側重:學校教育通過課程和文本培養學生的讀寫能力,傳承猶太文化;非正式教育則通過參與活動等親身體驗方式促進個體的社會化,強化猶太認同。作為一種教育方式,猶太非正式教育是受教育者自愿參與的、在團體氛圍中學習猶太經典文本(jewish content)、經歷猶太傳統體驗(jewish experience)、②猶太傳統體驗指親身參與家庭、會堂及社團等組織的與猶太傳統相關的活動與儀式慶祝,常見的有參加割禮、成人禮、安息日聚餐、禱告、猶太節日慶祝活動等。傳遞猶太價值(jewish value)③猶太價值指被猶太民族尤其是猶太教世代相傳的重要價值觀念,一般包含:熱愛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保持高尚人格,熱心慈善,重視家庭以及重視猶太同胞情誼等內容。的活動,其目的在于從知識、情感、態度和行為幾個層面幫助個體深入理解猶太文化,強化個體的猶太身份與群體的民族認同。[3]魯文·卡哈尼(Reuven Kahane)作為最早將猶太非正式教育理論化的學者,把猶太非正式教育的主要特點界定為:參加者的自愿性(voluntarism)、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平等互動關系(symmetry)、時間上的靈活性(moratorium)以及教育活動的模塊化設計(modularity)等。[4]在其之后,巴里·查森(Barry Chazan)進一步指出,猶太非正式教育影響了猶太人的生活方式和認同,而一般的非正式教育只是為了學習知識和提高技能,不涉及認同的塑造。[5]他將猶太非正式教育的特點概括為:關注個體需求,高度重視互動,充分利用團體氛圍進行體驗活動;教育者知識淵博、扎根猶太團體;將猶太價值觀念融入教育目標,重視教育環境的創設。[6]以色列的非正式教育承襲了猶太非正式教育中的教育方法和強化猶太民族身份(jewishness)的價值取向。同時,以色列作為民主國家,需要協調多方族群關系、踐行民主理念,因此在傳承猶太傳統的議題之外,以色列非正式教育還增加了諸如公民教育、幫助移民融入、幫助弱勢群體發展等主題,由此也體現出以色列的立國準則:既是一個猶太國家,也是一個民主國家。
(二)“補充教育”的歷史演變
“補充教育”雖然是以色列建國后建立的制度,但其實在建國前已經以非正式教育的實踐形式在海外流散地和巴勒斯坦地區存在良久,這些實踐為“補充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奠定了基礎。當時,海外流散地尤其是北美猶太社團存在著廣泛的猶太非正式教育,其中最常見的形式有猶太社區中心教育、家庭猶太教育、宿營活動等。它們為以色列建國之后推行非正式教育設定靈活多樣的活動形式提供了參考。與此同時,以色列建國前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針對特定人群和目標發展了青年非正式教育:一是通過志愿組織為需要幫助的學生提供公共服務,例如中小學生在學年中被安置在“學生之家”進行課后學習與休閑[7],放假時則被組織前往度假地進行休閑活動等;二是推行先鋒青年運動(Pioneering Youth Movement),培養青年領袖,踐行猶太復國主義①猶太復國主義,英語為Zionism,也稱“錫安主義”,主張結束世界各地猶太人的流散生活,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家園。它是主導以色列社會的基本意識形態,在歷史上直接推動了以色列國家的建立,在當前仍舊影響著以色列的政治生活和文化面貌。。與美國等地的猶太非正式教育相比,巴勒斯坦地區的非正式教育超出了猶太教育旨在強化猶太民族身份的一般范疇,成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一種途徑。這為建國后以色列非正式教育的問題導向發展提供了借鑒。
在這樣的歷史和傳統之下,以色列建國后非正式教育獲得長足發展。教育部接管了非正式教育,并正式創建了“補充教育”制度。此時的非正式教育活動主要在學校外進行,和學校的正式課程設置分離。[8]它們獨立于學校體系之外,擁有各自的機構和組織,主要目的是豐富學生的校外生活。
20世紀60年代移民大量涌入之后,新的社會背景導致以色列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的分離狀態有所改變,“補充教育”的內容和形式得到進一步豐富。在移民規模擴大的同時,中學生數量也急劇增長,學生主體越來越異質化,學校面臨一些從未出現的難題:學生的學習動力不足、出現嚴重的行為問題;新移民需要融入學校生活等。為此,學校將目光投向了課外活動。[9]學校開始利用“補充教育”,在傳授知識之外履行職責,建立起專門的部門組織學生度過他們的休閑時光,對他們進行社會層面、公民層面以及道德層面的價值教育。[10]
目前,負責以色列“補充教育”的兩個機構是教育部的社會與青年事務司(Society and Youth Administration)以及社區中心聯盟(The Association for Community Centers),它們統籌教育資源、制定教育目標。其他主體處于輔助地位,發起或組織具體活動。[11]學校也進一步成為非正式教育的合作者,經常通過組織學生參加議會、委員會、創辦和撰寫學生報紙和學生年度報告等活動,鍛煉青少年的民主參與能力和領袖能力。社會與青年事務司資助青年組織,也為學校非學術活動提供各種教育資源,組織學生在家庭、學校等場所參加各種教育項目,“補充教育”的個體發展功能得到進一步優化。
(三)“補充教育”的基本功能
“補充教育”作為一種課外活動教育,彌補了學校教育所不具備的功能。就時間而言,“補充教育”充實了青少年的課余生活,為其在課后提供了時間靈活的教育項目;就場所而言,“補充教育”拓寬了青少年獲取知識和進行實踐的場地與平臺,在多元場所中為青少年帶來豐富的教育活動;就內容而言,“補充教育”超越了學校的教學大綱,將知識、技能、情感、行為等融入教育過程。發展至今,以色列“補充教育”的功能日趨完善。對于青少年個體而言,“補充教育”的各種形式為其學校之外的休閑時光提供了活動基地和各種項目,他們可以根據自我意愿選擇適合的項目和場所,結交朋友,提升技能,實現社會化。對于國家和社會而言,“補充教育”搭建了青少年充分融合的平臺,傳遞民族文化和國家價值,有助于推動社會整合以及公民教育。
綜上所述,以色列的“補充教育”制度實質上是本土化的以色列青少年非正式教育,它是青少年在學校之外所參加的由以色列多種主體組織的課外活動,傳遞社會、公民等層面的價值,對青少年個體發展和國家的文化傳承與社會整合具有重要意義。
二、以色列“補充教育”的主要途徑
發展至今,以色列“補充教育”的途徑多樣,根據針對人群和問題的不同,其內容和作用也各有側重。筆者在此基于廣泛程度和代表性,選取以下主要類型,就參與人群、主要活動、特點與作用等進行介紹。
(一)青年運動(Youth Movement)
青年運動可謂以色列歷史最悠久的青年非正式教育形式,它的產生可以追溯至20世紀初反猶主義盛行時歐洲地區的猶太先鋒青年運動(Jewish Pioneering Youth Movement)。當時的猶太先鋒青年運動受到歐洲內部社會主義、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旨在凝聚青年群體力量,為猶太同胞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與生命威脅作斗爭。[12]向巴勒斯坦地區移民也是當時猶太先鋒青年運動參與者的主要目標,他們接受專業的軍事技能、情報和農業耕作訓練,為猶太同胞回到巴勒斯坦地區做準備。以色列建國之后,青年運動在國內得到傳承,并獲得官方認證,繼續發揮作用。當前以色列的青年運動依托政黨,根據不同的意識形態,建立了多個結構松散的青少年群體組織。青少年可根據需求,在課余時間自愿參加不同的青年運動組織,作為成員定期參與其舉辦的活動。
當代以色列青年運動組織的主要成員是13-18歲的在校學生。調查顯示,約有20%到25%的以色列青少年參與過青年運動及其相關活動。[13]青年運動的參與者呈現出階層分布差異的特征。研究顯示,目前以色列青年運動組織的成員中80%來自中上階層,只有20%來自較低階層。一些青年運動組織在欠發達地區中投入額外的精力和資源來招募成員,教育部也鼓勵并為邊遠地區的青年運動提供支持,甚至直接資助邊遠地區的參與者。[14]
教育部和政黨是青年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和負責機構,它們為青年運動提供經費支持、活動場所,組織人員,制定活動的主要綱領和章程。為了便于組織和進行針對性教育,青年運動組織內部多以年齡分層管理成員。不同年齡層的青少年組成小班,每個年齡組根據青年運動的意識形態以及成員自身的興趣和能力進行不同的訓練與活動。各青年運動組織設有自己的俱樂部房間(Club Room),用來舉辦研討會、日常會面等室內活動。同時,青年運動也貼合青少年的性格特質,擅長將思想教育、技能訓練融于趣味性活動,經常舉行宿營、遠足等寓教于樂的戶外活動。[15]青年運動的組織結構體現出青年自主性與成人主導相結合的特點:一方面,青年群體具有較大的活動自主性,無論是青年領袖的選拔還是多項活動的規劃與實施都會尊重成員的意見,及時聽取反饋,活動充分尊重和貼近青少年的想法與興趣;另一方面,組織綱領的制定、活動場所的選擇與維護以及青年領袖的培訓和管理都是在成人指導下進行。[16]
除承襲自英國童子軍的以色列童子軍(Scouts)意識形態淡化外,其他的青年運動均隸屬于不同的政黨,具有各自的意識形態。但就整體而言,意識形態性并非居于主導地位,能夠結識同輩群體、開展多樣興趣活動才是吸引青少年群體參加青年運動的主要原因。目前,以色列主要的青年運動組織有:以色列童子軍,注重培養青少年的領袖技能和個人魅力,傳播博愛、合作、平等等社會價值,經常舉行宿營、遠足等戶外活動,吸引了大量的在校生參與;體現宗教價值的“布奈·阿基瓦”(Bnei Akiva),是以色列現今規模最大的宗教性質的青年運動組織,旨在團結宗教青年群體,將猶太傳統和以色列現代國情結合起來,成員著裝與日常活動規定都體現出濃厚的宗教色彩;重視邊緣青年利益的“以色列工作青年”(Israeli Working Youth),關注工作青年的處境,為移民群體或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貧困家庭青年提供幫助,其成員活躍于以色列的欠發展區域以及以農業生產為主的集體社區基布茲(Kibbutz)。
雖然各個青年運動組織的主導價值和組織形式不同,但其行動綱領關注的議題大致相似,其中占據主導的是公共生活、個人道德、社會認同與民族構建。[17]青年運動為青少年認識自我、鍛煉技能提供了教育平臺,更為他們融入同輩群體、捍衛自身利益、發展并完善政治人格提供了社會化場域。就青少年個人而言,青年運動培養了同輩情誼,增長了他們的個人才干;就國家與社會而言,青年運動在歷史上推動了以色列國家的建立,在今天仍舊為塑造政治認同、促進青少年的社會化作貢獻。
(二)社區中心(Community Center)
社區中心是發揮社團力量的以色列特色組織,它承襲自大流散時期猶太人重視社團作用的傳統,它的建立直接受北美猶太社區中心(Jewish Community Center)的影響。在猶太民族流散的歷史中,猶太社團作為重要的生活單元,為成員提供了教育等多種社會功能。以色列建國之后,社團的作用同樣受到重視,社區中心發展成除教育部之外負責非正式教育的重要組織。1968年,由教育部在科亞特·施姆尼(Kiryat Shmoneh)成立了第一個社區中心,社區中心強調社群概念,注重建立社區人員與土地及文化歷史遺跡、傳統的聯系。[18]目前,以色列全國范圍內共有175個社區中心以及700個分支機構。它們由1969年成立的社區中心聯盟(The Israel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enters)統一管理,隸屬于教育部,由中央政府和地方議會聯合組成委員會監管,根據地方實際投入預算,制定活動計劃。
社區中心是整個社區的服務、娛樂和文化活動中心,其愿景是將居民、地方當局和商業社區聯系在一起。社區中心全天開放,面向所有人群和年齡層,根據其需求設置各類分屬活動委員會,猶太人、阿拉伯人、貝都因人、德魯茲人、世俗群體、極端正統派、新移民以及退伍軍人都能在社區中心找到相應的服務與項目。[19]社區中心往往由多個執行不同功能的建筑構成:如舉行聚會和紀念儀式的宴會廳、日常運動和舉行賽事的運動場地以及舉行研討會的大廳等。社區中心的建筑注重猶太文化特色,例如布置具有猶太文化傳統象征的燭臺與大衛星標志,播放猶太傳統音樂等,利用氛圍烘托,達到環境育人的功效。社區中心為居民提供不同領域的課程和豐富的活動,如體育競賽、表演、旅行等,同時還根據社區需要定制特別項目,如托兒所等早期兒童和家庭發展中心項目、多學科和各年齡段的團體學習中心項目、針對精神障礙患者的同伴計劃(Amitim Plan)以及為殘疾人制定的訪問社區項目(Kehila Negisha)等。[20]這些活動形式多樣,涉及主題豐富,能夠確保滿足每個社區居民的需要,幫助他們都能從中獲得意義和歸屬感。
以色列人習慣將社區中心稱為“Matnas”,它是希伯來語詞組“Merkaz Tarbut Noar and Sport”的簡稱,意為“文化、青年與運動中心”(The Center for Culture, Youth and Sport)。因此雖然社區中心服務于社區范圍內所有人群,但從其名稱就可以看出對青少年的格外關注。社區中心作為“補充教育”的形式之一,其特點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強調對普遍價值、國家規范以及社會義務的貫徹。這有別于美國猶太社區中心強化個體猶太民族身份的首要目標,以色列社區中心將價值教育的內容著眼于整個以色列社會的不同人群,服務于以色列國民意識(Israeliness)的整合和建立;二是強調通過自愿參與文化活動的形式,團結和組織青少年參與社區活動,形成社會紐帶;三是提供諸如志愿活動、技能培訓等社會服務和就業服務,在滿足青少年需求的同時,利用實踐活動開展價值觀教育和技能培訓,助其實現社會化;四是將家庭整合進社區,將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相結合,踐行了傳統文化,傳承了社會價值。發揮社團作用和“編織”社團紐帶是社區中心的突出作用,社區中心將公共服務和教育相結合,廣大青少年在有意義的文化實踐中既滿足了自身文化需求,又踐行了公共價值觀。
(三)青年村(Youth Village)
移民性是以色列社會的重要特征,解決移民青年的融入問題是推動社會整合的必要一環。青年村是以色列針對移民青年設立的包含學校和日常生活的教育場所,主要是利用團體關懷來幫助青少年度過移民初期的種種社會挑戰。以色列建國之后,移民涌入帶來了族群分裂的問題,社會整合成為難題。最初實行的“熔爐”政策,一刀切地以歐美猶太人的價值與行為規范作為標準,將其他族群進行同化,由此激化了社會矛盾,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色列的移民政策開始轉向文化上的多元取向,移民政策體現出新的原則:在社會整合方面,實施文化多元主義,注重利用非正式的社會化途徑。[21]青年村的產生正是在此背景下政府整合移民青年的新嘗試。
青年村由教育部監管,國家認證的高中一般成為青年村寄宿機構的一部分。[22]青年村往往選址遠離都市、靠近鄉村的地方,常和附近的基布茲建立合作關系。青年村里的新移民青年往往在學校里融入失敗或者經歷情緒危機之后在此尋求第二次機會。因此,在青年村中,青少年除學習學校課程外,在課下會參與各種集體活動,每人都配備有專業的心理疏導老師,幫助其克服移民初期的恐懼與不適。據統計,10%-15%的青年村學生尋求過專業的情緒疏導或治療。[23]青年村的教育目標重點不在于知識和技能的獲取,而在于疏導移民青少年的不適心理,幫助其融入以色列社會。
青年村的成員構成復雜,不僅有來自各種文化背景的移民,還有以色列本土邊遠地區或社會經濟狀況處于邊緣地位的青少年。為了滿足每個成員的需求,青年村在文化多元與文化互鑒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公共教育資源挖掘青少年所具備的潛力。[24]青年村既幫助新移民青少年通過寄宿教育平穩度過文化轉型期,也幫助一部分因為家庭問題尋求寄宿關懷的以色列本土青少年融入社會主流。
(四)猶太旅行(Jewish Trips)和徒步(Hiking)
猶太旅行和徒步是以色列“補充教育”中最具靈活性和自主性的形式。和一般的旅行與徒步不同,具有非正式教育意義的猶太旅行和徒步選擇的場地往往具有猶太歷史意義,能充分體現猶太文化傳統,其目的是有傳承歷史,塑造青少年的民族精神。
將旅行與徒步作為教育實踐,是將猶太傳統中兩種文化取向吸收并融合的結果:宗教文化將旅行作為了解土地的最佳方式,認為旅行能夠把人和其環境聯系在一起,以此帶有朝覲的神圣意味;猶太復國主義將旅行與徒步視為回歸自然、回歸以色列家園的途徑。[25]這兩種文化取向交織構成了以色列“補充教育”重視猶太旅行與徒步的思想基礎。同時,以色列本土的猶太旅行與徒步也是海外流散地猶太群體熱衷以色列之旅的鏡像反應,服務于加強猶太同胞紐帶的目標。公益基金會、學校、家庭都可以成為旅行的發起者和組織者,旅行途中的專業導游則負責目的地歷史和文化的講述;徒步則在一般旅行的基礎上加強了青年與自然、土地的聯系,使青少年在鍛煉身體、休閑娛樂的同時,習得價值觀念。通過猶太旅行與徒步,青少年親近自然,了解自然,提升美學旨趣,走進生活,感受歷史,塑造政治認同。較為流行的旅行目的地有以參觀大屠殺時期奧斯維辛集中營為主要活動的波蘭之旅,以此悼念受難同胞,深切體會大屠殺對于猶太群體的災難意義,增加猶太同胞的命運聯系;參觀以色列國道(Israel National Trial)的徒步,沿線有許多地標紀念猶太人重回這一片土地,加強個體與猶太土地的聯系等。
三、以色列“補充教育”的特色
“補充教育”制度是以色列本土化的非正式教育,其最突出的特點在于以下幾點:
第一,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學校、家庭、社會聯動,形成各有所長的教育合力,發揮教育影響的一致性和連貫性。一般而言,非正式教育的突出特征在于學校之外多個教育主體可以掌握教育話語權,政府干涉較少。無論是社區、青年組織還是基金會所提供的教育是不具有強制性的,青少年也是自愿參與。但在以色列,政府將“補充教育”制度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抓手,因此從財政支持、地域分布、機構設置到教育內容都對其做出一定的干預,調控“補充教育”的目標、內容與人群。政府的主導,一方面有利于保證教育的公平性,解決地域與社會經濟地位限制下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的問題,為大多數青少年提供參與非正式教育的機會,防止教育的精英化;另一方面也加強了非正式教育的目的性,實現了青少年課外活動教育中的意識形態控制及價值觀教育,有助于推動個體的政治社會化和社會規范的個體化。以色列政府主導作用的發揮,使“補充教育”形成了一批規模大、影響力強的青少年教育項目。在政府的主導之下,以色列的家庭、學校、社會同樣是青少年教育的主要參與者,它們相互協作,為青少年提供了豐富多樣的休閑、學習與成長平臺。
第二,突出問題意識,針對青少年的當前問題,細化青少年教育的不同內容,在促進其個體發展的同時,促進社會整合。現實中的青少年不是鐵板一塊的抽象概念,他們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也面臨各自的問題。同時,以色列最突出的社會特征在于移民屬性和猶太屬性,前者意味著整個社會族群多樣、生活方式迥異,后者則意味著在猶太價值的主導之下,難免出現傳統與現代、宗教與世俗的價值碰撞。因此,以色列的青少年面臨諸多的問題。以色列的“補充教育”制度從設置最初就是為了解決當時移民涌入后青少年異質化且難以融入社會的問題,隨后的發展過程中又具體分離出來一系列針對不同群體青少年的不同教育形式,始終呈現出問題導向的發展特點。“補充教育”具有形式靈活、平等開放、實踐性強的優勢,為不同背景的青少年提供了各種適合他們解決身份困惑、融入主流社會的平臺。在這里,他們可以發現和自己具有同樣問題的伙伴,放下心中憂慮、坦然面對問題;在這里,他們可以結識來自其他社會文化背景的同齡人,開放心態,彼此融合。這對于以色列構建包容、開放的社會文化,從而推動社會整合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注重教育公平,積極開發教育資源,推動建立廣泛覆蓋青少年的教育實踐。“補充教育”不是為了培育精英,而是為了大多數青少年的成長和發展。區別于一般的西方非正式教育所強調的培養青年領導力等個人技能的精英主義取向,以色列的“補充教育”強調任何人都可以享受,不受族群、社會經濟地位或是政治態度的影響。它的教育內容針對廣大青少年,希望促進整個社會的融合。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證所有青少年都可以在課外參加非正式教育,以色列“補充教育”的形式豐富,其中既有體育休閑類項目,也有研討會等探討社會實際問題的理論學習;既有個人技能提升項目,培養學習能力、動手能力、領袖氣質以及野外生存能力,也有團體項目,可以和同齡人一起參與基布茲生產活動、宿營與遠足活動,或是在社區內和家庭一起參加傳統節日的慶祝。青少年根據個人興趣自由選擇,并且在實踐的過程中達成目標。由此,以色列的“補充教育”遵循了所有青少年均可獲得的平等原則,反過來也成為促進整體教育公平的工具,其覆蓋人群廣,地域廣,價值傳遞廣泛,有效地助推了教育公平。
第四,發揮青少年的主體性,重視青少年領袖的作用。“補充教育”的多種教育形式都注重青少年主體性的發揮。一方面,“補充教育”的這些非正式教育形式強調教育活動組織者與參與者的地位平等,尊重青少年的自愿選擇,青少年是整個活動的參與者而非旁觀者,他們對于活動的實施方式、具體內容等具有一定的話語權;另一方面,各種教育活動都注重青年領袖的培養,以青少年團結和帶領青少年。這樣既最大化地代表了青少年的利益和興趣,也鍛煉了他們的能力,激發他們參與活動的積極性。
第五,注重文化傳統滋養,重視價值觀的傳遞。以色列的建國目標是建立猶太國家和民主國家。這決定了以色列的教育既要傳承猶太復國主義傳統,強化猶太民族身份,也要提供公民教育,培養現代公民。“補充教育”一方面繼承了猶太非正式教育對于體驗和實踐的重視,利用儀式教育、歷史教育和社團教育傳承并發揚猶太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也提供平臺促進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等族群的平等交流,塑造以色列國民意識。這些傳統與價值成為滋養青少年的精神源泉,“補充教育”活動通過情感凝聚、價值傳承,強化了青少年的歸屬感、認同感與責任感,在客觀上為保存以色列文化傳統、傳承民族精神帶來了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