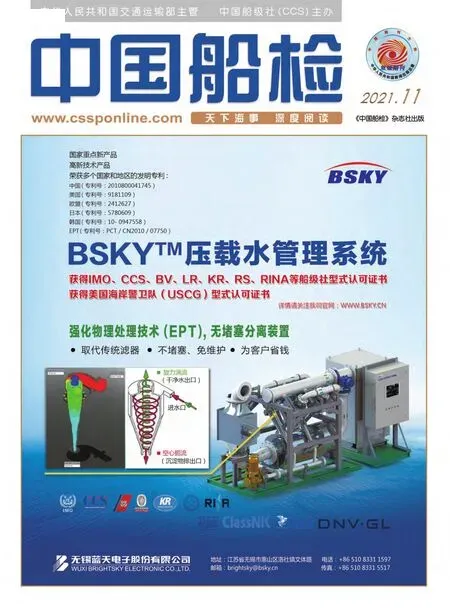多維視角下的航運減排當下與未來
中國船級社《航運低碳發展展望2021》編寫組
低碳減排已成為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碳達峰、碳中和是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航運業作為世界貿易的領頭羊和服務全球貿易發展的基礎力量,也將不可避免地融入到這場變革中。航運綠色低碳發展事關各相關方的共同利益,也關系行業發展的未來。我們必須立足當下,著眼未來,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推動航運減排不斷取得新成效。CCS組織專家團隊,在對溫室氣體減排政策走向和減排技術路徑綜合研判的基礎上,對未來低碳航運的發展趨勢做出展望。

一、風云激蕩:減排方向的確定性與目標和路徑的不確定性交織相伴
如前所述,國際海事組織、各國及區域性組織、海事領域其它行業和政府間組織,對于航運減碳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尚未達成完全一致,但航運業需要加速實現碳減排的方向已經非常確定,而且時間表可能比原計劃提前,減排強度也會更高。而在溫室氣體減排的路徑方面,技術手段從船舶能效提升轉向清潔替代燃料的方向也已經基本確定。
盡管在減排方向上基本達成一致,但各方在國際航運減排目標和路徑方面的觀點不盡相同甚至存在較大分歧,這就決定了在航運業通向凈零排放的道路上將充滿不確定性。
在政策法規制定層面,國際航運領域的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最終實現全球航運凈零排放的時間表及各階段的減排目標、船舶燃料全生命周期溫室氣體排放評估方法等方面,而且其中的部分政策法規對不同種類清潔燃料的應用前景有重大影響;相對而言,中國的國內航運領域二氧化碳減排的時間表和實施路徑將會清晰而確定。
在市場機制層面,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全球性和地區性碳排放控制市場機制的覆蓋范圍和價格方面、實施以碳稅為主導還是以碳交易為主導的市場機制方面、碳稅或碳交易的價格及收取資金的分配和使用方式方面,各相關方目前還未能達成一致,或將會有較長時間的爭論甚至博弈,從而給航運業相關方的經濟性測算和收益預測帶來較大不確定性,進而影響整個航運業脫碳進程和技術路線的選擇。
在技術路徑選擇層面,不確定性主要表現為在可供選擇的脫碳技術路徑中,航運業完全可控的部分僅限于船舶端的能效提升技術、碳捕捉和儲存技術。單純依靠能效提升技術不能達成凈零排放的目標,而排放端的碳捕捉和儲存技術則因為其技術不成熟、實施成本高、小型化困難、船上操作復雜、岸基接收困難等應用障礙短期內難以解決,因此不能作為現階段航運業通向凈零排放的首選技術路徑。船舶端技術路徑的不確定性也在于碳捕捉和儲存技術的未來發展,如果能夠實現成本可控的船舶端應用,則將對船舶脫碳技術路徑和船舶燃料端的相關產業有重大影響。相比較而言,燃料端的脫碳技術路徑清晰而明確,但其不確定性在于航運業無法決定化工和能源領域綠色燃料的制備工藝和生產供應布局,從而使得替代燃料的供應和技術路徑的選擇陷入“蛋-雞之問”的困擾。
在航運業實現凈零排放的道路上,政策法規、市場機制、技術路徑將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其中政策法規無疑是最有決定性的因素。我們提請業界的各利益相關方密切關注政策法規制定的動向,并積極貢獻觀點和解決方案,使得最終制定的政策法規最大限度顧及不同國家、地區和各相關方的實際情況和利益,使減排目標和配套措施既有雄心,又可持續。
二、重裝出發:零碳清潔燃料將在2030年前后實現商業化應用
我們的研究分析顯示,2030年對于航運業溫室氣體減排而言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主要基于以下三個判斷:
1、眾多地區性和行業組織倡議的實現航運業凈零排放的時間點均指向2050年,按照船舶平均營運壽命20年計算,2030年前后,零碳清潔燃料需要在新建船舶上實現商業化應用。
2、清潔船用燃料,尤其是電制低碳或零碳燃料實現規模化和可持續供應的時間點將在2030年前后;
3、清潔替代燃料船舶應用技術成熟并全面實現規模化和工程化應用的時間點也將在2030年前后。
因此,我們認為,2030年既是航運領域實現規模化零碳運營的起始點,也將是航運業加速脫碳的起始點。可以預期,屆時將有新的法規類強制性政策和碳交易、碳稅等市場性政策配合,加速國際航運業溫室氣體減排進程。
三、負重前行:低碳和零碳燃料應用過程中的挑戰不容忽視
實現清潔燃料在航運業規模化應用的最大挑戰,來自燃料的可獲得性。盡管部分替代燃料(如甲醇、氨等)作為化工產品的規模化生產和儲運、分銷已經非常成熟,但航運減碳政策中對全生命周期碳強度的關注,需要供應采用綠色制備工藝生產的清潔燃料。與國際航運業所需的億噸級的燃料消耗量相比,目前綠色制備工藝生產的電制燃料仍在百萬噸級的規模,遠不能滿足需求;而生物質綠色燃料的規劃產量,相較于航運業的需求,更是杯水車薪。低碳和零碳燃料的可獲得性和可持續性,是規模化應用和實現減碳目標的瓶頸問題。

在船舶端,現階段可供航運業選擇的低碳和零碳替代燃料主要有LNG、甲醇、氨、氫等四種,與常規燃油相比,替代燃料多數具有更易燃爆、生物毒性、材料兼容性有特殊要求等特點,部分燃料還需要低溫甚至極低溫度圍護系統儲存,這些都對燃料的安全加注、儲存、使用等構成挑戰。
在船舶經營端,航運公司除需要應對燃料的供應和使用等中觀和微觀層面的經營性和技術性問題以外,還要面對在全球經濟和社會實現脫碳的進程中和實現碳中和以后,國際間和各國國內水運的貨物種類、物流方向、運輸總量會發生何種變化等戰略性問題。航運業在進行中遠期發展規劃時,宏觀視角有助于減少決策性和方向性風險。
四、場景為王:不同的航運領域需要量身定制的最佳方案
低碳和零碳替代燃料在燃料特性、經濟性、可獲得性等方面的顯著差異,決定了其最佳應用場景將有較大不同,不存在贏者通吃的單一解決方案。
對于遠洋和近海航運而言,燃料的可獲得性、體積能量密度和燃料儲存條件將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近期可選方案主要有LNG、甲醇、氨等燃料,在氫的高能量密度儲存問題解決后,中遠期氫燃料將成為具有競爭力的方案之一。
對于近岸和內河航運而言,燃料的儲存和補給等相對容易實現,因此基于零碳燃料的動力方案選項會更加易于實施。現階段國內船舶圍繞LNG、甲醇、電池動力、氫、氨等其他清潔能源的應用開展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實踐,但尚未就船舶能源的低碳發展形成明確路徑。相比較而言,現階段的電池動力,尤其是可換電的電池動力方案,以及近中期可能形成技術突破的燃料電池方案,將會是比較有競爭力的零碳航運方案選項之一。
五、持續驅動:脫碳過程中經濟性因素的考量不可或缺
低碳和零碳清潔燃料相較于常規化石燃料而言,其理化特性特殊、制備工藝特殊復雜,其生產端和應用端的成本都將顯著高于化石燃料。目前其生產規模和使用經濟性遠低于常規燃油,并且預計將持續較長一段時間。
在船舶應用端,清潔替代燃料的體積能量密度均明顯偏低,在相同續航力的情景下,加大的燃料艙將占據一部分載貨空間,進而對載貨重量和運營經濟性有不可忽略的影響。據模型測算,載重噸為85,000噸的巴拿馬型散貨船因使用氨燃料導致的貨艙容積損失約為10%,載貨重量損失大約為10,000噸,對船舶運營收益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在這方面,遠洋中小尺度船舶的替代燃料艙布置更具挑戰性。實際上,燃料艙的布置對于船舶設計和建造是最具有挑戰性的技術問題之一。
在燃料生產端,綠氫是生產其它清潔燃料的主要原料,但僅能通過可再生能源生產的電力電解水來制備,其制備成本高企、規模受限,因此綠色替代燃料的生產規模普遍較小,成本較高。清潔燃料的價格和船舶運營方對燃料成本接受程度將成為航運脫碳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
不論是在燃料成本還是運營收益方面,低碳和零碳燃料的應用都可能對航運業的盈利能力造成負面影響,單純依靠航運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和法規等強制性政策驅動,脫碳進程將很難持續。因此,政策法規的制定方、替代燃料的供應方、船舶和設備的制造方、船舶運營方等,均需要將經濟性方面的可持續性作為選擇航運脫碳路徑過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六、攜手同心:各相關方協同聯動才是實現航運減排目標的正確路徑
航運業要實現減排目標,涉及到上游燃料生產和供應,中游船舶和設備制造、下游船舶運營的全產業鏈諸多環節,其中關鍵性環節就包括:IMO和國際地區層面減排法規政策的制定者、負責綠色燃料生產的化工或能源企業、負責燃料儲運和加注的燃料供應企業、負責動力裝置等關鍵設備供應的船用設備生產企業、船舶設計和建造方、提供配套設施和加注能力的港口、提供風險管理和安全技術標準的船級社、執行運營安全監管的海事主管機關等,缺少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清潔燃料的應用就不可實現或不可持續。這就需要整個產業鏈上的各相關方打破“蛋-雞之問”的困擾,早日解決低碳和零碳燃料規模化應用過程中的諸多瓶頸和障礙。更需要各個國家和地區秉承“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以堅定、積極、互信的姿態同心協力,在政策法規制定、市場機制構建等方面協調立場,明確目標和路徑,為實現航運業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的宏大目標和美好愿景攜手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