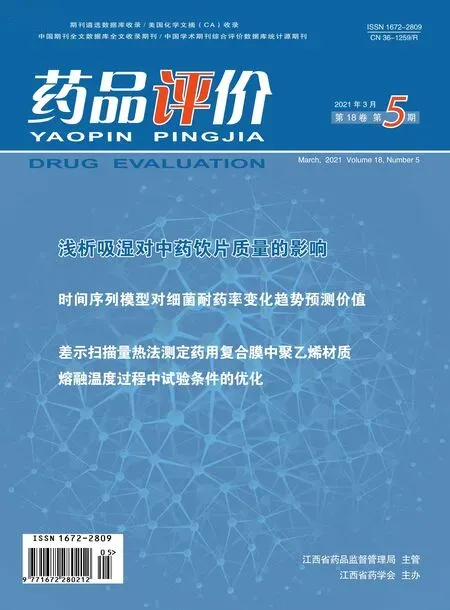宮頸癌多發(fā)轉(zhuǎn)移患者免疫治療聯(lián)合放療中并發(fā)肺炎1 例分析
宋艷麗,王景,杜娟
1.中國人民解放軍聯(lián)勤保障部隊第九八八醫(yī)院,河南 鄭州 450042;2.河南省腫瘤醫(yī)院,河南 鄭州 450008
近年來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s)在腫瘤治療領(lǐng)域取得了重大進(jìn)展,為晚期黑色素瘤、腎癌、非小細(xì)胞肺癌等多種惡性腫瘤的患者帶來了福音[1],帕博利珠單抗已被FDA批準(zhǔn)用于復(fù)發(fā)或轉(zhuǎn)移宮頸癌的二線治療。隨著ICIs臨床應(yīng)用的增多,其導(dǎo)致的副作用,如免疫相關(guān)性肺炎的病例時有報道,而該類不良反應(yīng)有潛在致死性、增加患者的死亡率[2],且免疫相關(guān)性肺炎發(fā)生的風(fēng)險與肺部疾病、肺部放射史、聯(lián)合放療及曾接觸與肺間質(zhì)性肺炎相關(guān)的藥物等有關(guān)[3],早期識別、及時治療對于患者有重要意義[4]。
本文報道1 例老年宮頸癌多發(fā)轉(zhuǎn)移伴房顫患者帕博利珠單抗聯(lián)合放療治療3個月出現(xiàn)肺炎的病例,探討引起患者肺炎的原因,并給予用藥監(jiān)護(hù),以期為臨床和藥師在腫瘤復(fù)雜治療中及早識別免疫相關(guān)性不良反應(yīng)及臨床安全合理用藥提供參考。
1 病例摘要
女,67 歲,身高160 cm,體重54 kg,ECOG評分2 分。2018 年3 月外院確診為“宮頸鱗癌ⅢB期”(FIGO2009),于2018 年3 月4 日行“紫杉醇脂質(zhì)體(210 mg)+奈達(dá)鉑(110 mg)”方案1 周期后,因出現(xiàn)“Ⅳ度骨髓抑制、感染性休克、快速房顫”中斷化療;2018 年4 月8 日至5 月23 日行全量放療(IMRT 6MV-XPTV 50Gy/25f),并給予銥192 三維腔內(nèi)后裝治療,HR-CTV D90(包含A點)30Gy/6f;2019.10.24 CT 示:右肺多發(fā)結(jié)節(jié),考慮轉(zhuǎn)移。2019 年12 月就診中國人民解放軍聯(lián)勤保障部隊第九八八醫(yī)院,完善檢查后于2020 年1 月9日、2 月12 日、3 月9 日、4 月3 日行“貝伐珠單抗(500 mg d1)+多西他賽(90 mg d2)+順鉑(30 mg,d3-d5)”方案化療4 周期,并在輸注時給予心電監(jiān)護(hù)。2020 年8 月2 日復(fù)查,CT 示:兩肺多發(fā)結(jié)節(jié),其一較前增大(右肺),直徑約17 mm,余較前變化不大。疾病進(jìn)展,于8 月3 日給予“帕博利珠單抗(200 mg)”治療1 周期,并給予右肺病變部位三維適形放射治療(8 月8 日~19 日,DT:18Gy/9f),放射治療中出現(xiàn)房顫并快速心率,轉(zhuǎn)ICU 治療后好轉(zhuǎn)。8 月30 日、10 月8 日、10 月29 日繼續(xù)給予“帕博利珠單抗”治療3 周期。9 月19 日胸部CT 示(與8 月2 日比較):雙肺多發(fā)結(jié)節(jié),較前相仿,右下肺炎性改變。免疫治療期間患者右側(cè)肩部疼痛,10 月15 日MRI 示:右側(cè)肩胛骨骨質(zhì)破壞,考慮轉(zhuǎn)移;雙肺內(nèi)多發(fā)結(jié)節(jié),較前相仿。給予右側(cè)肩部轉(zhuǎn)移灶三維適形放射治療(10 月17 日~31 日,DT:30Gy/10f)。
患者既往有快速房顫史,2020 年8 月19 日至今給予胺碘酮治療,控制可。
11 月4 日患者因咳嗽咳痰2 d,加重1 d 伴胸悶、氣促、乏力入院,入院時精神狀態(tài)較差,無發(fā)熱。否認(rèn)其他病史和食物藥物過敏史。入院查體:T 36.6 ℃,P 85 次/min,R 20 次/min,BP 120/80 mm Hg,入院檢查WBC 11.23×109/L,NEU 89.9%,LYM 10.6%,CRP 83.4 mg/L,PCT 0.07 ng/mL。增強CT(11.4)示:(1)兩肺多發(fā)結(jié)節(jié),較前增大增多。(2)兩肺炎性改變,較前范圍增大。(3)右側(cè)胸腔少量積液。與9 月19 日肺部CT 比較,雙肺炎癥面積較前增大,呈磨玻璃影。結(jié)合既往胺碘酮和帕博利珠單抗用藥史和肺部放射史,首先考慮帕博利珠單抗相關(guān)不良反應(yīng)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合并肺部感染存在,給予注射用甲潑尼龍(80 mg/d),同時給予吸氧,經(jīng)驗性給予“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抗感染治療,并給予鹽酸氨溴索注射液、多索茶堿注射液化痰平喘等藥物治療。11 月7 日患者咳嗽咳痰及胸悶較前明顯好轉(zhuǎn),痰培養(yǎng)口腔正常菌,WBC 8.59×109/L,NEU 94.3%,CRP 15.23 mg/L,PCT 0.07 ng/mL。11月8日G試驗:58.67(0~95),GM試驗:0.26(0~0.85),痰培養(yǎng):白假絲酵母菌(優(yōu)勢菌),給予注射用伏立康唑抗真菌治療,注射用甲潑尼龍減量至40 mg/d。11月11日復(fù)查CT(較11.4 CT比較)示:(1)兩肺多發(fā)結(jié)節(jié),右肺尖者較前縮小。(2)兩肺多發(fā)炎癥,較前范圍稍縮小。繼續(xù)當(dāng)前抗感染治療,連續(xù)送檢痰培養(yǎng)+藥敏。11 月18 日再次復(fù)查CT(較11 月11 日CT 比較)示:(1)兩肺多發(fā)結(jié)節(jié),大小較前相仿,部分新見空洞。(2)兩肺多發(fā)炎癥,較前范圍稍縮小。(3)右側(cè)胸腔少量積液,較前稍減少。患者癥狀好轉(zhuǎn),痰培養(yǎng)連續(xù)兩次陰性,給予口服潑尼松片(30 mg/d,每周遞減5 mg)和伏立康唑片(前24 h 400 mg,2 次/d,之后200 mg,2 次/d),建議停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出院。
2 患者發(fā)生肺炎的原因分析
2.1 胺碘酮的肺毒性
胺碘酮是常用的抗心律失常藥之一,臨床用于房顫及室性心律失常等的預(yù)防及治療[5]。本品藥理學(xué)特征復(fù)雜,且半衰期長,長期應(yīng)用可引起多種不良反應(yīng),其中胺碘酮導(dǎo)致的肺部毒性最為嚴(yán)重[6,8]。肺毒性CT 表現(xiàn)呈多樣性,最常見的是間質(zhì)性肺炎,主要表現(xiàn)為雙肺小葉間隔或小葉內(nèi)間隔增厚,雙肺彌漫的磨玻璃影、細(xì)網(wǎng)格影[7]。文獻(xiàn)報道胺碘酮肺毒性的發(fā)生率為 5%~15%,且與服用劑量、療程、患者年齡、肺部疾病等風(fēng)險因素有關(guān)[8-9],特別是年齡大于60 歲的存在基礎(chǔ)肺部疾病的患者更易發(fā)生。但也有文獻(xiàn)報道[10],小劑量、短療程使用胺碘酮也可能會導(dǎo)致嚴(yán)重的間質(zhì)性肺炎,甚至在靜脈使用胺碘酮數(shù)分鐘后就可出現(xiàn)咳嗽等呼吸道癥狀。
胺碘酮的肺毒性可能與不同機制的組合有關(guān)[8]:(1)胺碘酮可對肺臟內(nèi)皮細(xì)胞產(chǎn)生直接毒性作用;(2)具有遺傳易感性的患者的“免疫”介導(dǎo)機制:炎癥反應(yīng)和過敏反應(yīng);(3)血管緊張素酶系統(tǒng)的激活等。胺碘酮的肺毒性診斷明確后,須立即停用胺碘酮,癥狀明顯且嚴(yán)重者可給予糖皮質(zhì)激素治療,早期診斷和治療至關(guān)重要。
患者宮頸癌肺轉(zhuǎn)移,且患者年齡67 歲,胺碘酮治療2.5 個月,依據(jù)胺碘酮致肺毒性的風(fēng)險因素[8],不能排除胺碘酮對患者肺部炎癥的影響。
2.2 帕博利珠單抗致免疫相關(guān)性肺炎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guān)性肺炎(checkpoint inhibitor pneumonitis,CIP)是由ICIs 治療相關(guān)并發(fā)癥的一種,CIP 常見臨床表現(xiàn)包括呼吸困難、咳嗽、乏力、發(fā)熱或胸痛等,但是約有1/3 患者無任何癥狀,僅有影像學(xué)異常[11]。CIP 的影像學(xué)表現(xiàn)呈多樣性,最常見表現(xiàn)為磨玻璃影、實變、纖維條索、小葉間隔增厚、網(wǎng)格狀影等,結(jié)合病理的影像學(xué)類型常見為機化性肺炎樣、非特異性間質(zhì)性肺炎、過敏性肺炎等[12]。CIP 發(fā)生的時間范圍變化很大,從給藥開始到停藥后均可出現(xiàn)。
帕博利珠單抗是一種高選擇性的人源性IgG4單克隆抗體,可阻斷程序性死亡受體-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和程序性細(xì)胞死亡蛋白配體1、2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ligand 1、2,PDL1、PD-L2) 間的相互作用,從而解除PD-1 通路介導(dǎo)的免疫抑制,發(fā)揮腫瘤免疫作用[13]。隨著帕博利珠單抗在臨床的應(yīng)用增多,其不良反應(yīng)也被廣泛關(guān)注,除了說明書中記載的肺炎、肝炎、垂體炎、甲狀腺炎等外,文獻(xiàn)報道[14]還發(fā)現(xiàn)了內(nèi)分泌紊亂、呼吸系統(tǒng)損害(肺纖維化、支氣管狹窄等)和肝膽系統(tǒng)損害。臨床研究的數(shù)據(jù)顯示,接受PD-1/PDL-1 抑制劑治療的患者,CIP 發(fā)生率小于5%,3 級以上的肺炎0%~1.5%,但真實世界中ICIs 引起的CIP 發(fā)生率似乎更高(19%)[15]。據(jù)報道[16]CIP發(fā)生的風(fēng)險因素包括:肺部疾病、吸煙史、肺部放射史、既往治療使用與肺間質(zhì)性肺炎相關(guān)的藥物如EGFR-TKI、紫杉類、吉西他濱等。患者既往有紫杉類藥物治療史、且聯(lián)合肺部放射治療,增加了患者發(fā)生CIP 的風(fēng)險。
2.3 放射性肺損傷(RILI)
放射性肺損傷(RILI)是胸部放射治療的常見并發(fā)癥,表現(xiàn)為早期放射性肺炎和晚期纖維化[17]。依據(jù)“放射性肺損傷的診斷及治療(共識)2015 年”,既往有肺放射病史,RILI 多發(fā)生于放療開始后6 個月內(nèi),最常發(fā)生在肺部放療后2~6 個月;肺部體征最常見表現(xiàn)為呼吸音粗糙,其他包括干啰音、濕啰音、呼吸音減低等;血象多表現(xiàn)為中性粒細(xì)胞百分比高于正常,白細(xì)胞總數(shù)多無明顯升高;C 反應(yīng)蛋白、血清LDH、血沉等可能升高;動脈血氣分析氧分壓下降;肺功能異常。對于RILI 的治療,臨床一般根據(jù)RILI 的分級,對于2 級伴發(fā)熱且CT 上有急性滲出性改變者或有中性粒細(xì)胞比例升高及3 級以上的RILI,依據(jù)共識建議給予糖皮質(zhì)激素、抗生素及對癥治療。患者在右肺部病變部位放射治療(8.8~8.19 DT18Gy/9Gy)后近3 個月出現(xiàn)肺部炎癥,具有時間相關(guān)性,不能排除放射性肺損傷。
2.4 免疫治療聯(lián)合放療致肺損傷
ICIs 聯(lián)合放療已被證實具有協(xié)同作用[18],但聯(lián)合治療模式是否增加不良反應(yīng)特別是3 級以上不良反應(yīng)的發(fā)生率,將決定該模式在臨床實踐的可行性。
孫楓淏等[19]對近年來重要的放療聯(lián)合ICIs 相關(guān)研究進(jìn)行綜述,分析免疫相關(guān)不良反應(yīng)(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發(fā)生的特點發(fā)現(xiàn),聯(lián)合治療可能導(dǎo)致不良反應(yīng)特征方面的重疊,但根據(jù)目前的回顧性研究,聯(lián)合治療并未顯著增加除肺部不良反應(yīng)的發(fā)生,而聯(lián)合治療時間間隔是irAEs 的風(fēng)險因素。
放射腫瘤學(xué)免疫聯(lián)合治療專家組對放療聯(lián)合免疫治療的療效、安全性等熱點學(xué)術(shù)問題進(jìn)行探討分析顯示[20],放療聯(lián)合免疫治療療效明確,安全可控,未顯著增加3 級以上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率,但免疫治療聯(lián)合放療的時間順序、不同的放療技術(shù)、不同人群等都會影響聯(lián)合治療的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率。患者在帕博利珠單抗治療期間,行右肺部病變部位放射治療(8.8~8.19 DT18Gy/9Gy),可能增加了患者肺炎的發(fā)生率。
綜上所述,結(jié)合患者治療史、用藥史及檢驗和檢查,分析誘發(fā)患者肺部炎癥增大增多的原因,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帕博利珠單抗、胺碘酮及免疫聯(lián)合肺部放射治療都可能引起肺部的損傷,且不能排除肺部感染。但有研究分析提示[16],PD-1/PD-L1 抑制劑治療相關(guān)的總體死亡率為0.45%(82/18353),而其中以CIP 引起的死亡最為常見(23/82,28.0%)。由此可見,CIP 的總體發(fā)生率雖然不高,但是嚴(yán)重的CIP 如果處理不當(dāng),則可能出現(xiàn)危及生命的嚴(yán)重后果。當(dāng)本例患者出現(xiàn)相關(guān)臨床癥狀及雙肺炎癥增多呈磨玻璃影時,考慮到免疫相關(guān)性肺炎的致死性風(fēng)險,臨床首先考慮患者肺部炎癥是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guān)性肺炎合理,并根據(jù)CIP 的分級診斷為CIP 3 級,給予糖皮質(zhì)激素和抗感染治療7 d后癥狀明顯好轉(zhuǎn)。
3 患者用藥監(jiān)護(hù)
3.1 糖皮質(zhì)激素的用藥監(jiān)護(hù)
長期的激素治療會帶來一系列的毒副作用,累及全身多個系統(tǒng),包括:骨骼肌肉副作用、消化系統(tǒng)、心血管系統(tǒng)、代謝內(nèi)分泌副作用如水鈉潴留(排鉀保鈉)、電解質(zhì)紊亂;精神行為方面,如失眠、情緒不穩(wěn)、認(rèn)知障礙;合并機會性感染(包括真菌、TB、PCP 等)等[21]。結(jié)合患者具體情況,給予患者用藥監(jiān)護(hù):患者出院時復(fù)查電解質(zhì),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低鉀,因排鉀保鈉導(dǎo)致的低鉀血癥可出現(xiàn)肌肉麻痹,嚴(yán)重者可出現(xiàn)心力衰竭[22]。患者本身房顫并快速心率,注意復(fù)查電解質(zhì),必要時補鉀;并注意監(jiān)測患者心率。另外,患者高齡且骨轉(zhuǎn)移并進(jìn)行了放療,《CSCO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guān)的毒性管理指南》(2019 年版)建議在長期使用糖皮質(zhì)激素時需補鈣及維生素D3,以防出現(xiàn)骨質(zhì)疏松及骨折;如出現(xiàn)胃腸道反應(yīng)還要注意使用質(zhì)子泵抑制劑;并注意避免感染,注意飲食控制,監(jiān)測血糖等。
3.2 伏立康唑的用藥監(jiān)護(hù)
伏立康唑常見的不良事件包括肝功能異常、神經(jīng)/精神障礙、視覺障礙、心臟異常和皮膚及皮下異常等。伏立康唑存在較大的個體差異[23],注意監(jiān)測患者的肝功能;且患者同時服用糖皮質(zhì)激素,囑患者若出現(xiàn)煩躁、失眠、視覺異常等不適時及時告知醫(yī)師。另外,伏立康唑與QTc 間期延長有關(guān),已有報道極少數(shù)使用本品的患者發(fā)生了尖端扭轉(zhuǎn)型室性心動過速[24],而這些患者通常伴有一些危險因素,如曾經(jīng)接受過具有心臟毒性的化療藥物、心肌病、低血鉀癥等,患者本身有房顫并快速心率,輕微的低鉀,囑患者注意復(fù)查電解質(zhì)并監(jiān)測心率,一旦出現(xiàn)心慌等不適,及時就診。
4 小結(jié)
隨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臨床越來越廣泛地使用,免疫相關(guān)性肺炎的發(fā)生與報道逐漸增多。但因為免疫治療藥物在我國上市時間短,臨床尚缺乏鑒別免疫治療相關(guān)不良反應(yīng)的經(jīng)驗,并且腫瘤患者合并用藥較多、治療復(fù)雜,影響并增加了免疫相關(guān)性肺炎的識別難度。因此,臨床藥師應(yīng)積極參與臨床治療,做好用藥監(jiān)護(hù),并提醒臨床充分考慮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的風(fēng)險因素,尤其是患者既往有肺部放療史、免疫治療聯(lián)合放療、正在接受具有肺毒性的藥物治療等高危因素時,密切監(jiān)測各項指標(biāo),對于免疫相關(guān)性不良反應(yīng)做到早發(fā)現(xiàn)、早診斷、早治療,提高患者的臨床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