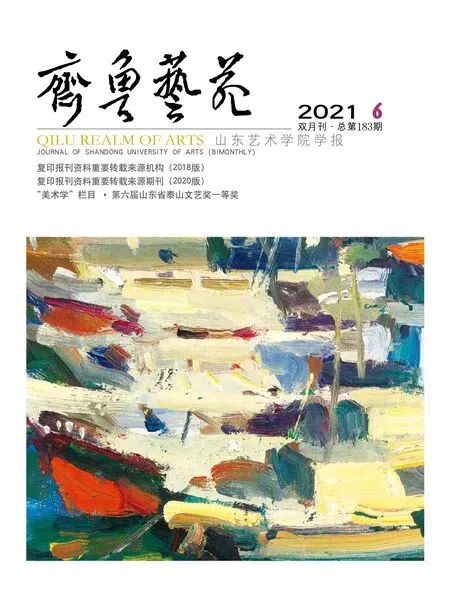中國“諜戰電影”中的親緣倫理話語表述
葉 凱
(山東藝術學院學報編輯部,山東 濟南 250014)
從藝術本體層面遷延的審美旨趣關注出發,沿著電影敘事情節結構核心動力探究的思路,可以發現,即便是細化藝術形態分類學的概念,而定義為電影類型的區分,“諜戰電影”牽涉的核心元素辨識,仍然會落腳于“諜戰”斗爭行動中諸種事件構成的因果鏈條,并由此演化出的可能性結局及其對之進行推斷而產生懸念疑問的刺激感。它以“間諜”人物及與其對立的反面——反間諜行為人之于“諜戰”場域內部的沖突為圓心,預設極端生存境遇的藝術情境想象,在其中顯影雙方面對可以預判或者突如其來的事件激變時的行動反應、情緒處理與命運選擇。在此種意義上,它與電影類型的經典分類——警匪片的構成體系與審美期待,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卻是在其之上的沖突極化與烈度加強的超類型版本,也更能體現出人類面對人性拷問時的艱難判斷與困境掙扎,而擁有更為細膩地描摹人物情感漸變邏輯的藝術空間。
一、形態分類的核心動力與民族文化的傳承認知
理查德·麥克白將能夠表征形態分類的核心標的,命名為“類型元素”,而將其中最為關鍵的要素描述為“共享的一套期望系統”[1](P70)。對于建立在形態分類學基礎上的類型特征而言,“諜戰電影”的“期望系統”,或可總結為遵循“懸念營構”——“人性凸顯”——“情感共振”逐層遞進的邏輯公式,在其中也許會有不同節點適用程度強弱之分,但似乎多少都是不可或缺的構成。那么,這種之于“諜戰”斗爭現實殘酷性展示與極端藝術情境假定性建構體系內的特定情感表達,便與日常生活境遇中的普泛性認知,形成反差強烈的沖突與對列,從而在極度的情緒震驚與波動下,產生感性精神域界的量子糾纏與生化反應,而帶有意識形態觀念編碼的“主體”認同機制,隨其運動打開的缺口融入而被無痕跡般地自然接受,便是話語言說行為之于電影敘事情節演進中的暈輪效應,而關乎情感抒敘的“共情”氛圍渲染,即“個體感知或想象其他個體的情感,并部分體驗到其他個體感受的心理過程”[2](P1229-1238)形成,便是其能夠完成并發揮效用的關鍵所在。
涉及情感認知的震驚與共享,“諜戰”類型將之實現的機制著落于一種被視為普遍感知的正常性情感,而置放于非常態的極端情境設定中,形成激烈矛盾沖突下的對比,去形成碰撞。那么,兩者反差的正比乘數,就是“諜戰電影”混合類型本體營構、敘事抒情表達、意識形態話語陳述等諸多功能實現的必要條件,而實現這種正比反差的前提,就是對應“正常情感”認知的大眾公約數與極端情境不可承受烈度之間的距離。因此,越是被普遍接受的基礎性情感,越容易在“諜戰”對抗的殘酷行為中被摧毀,此種聯動關系的設置,就成為這一形態能夠多大限度完滿其藝術表達的關鍵。在“諜戰電影”創作的具體實踐中,這種容易被接受與廣泛認同的基礎性情感,往往首先來源于一種對親緣倫理關系的描述與處理。之于人類情感與人性構成意義而定義的人的價值,關乎“親情”的倫理定位與話語表述,不僅僅是“透過修養和教育,經由藝術與人文,方能成為其真正的人”[3](P4-5)的人文主義理想想象,而且是其能夠通過生物學和社會學基礎理念確立自我為何的原始因子。
從“人類”更新換代的視角,看待“親緣”關系的產生,可以把其追溯到自然生命系統內“個體”與“種群”延續需要的物質實現方式,這是“人”與這個世界目前已知的主要生命形式,共享的“生物學”意義上的“血統”傳承路徑。經由人類歷史由低級到高級階段的發展演變,脫離動物原始本能層面,僅僅依靠“無意識”的簡單群居關系維持的形態,并結合人的“生理”經驗積累,而得出的原初知識判斷,“文明化”的社會開始建立一種從“非正式”到“正規化”的家庭族群倫理規范。這種“規范”的出現,確立了“人類”與“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與關系結構,而以世世代代生活中“固化”下來的“群體”理念傳承,在“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感性體驗碰撞中,構成關于“親情”的理性認知與言說。
在數千年來接續的中國傳統觀念中,以血統親緣傳承與婚姻家庭組織構成的基本群體關系為核心,結合農耕文明長期以來,較為封閉的生活地理空間,造就的意識慣性,一種由若干“原生家庭”(1)“原生家庭”是指“個體”出生后,由幼年到成年的成長階段所生活的家庭,一般由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親緣關系構成,它與“個體”通過婚姻而建立的“新生家庭”區別存在。參見陳公. 原生家庭[M]. 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7:3.為圓心,以父系“宗族”為主,母系“戚族”為輔,婚姻拓展的“家族”網絡為支架,延伸到共同“鄉土”身份的“親緣”關系擴大認同,逐步遞進產生了一種“家國一體”(2)中國儒家文化傳統經典訓示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詞句,是證實其存在的最佳注腳。參見茍琳編著. 溯源:中國傳統文化之旅[M].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142.的倫理觀念,成為中國社會結構現實存在與思維認知的基本模式。
將這種“親緣”生發的倫理關系,作為榮格認定的“集體無意識”傳承的主觀理念與客觀現實來認知,或可理解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經受歷史巨變的過程中,“個體”之人及其所屬“群體”結構所承受的沖擊。先后經歷百余年的“戰爭與革命”“改革與發展”兩大歷史階段的時代“洗禮”,中國人對于“親緣”關系的普遍認知,已然產生了巨大變化,而有關“人性”范疇的“親情”價值,也在“個體”遭遇的具體歷史語境中,呈現出自己的“階段性”與“對象化”特征(3)它對應著時代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觀念的要求,而演變出自我不斷發展的存在狀態,成為一種話語表述的對象之物。。
中國“諜戰電影”創作于不同歷史階段的藝術實踐中,融入時代主流意識形態決定的親緣倫理觀念,在敘事情節、人物關系與場景構設的鋪排下,著力形構了一套符合大眾道德判斷認同的表層話語言說機制,關乎日常生活形態的樸素價值觀念表達,被嵌入“諜戰”對抗的特殊情境,而經由意識形態化的邏輯自證體系所重構,形成符合其目的意識的符碼編程模式,便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不斷復制的“神話”形態,其“基本結構始終如一……里頭的內容就不同……是可以變化的”[4](P61),從而以之尋求某種不變的結構主義式話語模態,而相應變化的是具體社會歷史語境下的敘事構成。
二、社會歷史分期視野下的實踐呈現與邏輯遞進
在中國早期“諜戰電影”創作實踐中,業已有人性“情感”話語言說的自覺應用。“親情”呈現,在注重家庭倫理表達的文藝美學傳統中,也成為不可或缺的“習慣”構成。
在影片《孤島天堂》(1937)中,幫助“特工”殺手搜集情報的東北舞女,回憶“家鄉”淪陷情景而唱起歌曲時(4)東北舞女在自己居住的租屋內,感憐“身世”悲歡與懷戀故土“親情”時,唱起了歌曲《松花江上》,它是20世紀30年代產生,描述“九一八”事變后,國土淪喪與家園被毀的東北民眾悲苦情感的音樂作品。,“親情”作為一種“缺席的存在”,演化成控訴造成這一悲劇的“戰爭”侵略行為的內在意指。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話語表述,同時意在證明“潛伏”間諜組織“暗殺”行動的“合法性”,即為被剝奪安逸與幸福家庭生活的“中國人”討回公道;也希冀通過趕走侵略者,光復國家領土與主權,為國人奪回屬于自己“家園”的地理空間。由此“個人”的家庭生活與倫理親情,便與“國家”命運和“主體”價值觀念連接起來。
影片結尾處取得階段性勝利后,眾人仰望冉冉升起的國旗時的場景,在“家國合一”的言說中,將其由“個人”的情感經歷,延伸到“國族”的群體感受層面,“大主體”的召喚之力就此凸顯。在電影作品文本內,大量對 “都市”空間內貧苦家庭“親情”關系的細致描摹,刻畫出深受戰爭之苦、背井離鄉、顛沛流離的“流浪者”群像,亦是在更為廣闊的社會背景下,對這一話語言說策略的豐富佐證。一種為了國族認同的共有“親情”而“舍生忘死”的精神激勵,就此成為“主體”對于“個體”的“情感”召喚。
《忠義之家》(1946)一片中,國民黨地下“間諜”組織,聯絡隱藏于日軍內部韓國裔情報人員的工作,得到了一位上海老人的幫助,而老人的兒子作為空軍軍官,也因參與抗日救國戰爭以身殉職。親人喪失的情感創痛,化作對國家與民族的責任與忠貞之情,成為其參與“諜戰”行動的動力,影片以正統的“忠義”思想與價值,實現了對民眾“個體”的意識形態話語“詢喚”(5)影片《忠義之家》(1946)結尾處,讓老人以直接宣講的口氣,強調了“個體”應肩負起的國家責任,充滿了意識形態話語味道。參見虞吉. 中國電影史[M]. 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88.。影片《天字第一號》(1947)亦將“間諜”活動的主要場景與范圍,設置于一個家庭之內,多個“潛伏者”圍繞著貌似親密的“親緣”情感展開行動,實際是一種“偽裝”的虛假關系。
在影片《日本間諜》(1943)中,時代興衰榮辱的家國情懷之于民族反侵略戰爭的話語言說,因其角色設置擴大到了第三國國際友人的選擇,而將中國抗戰斗爭的“正義性”延伸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時代大潮中,由此賦予了其更為宏闊的政治格局論說。曾為中國政府服務的意大利人范斯伯,被日本特務機關以家人性命脅迫加入“日偽”組織,卻因其良知未泯,而暗自協助哈爾濱周邊的地下抗日“義勇軍”進行反日斗爭。雖成為一體兩面的雙重間諜,但最終身份面臨暴露,范斯伯被迫逃離而必須與家人別離時,那份不舍的親情令人感動,并順其自然地激發出對侵略者痛恨的“共情”感受。對日本特務機關貪婪而殘忍行為的描述,亦表現在僑居的猶太富商因不肯合作,而遭受兒子被綁架折磨境遇的敘事書寫中,最普泛的家庭倫理與親情撫慰的慘遭扼殺,亦是從最樸素的道德層面對“法西斯”意識形態的否定與控訴,而從反面印證了中國“抗戰”的歷史“合法性”。
在20世紀60、70年代出產的一些“反特”題材“諜戰電影”中,由于“階級斗爭”觀念的過度強調,而把時代意識形態“話語”,附加于“諜戰對抗”的情節。事關“革命”與“階級”的“情感”呈現,在某種“規定性”表達的約束下,成為改變傳統社會結構內“親緣”關系面貌的重要動因。
影片《岸邊激浪》(1964)將“諜戰”故事發生的場景,設置于中國東南沿海小漁村內的限定區域,而這一“有限性”的“空間”,是具備“宗族”倫理結構模式的“鄉土社會”,也是一種歷史演進中的“文化”現實存在。《岸邊激浪》一片截取歷史斷面,在十余年的時間設定內(6)影片將時間設定為1949年、1950年、1962年三個段落,在敘事情節中對應著“漁村”限定空間內,“斗爭”情況的變化:解放軍到來,地主惡霸“蛇頭疔”逃走;基層政權建立,“蛇頭疔”之妻“潛伏”;“間諜”潛入,敵人準備秘密反攻;以鄉村一隅的變化,應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社會結構與族群關系的宏觀變遷。,于敘事言說的“表象”層面,講述了“革命”與“解放”的力量到來,改變了“階級”壓迫的舊有格局,窮苦人就此翻身做主人,而以往的“壓迫者”或者逃離、或者“潛隱”起來,于是往日“鄉土”空間的統治力量,便因權力遭剝奪而地位喪失,淪落為被“放逐”且“邊緣化”的存在。
由“顯在”的優勢而轉為“尷尬”的劣勢之時,不甘心失敗的昔日“統治者”,希冀重新恢復往日的利益與“榮光”。因此“對抗”仍會持續下去,但實力對比的此消彼長,使得他們“斗爭”采取的方式,由“地上”轉為“地下”,不同的“階級”群體由此攻守易位,而被推翻的勢力隱藏起來,成為時刻準備實施破壞與顛覆活動的“威脅”存在。一種“間諜”式的行動與斗爭方式,便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7)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大會依據對國內“階級斗爭”常態化的認知判斷,而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參見吳象. 中國農村改革實錄[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28.的時代意識形態“想象”建構中,變為針對“隱藏”敵人之“反特”行動的敘事緣起。
在這其中,被“階級對立”的觀念主導的“鄉村”生活形貌、人際交往與情感關系,成為受“意識形態”主體價值左右的“想象”呈現。即便如此,依然無法規避傳統鄉村“宗族”親緣關系的展示;即使是作為被隱含否定而彰顯“階級”本位意識的重要手段時,它也成為一種被設定的“對象”。
影片將這種源自傳統“宗族”親緣情感的書寫刻畫,著落于漁村長者“三叔公”與惡霸“蛇頭疔”之妻“淑珍”(8)在承擔影片“諜戰”敘事環節的“人物”功能性設計體系中,淑珍實際是被視作由“昔日統治者”轉化,而留存在原有“鄉土”空間內的“潛伏者”形象。她平常過著普通而“消隱”的生活,而一旦流亡在外的“接應者”發出回歸反攻的信號,“淑珍”這樣的人物,就會成為幫助搜集與傳遞情報的“內應”,她是一種隨時會啟動的備用“間諜”。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出產的不少“諜戰電影”作品中,幾乎都包含著比較類似的“人物”設計,這些配角人物作為“邪惡”主腦的幫兇,以“符號化”的功用存在,其“性格”特征的塑造較為單一,很少有發展變化,行為表現也主要依據環境不同給出反應,但缺乏內心觸動的展示,這是作品對其“人性”刻畫不足的表現,諸如《海霞》中的“尤二狗”、《南海長城》中的“衛太利”都是這類人物。的關系呈現中。在解放軍到來之前,貧苦漁民劉阿炳因抗交“保護費”,而被“蛇頭疔”抓住并要“活埋”處死。作為村中長輩的老者“三叔公”,去乞求“疔”妻“淑珍”放過阿炳,這時弱勢的“三叔公”表現出謙卑而局促的“下位者”狀態,語氣緩慢而小心翼翼,試圖通過某種同村“宗族”式的“親情”倫理與年長者的微薄“臉面”,去換取“淑珍”的寬宥,救下阿炳的性命。
“淑珍”似乎也做出留有“情面”的表示,并拿出些許錢財,讓“三叔公”以長輩的身份帶頭交錢,為對抗征收的漁民做出表率,兩者以表面化的“宗族”親情,為緩和矛盾的立足點,努力達成了某種利益的“妥協”與“默契”(9)這是封閉性的“鄉土社會”處理利益之爭時的某種“智慧”與“狡黠”,它基于“宗族”親緣的倫理“情面”為依托,是彼此爭斗而又依存的“群體”社會結構中,維持社群關系平衡的有效范式。。
在1962年的情節段落中,雙方的身份地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三叔公”成為新生政權中的基層領導力量,擔任所在區域的公社社長與書記職務,而淑珍變為喪失財產、地位與親人的孤寡中年婦女。當她“潛隱”多年,與丈夫“蛇頭疔”派來的“間諜”接頭后,便試圖借用同鄉“親緣”關系的“情面”,去“三叔公”處尋找將情報傳遞出去的機會與途徑。
此時兩人的位置關系已經互換,“淑珍”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宗族”內孤苦女性親屬的可憐形象,去向“三叔公”哭訴阿炳對其的“不公”,并以自稱的“晚輩”名義,為“三叔公”打掃房間,這也是影片于敘事情節的細微之處,對“人性”微妙不可言說的自覺把握(10)“三叔公”去找“淑珍”為阿炳求情時,“淑珍”并未趕盡殺絕的做法,使得之后“三叔公”內心的“無意識”思維中,也認為自己應該對其留有一些“情面”。這是將彼此定位于鄉土“宗族”親緣內部矛盾的處理方式,而并未站在雙方彼此對立的“階級立場”上,以“敵我矛盾”觀念對待的選擇認知,因此他與阿炳產生了分歧。影片結局處的設置,亦是表明了時代意識形態話語對于“階級”觀念與“斗爭”關系定位的絕對表述,它將“階級”主體視作高于一切的“真理”存在,而否定“調和”式的觀點做法與所謂“不堅定”的立場“站位”。。“淑珍”的這一行為,觸發了“三叔公”對“傳統”鄉土“宗族”親緣關系的“眷戀”之情,因此被“珍”找到漏洞,讓其偷取了蓋有公章的“路條”,從而使“潛入”的間諜擁有了從事破壞活動的機會。
影片以最終“間諜”被拿獲,“三叔公”痛悔檢討自己沒看清“地主婆”真實面目的“話語”表達,對傳統鄉土“宗族”親緣關系的固化思維給予了隱晦的否定。因為它是影響“階級立場”認同的異質因素,而將其設置于“諜戰”敘事的轉折之處,恰是為了以符合“人性”情感與認知邏輯習慣的方式,將意識形態“話語”主張的價值觀念與判斷,“自然化”地鑲嵌于電影文本的情節構設之中,讓觀者將其認同為一種合乎現實邏輯的“事實”與“真理”。
除去“鄉村”空間內“宗族”式的“親緣”關系呈現外,中國“諜戰電影”作品,亦未忘記在“都市”場景內,涉獵間諜活動中的“親情”關注書寫,意識形態話語加諸于這一敘事主題的言說表述,同樣以否定方式,確證了“情感”能夠延續與存在的可能。
在影片《天羅地網》(1955)中,由香港潛入東南沿海某城市的國民黨“間諜”——郭浩,就利用了自己的家庭空間,作為身份掩護的手段。他離家出國多年,回來后與老父及外甥女高興親切地傾訴交流,一種其樂融融的陽光氛圍,簡單的“鏡語”對話,渲染出樸素親切的親人重逢場景。
郭浩成熟鎮定、情商極高,很快就跟外甥女金一萍拉近關系(11)金一萍是一位十多歲的少女中學生,是郭浩姐姐的女兒,影片中“金”的父母是“缺席”而不在的,只與隔代的外公相依為命,這時作為舅舅的“郭”出現,以一種寵溺子女的長輩形象,在情感上適時填補孩子“父輩”親情的缺失,也是符合普泛的“人性”倫理的設置。然而,影片在初次見面的場景中,已然為其后來自“親人”的傷害言說埋下伏筆。郭浩首次見面送給外甥女的香港高級圍巾,被女孩兒直接拒絕,她表示自己有“紅領巾”就足夠,郭亦反應迅速,問“金”喜歡什么,“舅舅”可以給其買來。“紅領巾”,在這里是明顯具有政治意識形態意義的象征之物,“金”在此對其珍視,而拒絕域外時尚消費品的行為,實際在此指涉了受社會主義教育的少年兒童,拒斥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思想立場表達。結合時代政治話語特點,也就容易理解影片敘事設計,對這一細節的處理了,“金”接受的思想教育方式,決定了他們甥舅之間所處立場陣營的對立,因此最終的沖突也就難以避免。這一時期電影創作中對“親情”的刻畫,仍然遵循“政治”與“階級”陣營對立關系的“先在”需要,因此“非政治化”的親情言說,就成為不可顯現的存在。,并且在孩子不知情的情況下,讓其代替自己去跟當地的“潛伏”間諜——林金標見面,接頭并傳遞相應的情報。電影作品在此把郭浩描述為一個利用“親人”,哄騙未成年少女卷入危險活動的“欺詐者”,從關涉人倫親情的“人性”價值層面,對其“品行”進行了負面評判,而將意識形態話語立場的表達隱藏于其后(12)郭浩歸家時,影片借金一萍與郭父之口,給其講述了新生政權執掌國家后,生活帶來的可喜變化,一種“老有所養”的欣悅之情,恰恰映襯了“郭”所代表政治陣營的孤立感,因為來自民眾與親人雙重身份的否定,而相應給對手做出的積極評價,就以對比模式傳遞了究竟誰為國家“合格”執政者的話語“確證”。在國人“家國一體”的慣性思維機制中,長輩與晚輩“親人”的一致觀點表達,就是對“郭”所持政治立場與行動作為的最大否認,這種源自“親情”倫理的“話語”表達極其有力。。
在影片的結尾處,郭浩“間諜”身份與行動的暴露,亦與金一萍向老師和“反特”公安偵察員王英的舉報有關。“郭”在逃跑時也將“金”打成重傷,由此一種源自血緣親情的“人性”倫理關系,便在這種“諜戰”對抗生死博弈的局面中,因“親人”間政治立場不同,互相傷害的結局,而最終歸于消解,呈現出不可正常存續與發展的狀態(13)在影片《天羅地網》的結尾之處,身為“戀人”的教師何瑞先與公安人員王英一起,牽著少女金一萍之手,于海邊公園快樂游玩的場景,以象征化地手段,形構了一個被“政治”話語替代補償的幸福家庭場景。“親緣”之情突破了自然血統界限,成為一種被“泛化”的言說。電影作品亦在傳遞社會主義的新型“親情”倫理觀,它也是源自“幼有所教”的儒家傳統思想觀念,包含著某種“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政治意識形態話語,就此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樸素倫理觀念,完成了有效對接,更易為一種“人性化”的面貌出現。“十七年”時期的中國“諜戰電影”作品中,這是經常被拿來使用的慣性敘事設置與話語表述模式,在《三八線上》(1960)、《冰山上的來客》(1963)等影片中都有類似的體現。。
新時期之后,由于時代意識形態主題的改變,電影作品不再強調“革命”與“階級”的政治話語立場。因此“親情”倫理表述的“日常化”成為常態,取代了之前過于“單一化”且“立體化”不足的呈現方式,而以艱難生存境遇中的“個體”行為選擇過程,描摹“人性”在多重復雜價值理念加成下的多向發展“可能性”。
《波斯貓在行動》(1986),就刻畫了一位極為珍視“母子”親情的軍統特工殺手胡鐵雄的形象。影片將其執行“間諜”任務的執著與對倫理親情的渴望雙重“性情”融合起來,構設了其人物性格的內在統一性,而更于兩者互相抵觸的矛盾沖突中,凸顯電影作品藝術創作的敘事張力。去除以往固化的政治立場表述,彰顯了該時期文藝創作中,日益增強的“普泛性”人文關懷意識。在主流意識形態觀念重新厘定的話語修飾策略中,影片對待敵方“間諜”的態度,也是希望以“寬宥大氣”的格調,試圖完成與“歷史”的和解,亦體現出時代“主體”意志中,期盼完成“國族”話語的重述,實現和平統一的民族復興愿望(14)軍統特派殺手胡鐵雄執著地要完成刺殺陳毅的任務,而陳毅卻大度表示不計私人恩怨而希望其迷途知返;“胡”的執念,一方面使其不顧“陳”當年的救命之恩,另一方面也拒絕母親的“親情”勸導與召喚;影片以樸素的人情倫理價值層面,而不是傳統的“階級斗爭”言說模式,對“胡”行為進行了一種間接隱藏的否定,從而實現了時代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重構。。
《與魔鬼打交道的人》(1980),則從另一角度,顯現了秘密戰線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艱難心路歷程與潛伏斗爭面臨的復雜性。它不是“十七年”時期革命英雄主義式的詩性吟詠與光輝展示,也不是簡單地不怕犧牲與智勇雙全的神話人物再造,而是真正從人性與人的情感經歷的痛苦煎熬出發,來描摹一個地下工作者所要經歷的磨練與考驗。主人公于海濤/張公甫在面對親人時需要隱藏身份,不能真實表達自己立場,而被同屬革命陣營的親屬誤解,仍舊堅持不動聲色游走于敵營完成任務的艱辛與苦痛,反而在一種強烈的“情感”詢喚邏輯中,表明了革命英雄對于自我信仰的忠誠與堅守。“主體”意志的精神力量和話語表述的自洽體系,恰恰與時代文藝創作思潮中涌動的“人道主義”氛圍與傷痕言說相呼應。受到冤屈而癡心不改的道德化人物塑造與書寫,也深受這一時期所流行的“謝晉模式”電影創作實踐的影響,而呈現出特定歷史階段藝術審美認知與社會價值觀念的普泛效應。
新世紀之后的“諜戰電影”作品,由于受到消費主義價值觀念的影響,傾向于過度商業化的“類型”形式感營造,注重動作場面的“激烈性”與劇情沖突的“復雜性”。崇尚“高概念”(15)“高概念”電影是對20世紀后期,好萊塢大工業化制作的“超真實”、大場面的影像風格,以及相應的市場推廣標識與策略的總結表述。它注重敘事情節的簡單明確,人物角色功能設置單一,強化“視聽”技術手段運用,帶來的感官刺激,偏重“明星魅力”與“工業標準”,是一種具備超強“形式感”的電影風格追求。參見邱章紅. 高概念電影:形式、風格與市場[J]. 電影藝術,2011,(4):132-138.、快節奏的影像風格,而疏于細膩描摹較為平淡的“親情”關系呈現,因此在創作上,多少表現出人文倫理精神的欠奉與歷史現實主義的缺失,其不足之處值得深思。
《東風雨》(2010)中,僅以軍統頭目“寓公”的間接口述,介紹了特工“歡顏”一家十幾口死于南京大屠殺的慘劇,試圖營造一種“家國同殤”的悲壯言說,但似乎淹沒在紛繁蕪雜的情節中。《誰是臥底之王牌》(2014),雖有作為共產黨人的王霞芬勇于擔當、慷慨赴死,犧牲了自己和未出生孩子性命的強化書寫,但最終所有承受酷刑的地下黨人所保護的秘密——“王牌”到底意義為何,也在過于追求神秘懸念的構設中不了了之,那么“主體”價值“詢喚”的缺失和英雄犧牲的歷史“沉沒”,乃至數名柔弱女性遭受的殘酷刑虐與其親人生命的逝去,又該怎樣獲得“倫理”話語的合法報償?過于殘酷陰暗的情境設置和“主體”形象的模糊缺席,由此造成了話語價值自證環節的短路。《密戰》(2017)中,僅僅依賴林翔講述父親犧牲的故事,就能促成梁棟從與“日偽”合作的租界巡捕到“抗日”活動支持者的轉化?未曾謀面的血緣傳承,真得能夠替代缺失了的親情陪伴成長與觀念教育養成?這一系列作品中的情節邏輯,顯然因為過于牽強,而造成了“主體”詢喚的某種斷裂。《懸崖之上》(2021)一片是近年來鮮有的以較為完備的類型書寫,充盈“諜戰”序列創作的實踐范本,其中亦涉及了為赴敵后完成特殊任務而壯烈犧牲的“抗日特工”做出巨大親情犧牲的敘事言說,但由于電影文本時長所限及創作者基于審美節制需要而惜墨如金般一筆帶過,使得關乎“諜戰”殘酷情境下情感與心理創傷的深度挖掘難以從容展開,因此僅僅只是作為一條副線補充人物塑造的間隙而簡單勾勒,那么電影作品對于意識形態主體價值情感“詢喚”與共振幅度,就會略顯不足,這也是一種藝術取舍之間難以完滿的缺陷與遺憾。
三、不可實現的無限延拓與“主體”自證體系的構成
作為人類普泛情感認知中的基礎性存在和社會倫理價值的基本組成因素,之于日常生活環境內的思維邏輯與秩序體系,親緣關系和親情呈現被放置于“諜戰”對抗的極端藝術情境,成為造成文本戲劇張力與提出終極人性拷問的激烈沖突節點,而顯現出藝術本體形態分類核心要點和審美接受期待系統的功用性定位。情境沖突之內構成的敘事書寫,以正常的親情倫理不可實現的無限延拓,構筑美好事物被殘酷現實摧毀的悲劇美學演繹的“崇高”與“肅穆”之情,而形成其追尋的最高價值話語體系的言說渠道,關乎“主體”意志的“詢喚”,成為證明“主體”合法存在與永恒正義的神話敘述。
親緣關系的非正常化與親情表達的不可實現,一方面是文本之外社會歷史造就的戰爭之慘烈現實與“諜戰”本身更為極端殘酷的事實所致,電影敘事以現實主義美學追求對其進行還原再造,由此對發動侵略戰爭的一方及其“間諜”活動破壞性存在的“非義性”提出詰問,那么與之對立的反戰、反侵略乃至“反間諜”的“主體性”立場,自然因為維護正常秩序以求親情美好得以延續存在的情感話語邏輯而獲取“合法性”的自我證明。另一方面,將“間諜”作為正面形象加以塑造,那么其親情關系的不可存續,則成為隱蔽戰線的英雄自我奉獻與犧牲的代價與“獻祭”,唯有在這種受難的考驗與展示中,英雄的“主體性”價值才能經由儀式化過程而獲得神圣命名,基于普遍倫理感受的“共情”認同,則得以通過“情感”“詢喚”的路徑,成為“大主體”建構自我價值的隱性訴說。
在文本內外的社會歷史與藝術歷史疊加的復雜語境中,不同時期的中國“諜戰電影”關于親緣情感的敘寫,受到意識形態話語的影響,而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從抗戰前后樸素的“家國情懷”召喚,到“十七年”時期階級斗爭觀念指導下,對傳統宗族親緣關系的否定,而企圖建構社會主義制度與“革命”話語下的新型情感認同,再到新時期之后,轉向關注歷史大背景下的“個體”命運及人道主義視角下的微觀情感,由此上升到關于人性價值的一般思考,最后演化成新世紀之后消費主義文化主導及“新主流”觀念意圖重寫歷史的訴求下,難以界定而近乎失焦的隱形書寫,中國“諜戰電影”中的親緣倫理話語表述,顯現出在超越時間的一般邏輯自證體系之外,與時代現實及主流認知相契合的言說方式與敘事設定,“主體”包含的價值內涵也隨其而動,延伸成為符合歷史“具體性”變化的動態曲線與特殊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