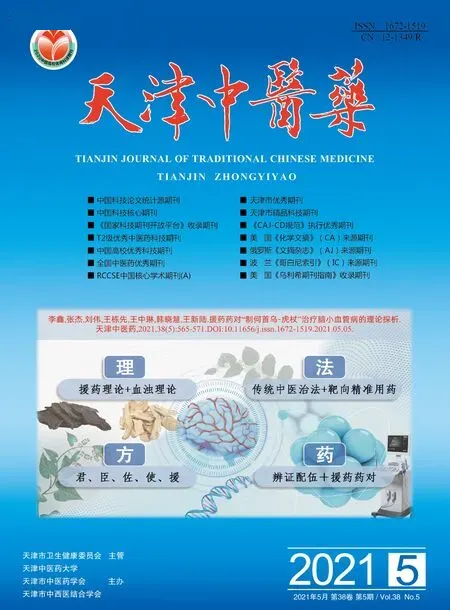馬曉北教授從調氣機論治尋常型痤瘡思路*
姚淵,馬曉北
(1.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所,北京 100700;2.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00)
尋常型痤瘡是累及毛囊皮脂腺的一種慢性炎癥性皮膚病,好發于青年男女,臨床表現為粉刺、丘疹、膿皰、囊腫、結節等多形性皮損,散在對稱分布于面、胸、背。嚴重者遺留色素沉著和永久性瘢痕,影響患者面容,產生心理壓力。西醫認為尋常型痤瘡的發病主要與雄激素的升高及皮脂的增加,毛囊皮脂腺開口處過度角化,痤瘡丙酸桿菌感染及繼發炎癥反應等四大原因相關,部分還與遺傳、免疫、情緒、飲食、內分泌等因素相關[1]。
本病在中醫中又稱為“痤痛”“痤”“痤疽”“面上粉 刺 ”“ 酒 皶 ”“ 瘡 ”“ 面 皯 ”“ 面 皯 皰 ”“ 面 渣 皰 ”“ 面 粉滓”“粉刺”[2]等,多由火熱耗氣傷津致瘀或外感風寒內有郁熱成瘀[3],脈絡閉阻,脂凝邪聚[4],病變涉及多個臟腑,病情復雜,治療重點在“瘀”。馬曉北研究員系中國中醫科學院博士研究生導師,從事中醫內科臨床近30年。馬曉北教授認為尋常型痤瘡的根本病機為氣機升降失常,治療重點在“調氣機”,筆者有幸跟診學習,現總結治療思路如下。
1 病因病機
馬曉北教授認為,與痤瘡發生關系最密切的臟腑是肝脾胃。《傅青主女科》中云:“肝屬木,其中有火,舒則通暢,郁則不揚。”[5]肝主疏泄,調暢情志,由于現代人工作壓力增大,生活習慣改變,情緒波動較大,情志不舒,必然會影響肝的功能,致使氣機不暢,郁而化火,火性炎上,發于顏面而為痤瘡,表現多為毛囊性的丘疹,顏色呈淡紅或暗紅色,伴有易惱怒,性情急躁,月經不規律,舌暗紅或有瘀斑,脈弦而數等。
中醫認為“脾胃為氣機升降之樞紐,氣血生化的根本來源”[6],氣機升降出入溝通身體內外,助運五臟六腑,促進人體正常新陳代謝。無論風熱、痰濕、血熱,均影響到氣的運動,使得氣機上下升降失常,濁氣應降而反升,氣夾痰濁等邪上應于面、胸、背而出現痤瘡。所以馬曉北教授認為,尋常型痤瘡的發生,其本在于氣機逆亂,升降失調,其標在于風熱、血熱、濕熱、痰濁等,病位主要在肝脾胃,進而影響肺腎。
2 治則治法
馬曉北教授認為尋常型痤瘡由臟腑功能失和引起,與肝脾胃皆有關聯,最終影響到氣的升降,并且與個人體質情況和飲食生活習慣有很大聯系。平素飲食肥甘厚味,情志抑郁不暢,致使脾胃失和,運化失常,肝失疏泄,臟腑功能失調,氣上下升降失常,夾邪發痤瘡于面、胸、背。所以馬曉北教授對尋常型痤瘡辨證仔細,對證治療,重點放在氣機的條暢方面,兼顧肝脾胃,舒暢氣機,調肝健脾。
2.1 調肝以通氣機 《靈樞·經脈篇》曰:“肝足厥陰之脈,起于大趾叢毛之際,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于巔。其支者,以目系、下頰里,環唇內。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足厥陰肝經經過口面唇額部,所以這些部位發生痤瘡可以將肝經郁滯作為原發因素考慮[7]。肝主疏泄的作用使其參與并協調各臟腑進行水液代謝,對于維持脾胃氣機升降起到了重要作用,又可調節全身氣血運行,保證氣血運行無阻到達全身,肝的功能失常,氣血運行受阻,經脈郁滯,則發痤瘡。所以馬曉北教授認為痤瘡的治療要注意疏肝氣,調肝血。肝血足,氣機暢,氣血運行無阻,則痤瘡易愈。
2.2 運脾胃暢氣機 《素問·生氣通天論》載:“汗出見濕,乃生痤疿。”患者汗出,汗聚于表,汗多成濕,郁閉肌膚,阻塞玄府,故成痤瘡,此為外濕為患,對氣機的升降產生一定的影響。有一類患者平素嗜食肥甘厚味,辛辣油膩,導致脾虛運化失職,飲食水谷難以運化,聚而成痰,水不化而為濕,痰濕內蘊,隨失常之氣機,凝聚肌表,毛孔阻塞,出現痤瘡。
馬曉北教授認為濕邪的產生與中焦脾胃關系密切,脾喜燥而惡濕,脾失健運,濕不得化,故易生痤瘡,所以治療應運脾胃而化濕,濕邪去而氣機暢。濕邪為患多纏綿難愈,所以病情反復在所難免。而濕又有內外之分,所以馬教授在臨床遇患者痤瘡反復發作的時候,均考慮內外濕對氣機的影響。并囑禁食辛辣刺激性食物,多食蔬菜,清淡飲食。
3 臨證選方
基于以上對尋常型痤瘡的認識,馬曉北教授經過多年的臨床總結,運用升降散合四逆散,并合知柏地黃湯、五味消毒飲、龍膽瀉肝湯、清胃理脾湯等經典名方治療,得心應手。并在此基礎上,病證結合,靈活加減,治療尋常型痤瘡療效顯著。
四逆散疏肝理氣,調理氣機,適用于以肝郁氣滯為主,痤瘡表現為毛囊性的丘疹,淡紅或暗紅色,伴有易惱怒,性急躁,月經不規律,舌暗紅或有瘀斑,脈弦而數者;知柏地黃湯滋陰補腎降火,調理肝腎,適用于陰虛火旺,痤瘡表現為病程長,顏色暗紅,跟腳散漫,有結節,無膿尖,不瘙癢等特點,并伴隨失眠多夢,盜汗,五心煩熱,舌紅苔少脈細數等陰虛癥狀患者;五味消毒飲清熱解毒之力強,適用于熱毒熾盛,臨床表現多為痤瘡顏色鮮紅,跟腳緊束,疼痛較甚,或伴有膿皰,有白頭或黑頭粉刺,伴隨舌紅少苔,脈洪大而數者;龍膽瀉肝湯泄郁火,清濕熱,適用于肝膽火郁,下焦濕熱,臨床表現痤瘡有膿,或有疼痛瘙癢,面部潮紅灼熱,伴隨胸脅脹滿,口苦咽干,舌紅苔薄黃或膩,脈弦滑數者;清胃理脾湯燥濕運脾,清利濕熱,適用于濕邪較重困阻脾陽,臨床患者痤瘡多表現有結節或囊腫,色紅不鮮,破潰后易留疤痕,并伴有有四肢沉重,倦怠嗜睡等癥狀。
臨床中,馬教授根據患者具體癥狀,以升降散為主方加減合用,使得氣機通暢,熱毒盡解,痰濕皆消,痤瘡即愈。
4 典型病案
4.1 病案1 患者女性,15歲,2019年2月24日初診,面部痤瘡3年,加重1年余。12歲月經初潮,前額部,后背部痤瘡,近1年鼻翼兩側、面部均出現痤瘡,有加重趨勢,顏色暗紅,油脂多,破潰后有瘢痕。月經規律,末次月經:1月18日來潮,持續7 d,色紅,量多,經前無乳房脹痛,白帶不多,偶爾有痛經。平素易外感,易發熱,咽痛,咳嗽,手足冰涼,納一般,眠可,大便2~4 d 1行,質偏干,煩躁易怒,頭發出油多,口苦,口干。觀其舌淡胖苔白微膩、脈沉弦滑。西醫診斷:尋常型痤瘡;中醫診斷:面上粉刺,中醫辨證:氣郁化火,痰濕內蘊,治當疏肝解郁,消痰祛濕。處方:酒大黃9 g,蟬蛻6 g,僵蠶10 g,姜黃10 g,柴胡 15 g,枳實 12 g,白芍 12 g,甘草 10 g,黃芩 9 g,黃連 9 g,蒲公英 15 g,茵陳 15 g,紫花地丁 12 g,連翹 15 g,浙貝母 12 g,玄參 18 g,牡丹皮12 g,當歸 15 g,金銀花 15 g,大棗 10 g,7 劑,水煎服,每日1劑,早晚溫服,囑:少食辛辣油膩。2診:上方藥后痤瘡未再新起,大便每日1行,不成形,無腹痛,口干口苦減輕,口中異味無,仍煩躁。觀其舌淡紅苔不膩、脈弦滑。處方:前方去黃連加法半夏10 g,炒梔子9 g。7劑,服法同前。3診:口不干,不苦,仍煩躁,大便每日1行。末次月經:2月5日至今。面額頭部起大約1~2個痤瘡,大便不成形。舌淡紅苔薄白、脈細滑。續服7劑。
按語:本例患者為尋常型痤瘡,證屬氣機不暢,郁而化火,痰濕內蘊。肝氣郁滯,氣機不暢,故而煩躁易怒,口干而苦;痰濕困脾,濕邪聚于內,出現頭發出油多,苔膩。總體來說,是氣機不暢,郁而化火,兼有痰濕。治療以升降氣機,條暢上下,疏肝解郁,方用四逆散合升降散加減。升降散通行上下,內外調和,使氣順達,四逆散解郁疏肝兼以理脾,使得肝舒而脾健,郁火散而痰濕行。再加黃連、黃芩、牡丹皮、蒲公英、連翹、金銀花、紫花地丁等清熱解毒取五味消毒飲之意。加玄參消散腫毒,浙貝母能增強化痰之效,《神農本草經百種錄》提及當歸“主諸惡瘡瘍,金瘡,榮血火郁及受傷之病”,所以當歸能消瘡瘍,對于痤瘡有一定的治療作用;加大棗健中焦,助運化,從而取得療效。2診痤瘡得以控制,加強清熱消痰之力加以半夏、梔子。3診,痤瘡幾近痊愈,故續服鞏固療效。
4.2 病案2 患者女性,12歲,2018年11月28日初診,面部痤瘡3年。面部多發痤瘡,顴部較多,粟粒樣小丘疹,無膿尖,無瘙癢。出生時早產20 d,體質量1 800 g。入眠難而多夢,大便質干,2~3 d 1行。小便不黃。納可,喜甜食,如奶糖等。汗出不多。舌淡紅苔根厚膩,脈沉。西醫診斷:閉合型粉刺。中醫診斷:痤瘡。中醫辨證:陰虛火旺,氣機不暢,治以滋腎陰,調氣機。處方:酒大黃6 g,蟬蛻6 g,僵蠶9 g,片姜黃10 g,山藥15 g,山茱萸9 g,牡丹皮9 g,茯苓15 g,澤瀉 10 g,生地黃 15 g,玄參 20 g,麥冬 15 g,首烏藤 18 g,遠志 9 g,炒酸棗仁 15 g,百合 10 g,知母 6 g,連翹 12 g,浙貝母 10 g,7 劑,水煎服,每日1劑。2診:藥后面部痤瘡減少,大便每日1行,眠較前轉佳,納可,不再喜食奶糖,舌淡紅根白膩浮起,脈細滑。處方:前方去百合,遠志,炒棗仁,酒大黃減至3 g,連翹加至15g,續服14劑鞏固療效。
按語:本例患者證屬腎水不足,陰虛火旺,致使氣機上下失常。痤瘡由虛火所致,故而其表現為粟粒樣,無膿尖,亦無瘙癢的特點;腎水不足,不能上濟心火,故而出現眠而多夢。治療總體是以滋養腎陰,調暢氣機為主,處方以升降散合知柏地黃湯加減。連翹能治療一切癰瘍腫毒,苦寒之性弱于黃柏,故以連翹代黃柏,既不至于苦寒傷陽,又能清其虛熱;因患者有大便干燥,故而熟地黃改生地黃,并加玄參、麥冬為增液湯以滋陰潤燥通便;首烏藤、百合、遠志、炒酸棗仁安心神,滋腎陰,助睡眠;因其舌苔厚膩,內有輕微痰濕,故加浙貝母以增化痰清熱之效。2診眠佳,故減去百合、遠志、炒酸棗仁;大便通暢,故減少酒大黃用量;加大連翹用量以增強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