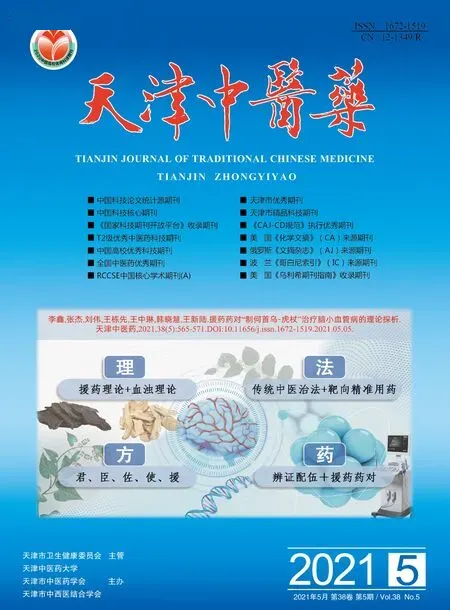《理瀹駢文》外治思想在胃腸惡性腫瘤綜合治療中的應用*
王一同 ,左明煥 ,鄭俊超 ,王超然 ,李彬彬 ,周琴
(1.北京中醫(yī)藥大學,北京 100029;2.北京中醫(yī)藥大學東方醫(yī)院,北京 100078)
《理瀹駢文》取“醫(yī)者理也,藥者瀹也”之義,原名《外治醫(yī)說》,由清代醫(yī)家吳尚先所著,是他一生外治經驗的總結。該書自《素問》《靈樞》而下,博采眾長,囊括靡遺,是中國醫(yī)學史上第一部外治法專著,被后人稱為“外治之宗”。書中提出的“外治之理即內治之理”“外治亦本于辨證”“三焦分治”“藥專力厚”“拔截相得”“膏統(tǒng)百病”“針藥并施”“以通為用”等外治理、法在內外婦兒諸多病種的治療中發(fā)揮重要作用[1]。
近年來,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飲食結構的改變,胃腸惡性腫瘤的發(fā)病率逐年增高,嚴重威脅人們的健康[2]。隨著相關檢驗、檢查技術及治療手段的進步,手術、放化療、靶向治療、中醫(yī)藥治療共同構成胃腸惡性腫瘤綜合治療模式,改善了預后。中醫(yī)外治法作為胃腸惡性腫瘤中醫(yī)藥治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劑型多變,局部用藥,直達病所等優(yōu)勢。由于中醫(yī)外治法能減輕患者的胃腸負擔,對于脾胃虛弱的胃腸惡性腫瘤患者尤為適宜[3-6],特別是在胃腸惡性腫瘤術后并發(fā)癥(如胃癱、腸梗阻)、化療相關惡心嘔吐、放射性腸炎及晚期患者腹水、癌痛控制等方面的綜合治療中得到廣泛的應用。文章現(xiàn)將《理瀹駢文》外治理、法在治療上述病證時的指導意義進行詳細闡述,以期為胃腸惡性腫瘤的綜合治療提供更多元化的治療思路及方法。
1 辨證為本,局部為先
《理瀹駢文·略言》記載:“外治之理即內治之理,外治之藥亦即內治之藥,所異者法耳,醫(yī)理藥性無二,而法則神奇變幻。”指出外治法與內治法都應在中醫(yī)辨證論治為核心的指導思想下進行,應明陰陽,識臟腑,求病之本。吳尚先明確了八綱辨證亦是中醫(yī)外治法的總則,在審四時五行,查病形病候的基礎上,明寒熱、表里、虛實病機,施以不同的劑型及藥物,方可達事半功倍之效。該書闡述膏藥亦有陰陽、寒熱之別,是辨證外治的重要體現(xiàn)。
因外治法主要針對局部病證,因此辨證的依據應以局部癥狀為先。局部辨證是中醫(yī)辨證論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時比整體辨證更直接、更明顯、更具體[7]。如胃腸惡性腫瘤患者,在經歷了手術、放化療等治療后,尤其是晚期患者,常出現(xiàn)整體(氣血虧虛)與局部(寒、痰、瘀、毒壅滯)辨證不統(tǒng)一的情況,此時外治法則多發(fā)揮祛除痰瘀癌毒等治標之用,與補益藥物的內服相互配合,內外兼治,增強療效。對于胃癌術后胃癱患者,可予行氣消痞之胃癱外敷方敷于中脘和神闕穴(避開刀口),該方以木香、丁香、枳殼、全蝎、穿山甲為底,根據脘腹部對寒熱的偏嗜進行辨證,畏寒喜溫者酌加干姜、肉桂、吳茱萸等,生姜汁調藥,并于敷藥前后配合艾灸,防止對局部的冷刺激,促進藥物更好吸收;惡熱喜涼者酌加大黃、冰片等,涼綠茶汁調藥,直接貼敷于局部,療效顯著[8]。對于腸道惡性腫瘤術后功能性腸梗阻的患者,由于術中清洗、術中暴露,可使寒濕直入,陽氣受損,局部辨證多見寒濕內阻證,外治貼敷、灌腸時多以溫通、溫化之品,切忌不辨寒熱,誤用大黃、芒硝等藥,一味通下。對于晚期胃腸惡性腫瘤伴腹水的患者,可采用辨證中成藥注射液腹腔局部灌注的方法進行治療,腹腔灌注使藥物直接作用于腹腔,是基于現(xiàn)代醫(yī)學技術的中醫(yī)外治法的延伸。《素問·至真要大論》記載:“水液混濁,皆屬于熱;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于寒。”因此對于血性、渾濁腹水,腹部喜涼,局部辨證屬于濕熱毒證者更宜使用寒性藥物如華蟾素注射液、復方苦參注射液等[9],對于澄清、黃色腹水,腹部喜溫,局部辨證為寒濕毒證的患者更宜使用溫性藥物,如鴉膽子油乳、康萊特注射液等[10]。辨證外治思想的提出是確立外治用藥、劑型、給藥途徑及劑量的根本,也避免了后世一法一方混治一病諸證的誤區(qū),指導意義重大。
2 三焦分治,各行其徑
“三焦分治”是《理瀹駢文》中最具代表性的外治思想,該書略言中記載:“大凡上焦之病,以藥研細末,鼻取嚏發(fā)散為第一捷法,蓋一嚏實兼汗、吐二法;中焦之病,以藥切粗末炒香,布包縛臍上為第一捷法;下焦之病,以藥或研或炒,或隨癥而制,布包坐于身下為第一捷法。”指出上焦、外感之病應用引嚏、催吐、發(fā)汗之法使病邪從上而出,從表而出;中焦之病以藥敷臍,或填、熏、蒸臍,隨癥酌用;下焦之病,無不可坐,此為釜底抽薪之法。該分治理論也是《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記載的“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寫之于內”理論在外治應用中的具體發(fā)揮,兩者均提示在外治疾病時亦應辨明病位,因勢利導。
胃腸惡性腫瘤患者病在中、下焦。胃癌術后胃癱、化療后惡心嘔吐等癥病屬中焦,可用粉劑、膏劑外敷于胃脘部,或加用按摩手法,即膏摩外治法,促進局部氣血循環(huán)及藥物吸收,加強療效[11]。李佩文等[12]研究發(fā)現(xiàn),中藥敷臍可促進胃腸惡性腫瘤根治術后患者的胃腸蠕動功能的恢復。放射性腸炎病屬下焦,若出現(xiàn)放療后肛周紅、腫、熱、痛,可采用清熱涼血解毒之品(苦參、蛇床子、牡丹皮、赤芍、皂角刺等)熏洗、坐浴,緩解局部癥狀。金宗英等[13]研究顯示,中醫(yī)辨證熏洗可促進低位直腸癌保肛術后患者排便功能的恢復,可見坐法在下焦腸腑疾病中的廣泛應用。根據《理瀹駢文》中的“三焦分治”理論,結合胃腸病位的特點,可使藥物能更好地順應三焦生理特點而發(fā)揮效用,其法妙哉。
3 直達病所,峻藥為引
清代醫(yī)家徐靈胎云:“湯藥不足盡病……若其病既有定所,在皮膚筋骨之間,用膏貼之,或提而除之,或攻而散之,較服藥尤捷。”道出了中藥外治法可使藥物直達病所的優(yōu)勢。《理瀹駢文·略言》記載:“外治之法與內治并行,能補內治之不及”,“治在外則無禁制,無窒礙,無牽掣,無黏滯”,中醫(yī)外治,藥物直接滲透于病灶,對于胃腸惡性腫瘤患者正無礙胃之牽掣。《理瀹駢文》對于外用藥引藥的選擇上,推薦使用峻藥,如書中記載:“膏中用藥味,必得通經走絡,開竅透骨,拔病外出之品為引。”因外用藥要透過局部皮膚的屏障作用,因此在藥物選擇上應多用一些藥力專厚、氣味濃烈之峻藥,才能更好地引藥入病所。基于此,在胃癱外敷方中選用穿山甲、細辛、木香等辛香走竄之品;在化療后手足綜合癥外洗方中選用川烏、草烏、桑枝等通絡力猛之品;對晚期癌痛患者,予生阿魏、生天南星、乳香、沒藥、水蛭、冰片等藥打粉外敷。生藥的應用是鑒于書中“炒用、蒸用皆不如生用”的觀點。一般炮制藥物是為了緩和藥性,而生用藥保存了藥物最原始的峻猛性味,從而引藥入里,使局部瘀滯得散,或拔毒外出,使經絡腸腑得通。峻藥的應用,是中醫(yī)外治與內治選方用藥時的重要區(qū)別,重劑直投,效如桴鼓。
4 拔截新用,斷其傳變
《理瀹駢文》在闡述拔、截法時記載:“凡病有所結聚之處,拔之則病自出,無深入內陷之患;病所經由之處,截之則邪自斷無妄行之虞。”可見拔、截之法是阻斷疾病傳變的重要方法,該法對于易發(fā)生全身轉移的胃腸惡性腫瘤疾病意義尤為重大。拔法在古時主要用于膿毒蘊積之瘡瘍,藥物使腐肉脫落,促進愈合。而西醫(yī)采用腫瘤根治手術或局部姑息性手術(如氬氦刀、射頻消融)將瘤體從體內拔除的過程是拔法新用的具體體現(xiàn)。胃腸惡性腫瘤容易發(fā)生肝轉移,肝動脈栓塞療法直接阻斷瘤體血供,是治療肝轉移的常用療法。黃瓊等[14]、施航等[15]研究發(fā)現(xiàn),華蟾素注射液配合化療藥肝動脈灌注治療胃腸惡性腫瘤肝轉移有減毒增效作用,其機制與華蟾素注射液局部高濃度給藥可抑制腫瘤血管新生有關[16]。以上截斷瘤體血供的治療方法,可直接發(fā)揮抑瘤作用并阻止其進一步轉移,是外治截法新用的具體體現(xiàn),斷其傳變,延緩病情進展。
5 針膏并施,以通為用
《理瀹駢文》提出的用膏之法是該書的重點,后世總結吳尚先的一項重要學術觀點即為“膏統(tǒng)百病”。吳尚先認為“凡湯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并在《內經》《難經》的理論基礎上總結出“審陰陽,察四時五行,求病機,度病情,辨病形”的用膏五法,提出“膏藥,熱者易效,涼者次之;攻者易效,補者次之”,“膏用藥味,必得氣味俱厚者方能得力”等理論,為后人運用膏方療法提供了指導。吳尚先推崇“膏統(tǒng)百病”,意在因外治膏方既可避免內服湯藥煎服之繁瑣、苦口之弊端,又可防止因辨證失誤或用藥不當,避免“陡然下咽,入胃,并可以斃”的嚴重后果,在疾病治療范圍方面,膏方甚至可超過湯藥,因此,提出膏方可治百病的觀點,強調膏方的使用范圍廣泛,對世人認為膏方使用有局限性這一認識進行糾正。
膏雖可統(tǒng)百病,但吳尚先在外治時不排斥聯(lián)用他法。《理瀹駢文》提出的針膏并施是該書的另一大特色。在選擇用膏部位時,吳尚先結合針灸經絡腧穴理論,將膏藥貼敷于特定經絡走行部位,如上焦之病選膻中、背心等穴,中焦之病選神闕、脾俞、胃俞等穴,下焦之病選命門、關元、涌泉等穴。還借鑒古針灸法“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取之旁”的遠端取穴法,將針灸選穴原則適用于膏貼選穴。將該法應用于胃腸惡性腫瘤的治療,如術后胃癱的治療,以外敷加針刺中脘、神闕兩穴為主,腑會中脘,胃腸疾病均屬腑病,神闕位于腹部中央,有健脾和胃、調暢氣機之功,針、膏施于此,通過刺激經絡,溝通表里,運行氣血,使藥物由肌膚、孔竅深入腠理,由經入絡,最終直達臟腑;如晚期患者的癌痛治療,選擇疼痛點外敷中藥加針刺,可減少西醫(yī)止疼藥物的攝入量,提高患者生活質量[17]。
針、膏共施于局部,可加強氣血流通,《靈樞》記載:“經脈者,所以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不可不通。”《臨證指南醫(yī)案》記載:“腑宜通即是補。”胃腸疾患,病位在胃腸,其臟腑屬性決定其應以通為用,又因腫瘤疾患虛實夾雜,故須通補兼施,而《理瀹駢文·略言》云:“須知外治者,氣血流通即是補,不藥補亦可。”故并用針膏,既防補益藥物滋膩礙胃,又防通泄藥物攻伐傷正,寓補于通,增強胃腸蠕動,并激發(fā)多種鎮(zhèn)痛物質的分泌,有效緩解胃腸惡性腫瘤術后胃癱、腸梗阻及晚期癌痛諸癥[18-19]。
6 典型病案
患者女性,60歲,2018年12月確診結腸癌,行右半結腸切除術,術后病理:低分化腺癌,癌組織侵及腸壁全層,可見脈管瘤栓及神經侵犯,淋巴結轉移(8/35),免疫組化:MLH1(+),MSH2(+),MSH6(+),PMS2(+)。術后予奧沙利鉑+5氟尿嘧啶化療8個療程。2019年8月出現(xiàn)腸梗阻,行開腹探查術:腹膜、腸管、腸系膜表面廣泛轉移性結節(jié),切除左下腹部分腹膜。患者于2019年9月于本科就診,刻下癥見:腹脹、腹痛、止痛藥控制,腹部喜溫,留置胃管行胃腸減壓,納不進,眠差,無排氣排便。舌紅苔白,脈沉弦。查體:下腹部膨隆,觸之較硬,輕壓痛,無反跳痛,叩診腹部呈鼓音,腸鳴音弱。輔助檢查:腹部X線示:腸管多處積氣,腸管擴張,蠕動緩慢,可見多個小氣液平面。診斷:術后腸粘連、粘連性腸梗阻。中醫(yī)辨證:寒凝氣滯證。治療以行氣止痛、溫陽通腑法為主。予外治法丁香止痛方加減外敷,整方如下:丁香 15 g,木香 10 g,枳殼 20 g,全蝎 6 g,穿山甲6 g,厚樸 15 g,肉桂 15 g,艾葉 30 g,延胡索 20 g,香附12 g,取以上中藥顆粒,溫水調敷于肚臍部位,敷后加用艾灸施灸20 min,每次貼敷4~6 h。1周后2診,胃管已拔除,腹痛減輕,稍惡心,仍腹脹,恢復排氣,能進少量流食。原方加吳茱萸30 g,用法同上。5日后家屬代診,述腹脹、腹痛均減輕,排氣恢復,排少量稀便。2周后復查腹部X線示:腹部術后改變,腸管輕度擴張,未見氣液平面。隨訪至今,患者腫瘤病情較穩(wěn)定,未再發(fā)嚴重腸梗阻。
按語:粘連性腸梗阻是腹部手術后最常見的并發(fā)癥,由于腸梗阻患者無法進食,促進了中醫(yī)外治法的使用。患者病程較短,因手術金刀之器損傷腸絡,導致腑氣不通,故見腹脹、腹痛等證;結合患者平素腹部喜溫、喜熱食,辨證為寒凝胃腸證,病性為虛實夾雜。在辨證外治思想指導下,予丁香、木香、枳殼、厚樸、延胡索、香附等通氣滯,止脹痛;予肉桂、艾葉溫陽散寒,以補為通;全蝎、穿山甲通絡止痛,引藥入里。二診加吳茱萸散寒止痛兼止嘔。采用的敷臍療法也是《理瀹駢文》一書中著重記載的外治法。患者經過外治治療有效緩解了梗阻急癥,提高了生活質量。
按語:《周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中醫(yī)外治法正因其用法靈活多變,對“不能服藥之人,不能服藥之癥”更能顯示出其獨特的治療優(yōu)勢,使患者有更好的依從性。文章闡述了部分《理瀹駢文》外治思想在胃腸惡性腫瘤患者特定治療階段的應用,從辨證外治的具體施藥方法、辨病位確定給藥途徑、選用峻藥、拔截新用、針藥并施等角度為臨床提供了一定指導,補內治之不足。隨著現(xiàn)代科技的進步,傳統(tǒng)中醫(yī)外治法將與新興技術緊密結合,如離子導入、改良透皮貼劑、介入手術等,從技術層面優(yōu)化中醫(yī)外治療法,擴大其應用范圍,方可做到“良工不廢外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