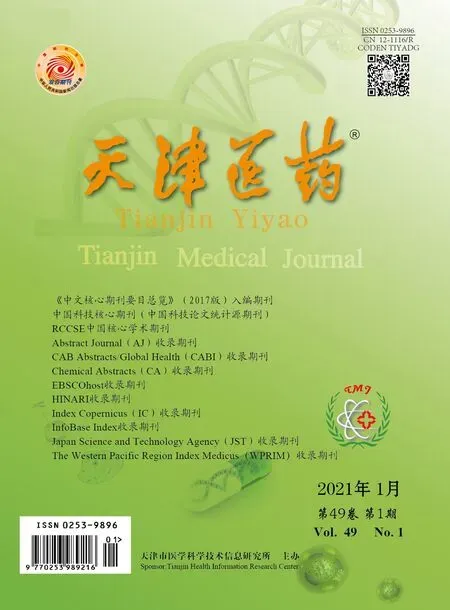顳下頜關節紊亂病在正畸治療中的研究進展
武杰,孟昭松,趙艷紅△
顳下頜關節紊亂病(temporomandibular disorder,TMD)是口腔頜面部最常見的疾病之一,其發病機制尚不完全明確,嚴重者可發生顳下頜關節的器質性病變,包括髁突骨質的吸收和關節盤的破壞,其治療常需要通過外科手術對破損的骨和軟骨進行修復。近年來,功能性咬合可以治療部分TMD,但針對功能性咬合在TMD中的作用產生了不同觀點和爭議[1-3]。目前,一部分學者認為任何可能改變咬合關系的口腔治療均必須以顳下頜關節(temporomandibular joint,TMJ)為第一要素進行診斷設計;另一部分學者認為咬合僅是影響TMJ的眾多因素之一,因此無論在何種頜位上建立咬合關系,TMJ均能適應和改建,并且保持長期的穩定[4-5]。
1 顳下頜關節紊亂病
TMJ在解剖形態和生理功能方面均為全身最復雜的關節之一,左右關節同時協調才能實現六個方向的下頜運動[7]。TMD根據部位不同可分為關節內和關節外,常見癥狀包括下頜疼痛或者功能障礙、耳痛、頭痛和面部疼痛[8],其病因尚未完全明確,目前認為主要的影響因素有心理因素、創傷因素、咬合因素、代謝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等[9]。
1.1 TMD的分類我國目前常用的對TMD的分類有2種,一是由馬緒臣等[10]提出:(1)咀嚼肌紊亂疾病。肌筋膜痛、肌炎、肌痙攣、不能分類的局部性肌痛、纖維變性攣縮。(2)結構紊亂疾病。可復性盤前移位(ADDWR)、不可復性盤前移位(ADDWOR)、關節盤其他類型的移位等。(3)炎性疾病。關節滑膜炎和(或)關節囊炎。(4)骨關節病。可分為原發性、繼發性2類,表現為髁突骨質破壞、變平、囊樣變、骨贅等。二是雙軸診斷標準:軸Ⅰ是針對軀體疾病診斷和分類,主要有肌病類、關節盤移位類和關節病類;軸Ⅱ是與疼痛相關的功能喪失和心理狀況,主要為對患者的疼痛及精神心理狀況進行評估。雙軸診斷是從2個不同方面評估TMD[11]。
1.2 TMD的評估和診斷2014年最新的TMD診斷標準包含5種疼痛相關疾病(3種來源于相關肌肉,1種來源于TMJ本身,1種來源于頭痛引發的疼痛)和5種TMJ囊內結構紊亂疾病,此外中國專家共識還強調醫師在診斷以上病理問題的同時,還應考慮患者的社會心理狀態[12]。有研究表明TMD在美國人群的患病率為5%~12%,痛性TMD體征/癥狀出現頻率為3.4%~65.7%,非痛性體征/癥狀出現頻率為3.1%~40.8%,女性相比于男性更易出現TMD,18歲以上的人群更易患病[13]。臨床中許多錯 畸形的患者伴有TMD體征或癥狀,因此診療中在調整牙齒最佳咬合關系的同時,應加強對關節問題的考慮,以實現整個口頜系統功能的協調。
關于TMD的診斷,主要可以從癥狀、體征和影像學檢查來進行綜合評估。錐形束CT(CBCT)可以清楚地顯示髁突骨組織的形態和結構[14],還可以測量關節間隙,判斷髁突在關節窩中的相對位置,從而間接判斷關節盤的位置情況[15-16]。MRI可以準確清晰地顯示關節盤形態、位置以及病變程度[17],有利于臨床早發現、診斷關節盤病變。
嚴重的咬合不良會導致TMJ更大的損害。在咬合發育中,早期齲齒、乳牙早失、扭轉、第一磨牙前移、咬合干擾、后牙反和下頜移位使個體易于發生TMD,并增加骨骼肌敏感性。在Godoy等[23]的研究中,TMD在安氏Ⅲ類錯同、雙頜前突、深或淺覆蓋、深覆或開以及后牙鎖的兒童中患病率較高,因而對許多伴有錯畸形的TMD患者,早期治療對于預防嚴重的TMD具有重要意義;研究還表明TMD與后牙鎖、前牙開、AngleⅡ類和Ⅲ類錯畸形以及上頜骨過度生長密切相關。
此外,根據人類顱頜面退化機制,目前第三磨牙的萌出常使第二磨牙發生近中軸向傾斜,使得該區域產生咬合干擾,短時間內引起牙尖磨耗,而這種不自然的咀嚼模式大多在夜間不自主發生,TMJ作為一種補償機制將會失去平衡,偏離其生理位置;后方垂直向的任何微小變化都會對TMJ和肌肉系統產生更大的影響,最終導致TMJ及其周圍結構脫位、關節雜音和疼痛,因此有關第三磨牙的萌出和咬合情況需要得到監控和治療。對于存在TMJ問題的患者要關注牙弓后部問題,建立咬合支撐,去除咬合干擾。有研究得出一些咬合與TMD的相關結論:(1)TMD病因中的咬合因素不是絕對的。(2)咬合干擾影響TMD。(3)TMD是多因素的,因此會受到不同治療模式的影響。(4)TMD隨時間波動。(5)適應是人類的一種重要能力,更具體地體現在口頜系統上[24]。
2.3 正畸治療不增加或減少TMD的發生相關研究顯示,沒有證據表明正畸治療可增加或減小TMD的發生風險[27]。為了進一步證明此觀點,有學者選取40例無TMD癥狀及病史的患者,在放置雙側彈性Ⅱ類牽引后口面部出現疼痛,最大張口度變化輕微短暫,屬于咀嚼肌適應性反應,并在1周后恢復正常,因此認為正畸治療不會引起TMD的發生[23]。有學者做了固定或活動矯治器矯治Ⅱ、Ⅲ類錯青少年患者是否與TMD發生相關的研究,共納入7篇文獻,其中4篇為臨床對照試驗,3篇為隨機對照試驗,研究結果表明固定或活動矯治器不是TMD發生的危險因素[28]。還有學者對Herbst矯治器治療Ⅱ類錯在TMD發生發展情況進行了長期隨訪研究,分別在正畸治療前、后以及15年后這3個時間段進行相關TMD評估,結果顯示正畸治療既不會增加、也不會降低患TMD的風險[29]。
TMJ相關問題在普通人群中的發生率較高,在正畸人群中的發生率可能更高。目前有證據顯示TMD可導致咬合關系的改變,即TMJ病變可致錯畸形的產生或進一步加重[30]。對正畸醫生而言,是否存在與TMD相關的典型因素對治療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同時咬合位置和關節位置之間不協調也可能是增加結構功能障礙的危險因素[31]。
3.1 功能 與TMD之間的聯系 以 學為主導的理論認為咀嚼系統是一個整體,治療目標應達到整個口頜系統功能和解剖的協調統一。Roth[32]提出,當牙尖交錯位(intercuspal position,ICP)與后退接觸位(retruded contact position,RCP)不一致時,牙齒在咬合時會有更多的水平向分力,易導致牙齒移位。為了避免正畸后復發、咬合磨損、牙周病、TMJ功能障礙等方面的問題,在制定治療目標時還要進行動態咬合診斷,這有利于正畸醫師對錯畸形診療的風險防范。
3.2.1 對TMD體征或癥狀進行鑒別和評估正畸治療前,對TMJ相關問題的高風險患者進行詳細的篩查十分必要,尤其是特發性髁突吸收、青少年特發性關節炎、TMJ退行性變和骨關節病、顏面偏斜、頜面部肌肉疼痛以及咬合相關的主觀癥狀與客觀體征不符的患者。每例患者都是獨立的個體,不能一概而論,臨床醫生需要個性化診斷并制定相應的措施,充分考慮TMJ形態與功能的生物學正常變異情況。并不是所有關節癥狀都需要治療,因為多數人身體各部分結構均可能出現短暫的不適或功能紊亂,大部分情況是可以自愈的。
臨床和影像學檢查對準確診斷關節囊內紊亂分期和牙頜面畸形具有重要意義。肌筋膜疼痛和功能障礙與關節內結構紊亂要進行區分[34]。早期和中期囊內錯亂的患者可以在正頜手術前進行非手術治療,以減輕疼痛、增加活動范圍,并允許進行正畸治療,大多數患者在牙頜畸形得到治療后,TMD癥狀也都得到改善。
3.2.2 建立穩定的正畸治療位在正畸治療前要使髁突處于唯一重復且穩定的位置[35]。臨床中通常記錄CR位來確定這一位置,常用的工具有架、面弓、髁突運動軌跡描記儀、面弓描記儀、髁突位置指示器等[36]。但是,以動態咬合作為正畸臨床的治療目標,則必須模擬下頜運動,架是最常使用的工具。通過架可以確定正確的髁突和關節盤的位置關系,這也是正畸治療以功能為目標的基礎,因此正確運用正畸手段不會對TMJ造成不良影響。如在矯形治療中,關節腔內的壓力會導致髁突生長或抑制以及TMJ結構的改變。青少年骨性Ⅱ類錯前導下頜的患者,當關節盤重新定位到正常位置時,髁突頂部的應力被釋放,使得髁突在青少年患者處于生長高峰期時迅速生長。有研究顯示髁突的生長主要在盤髁復位正常時[37]。因此,解除髁突的生長抑制、重新定位盤髁關系至關重要,矯治后咬合穩定才是正畸治療成功的關鍵。
3.3 正畸患者TMD的治療首先,在正畸治療前通過各種手段對患者關節情況作出明確的診斷、評估可以預防治療中出現的關節問題。如患者存在TMD,可針對不同情況進行相應處理。首選可逆性治療,如服藥、理療封閉或板等;其次用不可逆性保守治療,如調、正畸治療等[40];最后選擇關節鏡外科或各種手術治療[41]。如果患者在正畸過程中出現TMD,正畸醫生需要對患者進行診斷分析,評估患者的咬合狀況,如有無咬合干擾、有無早接觸點以及患者的精神心理狀態,判斷治療時機,從而進行相應的處理。
4 小結
正畸治療前應全面了解患者TMJ的狀態,對TMJ相關問題進行嚴格篩查,并對相關預后作出有效預判,這也是避免TMJ相關風險的關鍵。若患者在正畸治療中或正畸治療后出現TMD相關癥狀,則需警惕并鑒別這些癥狀與咬合變化的相關性。慎用不可逆的治療方法,盡量選用可逆且預后可預測性較高的治療方案。